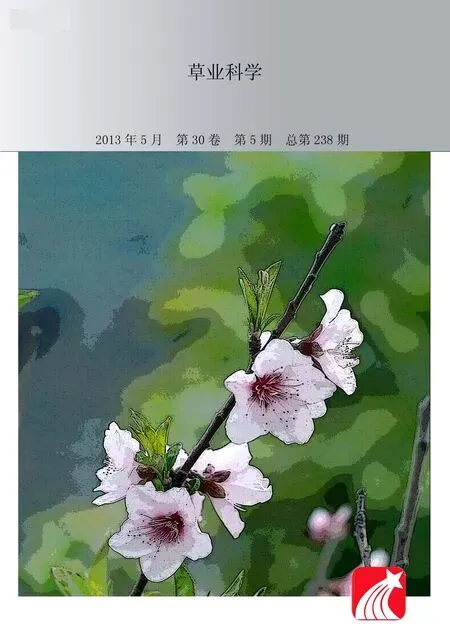高尔夫球手功能依赖和情感依恋与购后行为关系研究
吴克祥,张园园,蒙小育
(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广东 深圳518053)
截至2011年,我国拥有663家高尔夫球场,高尔夫核心人口达35.8万人次[1]。目前,我国99.4%的高尔夫俱乐部是会员制或者半会员制性质,大多采取商业性俱乐部的盈利模式,即球会通过发展会员,吸引会员和嘉宾前来打球来盈利。这种经营模式在一定时间内受到会员总体规模的限制,其盈利的关键在于俱乐部会员的数量和球手的重购率,即球手的打球轮次。然而,目前我国营业的球场中只有41.3%的球会能够盈利,11.1%的球会亏损较为严重,其发展前景堪忧[1],这主要与我国高尔夫球场经营策略失当有关。我国高尔夫球场经营者无法准确定位球手的需求,同时由于缺乏具备专业知识的人才,导致球场的维护工作不到位,而早期球场在球道斑驳、沙坑长草以及水障碍浑浊等问题上尤为凸显。这不但影响了球场的美观,而且不利于球手打球水平的发挥,导致许多球手的满意度不高、对球场的忠诚度较低,甚至对球场产生抱怨和投诉。
人们在某个场所开展的一系列无意识的日常活动能够制造个体作为“内部人员”的意识[2],而人们的参与行为和日常行为习惯会影响个体对特定场所的情感。与其它运动项目相比,高尔夫运动对场地的要求更专业,球手必须在一定的场地范围内(如室内外高尔夫练习场和高尔夫球场)进行与打球相关的活动。球手经常前往与高尔夫相关的场地,通过挥杆打球和与球友的交流等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对高尔夫球场产生一定的情感(如熟悉感、安全感、归属感和成就感等),进而对球场产生场所依恋感,这些积极或消极的情感能够对其未来的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本研究引入“场所依恋”理论以探讨球手的球场依恋程度对其购后行为的影响。
“场所依赖”理论认为:个体在特定场所进行活动会对该空间环境产生依赖感[3]。Lee等[4]强调心理依赖对于理解旅游者行为(包括重游行为)有重大意义,同时也指出多次到某一旅游目的地旅游会增加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推荐行为和口传行为。表明场所依恋通过满意度的中介作用能够影响消费者的购后行为。在高尔夫球场上,球手通过挥杆和与球友的交流等活动容易对球场产生场所依赖感,球场经营者如何利用这种情感依附将其转化为球场利润并获得球手的忠诚度正是本研究的重点。
1 理论模式
1.1 “场所依恋”理论及其基本构成维度“场所依恋”理论认为,个体在特定场所进行活动会对该空间环境产生依赖感[3]。“场所依恋”是在感情(情绪、感觉)、认知(思想、知识和信仰)和实践(行动、行为)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人与场所之间的一种联系[5]。一般认为,场所依恋是由场所依靠和场所认同两个维度组成的。黄向和保继刚[6]将“场所依恋”理论引入我国休闲游憩研究时,接受并使用这两个维度作为基本维度。场所依靠是个体对特殊场所的社会与资源可用性的评价,是场所存在必要性的体现,是一种功能性的依赖;场所认同指个体与客观环境间存在的一种情感依赖关系,是个体心理层面在情感和符号表象上产生的地方情感,是人对场所在思想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映射[7],是一种情感性的依赖。本研究选取功能依赖和情感依恋两个维度衡量球手的场所依恋水平,通过球场风格、球道(包括障碍区)品质、果岭品质和场地地理位置等衡量功能依赖,利用球场氛围、球童专业性、球场认同(偏好)和归属感衡量球手的情感依恋。
1.2 研究假设 回顾近年来对“场所依恋”理论的探讨,学者们的研究多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永久性住所的场所依恋感(如社区等);二是非永久性住所的场所依恋感(如购物中心、避暑别墅、风景区、森林、湖泊以及其他旅游场所等)。在针对非永久性居所的场所依恋研究中,场所依恋对忠诚度(体现在重购意向、推荐意向和口碑宣传意向)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8]。江春娥和黄成林[9]的研究认为,旅游者对目的地的依恋情感越深,再次到访的意愿会越强,并且场所认同对游后行为的影响程度高于场所依靠的作用。所以本研究把满意度作为研究的中介变量,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球手购后行为的发生机制(图1)。

图1 场所依恋、球手满意度与球手购后行为研究模型Fig.1 The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lace attachment,golfers’satisfaction and golfers’after-purchase behaviors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下列假设:
H1:球手场所依恋(功能依赖和情感依恋)与球手满意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H2:球手场所依恋(功能依赖和情感依恋)与球手购后行为(重购意向和推荐意向)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H3:球手满意度与球手购后行为(重购意向和推荐意向)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H4:球手场所依恋(功能依赖和情感依恋)通过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对球手购后行为(重购意向和推荐意向)产生正向影响。
2 研究方法
2.1 问卷调查法 本研究的问卷分为三部分,前两部分运用7级李克特量表分别对球手的场所依恋和购后行为进行测量,第三部分是对球手的社会学特征进行调查,包括性别、年龄、学历、球龄和收入水平。其中场所依恋部分借鉴 Williams等[10]根据成熟场所依恋量表,结合高尔夫运动的特点,通过语句转换开发的高尔夫球手场所依恋的量表(表1)。在借鉴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主要通过衡量球手的总体满意度测量球手在球场打球的满意度水平,购后行为主要关注的是重购意向(即再次打球的意向)和推荐意向。对于球场而言,较高的重购意向和积极的推荐意向能够为球场的经营带来最直接的经济效益。
2.2 案例地选择 本研究的案例地选择在深圳。深圳处于珠三角地区,该地区是我国高尔夫球场分布较为集中的区域之一。深圳是珠三角地区中高尔夫球场较多的城市,有15家高尔夫球场,占整个珠三角地区高尔夫球场总数的17%左右,所以选择该地区作为研究案例地具有可行性和代表性。本研究于2012年12月上旬,在深圳市的5家高尔夫俱乐部对打球者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共发放350份问卷,回收317份,其中有效问卷298份,问卷有效率94%。在调查样本中,女性球手占18.8%,基本符合中国高尔夫球人口中男多女少的情况。87.5%的被调查者年龄集中在18岁到50岁之间。1年以下球龄(包括1年)的人数占35.2%;1年到2年球龄(包括2年)的球手占28.5%;2年到4年球龄(包括4年)的球手人数占21.8%;4年以上球龄的人数占14.5%。另外,75.2%的被调查者拥有高中及以上学历,其中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的占52.5%,因此被调查者可以很好理解调查问卷的内容。

表1 高尔夫球手场所依恋测量指标源Table 1 Measurement scale and references of golfers’place attachment
2.3 数据处理 用SPSS 17.0软件进行数据的录入,及问卷题项的信度和效度分析,用AMOS 17.0软件进行SEM分析,分析假设模型和问卷数据之间的拟合度,以及验证假设是否成立。
3 结果
3.1 问卷的信度效度分析 通过信度和效度分析,对问卷的可靠性进行检查,分析题项能否测量所要测量的变量,能否达到测量的目的。一般认为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α≥0.70,则表示量表的内在信度比较高,且越趋近于1数据的信度越高。结果显示,测量维度的α值均大于0.72,总量表的信度系数大于0.84,这表明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本研究采用KMO样本测度和巴特莱特球状检验,检验测量项目的效度。场所依恋和球手忠诚度的KMO值分别为0.84、0.75、和0.77,均大于0.70,同时巴特莱特球体检验表明变量之间极显著相关(α<0.001),因此指标的选取比较恰当。
3.2 模型的拟合度分析 适配度指标可用来评价理论模型与实际数据的一致性程度。本研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基于极大似然估计法(ML法)概念模型 进 行 数 据 的 拟 合 检 验 (Model Fit Test)。Goodness of Fit Statistics报表结果显示,(ML)χ2为137.351(表2),数值略大,而χ2容易受到样本容量的影响,因而该结果并不影响假设研究模型的整体拟合度。其它指标中除RMSEA外均达到理想水平,其中GFI为0.910,RMR(适配残差方差协方差的平均值的平方根)为0.045,RMSEA=(F0/df)1/2=0.062,CFI为0.965,IFI为0.946等。该结构模型中的适配度指数说明了本研究的假设模型在总体上是可以被接受的[11]。结构模型分析结果表明调查数据基本支持了结构模型的假设,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图2)。研究结果表明场所依恋水平与高尔夫球手购后行为之间存在着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0.001)。高尔夫球手通过使用高尔夫俱乐部的设施与服务,同时通过接触高尔夫球场的服务人员(特别是球童),在心理上对高尔夫俱乐部形成认同感、归属感等,进而对高尔夫俱乐部形成强烈的场所依恋。而这种依恋感促使高尔夫球手以各种形式(如邀请好友一同前往打球、参与俱乐部组织的赛事活动等)不断地到高尔夫俱乐部参与高尔夫运动,这一过程将逐渐加深球手对俱乐部的依恋程度。对球场产生依恋感的球手不仅不会进行球场转换、球场转移或者球场退出行为,还会积极推荐球场。

表2 模型拟合指标结果Table 2 Results of indices of fitness

图2 测量模型路径图Fig.2 Path analysis
3.3 场所依恋和满意度与球手购后行为之间的关系 研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中潜在变量的路径分析法PA-LV模型)的递归模型(Recursive Model)探索5个潜在变量之间的作用关系。该方法结合了传统的路径分析与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测量模型,避免了传统的回归分析中只能探究路径系数的影响是否达到显著水平,无法就整体路径分析的假设模型作为整体契合度检验的缺陷,同时能够检测测量误差。
根据路径图,本研究的测量方程为:

式中,ξ1代表功能依赖,ξ2代表情感依恋,η1代表满意度,η2代表重购意向,η3代表推荐意向,γip代表第i个观察变量在内因潜变量p上的因子负荷,ξmn代表第m个观察变量在内因潜变量上的因子负荷,εi代表内因潜变量的测量残差。
3.3.1 功能依赖对高尔夫球手购后行为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场所依恋对高尔夫球手的购后行为具有较强的正向影响力,但场所依恋的两个维度对购后行为的影响方式是不同的。功能依赖对购后行为产生较为直接的影响力(对重购意向和推荐意向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45和0.51),而满意度的中介作用相对较弱。球场风格、球道品质、果岭速度以及球场位置带来的交通成本和时间成本等因素,在球手对球场产生场所依恋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人们通过消费场所的功能,对场所的设施设备或服务渐渐熟悉并转变成为一种习惯,这使得人们更加容易接受或理解场所,对场所满足其需求的预期也更接近实际值[12]。由此可见,功能依赖对球手产生的是基础而直接的依恋,场所对球手功能性的满足是产生场所依恋的基础,球场自身功能的发挥直接影响到球手的打球需求能否得到满足,是其在下次产生需求时再次选择该球场的直接动因,也是决定性的因素。打球体验满足球手的需求,球手会积极向周围的高尔夫人群推荐该球场,为球场带来良好的口碑。
3.3.2 情感依恋对球手的购后行为的影响 情感依恋对购后行为具有间接影响,可通过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对购后行为产生作用。情感依恋作为一种心理上的感受,必须通过在场所内的活动体验转化为现实的行为。认同是满意的前提,是实际体验符合个人期望或价值感受的结果,满意也因此而生。满意是积极购后行为的基础,无论是再次购买还是向周围亲朋好友推荐,往往都是基于前一次满意体验的结果。
与人们对其它场所的依恋程度不同,球手的情感依恋对球手的购后行为的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29和0.26)明显弱于功能依赖,即使通过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影响力仍旧较小(路径系数为0.62和0.55)(图3)。在高尔夫球场,球手关注的重点是球场设施的功能能否满足其打球的需求。而功能依赖体现的是球场的功能性内涵,高尔夫球场提供的活动场所对于球手而言是独一无二的,它能够在功能层面满足球手的需求,通过美丽的球场风景、数量适宜的障碍区、难度恰当的球场以及合适的果岭速度等,使球手可以在其中尽情的挥杆,体验高尔夫运动带来的乐趣。但是情感依恋是个体在心理层面产生的地方情感,对于球手而言,在一个球场的打球过程也是一个情感的累积过程,因而情感依恋对球手的影响主要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直接的影响力较小,因而在短期内无法发挥相应的作用,特别是我国的高尔夫起步较晚,情感依恋的作用尚未完全显现。
3.3.3 满意度在场所依恋和购后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由结构方程的分析可知,场所依恋通过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尤其是情感依恋这一维度,增强了其对购后行为的影响作用。因此,满意度是场所依恋对购后行为产生影响的重要条件。由于球场的功能依赖对球手购后行为具有直接而显著的影响,使得球手对于打球过程中的一些不满意行为也可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忽略或者包容,并形成一种整体上的满意感,从而促成积极的购后行为发生。由于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微弱,球会若是要提高高尔夫球手的重复购买率必须要从球场功能着手,同时通过不断累积满意的体验,改善球会的经营状况。

图3 结构模型分析结果Fig.3 Results of structural model analysis
4 讨论
高尔夫球场作为高尔夫运动的依托,具有“场所”的概念,不仅包含了地理位置、物质形式,还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因此,球手在球场开展与打球相关的活动时才能对其产生熟悉感、依赖感,并通过欣赏球场秀丽的风景、提升球技、与球友交流和接受服务人员的服务等活动不断加深对球场的情感,进而构成了球手对高尔夫球场的功能依赖和情感依恋。本研究表明,功能性依恋对球手的购后行为有强烈的正向影响,而情感依恋则是通过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对球手购后行为产生正向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与其它场所不同,球手对高尔夫球场的依恋主要源自功能依赖,而情感依恋需要借助满意度的中介作用才能对球手的购后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尽管满意度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情感依恋对购后行为的影响力,但是满意度所起的中介作用相比而言并不明显。可见,对场所产生的依赖感是球手产生再次购买动机的重要因素。因此,在高尔夫俱乐部的市场营销中,应该从场所依恋和场所认同两个方面培养与提升球手的场所依赖水平,以维持较高的球手忠诚度。这对于球场的管理者和经营者来说具有重大的实践与指导意义。
[1] 朝向管理集团.朝向白皮书——中国高尔夫行业报告[M].朝向集团,2011.
[2] Lewicka M.Place attachment:How far have we come in the last 40 years[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2011,31(3):207-230.
[3] Hidalgo M C,Hernández B.Place attachment: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questions[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2001,21(3):273-281.
[4] Lee C,Beckman K,Beckman S.Understanding antecedents of repeat visitation and tourists’loyalty to a resort destination[A].Proceedings of the 1997 Travel and Tourism Research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C].Boulder,CO:TTRA,1997.
[5] Gieryn T F.A space for place in sociology[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000,26:463-496.
[6] 黄向,保继刚,Wall G.场所依赖(place attachment):一种游憩行为现象的研究框架[J].旅游学刊,2006,21(9):19-24.
[7] 白凯.乡村旅游地场所依赖和游客忠诚度关联研究——以西安市长安区“农家乐”为例[J].人文地理,2010(4):120-125.
[8] 钱树伟,苏勤,祝玲丽.历史街区旅游者地方依恋对购物行为的影响分析——以屯溪老街为例[J].资源科学,2010,32(1):98-106.
[9] 江春娥,黄成林.九华山游客地方依恋与游后行为研究[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1,23(1):71-75.
[10] Williams D R,Patterson M E,Roggenbuck J W.Beyond the commodity metaphor:Examining emotional and symbolic attachment to place[J].Leisure Studies,1992,14:29-46.
[11] 吴明隆.结构方程模型——AMOS的操作与应用[M].第二版.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
[12] Marsh K L,Johnson L,Richardson M J,etal.Toward a radically embodied,embedded social psychology[J].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2009,39:1217-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