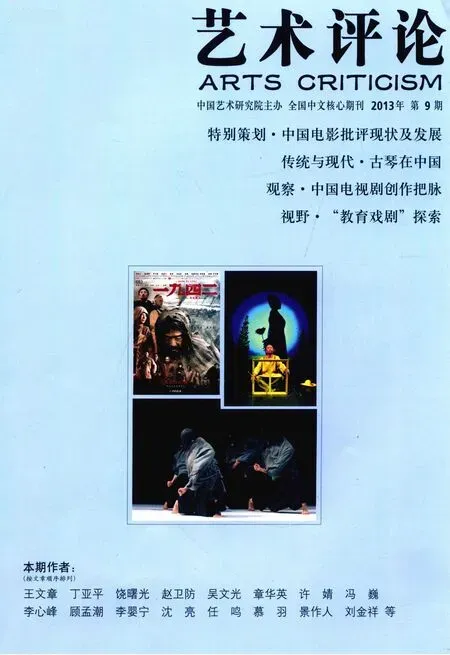电视剧特性新议
冯 巍

自1980年电视剧艺委会倡导“电视剧特性”研究以来,时光荏苒,已走过了三十多个年头。2013年的中国电视剧格局,正在展开。在这三十多年的发展进程中,电视剧创作始终踩踏着时代的节拍,从题材内容的拓展、表现形式的丰富到市场宣发的完善,多维度地推动了这一艺术门类的成长。如果说1980年代的电视剧特性研究主要在为电视剧艺术的形式独立而奋斗,那么,21世纪新十年过后的电视剧特性讨论,已经指向了电视剧内容、形式,乃至产业运作的总体成熟模式,以及全球化背景下艺术、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博弈与均衡问题。归根结底,无论何时研究电视剧的特性,都是在研究中国电视剧发展的未来走向。下面的论述,不过是在电视剧众多新特性中拣选了较为突出的三个方面。但无论是谈技术、谈产业,还是谈艺术、谈文化,都是在谈电视剧作为一种艺术样式如何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与互动。即使资本的力量,也就是商业化的超我逻辑,主导着电视剧产业的运行,一部电视剧作品的经济效益也已经与它的社会效益不可分割。这两者哪一个是第一位的,就实践层面而言已经成为一个难以辨明的问题。
在中国电视剧“走出去”的路途中,人们日甚一日地发现作品的文化现状问题,才是中国电视剧面临的长远挑战。如果轻视甚至放弃文化的力量,或者重视但不能妥善处理文化的力量,就会失去电视剧做“中国梦”的机会和能力,也就失去了把梦想变成现实的机会和能力。弗雷德里克 · 马特尔在访谈了世界各国的众多业内人士之后指出,“电视剧和电视剧形式的世界战争只是刚刚打响。就像一部优秀的电视剧的情节一样,这个市场往往会引发觊觎、抵制、同盟关系转变以及常有的嫉妒。……这是一场真正的文化战争,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就呈现在我们的屏幕上。”只有从事“中国制作”、打造“中国模式”,中国电视剧才有机会打赢这一轮全球文化战争。只有成为“文化赢家”,中国的电视剧艺术才能在全球市场获得长久的经济保障。
一、民族性的开掘
中国电视剧在1980年代处于创作复兴的初期,要确立其独立的艺术地位,首先就面对辨析电视剧与戏剧、电影、广播剧的近缘关系问题。于是,新时期的电视剧批评都明确聚焦于从形式特性入手讨论电视剧的艺术独立,比如,蔡骧1982年发表的《关于电视剧的“电影化”和“广播化”》一文,就鲜明指出中国电视剧发展所面临的两条道路的选择,强调对于电视剧而言视觉效果和听觉效果同等重要。但与此同时,电视剧创作格局本身已经凸显出内容上的民族性问题。为了弥补电视产品供应不足而形成的引进剧狂潮,既激发了复兴中的中国电视剧创作,也对中国人的文化底线构成了挑战。人们选择回到文学经典,以寻求支撑中国电视剧复兴的文化力量。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和一些当代文学名著,先后被改编为电视剧。这一系列的举措延续到1990年代,为描绘中华文化的总体面貌奠定了基础。
经历了21世纪新十年的繁荣发展,如今的艺术图景更为复杂微妙,挑战与危机更加严峻。全媒体时代的中国电视剧从多个媒介渠道经受着欧风美雨、日剧韩流的冲击,不可能简单照搬百废待兴的1980年代的应对方式。除了改编文学名著,大力发展原创的“民族电视剧”,可以说在21世纪新十年之后适逢其时。这也是从根本上挣脱外来电视剧的文化包围圈、确立中华民族自身文化立场的必然艺术选择。虽然厘清“民族性”或“中华性”的内涵还需要开展大量的跨学科研究工作,但是,近两年的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接连上演了几台民族大戏,已经在实践层面提供了一些令人欣喜的范例。从《木府风云》、《长白山下我的家》、《温州一家人》,到《全家福》,共同推动了一个“民族电视剧”的热潮,共同讲述了一个“华夏是一家”的中国故事。《赵氏孤儿案》2013年在中央一套的第一轮热播,也再次掀开“正典正说”的古典题材电视剧的帷幕。对于民族文化身份的迷失、“民族传统和人文精神认同的垂直建构上的断裂”,这些作品可以说携手发挥了纠偏和接续的审美功能,在一定意义上建构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话语权的新一轮崛起。
雷蒙 · 威廉斯在《文化研究》中指出,电视剧不是单纯的商品,它负载着特定人群特殊的“文化经验”和“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s)。只有编码者与解码者的文化经验和情感结构相互交流碰撞,内化于视像之中的意义才能被激活并释放出来。因此,强调电视剧的民族性,就是在强调电视剧的本土文化体验性和弥散性。随着中国的电视剧产业逐渐吸纳电影产业的中外合拍方式,文化权归属问题就更加迫切地要提上讨论日程,而且比起艺术作品的产权归属,它是一个更加深层次的问题。这个问题必然要追溯到民族性的层面来看待。一个拥有明晰而坚定的民族性的文化产业,才是一个能够持续发展的产业。这样的民族性,并不是固守曾经辉煌的文化传统,而是承继传统的前提下创造出立足于当代的新意。创意之“意”是意义之意,不是创“钱”之意。创意即创立意义。所谓内在主体性的缺失或者正能量的缺失,就是向上的价值与意义的缺失。充分开掘民族性,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精神缺失问题,提升创作出更多的高品质电视剧的可能。电视剧作品只有被充分赋予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才能让观众在审美欣赏的过程中完成个体化的但又是民族性的精神成长。
二、技术流的反思
自从《阿凡达》热映中国以来,艺术与技术“在共谋中的冲突”愈演愈烈。21世纪新十年之后,“收视率至上”所导致的“技术至上”,即电视剧创作热衷于引入高科技手段,也成为了一种创作趋势。在这一历史节点上,新版《红楼梦》(2010)、新版《西游记》(2011)这两部古典名著的重拍剧,既关联到民族精神的跨世纪探寻,也关联到技术异化了艺术的创作危机。因其改编对象原生性的文化底蕴深厚,就令人格外期待其能够创造出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电视剧作品,而技术对此的增益或损毁也就格外引人瞩目。如果说时代变迁和创作者审美趣味的不同一起带来了艺术风格的迥异和改编思想立场的不同,还属于可以见仁见智的方面,那么,这两部新版电视剧与老版《西游记》(1986)迟至1998年补拍的16集一样,其拍摄技术和制作技术的明显提升,伴随着“叫座不叫好”的悖论,让人们对于电视剧创作领域中艺术与技术二者关系的现状产生了疑问。
虽然中国电视剧的家庭伦理题材持续繁荣,其平实的日常生活化审美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技术至上的态势,但也不能忽视神话题材、战争题材等电视剧作品中的过度炫技倾向。这也是反思电视剧“过度娱乐化”现象的门径之一。艺术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已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话题。电视剧创作所借助的各种技术手段,显然归属于这一组二元辩证中的形式维度。不但炫技本身无法替代丰沛的内容,而且脱离了内容的技术,再绚丽也是贫乏的、苍白的。高科技所创造的视听奇观,如果在吸引观众耳目的同时能够不止于视觉和听觉,而且有助于击中观众的心灵,显然才符合技术为艺术服务的初衷和本分。反之,就纵容了技术,使其超越并凌驾于艺术之上。重技术、轻艺术所造成的技术与艺术的断裂,必然会降低电视剧作品的整体价值。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此时的技术,不仅异化了艺术,也异化了自身。
电视剧本身就是一种家庭化、日常化的艺术形式。电视创造了一个聚集地,在全球化的时代把一个家庭的客厅变成了“全球客厅”,将互不相识的人们变成了“观众共同体”。《蜗居》之类的“事件电视剧”之所以能够出现,就是因为有成千上万的观众在一起观看同一部剧集,并且在闲谈、争论中共同成为一个文化事件的参与者。这种无法逃避的文化承载与传播功能,决定了电视剧创作可以选择“技术流”,但不能让技术成为主导艺术的力量。只有理顺艺术与技术的关系,即在艺术创作领域中确定艺术在统辖技术、技术在为艺术服务,才能在科技飞速进步的当代中国依然敬畏艺术、敬畏文化,创作出既养眼又养心的电视剧作品。
三、播出季的探索
从早期单本电视剧的“直播性”到新时期以来长篇电视剧的“连续性”,电视剧作品在长度上的量变已经带来了其艺术特性上的质的变化。从电视剧制作环节到播出环节的产业式发展,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播出编排规律不再能满足相关的实践需要。就如同电影产业要迎战“好莱坞”,不仅需要提升作品的文化内蕴和艺术品质,也需要探索电影档期一类的市场问题一样,那么,面对美国电视剧日甚一日的“致命诱惑”,中国电视剧产业也从2005年开始尝试运作播出季。
从电视剧产业的常规流程来看,中国电视剧只能是先制后播,而不可能系统采用美剧边拍边播的模式。尽管周播剧在这种制约下“试水”初见成效,其实质却停留在栏目剧层面,没有形成制播环节与观众反馈的全程互动。美式播出季确实有其利于产业推进的一面,但要使其最终能够“服”了中国的水土,还需要在立项审批、制播衔接、观众养成等方面进行漫长的努力。与此同时,诸如“开年大戏”、黄金周特排剧、电视剧暑期档之类的中国特色播出季,近年来却已经成为常态。正如约翰 · 埃里斯所说的,“节目编排是电视力量之所在,它成功地将对人口学的预测转化为控制收看经验的机制。任何编排都包含了对一个频道的历史、广播电视整体以及民族生活特定习惯的精炼反应。”虽然这些播出季的出现,也像周播剧一样源自播出平台的主观编排,但充分考虑和高度适应了中国观众的收看习惯,因而让“季”这一引进范畴逐渐在中国生根发芽。
另外,由于电视剧的视频网站播出量迅猛增长,单一的电视台播出垄断已经被打破,电视剧的播出生态面临一系列新问题。为了抢占最佳播出时机,电视台和视频网站都从各自的媒介优势,以及观众群体的收视特点出发,重新设计了电视剧的播出格局。电视台加快了播出节奏,采取每天固定时段三集甚至五集联播,以及热播剧连续重播等方式,努力找回流失到网络的电视剧作品和粉丝们。视频网站则自建实时片库,同步跟进国内外的电视剧生产,并且介入了制作环节,网络自制剧开始“逆袭”电视台。至于电视剧发行方,倾向于选择将白热化的“台网对抗”转为“台网对接”,统筹规划一部电视剧的联动播出,以求谋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这样,播出季的问题就更加复杂化了,需要从“台网联动”的角度来综合考虑。无论目前电视剧播出季的运行成功与否、褒贬如何,就实际发展态势而言,为了建构中国电视剧自身成熟顺畅的产业链条,也为了电视剧走出国门传播中华文化,现在已经到了深入研究电视剧播出季这一新特性的时刻。
注释:
[1] [法]弗雷德里克 · 马特尔:《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50页。
[2] 蔡骧:《关于电视剧的“电影化”和“广播化”》,载于《文艺研究》1982年第4期。
[3] 黄式宪:《略论中国电视剧文化生态的再整合》,选自《中国传播论坛(2002)——中国电视剧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4] 陆扬在《文化研究的三个范式》(《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在雷蒙 · 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中,“情感结构一方面是指文化的正式构造,一方面又是指文化被感受经历的直接经验,具体说,它就是某个特定阶级、社会和集团的共享价值,或者说,一种集体文化无意识。”
[5] 仲呈祥:《高等美术院校是民族美术思维的先锋阵地》,选自《仲呈祥演讲录》,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29页。
[6] [英]迈克 · 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123页。
[7] [英]乔纳森 · 比格纳尔、杰里米 · 奥莱巴:《21世纪电视人生存手册(第三版)》,栾轶玫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