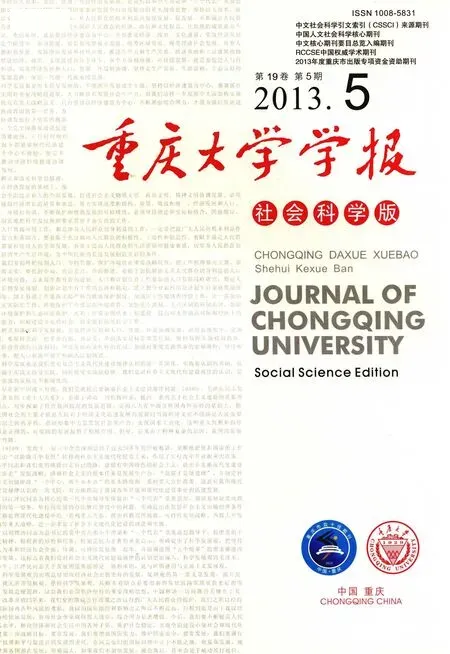协同创新效率的国际比较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江成山,孟卫东,熊维勤
(1.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重庆 400044;2.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重庆 400067)
技术创新是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关键因素,然而创新活动本身又是一个牵涉政府、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金融和其他中介机构等多个创新主体的复杂系统工程,如何整合各种要素,优化创新资源配置以促进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一直是各国政府高度关注的问题。中国政府早在1985年就在《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中首次提出了“促进产学研合作创新”问题。2011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的讲话中进一步明确了推动协同创新的战略部署,2012年教育部和财政部开始共同推进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2011计划”),从而把促进协同创新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此背景下,通过对不同国家协同创新效率的差异分析,并进一步明确其主要影响因素,对于科技政策的制定,并以政策促进协同创新,进而促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文献回顾
自哈肯创立协同学,Freeman[1]、Nelson[2]等将其引入国家创新体系分析以来,协同创新即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协同创新理论的发展以及微观企业层面协同创新机理、机制的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协同创新开始成为研究重点,然而关于协同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并不多见,近来年才逐渐得到国内外,特别是国内学者的关注,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散见于区域创新和国家创新两个领域,其基本研究思路都是通过测度不同区域或不同国家创新效率的差异并分析其影响因素,进而对不同创新主体间的协同创新效率进行分析。
在区域创新研究领域,池仁勇和唐根年[3]使用DEA法分析了浙江省11个地区技术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投入并不能显著提高创新效率,从而证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协同是缺乏效率的;李习保[4]则利用随机前沿法(SFA)分析了中国30个省份1998-2006年的区域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认为政府对科技活动的支持力度可以显著提高区域创新效率,高校和科研院所则对区域效率创新产生了负向影响,金融机构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则不确定;白俊红等[5]则首次从研究区域创新效率的角度明确检验了各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创新效率,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金融中介等创新主体及其联结关系对区域创新效率均产生了负向影响。
在国家创新研究领域,Furman,Porter and Stern[6]首先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框架(FPS)用于分析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认为创新基础设施、创新集群环境以及二者之间的联系是影响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Hu and Mathews[7]以东亚5国为样本重新整理了FPS方法,除了得到了相近的发现外,他们还进一步强调了制度对国家创新能力形成的重要性。此后关于国家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也基本沿袭了上述研究方法。如Hu等[8]使用距离函数SFA法评估了24个国家研发效率的影响因素,发现知识产权保护、人力资本积累以及高校与企业的技术合作能显著提高一国 R&D效率。Guan and Chen[9]进一步把国家创新划分为知识生产和知识转化两个阶段,通过对22个OECD国家的实证分析,发现影响国家创新效率的关键在于知识转化效率,而制度环境对知识生产和转化效率均有显著影响。吕新军和胡晓绵[10]利用28个国家2000-2006年的样本数据,集中分析了影响国家创新效率的制度性因素,发现良好的政治制度、市场化程度和贸易制度都能显著提高一国创新效率,而法律制度对发展中国家创新效率的影响却并不显著。郭淡泊等[11]的分析则表明FDI流入抑制了发达国家的创新经济效率,但对发展中国家却有促进作用;贸易保护显著提高了发达国家的创新技术效率,但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创新技术效率的提高;人才的自由流动对两类国家的创新技术效率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国家创新效率本质上是由官、产、学、研等多主体的创新活动所决定的,尽管现有研究文献已经对国家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然而若从协同创新的研究视角出发,则现有的研究对于两个基本问题仍然缺乏系统的回答:第一,“官、产、学、研”协同创新是推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核心,因此从国家层面看,各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是否有效?换句话说,政府、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创新活动是否有效促进了国家创新效率?第二,尽管企业是无庸置疑的创新主体,但政府在协同创新中却具有特殊的地位,其既通过国有科研机构直接从事创新活动,还通过基础设施和制度建设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更重要的是通过制定政策引导和影响其他创新主体的行为,从而最终影响一国创新效率。已有的研究对政府在创新基础设施和创新环境建设中的作用作过充分考察,然而对政府政策,特别是税收政策对国家创新效率的影响却几乎没有文献涉及。因此本文将在比较国家创新效率的基础上,主要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
为了分析各创新主体的创新行为是否协同有效,即是否显著促进了国家创新效率的提高,理论上可以通过两种方法实现。一是利用一国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数据计算出国家创新效率,然后分析不同创新主体的创新投入是否显著促进了国家创新效率,若是,则说明各创新主体之间的创新行为是协同有效的。反之,若某一创新主体的创新投入不能显著提高国家创新效率,则说明该主体的创新行为与其他创新主体之间不存在协同有效关系,从政策角度看应该将其创新投入更多转移到协同有效的创新主体上,或者设法提高其创新效率;二是在计算出国家创新效率后,还可以利用不同创新主体的创新投入和产出数据计算出不同创新主体的创新效率,在合理假定国家创新效率和不同创新主体创新效率关系的基础上(一种合理的假定是:国家创新效率与不同创新主体创新效率之间存在Cobb-Douglass生产函数关系或者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关系),也可以分析不同创新主体的创新行为是否存在协同有效关系。由于现有统计数据难以区分不同创新主体的创新产出,因此出于数据获取的难度,目前尚未见到相关研究文献使用第二种研究方法。基于同样的原因,本文也将采用第一种研究思路。
二、研究方法及样本选择
现有关于效率比较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的文献主要使用两类方法,即基于参数估计的随机前沿法(SFA)和基于非参数估计的数据包络分析(DEA)-Tobit两步法。两种方法各具特点:随机前沿法认为,生产效率除受确定性的投入产出变量影响外,还会受众多随机因素影响,因此在效率分析中必须将这些随机因素考虑在内;同时,通过在模型中设定技术无效率项的影响因素,SFA可以在进行效率排序的同时进行效率影响因素分析,从而达到通过一步分析同时解决两个问题的目标[12]。其局限在于,使用SFA法需要设定投入产出之间的具体函数关系,并且只能使用单一指标衡量产出。尽管Wang[13]曾经使用加权方式将多种产出总合为一种,然而解决加权法面临的理论基础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数据包络分析可以克服SFA法的局限,首先,DEA可以使用多个指标来衡量产出,其次,使用DEA进行效率分析时无需设定投入产出之间的具体函数关系。但同时SFA的长处则变成了DEA局限:DEA无法考虑随机因素对投入产出效率的影响,且必须使用二步法才能进行效率影响因素的分析,即首先必须使用主要投入产出指标估计出各决策单元的效率值,然后以此作为被解释变量,各影响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回归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和检验。
在评价国家创新效率时,创新产出难以使用单一指标进行准确刻画,故本文选择使用DEA法。但在使用经典DEA模型进行效率评价时,可能出现多个决策单元同时位于效率前沿面,从而无法进一步对其进行效率排序的情况,因此 Andersen and Petersen[14]提出了超效率DEA模型以解决该问题。由于超效率DEA分析所得到的各决策单元的效率值均大于零,属于截断数据,因此将其作为因变量进行效率影响因素分析时,若直接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则得到的参数估计量是有偏且不一致的,因此一般使用受限因变量Tobit模型[15]进行效率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本文选择澳大利亚(AUS)、比利时(BEL)、加拿大(CAN)、捷克(CZE)、丹麦(DNK)、芬兰(FIN)、法国(FRA)、德国(DEU)、爱尔兰(IRL)、意大利(ITA)、日本(JPN)、韩国(KOR)、墨西哥(MEX)、荷兰(NLD)、新西兰(NZL)、挪威(NOR)、波兰(POL)、西班牙(ESP)、瑞典(SWE)、土耳其(TUR)、英国(GBR)和美国(USA)等22个OECD国家和俄罗斯(RUS)、新加坡(SGP)及中国(CHN)共25个国家作为研究样本,时间跨度为1996-2009年。所有数据若未加特别说明均来源于OECD、世界银行和IMF公开数据库。
三、国家创新效率的比较
(一)投入和产出指标选择
与现有研究文献一致,本文选择研发资本投入(GERD,单位:亿美元)和研发人员全时当量(RDFTE)两个指标作为一国创新活动的投入指标,其中各国研发资本投入数据均按购买力平价和美元价格指数折算为2005年的不变价格美元。Griliches[16]认为,研发资本投入是一项流量指标,它对创新产出的影响不仅反映在当期,而且会持续到未来,因此与多数研究文献一致,本文也采用永续盘存法将研发资本投入转换为研发资本存量(RDCapt,单位:亿美元)作为创新投入指标。具体计算方法为Ki,t=(1-δ)Ki,t-1+Rit。其中Ki,t和Ki,t-1分别表示第i国在第 t和 t-1 年的研发资本存量;Rit为其在第t年的研发资本投入。基年(1996年)的研发资本存量则得用公式Ki0=Ri0/(gi+δ)进行估计,其中gi为i国1996-2009年不变价研发资本投入的年均增长率。δ为折旧率,本文采用多数文献的观点取δ=15%。
专利、高质量科技论文、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和高技术产品出口值是现有文献衡量创新产出的主要指标,区别主要在于是采用专利授权数还是采用专利申请数。部分学者认为,使用欧洲专利局、日本专利局和美国专利商标局获准的三方专利数(TriPat)更能表征一国的科技创新质量,然而三方专利从申请到授权通常存在4年以上的时滞,获得美国专利商标局的授权时滞更可能长达6~9年(OECD:Ma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2012/1),因此将其与科技论文、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和高技术产品出口值并列作为产出指标并列使用时,不同指标之间的投入产出时滞将存在很大的差异,从而使分析结果受到影响。故本文选用与三方授权专利高度相关,但却不受授权时滞影响的、各国根据专利合作条约(PCT)申请的专利数(PatPct)、在物理/生物/化学/数学/临床医学/生物医学研究/工程和技术/地球和空间科学等领域发表的科技论文(Article)、高技术产业增加值(ValHitec:以2005年PPP美元计价,单位:亿美元)和高技术产品出口值(ExpHitec:以2005年PPP美元计价,单位:亿美元)作为创新产出指标。其中科技论文数量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来源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2》附表。
Cooper等[17]指出,在应用DEA法时,仅当投入产出变量数目m和s与决策单元数量n之间满足条件n≥ max{m×s,3(m+s) }时,DEA法才能得到较好的结果,结合前述分析可知本文的选择满足上述条件。表1给出了中国与其他24国相关投入产出指标概略对比。
从表1的简要数据可以看出几个基本事实:第一,在样本考察期内,中国年均研发资本投入是其余24国的1.87倍,而研发人力投入更是达到了4.46倍,人力和资本投入可能存在不匹配现象。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24国在14年间每单位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的年均研发资本投入平均为10.94万美元(2005年PPP),而中国的对应值仅为4.60万美元,因此尽管14年间中国研发资本投入的年均增长速度接近20%,是其余24国的4倍,但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有继续加大研发资本投入的必要;第二,三方专利授权是反映一国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作为其代理变量,中国在PCT的专利申请数量尽管在样本考察间高速增长(增速超过了24国均值的4倍),但从绝对数量上看,仅为24国均值的70%,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在原始创新能力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第三,在反映创新产出的其他三个指标方面,中国无论是从绝对数量和增长速度上都远高于其余24国,说明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在不断增加。但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与科技论文和PCT专利申请增速之比远低于其余24国,反映出中国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效率还有提升的余地。

表1 中国与24国投入产出指标的概略对比(1996-2009)
(二)各国创新效率的超效率值分析
由于创新投入和产出之间具有时滞性,而关于滞后期的选择国内外学者也进行过大量研究,研究结论也随指标选择的不同而不同。在选用专利申请量作为产出指标时,目前多数文献选择的时滞是2年。就本文所选择的投入产出指标而言,从后文效率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可以发现,选择1~3年的时滞均可以。因此本部分时滞暂定为2年(1年和3年时滞的结果并没有太大的差异)。表2给出了25国1996-2009年创新效率的超效率评价结果。

表2 各国1998-2009年创新效率的超效率评价结果
从表2可以看出,经济危机对各国国家创新效率影响巨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998年25国平均创新效率随即达到分析期内的第一个低谷,此后逐步回升,并于2000年达到分析期内的最大值,进而随着21世纪初网络泡沫的破灭,25国平均创新效率开始下降,至2003年达到低点后开始回升,而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又开始出现较大幅度下降,2009年更达到12年间的最低水平。
从表2还可以看出,创新能力强的国家并不一定意味着创新效率高,如美国、日本、法国的创新效率排名很低,而土耳其、新西兰、荷兰、墨西哥等创新能力并不突出的国家其创新效率却居于前列。因此本文猜测,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创新能力较弱的国家可能通过创新效率的提高而对创新能力较强的国家形成追赶效应,从而出现国家创新能力收敛的情形。
图1进一步描述了中国和其余24国平均创新效率的对比。结合表2和图1可以发现,中国的国家创新效率总体偏低,在25个国家中仅排第16位,并且自2000年后,中国的创新效率一直低于24国的平均水平。从动态发展的角度看,有一个事实特别值得关注,虽然样本考察期内中国的创新投入持续高速增长,但与之对应的创新效率却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尽管金融危机期间随着各界对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视,2009年的创新效率开始回升,并由此大幅度缩小了与24国的效率差异,但由此暴露出的创新资源的高效利用问题值得高度关注。

图1 中国和其余24国创新效率的比较
(三)各国创新效率的Malmquist指数分析
利用Malmquist指数分解可以方便分析各国全要素创新效率的变化情况(TFP)。一国TFP的变化可以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Effch)和技术进步(Tech),其中技术效率变化反映的是每个决策单元从t期至t+1期往生产前沿面的追赶程度。若Effch〉1,则表明该决策单元与最优生产前沿面的差距在缩小,它还可进一步细分为纯技术效率变化(Pech)和规模效率变化(Sech)。技术进步衡量的是相邻两个时期内决策单元的生产技术变化程度,即生产前沿面的移动,该指标大于1则表明生产前沿面在向前推移,生产技术有所进步。各指标之间的关系为TFP=Effch×Tech=(Pech×Sech)×Tech。表3和表4给出了Malmquist指数分解的相关结果。

表3 不同时期全部样本和中国的Malmquist指数分解
从表3和表4可以看出,样本考察期内,12个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其中多数为创新能力较弱的国家。25国的TFP平均下降了0.4%,其中主要的下降时期仍然集中在网络泡沫破灭和金融危机爆发期间。技术效率在此期间上升了1.4%,因此导致TFP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于技术退步。从表3可以看出,自网络泡沫破灭后,9个时期中有7个时期处于技术退步状态,这或许与电子信息技术成熟后全社会缺少新的技术创新热点有关。

表4 不同国家1998-2009年的Malmquist指数分解
25国中,中国的TFP下降率仅次于丹麦,平均高达4.7%,其中2000-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对中国TFP的冲击最大,当期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了大约20%,2007-2008金融危机爆发也使中国的TFP下降了大约12%。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作为衡量国家创新效率的重要指标,两次危机均对其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从而使全要素生产率出现大幅度下滑。尽管在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2009年间,中国的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了3.3%,但这种增长主要是靠投入驱动的,当期的规模效率创纪录地增长了21.6%,而同期的技术退步率同样创纪录地达到了15%。除了这种极端情况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样本考察期内,中国的平均技术退步率高达4.6%,是25国中最高的,且11个时期内有9期处于技术退步状态。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的出现?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①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观察结果具有稳健性。反复改变样本分析时期进行多次分析后发现,中国在创新活动中的技术退步状态长期存在,并且近年来还变得比较严重。。
四、国家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
(一)变量设定及研究假设
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是一个由政府、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多主体协同参与的复杂系统工程,同时还包含了基础设施、金融体系、教育体系、制度环境、文化环境等多个子系统的建设。因此影响一国创新效率的因素众多。依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并结合经典的FPS分析框架,本文所选择的影响因素包括以下五方面。
(1)不同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动:按照OECD的分类,企业、高校、政府所属科研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国外科研机构是一国技术创新的行为主体,不同主体的创新活动会对一国创新效率产生不同影响,但由于前三类机构在国家创新中居于主体地位,他们的研发支出占据了一国研发投入的绝大部分份额,因此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选择企业(BusPerf)、高校(UnivPerf)、政府所属科研机构(GovPerf)的研发支出占总研发投入的比重表征不同主体的创新活动。若三者均对国家创新效率产生了显著促进作用,则说明彼此之间是协同有效的。
(2)政府政策:政府对创新活动的财政投入和税收政策是影响一国创新效率最直接也最重要的政策因素。政府对创新活动的直接财政投入主要通过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实施,因此为保证变量间的独立性,该变量不能再列入模型。但若三者的创新活动能显著促进国家创新效率,则也就从侧面说明政府的财政投入是有效的。因此政策分析的重点是一国的税收政策。
从企业层面看,理论和实证的分析均表明,税收本质上是对企业创新成功的惩罚,它会削弱创新主体的创新积极性,从而既不利于提高企业创新的效率,也不利于扩大创新规模[18]。然而从国家层面看,低税率尽管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效率,但却不一定能促进国家创新效率的提高,因为:其一,企业并不是国家创新的惟一主体,高校和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创新协同是提高国家创新效率的重要途径,而两者的创新投入的源泉是国家税收,因此若税率过低导致其创新投入不足,势必抑制国家创新效率;其二,作为公共产品,创新基础设施和创新环境的培育皆由国家通过税收提供,因税收不足而导致的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和创新环境建设滞后同样会对创新效率产生负面影响。但另一方面,即使高税率能带来高税收,且税收的增加能相应带来高校、科研院所及创新基础设施等的投入增加,但其对国家创新效率的边际增量同样可能因为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削弱而抵消,因此本文假设一国税率对国家创新效率具有拉弗效应,即过低和过高的税率均不利于国家创新效率的提高。本文使用一国税收占GDP的比重表征税率(Tax)。
(3)创新基础设施及创新环境:选用每百人互联网用户(PerNet)、高等教育入学率②与创新活动直接相关的人力资源变量应该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但因缺乏中国相应的统计数据,因此本文用高等教育入学率替代。(HiEnrl)、公共医疗支出占GDP的比重(Health)表示创新基础设施;选用国家的民主化指数(Democ)、政局稳定性指数(Stabiliy)、政府行政效率(GovEff)、鼓励私营经济发展的规制质量指数(Regula)、法制指数(Legal)、反腐指数(AntiCor)表征创新环境,每个变量的取值区间均为[-2.5,2.5],变量取值越高,相应的环境状态越好。很显然,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创新环境有利于各创新主体的创新行为,从而促进国家创新效率提高,因此预期上述9个变量均应与因变量正相关。
(4)经济环境:选用人均GDP(PerGDP)、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FDI)、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Trade)和金融机构贷款占GDP的比重(Credit)表征国家创新的经济环境。
人均GDP衡量一国富裕程度,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是技术创新,因此穷国要实现追赶必须在国家创新效率上实现对富国的追赶,因此预期该变量与创新效率负相关;FDI对一国创新效率的影响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藉由FDI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能显著促进一国技术水平,从而对国家创新效率产生正面影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伴随FDI而来的先进技术会使东道国的技术投资不再具有盈利能力,从而抑制未来的创新投入,进而使东道国陷入对外技术依赖陷阱,因此预期FDI对国家创新效率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衡量一国贸易开放度,开放的进出口贸易不仅有利于一国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更能通过激烈的国际竞争促进本国创新效率,因此预期其与国家创新效率正相关;金融机构贷款占GDP的比重衡量一国金融机构对经济的服务能力,预期其与国家创新能力正相关。
(5)时间趋势:根据前文分析猜测各国创新效率具有时变趋势,因此将时间趋势项也纳入模型。
(二)模型设定及滞后期的选择
将前文计算出的各国创新效率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如下面板Tobit回归模型:

其中k为滞后期,EFF*i,t为潜变量,EFFi,t为DEA计算的真实创新效率值,二者之间满足:

已有文献通常事先设定滞后期k值,然而出于两个目的,本文将分别设定k=1,2,3,4:其一,通过设定不同的滞后期,可以对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查;其二,不同的滞后期实际上还能反映当期的创新投入和其他因素能在多长的时期内影响未来创新的效率。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表5结出了国家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的Tobit回归结果。
企业、高等院校、政府所属科研机构的创新活动在4个模型中都显著促进了国家创新效率的提高,说明三者在推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是协同有效的。回归结果同时说明,三者的当期的创新投入能对未来至少4年的国家创新效率产生积极的影响,这就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知识积累对创新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分析三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可以发现,三者的创新支出对国家创新效率的边际影响在滞后2年和3年时最高,从而也说明现有文献通常将滞后期设定为2年具有合理性。
税率和税率平方项在四个模型中都高度显著,并且二次方项符号为负,说明税率与创新效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前文关于税率对国家创新效率具有拉弗效应的假设得到了验证。然而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增税或减税有利于促进国家创新效率的简单结论,因为税率的变化是通过创新资源投入影响国家创新效率的。如果增加税收没有相应增加创新投入,那么即使现有税率低于最优税率,增税也不能促进国家创新效率;反之,如果在降低税率的同时并不削减国家创新投入,那么即使当前税率低于最优税率,进一步减税对创新效率的提高也是有利的。

表5 不同滞后期下国家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的Tobit回归
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对国家创新效率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其中政府在信息基础设施和高等教育方面的投资能够产生即时和长期的影响,而在医疗卫生上的投入则在滞后2年后才开始显著促进一国创新效率,并且其边际效应递增。
6个创新环境变量之中,一国政局的稳定性、政府行政效率和鼓励私营经济发展的规制质量指数都对国家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事前预期相符。而政治的民主性、反腐指数和法制指数变量均不显著。值得注意的是法制指数符号为负,与事前预期不符。原因可能在于,与创新效率紧密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包含在此变量之中,Schneide[19]的研究发现,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促进技术领先国的原始创新,但却不利于技术落后国家的创新扩散,从而使该变量变得不显著并且符号为负。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分离知识产权保护因素。
4个经济环境变量中,人均GDP变量符号为负且在四个模型中均显著,说明人均GDP越低的国家技术创新效率越高,即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穷国会对富国形成追赶效应,与事前预期相符;贸易开放度符号为正且在四个模型均显著,说明开放的贸易确实有助于提高国家创新效率。FDI在滞后1年时符号为正且显著,但之后变得不显著,且在滞后3年和4年时符号为负,说明就短期而言,FDI对国家创新效率有促进作用,而长期作用不显著,并且可能具有抑制趋势;金融机构的服务对国家创新效率没有显著影响,这与众多区域创新效率研究文献所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根本原因在于,创新活动具有高风险性,而信贷资本收益的固定性决定了信贷资本不可能投资于高风险的创新项目,因此各国主要是通过大力发展创业投资而非动员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资助创新活动,尽管传统金融机构通过对经济体系的服务可以间接促进国家创新,但显然这种间接效应对国家创新效率的提高并无显著影响。
五、结语
本文以25国1996-2009年间的创新数据为样本,应用超效率DEA法比较了各国的国家创新效率差异,并进一步运用DEA-Tobit两步法分析了相关创新主体的创新协同效应和国家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在1996-2009年间,中国单位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的年均研发资本投入、PCT专利申请数量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与科技论文和PCT专利申请增速之比与其余24国相比均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未来中国必须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并注重原始创新能力的建设和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
(2)各国创新效率均会受到经济危机影响,创新能力较弱的国家创新效率反而较高,因此各国创新效率存在收敛趋势。中国的国家创新效率目前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并且在样本考察期内总体呈现出下降趋势,因此创新资源的高效利用是未来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3)受两次经济危机的影响,各国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在样本考察期内呈下降趋势,其中技术退步是引起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幅度仅次于丹麦,而技术退步幅度则为25国最高,未来要实施国家创新效率的赶超必须弄清楚技术退步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一问题。
(4)在所考察的样本范围内,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创新活动能显著而持续地促进一国创新效率的提高,因此作为一国重要的创新主体,官产学研之间的创新协同是有效率的。这一结果同时说明,增加各创新主体的创新投入对提高国家创新效率是有利的。
(5)在影响国家创新效率的因素之中,一国宏观税率对国家创新效率具有拉弗效应,过高和过低的税率均不利于国家创新效率的提高。但在应用这一结论时必须与税率对创新效率影响的传导机制相结合,并不能简单得出增加或减少税率有助于提高国家创新效率的结论。
(6)创新基础设施建设能在短期或长期显著促进一国创新效率的提高;一国政局的稳定性、政府行政效率、对私营经济的扶持和贸易开放度也具有相同的效应;外资流入对国家创新效率有短期促进作用,而长期作用并不显著;金融机构的服务对国家创新效率不存在显著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在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创新环境变量的取值主要使用主观赋值法,不同的评估机构所使用的指标和评价方法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未来应该对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对比研究,以得出更加稳健的研究结论。
[1]FREEMAN C.Japan:A new 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M]//DOSI G,FREEMAN C,NELSON R,et al.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London:Pinter Publishers,1988.
[2]NELSON R.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A comparative analysis[M].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3]池仁勇,唐根年.基于投入与绩效评价的区域技术创新效率研究[J].科研管理,2004,25(4):23-27.
[4]李习保.区域创新环境对创新活动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8):13-24.
[5]白俊红,江可申,李婧.应用随机前沿模型评测中国区域研发创新效率[J].管理世界,2009(10):51-61.
[6]FURMAN J L,PORTER M E,STERN S.The determinants of national innovative capacity[J].Research Policy,2002,31(6):899-933.
[7]HU M C,MATHEWS J A.National innovative capacity in East AsiaJ].Research Policy,2005,34(9):1322-1349.
[8]HU J L,YANG C H,CHEN C P.R&D efficiency and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using the distance function approach[J].Bulletin of Economic Research,2011,Advance Online.
[9]GUAN J C,CHEN K H.Modeling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J].Research Policy,2012,41(1):102-115.
[10]吕新军,胡晓绵.到底是什么阻碍了国家创新?——影响国家创新的制度性因素分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31(5):115-120.
[11]郭淡泊,雷家骕,张俊芳,等.国家创新体系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DEA-Tobit两步法的分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7(2):142-151.
[12]BATTESE G E,COELLI T J.A model for technical inefficiency effects in a stochastic 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 for paneldata [J]. EmpiricalEconomics, 1995, 20(2):325-332.
[13]WANG E C,HUANG W.Relative efficiency of R&D activities:A cross-country study accounting for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the DEA approach[J].Research Policy,2007,36(2),260-273.
[14]ANDERSEN P,PETERSEN N C.A procedure for ranking efficient units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J].Management Science,1993,39(10):1261-1264.
[15] TIMMER C P.Using a probabilistic 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 to measure technical efficienc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1,79(4):776-794.
[16]GRILICHES Z.R&D and the productivity slowdow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0,70(2):343-348.
[17]COPPER W W,LI S,SEIFORD L M,et al..Sensitivity and stability analysis in DEA:Some recent development[J].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2001,15(2):217-246.
[18]熊维勤.税收和补贴政策对R&D效率和规模的影响——理论与实证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1,29(5):698-706.
[19] SCHNEIDER P H.International trade,economic growth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A panel data study of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5,78(2):529-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