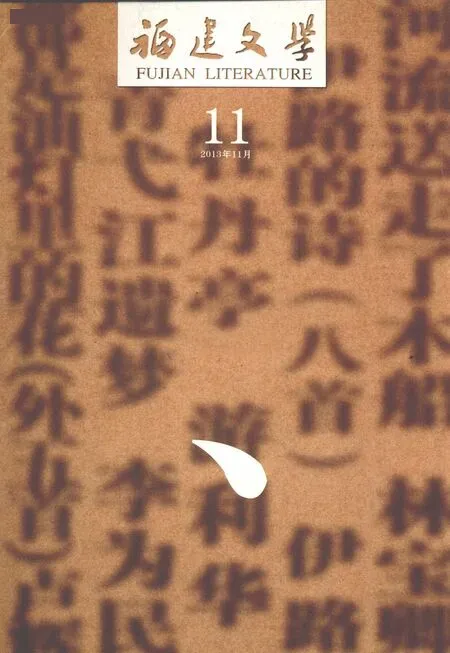我们感恩父母什么
□茅 草

1
这天下午,太阳被云朵遮掩了一部分,风像蝙蝠飞着飞着就不见了,跟上午晴空万里、气流通畅的天气不能比。我坐在办公室里写今天上午发生的新闻稿。我写道:
8月28日上午八时,这个经过选择的吉祥时间在一家新开张的酒店定格,省国信无线寻呼有限责任公司揭牌仪式隆重启动。至此,百年邮电开始了它拆分解体的命运。社会各界、省内新闻媒体近2两百人见证了这一时刻。
这是导语。写完它我停止敲键,抬起手来敲打自己的胸口——有些胸闷。是不是关着窗户的缘故?可是,窗户大开着,是天气沉闷。我们所处的这个城市经常气候反常。在若干年前,这里就是一个大湖底,一旦没有了风,湖底就会变成一个坛子,闷得人心慌。在这么难受的情况下我是写不出文字的,更何况我将要写到新任总经理雷新春,就更搜刮不出什么好词汇了,不如先搁一搁,到吸烟室抽一支烟,等心情变好一点再说吧。
我从六楼慢慢地踱到二楼,没有坐电梯。吸烟室的门是关着的,我推门,门缓缓地露出一条缝,一股烟味迅速从门缝里飘出来了,飘进我的鼻子。我看到一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男子坐在烟雾中大口大口地吸着烟,他是办公室秘书陈哲男。我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下,也点燃一支烟,边抽边跟他聊起来。
他说他刚才在办公室里写一个局长的讲话稿,开了一个头就不想写了,脑子里老想着今天上午的事儿。说完,他又重重地吸了一口,呼地吐出来:他妈的,跟我同样的年纪,就蹿到了这么高的级别……
看来,单位上的年轻人都有可能被今天上午的事搅得心绪不宁。我说,确实没想到,竟然把他提拔起来了,你看到他坐在主席台上没有?你听他讲话没有?
你是说他跟坐在旁边的老领导不相称,是吧?你是说他讲话像小学生念作文,是吧?
正是。
上午,我坐的位子比陈哲男离主席台近,我看到雷新春的表情像笑又像哭,看到他从座位上站起来时行为慌乱,步伐失调,看到他张望发言席和麦克风的眼神像小偷,看到他走到麦克锋前准备讲话时忘了掏上衣口袋里的发言稿,看到聚光灯照射下的他的脸上闪烁着汗水的反光。我们还听到台下有人纷纷议论:他就是新任总经理……一点都不像啊……怎么可能像呢?他刚满30岁,1990年大学毕业,在副处级的职位上工作不满一年,整个儿就是稚气未脱、乳臭未干啊。
陈哲男长叹了一口气,说,你晓得这里面有背景吗?
这谁不晓得?邮电行业有着百年历史,在社会上被广泛地称之为“铁饭碗”,干部的任用从来就是论资排辈的,四十多岁提科长、五十多岁提处长是常有的事,也是正常的事,雷新春能一步登上副厅级的宝座,怎么会没有背景?
我说,只是不晓得是什么背景罢了。
我告诉你吧,跟他老子有关。陈哲男说。
陈哲男作为局长的秘书,关注这些隐秘就像我关注新闻一样。我的两只耳朵嗖地竖起来,这似乎比我报道雷新春有意思多了。雷新春老子我们认得,退休前,跟我们同在省邮电管理局机关工作,任劳资处处长,是一个恭谦、和善、低调的人,看不出有什么活动能量。
他老子在位期间,替局长在邮电部扛了一件大事,陈哲男讲道,要不是他扛了这件事,局长有可能被免职……现在,局长不忘他老子的恩情,就以提拔他儿子为报。
哦,是这样……我感叹道,我们要是也有一个这么好的老子就好了,特别是你,真屈才!
你还不是一样,你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蹿到他那个位置上。
两个农民的儿子同病相怜,除了空羡慕,就是你一口我一口、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浓浓的烟雾挡得我们几乎睁不开眼。我大雷新春五岁,在邮电系统工作了13年,其中12年在基层,去年才调到省邮电管理局机关任《人民邮电》报驻地记者,如果不出现雷新春坐直升飞机这件事,我是满足的:全省邮电系统5万人,有多少人想到省邮电管理局机关工作,可是一辈子都不会有机会,而我还不到40岁就实现了这个梦想,然而相对雷新春而言,我的这一点愿望就显得相当的可怜了。
陈哲男被烟雾呛得两眼流泪,起身冲出了吸烟室,我继续坐在烟雾中没有动,我父亲的那张脸仿佛在烟雾中忽隐忽现……他7岁时死了亲娘,我祖父娶了一个比他前妻年轻、漂亮的女人,所以,我祖父对这个女人言听计从。新婚之初两个人成天抱在一起,不仅不管我爷还嫌他碍手碍脚。据我娘讲,爷的后娘连挨都没挨过我爷一下,好像挨了我爷就是挨了我祖父的前妻,她把对我祖父前妻的嫉恨转移到我爷身上,所以,她基本上把我爷当作我祖父的前妻来对待。我爷种水痘,她阻止我祖父为他治疗,还不断地加以虐待:每天早晨把他装在包袱里,捏着四只角提出去丢在巷子里让他一个人玩,天黑时才拎进屋;我爷发烧,她用冷水浇到他身上降温。就这样,我爷落下了满脸的麻子和失明的双目,好在保住了一条性命。别人家的孩子上学了,我爷上不了学,他跟了一个年纪大的瞎子学算命。我爷聪明、勤奋,蛮快就掌握了算命的要领,不久,来找他算命的人数就超过了他师傅。我爷赚了钱,赢得了资本。1954年,我姆妈家被划为地主强制离开本村到异地改造来到了我爷这个村,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的我姆妈一家住到了我祖父家的厢房里。我祖父是一个精明人,他哪里会这么心甘情愿地无偿提供一间厢房,他打定了主意——想把我外祖父的女儿变成我爷的媳妇。我外祖父的女儿毕竟是一个双目明亮的健康人,但最终还是被我祖父逼成了一对。这样,我爷的后娘就有理由让我爷离开他们单独过日子了,于是,就有了我姐、我妹和我以及度日如年的一家人。像我父亲这样的男人,或者说作为一个父亲,他能够把我们生出来、抚养成人就相当不容易了,更何况还把我送上了大学,让我参加了工作,这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他的能力所及。所以,在我老家,我一说我是我爷的儿子,几乎没有人敢相信:瞎说吧?你是他的儿子?他有一个这么大出息的儿子啊……我爷留给我的遗产就是山脚下的那一栋老屋,当年4000块钱死活卖不出去,现在成为了一堆烂泥;父亲留给我的精神财富只有两句话:一句是“人情大于天”;另一句是“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穷”,而这两句话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至死都不能忘记……
哦,我在想这些吗?我不知道……我不敢说我在想,谁敢嫌弃自己的父亲呢?更不敢说自己的父亲比不上人家的父亲,岂不是有违父亲对自己的教诲?岂不是对他老人家的不敬?可是,我又不敢说我没有想,毕竟我、雷新春、陈哲男都同处在一个单位,谁不希望自己的父亲对自己有更大的帮助呢……
2
2012年农历七月初七,我姆妈的生日,我从省城回到老家赤县。那一段时间,我姆妈从省城回到了老家,住在我妹妹家里。我姆妈说她不做生日,免得影响了大家。我妹妹非要为她过,说现在都兴过。我一副无所谓的态度,过也可,不过也可,只要我姆妈高兴就行。最终,我姆妈犟不过我妹妹,就说实在要过,那就简单一点。我妹妹找了一家普通的酒店,订了一桌家常菜,除了我们一家人以外,就是几个舅舅和晓得我回来了的几个老朋友,加在一起15个人。
朋友中有我曾经在赤县县委党校任教时的一个学员,因前年大病了一场提前两年从职位上退下来了。他见到我母亲时大发感慨:哎呀呀,人生七十古来稀,您老74岁了还这么健旺,一点都看不出年龄来呀,你们看看,你们看看,这哪像74岁的人,叫我看,顶多60岁,是吧?
在场的人随声附和:60岁都看不出来,像五十多岁。
我姆妈哈哈大笑。她本来一直站着,以显示她无所谓的态度,听了学员的话,这才稳稳重重地坐下来,显得像个老寿星的样子。她说,那是的,我的身体就是本钱,去年冬天,我还洗冷水澡哩,一般的人不敢,我几十年来不得大病,莫说一般的老人,就是后生也不敢夸这个海口……
学员坐在我姆妈的对面,目光落到我姆妈强壮的身板上,禁不住啧啧称赞。学员小我姆妈20岁,可是他的身体不能跟我姆妈比,莫说洗冷水澡,就连冷水洗脸都受不了。我要是有您这么好的身体就好喽。学员无比羡慕地说。
那是,我姆妈接过学员话,我现在住在我二女儿家里,什么事不是我做?我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他们哪一个的小伢不是我一把屎一把尿地带大的?现在的保姆光工钱就是一年3万,我给他们带伢,要算工钱的话就是大几十万了,还不算我给他们做饭、买菜、洗衣服、做清洁,我有这身板子,我在儿子那里的时候,楼上楼下的爹爹婆婆哪一个不是三天两天扶的扶、抬的抬,哼的哼、哭的哭去医院?有一个姓谢的婆婆长期住在医院里,长期要人端屎端尿送饭,不说医药费千把万把,就是服侍也服侍不过来吧?嘿嘿,我不但不要他们服侍我,我还服侍他们哩。
好福气,好福气……学员有些惭愧,与我姆妈比,他已经是未老先衰了。
我姆妈的笑声使包厢里充满了欢乐,散发到每一个人的脸上又还原成笑容。
几个女服务员来去如梭,菜很快上齐了。不用请,我姆妈主动挪到一席的位置上坐下来,然后招手请在场的亲戚朋友坐。桌子是圆的,大家坐成一个圆。我弟弟倒酒。我姆妈先端起酒杯,说感谢大家,但被我们制止了,说今天的第一杯酒应由我们敬寿星。我们一齐站起来,给我姆妈敬酒。我姆妈坐着,端起酒杯喝了。脸上有了一些酒晕,目光却暗淡下来:
唉,就是有一条,我不像城里的婆婆拿工资,我还得靠下人吃饭……
这事我姆妈说过好几回了,每次都说得我们心里酸酸的,我也劝过她:莫说了,姆妈,那有多少钱呢……我们又不缺钱……我姆妈说,好,不说了,不说了。可是,只要她一想起那些城里拿工资的爹爹婆婆,她的心里又不安起来,她总觉得她在白吃我们的粮食。这时,学员摆了摆手,劝我姆妈说:
您老人家千万莫那样想,千万莫那样想,拿工资是收入,不拿工资也是收入……
你是说我会节约?
我姆妈的反应还有这么快。
是呀,一个单位的收入来源除了增收还有节支呀,一个家庭也一样,您帮家里减少开支,不相当于在拿工资么!
学员不愧是乡镇干部,几句话说得我姆妈眉开眼笑。
学员说,来,我敬您一杯。
我姆妈站起身,与学员干了一大杯。
我、我姐、我妹以及全家人趁热打铁,一齐站起来涌到我姆妈面前,七八个酒杯凑到一起就像一簇盛开的百合。我们齐声说,感谢您为我们减少了开支;感谢您这么多年来身体健康,没有给我们添麻烦。
我姆妈连说了几个好,干了我们敬她的酒,她捏着空杯子,说:
我要是动不得了,就自己死,我不连累你们!
虽然是笑着说的,但仍然像掷出的一枚重型炸弹,立马让全场一片寂寞,我们几个儿女的心轰的一下,仿佛像被震碎的一地玻璃。
3
从赤县回来的第二天上午,我与陈哲男又在吸烟室相遇了。不过,眼前的这间吸烟室已经不是14年前的那一间了,这一间吸烟室在我们现在所在的单位,即省内新成立的一家移动电话运营公司。从1999年元月起,原庞大的全省性的邮电管理局不复存在了,被拆分成邮政与电信两家,我和陈哲男一起分到了邮政;2000年,省内新成立了这家移动电话运营公司,我和陈哲男约好于2001年7月辞职,来到了这家公司工作。可是,谁知我们刚刚报到不久,国资委下达文件:省国信无线寻呼有限责任公司成建制划归这家移动运营公司。于是,雷新春成为了我们的领导。这真是山不转水转,水不转路转啊。
陈哲男递给我一支烟,说是从家乡带来的,他也回了一趟老家。这些年城里的东西越做越假,而且许多东西遭受污染,所以乡里货大受青睐。我一边接过烟,一边掏出打火机,先给陈哲男点上,然后给我自己点。我说我昨天也回了一趟老家。我问他家里人都好吧?陈哲男脸上突然涌现出一股喜悦,好像找到了他的优势:别的不说,就这一点好,我家里人身体都好,不需要我操心。
我把昨天我姆妈过生日的情况讲给他听,说到那个学员说过的一些话,陈哲男听了,跟我姆妈一样兴奋。我们说着说着,又扯到雷新春身上去了。其实,老天是公平的……他说。
我的手机响了,看来电显示,是主任的电话号码。他要我赶快到他办公室里去一下,可是,陈哲男的话还没有说完,我只好向他拱拱手,说,实在对不起,主任有急事……陈哲男脸上浮现出遗憾的表情,像有一肚子非说不可的话,我说,改个时间说吧……朝主任办公室奔去。
主任见到我,说,你代表办公室,跟工会他们一起去看看雷总父亲吧。
工会叫了一辆商务车在楼下等,我和人力资源部的一位副部长一同下楼,工会副主席和一位负责老干部工作的漂亮女主管小武在车上等我们。看望的礼品小武都准备好了,不用我们操心。
我们上了车后,车子开始动起来,由慢到快驶出公司大门。工会副主席、我和人力资源部副部长年纪差不多大,熬了多年才熬到副处级的职位上,但我蛮知足:要是在原邮电管理局,我最多是个科长。工会副主席和人力资源部副部长就不一样了,也不晓得他们还有什么特殊的能耐或特别的背景,他们好像不仅表现出对雷新春的羡慕,而且希望有朝一日也能爬到他那个位置上。不过,说到雷新春父亲时,三个人又达成惊人的一致:老天好像真的蛮公平哩,虽然我们不像雷新春在上人身上受益,也不像他在上人身上受罪哩。猛然间我想到在吸烟室里陈哲男没有说完的话,禁不住笑了笑——陈哲男,你不必说了,你的意思我都晓得了。而奇怪的是,雷新春父亲在职时身体好好的,那时跟我们一起下象棋、打桌球,看不出有什么毛病,怎么一退休就这病那病都来了,三天两头地跑医院、住医院?这些年来,雷新春以及家里人基本上都在病房里陪雷新春父亲,而雷新春要不是父亲身体这么糟,受到拖累,雷新春很可能调到外省任总经理去了。现在,雷新春不仅没有了去外省任总经理的心情,甚至连本省的副总都不想干了,恨不得一天到晚就守着父亲。
有些细情我竟然不甚了解。有一次,我走出办公室准备到机要室去校对文件,在走廊上碰到小武。小武栽着头嘟嘟囔囔地不晓得在自言自语什么。我喊住她,问:
怎么啦?失恋啦?
小武扑哧一声笑出来:
哪里,本来公司的老干部就多,现在又来了一个,三天两头要联系住院,还要找好一点的医生做手术……
后来我才打听清楚小武说的就是雷新春父亲。雷新春父亲本来是电信公司的人,可是电信公司替他服务了这么多年没有耐心了,雷新春对他们不满意又拿他们没办法,只好把父亲转到我们公司来联系治疗,当然医药费还是由电信公司出,殊不知,我们公司的人也慢慢地失去了耐心。这就叫久病无孝子。
我们拿小武开玩笑,说老天是公平的,谁叫你长得比别人漂亮呢?所以你就要多付出一些。
小武嘟着嘴,说,照顾是不错,就是照顾不过来呀!
人力资源部副部长说,据我所知,人家就是冲着你来的哩,听说自从有了你照顾,病就好多了,是不是呀?
工会副主席说,漂亮真的能治病,还能提高办事效率,联系病房、联系专家、预订医药器材这些麻烦事,没有小武哪个办得到位呀。
说着笑着,协和医院到了。一路上,我几乎没有开口说话,说到别人的父亲总会想起自己的父亲,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似乎是得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语症。
雷新春父亲躺在病床上,见我们来了,在雷新春母亲的帮助下坐起来。雷新春母亲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女人,满脸堆着笑。当工会副主席代表我们把慰问的礼品送到雷新春母亲手里,雷新春母亲推辞了半天才肯接。雷新春父亲说,这哪要得……本来就给你们添麻烦了,还来看望,实在挺当不起啊。他老人家还是那么朴实,那么厚道。
算起来,我已经有15年没有见到雷新春父亲了。在我的想象中,既然他病了这么久,不是形销骨立,也是萎靡不振,可事实上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他虽然不如我姆妈那么硬朗,但气色和精神并不比我姆妈差多少,可见治疗得好,照顾得好,说明雷新春真的费了不少心。由此看来,付出和回报还是成正比的。我和雷新春父亲见面算是老同事重逢,所以,雷新春父亲跟我比跟其他人的话多。
他问我:在哪个部门?
我说,在办公室。
按理,他该问问我的职务,这是大多数老同事阔别之后都爱问的,但他没有问,好像这个话题比较敏感,不宜挂在嘴边。我特意告诉他:我现在在雷总手下工作。
雷新春父亲脸上掠过一丝笑意,但笑意很快就像电火一样熄了,他立即转移话题问我家里的情况。
父母还好吧?
他说。
母亲还好,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了。
我回答。
哦,不容易……
他晓得我是从乡里考大学来省城的,好像有些感慨,转过头去对另外几个人说,唉,人老了,没得用了,活在世上就是麻烦,既麻烦家里人,也麻烦你们,早点走何尝不是一件好事……
雷新春父亲的话戳到了我的痛处——我油然想起我父亲走的那一年……我鼻子发酸、眼睛发胀,眼泪在眼眶内打转,咕噜咕噜就要流出来了,我不得不栽下头,站起身,借故去上厕所。
1990年7月,我刚好大学毕业了,面临着工作分配,按我的所长和兴趣,我希望到出版社、杂志社工作,或者到作协、剧团当专业作家也可,可是,我父患肝复水已经两年,一直拿不出钱来好好治疗。我一直只能拿空洞的言语鼓励我父:再坚持一段时间,再坚持一段时间,我就要毕业了,等我拿了工资,好好给您治……我父摇头:那要等到几时啊,我怕是等不得了啊。我说,您一定要等,您这一辈子太苦,你生我们、养我们,不就是为了我们长大了,孝敬您么?我一定要让您过上好日子,享福……我父摇头:我这一辈子就冇想过要享你的福……我知道,父亲虽这么说,但心里未必真的这么想:哪个做父的不想享儿子带来的福呢?随着我毕业时间的迫近,我父的脸上渐渐地有了笑容,他失去光明的眸子似乎也闪烁出光亮。现在,我终于可以找工作了,我哪能不考虑单位的效益而只顾自己的爱好与兴趣?最终,我如愿以偿找到了一家效益不错的国营单位。我正准备回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父,哪料我父辞世的电报就发到了我手上。
我捏着电报,跪在地上,哇哇地痛哭起来:爷啊,爷啊,您怎么还是走了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快走啊……电报在我手心里被泪水浸泡成一坨纸泥。
那个夏天比冬天寒冷,我身上的温度仿佛下降到零度。当我扑倒在我父亲身上痛哭失声,跟我爷一起算命的邱老先生用力把我拉开,劝慰我道:
伢呀,这是命……
我挣脱邱老先生的手,继续扑在我爷身上:
爷,您的命怎么就这么苦……
邱老先生用力捏了捏我的胳膊:你爷的命苦,你的命不苦……你爷他安心地走了,对你来说是好事,带孝免灾……
我一把把邱先生推开,吼道:
你会不会说话啊?
邱先生一愣,知道我听不懂他的话。
等我爷下葬了,邱老先生又耐心地替我解释,说我爷这时候走是他选好的日子,我毕业了,不需要他扶持了,我参加工作了,拿得到钱了,他都放心了,也不拖累我了,我就可以一心一意地搞事业,图发展……
我还是接受不了邱先生的胡说八道,我捂着耳朵从他身边跑掉。但邱先生他相信,我总有一天会懂。
回到省城后,我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不管白天黑夜,我爷的身影总跟着我。别人递烟给我,我想到他——我爷一辈子抽最差的烟,我要把好烟留给他;陪客人吃饭,我想到他——我爷一辈子吃粗菜淡饭,最艰难的时候还吃过糠,从来没吃过一顿有营养的饭菜,即使在患肝病时,也没吃过一顿肉、喝过一碗汤;住上好房子了,我想到他——要是他老人家也能住进来,他该有多么享受;2002年我被任命为办公室副主任的时候,我把任命文带到我爷的坟前大声读出来,我希望他在地底下能够听到,希望他高兴地看到他的崽已经超过了他对他做一个公社秘书的想望……我几乎将我的全部生活都跟我爷联系在一起,我相信,我们虽然在阴阳两个世界,但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两个世界是相通的……现在,在雷新春父亲面前,我猛然回想起邱先生的话,幡然醒悟到了他话里的意义——可是,这是怎样的一种意义啊,这是这个世界上最高尚、最残忍的意义,这是语言系统里最美好、最绝望的意义……我在卫生间里把门反锁上,拧开水笼头,让哗哗的流水来掩盖我的哭声。
看望完了雷总父亲后,我们从医院里出来,工会副主席和人力资源副部长继续跟小武开着玩笑,他们的欢声笑语充溢了车内的空虚,却填不满我脑子里的空白。我扭头望着车外的高楼土崩瓦解一般急速地朝后倒塌,高远的蓝天上仿佛清晰地写着孟郊的诗句: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至此,我仿佛像一个小学生初步理解到它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