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卓见创新史 融古今于一炉
2013-08-28 09:48余光中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 2013年4期
余光中
木斋教授来西子湾客座一年,即将赋归,出示其四十年来创作之诗词及新诗作品,嘱我阅后抒感数言。我知道木斋教授近年深研古诗与曲词发生史,发为新论,轰动学界,不料他同时也热衷创作,而且积稿成笥。因思清末民初交替之际,豪杰之士有志一新旧体以赋大好新世界,前则有黄遵宪、梁启超之召唤,后则有胡适、闻一多辈应之以语体与新格律,但鲁迅、郁达夫以迄陈寅恪、高阳等仍寄情于所谓“旧体”。四十年代之王欣笛,新诗人之翘楚,晚年却皈依旧诗。旅美多年之学者周策纵则新旧双管齐下,晚年新诗层楼更上。
木斋教授之诗词,不拘于传统之旧律,有继武黄遵宪之志。其所作新诗,如下列《生命的刻度》一首,对仗中颇见张力与凝练:
别人用/岁月/来刻度/生命的/年轮/我却用/生命的/果实/来刻度/岁月
木斋教授面对的挑战,正是上述一世纪来有志拓展中华诗歌的才人所用力克服者。我盼望他以治史的卓见来创新史,而融古今于一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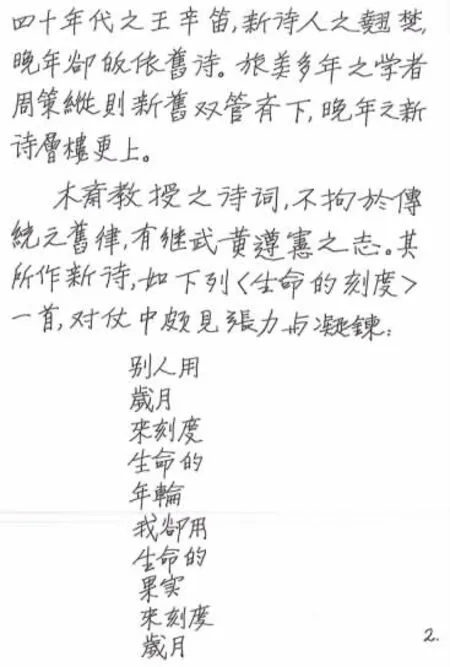

猜你喜欢
中华书画家(2021年12期)2022-01-06
网络文学评论(2021年1期)2021-03-06
海峡姐妹(2020年10期)2020-10-28
东坡赤壁诗词(2020年3期)2020-07-04
书香两岸(2020年3期)2020-06-29
文化学刊(2020年8期)2020-01-02
音乐教育与创作(2019年2期)2019-11-21
英语文摘(2019年6期)2019-09-18
作文周刊·高一版(2019年19期)2019-07-01
文史春秋(2017年9期)2017-1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