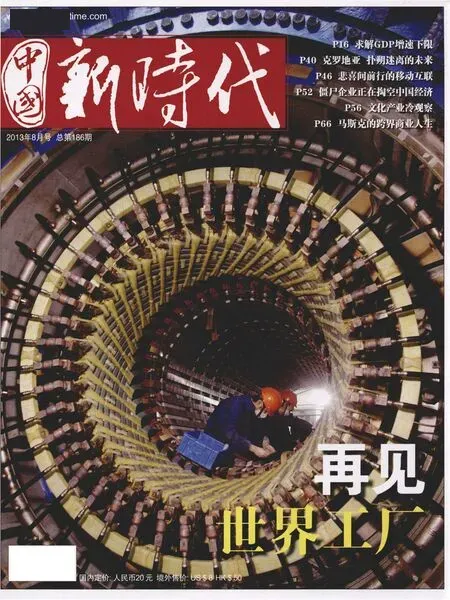经济转型与风险社会
| 文 · 朱敏
要论学者谁敢言,国家行政学院的竹立家教授是其中一个。早在2006年,他在《学习时报》上发表《政府管理改革的几个切入点》一文,针对政府公务开支提出了一组惊人数据,搅动了一池春水。
时过境迁,那些数据孰真孰假,早已无人再去深究。不过后来竹立家公开指出,育民德必先修官德,“三公”公开虽仍未能尽如人意,倒也取得了进步。
由于探索前行在公共行政管理前沿,很少有人视竹立家为经济学家,但这并不妨碍他以独特的哲学眼光和思维,审视经济发展与改革。竹立家坦言,近些年哲学有些失落了,人们已经习惯了用“经济思维”而不是“哲学思维”。但对“民富国强”或“国富民强”等一些命题的深度思考,必须深入哲学层面,即从“人类文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高度进行思考。
或许他是对的。如今,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正在进入“风险社会”。身处经济社会急剧变革的转型时代,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迫切需要有分量的哲思。
认清发展的“中国时刻”
朱敏:历经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在速度与规模上实现了高增长,但在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背后,“崩溃论”和“奇迹论”像DNA的双螺旋结构盘旋交锋,不绝于耳。您如何看待当前国际舆论对中国经济现象的热议?
竹立家:实事求是地讲,三十多年来,中国人的“现代叙事”确实很精彩,可圈可点的地方很多。当然,最值得我们骄傲的还是GDP的增速和总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GDP总量从1978年的2,683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5.879万亿美元,三十年间增长了20多倍,年均增速近10%,这在世界发展史上的确很少见。我们现在的GDP总量是世界第二,这当然是值得庆幸的事,说明我们的国力确实增强了。
但仅就国际关系而言,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中国作为大国的迅速复兴必然引起世界格局的重组,中国势必走到世界的前台,成为这个世界的“主角”之一。
如今,各种资料已经显示,利用军事资源、话语资源、地缘资源、经济资源等“围堵中国”的“大戏”已经开场。这说明,中国未来的发展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环境,对外关系面临重新“定位”和政策创新任务。能不能为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取决于我们高超的智慧和良好的决策。
朱敏:从国内情况来看,考虑到人均GDP相对较低、收入分配不公等现实问题,在中国经济规模跻身世界第二的背后,无疑蕴含着纷繁复杂的改革和利益诉求。
竹立家:没错。从1997年到2007年的十年快速增长期,劳动者薪酬占GDP比重从53%下降到40%左右;居民收入所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55%下降到2009年的42%左右。另外,全国大约有一半的职工近些年的工资没有增长或负增长,在经济成倍增长的情况下,这样的增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些数字说明,第一次分配就存在着严重的不公,使我们的“扩大消费”基本变成了一句空话,因为大多数“老百姓”手里确实没有钱。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有企业管理层薪资水平是普通职工的几十倍甚至是上百倍。
如果考虑第二次分配情况,现状也不容乐观。从2003年到2009年间,国家在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投入一直维持在28%左右,甚至2009年较2008年还下降了0.89%。这就是说,看起来每年的绝对数在增长,但相对数却没有增长,甚至在下降,因为财政收入增长更快,政府自身消费增长更快。当前,中国社会保障投入占财政收入的11%左右,占GDP的2.4%左右;而发达国家则占财政收入的50%以上,GDP的10%以上。由此可见,中国的二次分配不公现象也比较严重,“社会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
朱敏: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改革已经步入了“深水区”?
竹立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管理和改革滞后的现象也逐步显现,利益分化加剧,社会诚信度下降,社会不公正现象增加。可以说,改革的“议题”也由“如何做大蛋糕”变为“如何分好蛋糕”。换句话说,是由改革开放初期的解决“普遍贫穷”问题,变为目前的实现“社会公正”问题,将以“利益格局调整”为核心的改革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利益分配和利益格局的调整正在成为关键的“改革议题”,成为能不能成就中国道路的关键制度安排。改革确实已到“深水区”。
朱敏:也就是说,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为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但经济改革成果要从根本上得到保障,并进一步推进发展,还需要从制度改革上加以解决。
竹立家:是的,未来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较第一个三十年要严重得多。能不能在现有发展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发展,关键还在于未来几年社会管理体制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力度,在于改革是否能真正有效地消除贫富分化和特权腐败的制度性根源,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约束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保障民众幸福和尊严,让民众满意。
未来三十年,中国改革步入一个新阶段,踏上一个新台阶,改革的重点和中心任务都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这种转变是由我们社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决定的。换句话说,是由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制度逻辑决定的,不以人的愿望和意志为转移。对发展的片面认识或自我陶醉都是对社会、民族和历史不负责任的表现。
因此,回到问题的起点,对于经济总量世界第二,要有辩证思维,它既是新发展的起点,又为深化改革提出了新的迫切要求,经济发展与社会改革相对滞后的“时间差”,把我们带入一个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集中爆发的“复杂的改革期”。
民富国强是发展的目标
朱敏:在这样一个经济社会面临着矛盾和问题集中爆发的“复杂的改革期”,无疑需要从深层次去寻找改革突围的关键环节和突破口。在您看来,当下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能不能持续的最大危险是什么?
竹立家:我一直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能不能持续的最大危险,在于五个具有颠覆性的社会问题,即:贫富分化问题、三农问题、腐败和特权腐败问题、失业问题、社会诚信问题。这五大问题,既是未来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稳定的“燃点”问题,也是我们的“改革顶层设计”要重点关注的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是“中国改革突围”的关键环节和突破口。只有这五大问题从制度安排上得到根本解决,我们才能获得一个稳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和制度平台,也才能有效地解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问题,让民众满意和具有幸福感。
朱敏:确实如您所言,没有价值内涵和制度保证的经济增长,其结果很有可能造就一个“失败的社会”,这就犹如一个快速行驶在路基不实的轨道上的高速列车,出轨是迟早的事。未来三十年,中国经济想要再创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关键的制度前提是什么?
竹立家:习惯上,我们把那些匪夷所思的事称为“奇迹”。而中国三十年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则是改革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我们正确的改革策略和民众积极性充分调动的结果,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在我们的“政策设计”之中,并没多少“奇迹”可言。我们的改革与发展说到底是一个不断完善体制机制的过程,或者是体制自我完善过程,这一过程还正在“持续之中”。
未来三十年,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高速发展,续写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辉煌,除了从经济方面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消除一些生产要素方面的约束以外,关键的制度前提是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速度,使相对滞后的社会体制和政治行政体制尽快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为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创造较为完善的制度环境。
朱敏:正如您前面所讲,现在GDP总量的增长,似乎并没有引发民众幸福感的显著增强,甚至2009年以来“国进民退”成为了国内颇受争议的现象。因此有学者认为,由于国有企业是行政部门的一个衍生品,垄断利益背后往往是行政力量和部门利益,而行政部门的权力又不受约束,那么所谓“国进民退”,究其本质而言是“官进民退”,似乎与“藏富于民”这样的现代文明价值观及“共同富裕”这样的社会价值目标渐行渐远。
竹立家:你这里其实提到了一个本质上的“政治哲学”命题:“民富国强”或“国富民强”。虽然哲学近些年有些失落,我们已经习惯了用“经济思维”而不是“哲学思维”,但对“民富国强”或“国富民强”这一命题的深度思考必须深入哲学层面,即从“人类文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高度进行思考。
政治哲学主要研究“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一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或一个政府的合法性,一个国家的强盛,主要体现为社会资源与价值在社会公众之间得到了合理公平的分配。社会公正不公正,民众满意不满意,从哲学角度看,从社会基本价值角度看,最根本的还是公民权利和社会公平的实现程度。我们社会的最高道德标准是“民强”,民生幸福与社会公正相关联,而尊严则直接体现了民众在社会现实中基本权利的实现。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建成一个强国的基础是民众的富裕安康以及基本权利和幸福生活的实现,也就是目前一直强调的民主政治和“民生建设”。国家强大不强大,表现为三个基本方面:一是有一个公正的制度体系;二是有一套稳定合理的价值体系;三是社会财富的持续增长。而这三者最终都为全社会“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服务。
朱敏:是不是只有当“民权”和“产权”受制度和法律保护,才可能实现“民富国强”?
竹立家:是的。如果国家富裕了,而社会的大多数人没有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没有真正实现“民富”,或造成社会“贫富差距”的持续拉大,结果就会消解社会信任、消解社会凝聚力、消解“制度的优越性”、稀释和颠覆我们社会所崇奉的价值和理想,那么“国强”就是一句空话,甚至经济发展的成果或国家财富也会逐渐流失掉。
没有“民富”和“民强”,就没有“国强”,即使国家富裕了,但财富分配不公,或财富集中在少数特权阶层手中,而民众没有参与权和表达权,那么,结果就是国家失去向心力,社会就会像一盘散沙,民族就没了凝聚力。
制度改革关键的切入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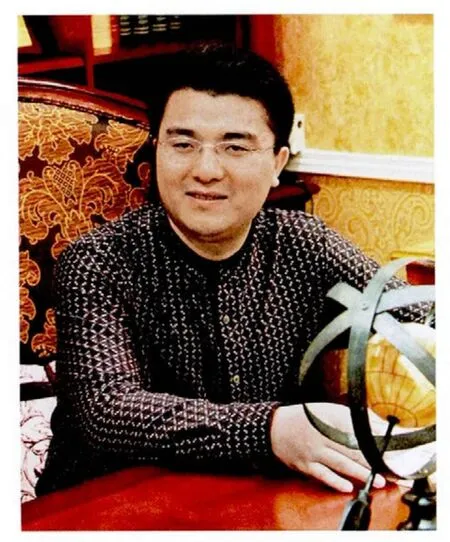
朱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中国企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现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经济导刊》执行总编辑,关心中国政经改革与新经济转轨,出版了《中国经济缺什么》、《转型的逻辑》、《通向彼岸之路》等著作。
朱敏:我想起一本书上有这样一段话:中国传统历史上有个谜团,十几次改朝换代获得了成功,而十几次大的改革却大都失败了,以至于有人说,国人可以向暴力屈服却拙于制度创新,真的是这样吗?
竹立家: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说法也对。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经济总量排世界第一,大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9.6%,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大约是8,000万两白银,通过茶叶、瓷器、丝绸贸易,世界70%的白银流往中国,当时的中国堪称富国。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富国和大国,却被小小的英国打得割地赔款。中国逐渐变成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演绎了“富而不强”的典型案例。
当时中国的统治阶层和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也在总结经验教训,结论是“技不如人”,于是才有了1850年之后长达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以及后来涉及制度改进的“维新改良”,企图挽回国运颓势。但由于洋务运动并未触及到根本制度层面,因此它未能改变中国的命运;“维新改良”由于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也失败了。
中国搞洋务运动之后,日本1868年也搞了“明治维新运动”。但日本面对“炮舰政策”,结论是“制度不如人”,因此他们派出了大量的留学生学习西方的社会科学,走宪政民主之路,进行现代化的制度设计和改革,限制和约束权力,为公民的政治参与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使国家发展与民生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日本有了长足的发展。而同期,中国却没有意图进行制度上的改革,依然是统治者的国家,而不是民主的国家。在总结日本如何能打败中国和俄国的教训时,晚清的统治者也意识到“制度不如人”。于是,清政府也想搞“宪政民主”,但一切都晚了,社会等不及了,辛亥革命爆发了。

朱敏:如此看来,只有拥有一个公正合理、公众认同的价值制度体系,“民富”才有可能实现,“国强”也才有坚实的、可持续性的基础。“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历史的经验教训带来了前车之鉴。
竹立家:是这样的。从目前来看,有两点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一是中国人均GDP还排在世界100位之后,这说明我们的人均富裕程度还不如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按平均数来看还谈不上“民富”;二是在“民不富”的情况下社会的不公正状况还在扩大,贫富差距继续拉大,这一状况发展的逻辑结果必然是社会矛盾和社会对立的加剧,社会诚信的流失,可能出现社会不稳定和“发展成果”的重新丧失。仅就一些常见的统计资料来看,我们就知道社会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到了何种程度,知道社会不稳定产生的根本原因,也知道为什么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具有紧迫性。
朱敏:倘若政府不能驾驭具体的部门,而部门权力又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追求部门利益最大化,日益坚固的部门利益就会成为改革深化的巨大障碍,也会给社会的公正与安定埋下隐患。以社会保障体系为例,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里对建立新的社保体系做出了框架性设计,但某些部门至今采取消极甚至抵制的态度,使该方案因国有企业老职工“空账户”补偿问题未获解决而未能实现。在您看来,遏制部门利益,防止改革目标在实践中“南辕北辙”,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真正实现包容性发展与民富国强,制度改革的关键应该从哪里切入?
竹立家:实现民富与国强的和谐发展,必须从社会价值或公共价值的高度进行思考。只有用一系列民主的制度安排和公共政策,切实保证民众的基本政治参与权,才能真正保证实现民强民富,也才能真正把我们社会的基本价值在制度上落到实处。因此,为了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真正实现“包容性发展”和民富国强,我认为,关键的制度改革切入点是进行公共政策制定体制改革。
首先,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公共政策,特别是社会政策制定过程的公开透明和程序民主,使社会公众对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政策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从根本上落实民主权利;其次,要从制度上确保新闻舆论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使媒体监督成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重要的民主手段;同时,还要切实发挥各级人大和政协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下决心逐步实现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制、专业化、常任制,使地方各级人大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能切实发挥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作用,减少公共政策的失误和政策浪费,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
朱敏:如您所说,在关于改革的话语体系中,“公共价值”和民主权利都是绕不开的话题。但目前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某些人的制度优越感(所谓“中国模式”);二是“稳增长”过程中行政权力的强化。殊不知,建设一样东西很难、破坏一样东西很容易,民主法治已有倒退迹象。
竹立家:有必要通过公共政策维护和创造公共价值,维护社会基本的公平正义,消解社会矛盾和问题,发挥和创新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最终实现“民主、民生、公正、和谐”的发展目标。
朱敏:这也是前面我们提到的社会理想,恐怕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吧?
竹立家:确实,急也急不来。要不古人怎么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呢?伏契克也说,“人们啊,我是爱你们的,但你们可要警惕呀!”当然,最后还是那句话,成败的结果取决于我们的智慧,取决于“社会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