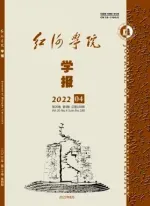《人间词话》“境界说”之再阐析
窦 薇
(1.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编辑部,昆明 650201;2.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昆明 650031)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的一部词学评论专著。这部专著在中国近代文论史、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一方面明确提出了“意境”论,第一次对这一美学范畴给予明确定位;另一方面引进了西方美学思想,用于对中国传统美学范畴的分析和评论。这是一种创举,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产物。但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使用最多的是“境界”一词。据统计,“境界”在作品中共出现22次,“境”出现23次,而“意境”一词,只使用了1次,出现在第四十二则的评姜夔词中。可见,《人间词话》的核心思想是“境界说”。王国维也专门论说过“意境”,最集中的表现在《人间词乙稿序》中。在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中,“意境”一词出现了16次之多。所以,在阐析《人间词话》之“境界”时,首先对“境界”和“意境”作一番辨析。
一 《人间词话》之“境界”和“意境”辨微
《人间词话》中,前九则是对“境界”的理论阐释,自第十则至第五十二则是关于“境界”的批评示范,自第五十三则至第六十四则是和诗词有关的一些话题(如:词和诗的比较、诗词的特点等等)。①从这六十四则词话出发,首先解释一下“境界”的内涵。何谓“境界”?首先引用《中国词学大词典》的解释。词典认为,王国维的“境界”有三层含义:一、境界是情与景、意与象、隐与秀、感情与想象的统一;二、境界要求再现的真实性;三、境界还要求文学语言能够直接引起鲜明生动的形象感。[1]仔细分析此解,发现其对境界的界说是从作品的艺术特征着手的,且含义的三个层次有交叉和重叠的地方。其中,第一层次偏重于作品内容方面的特征,第三方面偏重于作品语言即形式方面的特征。这两方面都要求作品具有生动、形象的特点,欲使作品生动形象,就必须具有真实性,这实际上涉及了作品第二层次的内涵。“再现的真实性”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景物的真实;二是主观情感的真实。例如:“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第六则)从《中国词学大词典》对“境界”的解释来看,笔者发现王国维在品评艺术作品时,境界与意境的含义是相同的。意境的基本特征表现为: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境生象外。这三个特征的最终目的是使艺术作品具有生动形象性,能够表现丰富的生活图景和思想感情,创造出生动的艺术画面。“境界”就品评艺术作品而言,也要求具备“意境”所具有的这几个基本的艺术特征。从这点出发,可知“境界”和“意境”在对作品艺术特征的要求上是一致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境界”和“意境”所说的就是同一回事。但是,如果再仔细分析一下上述“境界”的第二个层面“再现的真实”,可发现这个层面可以分解为客观景物的真实和主观情感的真实。“主观情感的真实”进一步具体分析,又可分解为:①从观物方式角度说,指作家对于外在景物和内在感情的“真实感受”;②从创作角度说,指作家的“真诚性情”。[2]其中,“真实感受”和“真诚性情”都是从作家主观精神出发而言的,尤其是“真诚的性情”,直接涉及作家的人生修养问题。从这一层面着手,笔者发现“境界”的内涵所包含的层次要多于“意境”。“意境”仅是作品的艺术特征论,“境界”不仅是作品的艺术特征论,而且还是作家的人生境界论。因此,下文就从“境界”这两方面的内涵着手,进行一番分析。
二 作为艺术作品特征论的“境界说”
在此层面中,“境界”和“意境”的基本特征相同,故可用“意境论”来分析“境界说”。《人间词话》上卷的六十四则,根据词人审美观照和境界构成方式的不同,境界可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由此产生的两种不同的美感效应为“壮美”与“优美”;根据创作方法的不同,可将“境界”分为“造境”与“写境”;从境界的语言表现着手,又有“隔”与“不隔”的观点。
所谓“有我之境”,指词人情感色彩强烈鲜明,直接外露的意象境界。在词话中,体现“有我之境”的词句为“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第三则),出自秦观《踏莎行•雾失楼台》。它们之所以被界定为“有我之境”,是因为词中所描述的景物里融入了词人过多的主观情感。句中的“孤”、“闭”、“寒”、“斜阳”、“暮”几个字,是作者主观情绪的一种映射。单从这几个字(词)出发,就可以体会到一种孤独、凄清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感投注于景物之上,使词句所描绘的景象显得非常黯淡。这样的词句因为作者的主观参与性太强,带有强烈的感伤色彩,所以,景物显现出一种悲壮性,难怪词话中说:“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第三则)。所谓“无我之境”,是指词人的情感较为隐蔽,完全融化于景物之中而不直接外露的意象境界。词话中,体现“无我之境”的词句为“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出自元好问《亭留别•故人重分携》。它们之所以被界定为“无我之境”,是因为,词句中作者的主观感情隐于景物之中,达到了情景交融,意与境妙和无垠,我与物浑然一体的状态。作者的感情在这里是淡泊的,没有强烈的主观参与欲望,词从心中自然流出。词句中的物我关系是和谐的,外物与“我”无冲突,“我”与物完全融为一体,“我”沉浸于物中,已经忘记了自身的存在,仿佛与外物合而为一。这时,作品中产生一种美,它愉悦、安适,概言之,为优美。优美往往和“无我之境”相联系,在此境界中,作者完全与景物融为一体。难怪词话中说:“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第三则)。
此外,词话中同时还提到了“造境”与“写境”。词话中说:“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第二则)和此说类似的还有“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第五则)这两则从作家的创作角度入手分析,提出“造境”、“写境”、“写实家”、“理想家”几对概念。在这里,理想家对应的是造境,写实家对应的是写境。它说明“境界”分“造”与“写”。“造”是一种类似于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它容许作家拥有想象的空间,并在此空间中进行发挥与创造。在此状态下所描绘的景,带有想象和虚构的成分,需要调动读者的各种感官去进行充分的审美体验。而“写”,是一种类似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它要求作家在描绘景物时,尽量忠实于现实,不要过多地游离于现实环境,过分地创造与发挥。但是,“造”与“写”在景物和情感相容和所生成的“境”中,是不可分割的。“造”中有“写”,“写”中有“造”,这就类似于“意境”特征的“虚”与“实”,不可分离,相伴相生一样。其实,“造境”就是“虚境”,“写境”就是“实境”。词境中“有造境,有写境”就是“意境”特征中的“虚实相生”。这种特征在词话中也有体现,比如:“‘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影’字,而境界全出矣。”(第七则)在这一则中,王国维盛赞的是词句中的“闹”与“弄”二字,以为,这两个字在词中一出现,便把境界衬托出来了。为什么说这两个字能够衬托出境界呢?那是因为它们使词句中的“境”呈现出“造”与“写”,即“虚”和“实”的层次。枝头的红杏增添了春景,这是写实的描绘,可以从视觉中直接感受到这一画面的美。但这一画面是静止的,但如果添上了“闹”字,整个画面就动了。此时,得调动除视觉而外的各种感官,比如:听觉、嗅觉、触觉等,并运用想象去充分地领会这种美。正是因为“闹”这一动词的使用,调动了想象力,所以,从这“写境”和“实境”中,我们看到了更多的“造境”和“虚境”。同样,“造境”与“写境”,“虚境”与“实境”还在“云破月来花弄影”中得到体现,此不赘述。
所谓“隔”与“不隔”,是从语言与意象的关系着眼区别境界之有无、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对“隔”与“不隔”的区别,王国维分别举了这样几个例子:“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第三十九则)这是从诗的角度提出的“隔”与“不隔”,词亦有此区别。王国维所举之词,以欧阳修《少年游•咏春草》为例,说:“上半阙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眼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第三十九则)除此之外,王国维又举“‘生年不满白,常怀千岁忧。昼夜苦短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写景如此,方为不隔。”(第四十则)从上述所举例子可见,王国维所谓隔与不隔的区分在于词境的鲜明具体,形象逼真,能写出真情真景。他认为东坡之诗不隔,而山谷之诗稍隔,那是因为东坡写诗境界开阔,不隐讳、曲折,能表现真情和真景。而黄庭坚诗之所隔,是因为他标举“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喜用典,讲出处,使诗歌充满了曲折性和学究气,令读者很难一眼悟到诗人真情,诗中真景。至于欧阳修《少年游•咏春草》词中景之所以不隔,是因为这描绘的景,语语皆在目前,鲜明具体。所谓“千里万里,二月三月”,令春草满山遍野之状,再现得栩栩如生。而“隔之景”,则是暗中套用了他人诗句,借他人诗句中所绘的景物来描述自己眼前所见之景。所谓“谢家池上”一句,借用的就是谢眺《登池上楼》中“池塘生春草”一句。所以,这样的景物描写便隔了一层。至于第四十则中所举之例,所谓“写情不隔”、“写景不隔”,采用的标准仍是“能否写真景物,真感情”,能否形象体地运用所抒之情,所绘之景,烘托出鲜明具体、形象逼真的词境。
三 作为人生修养论的“境界说”
此一层面的“境界”,直指作家的灵魂与生命,是作品艺术特征背后最深层次的东西。作品艺术成就的高低直接取决于作家的人生修养所达到的境界。王国维所标举的“境界”在此是一种“人生论”。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把人生论分为: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人生理想论、人生问题论四个方面的内容。[3]
人生论的核心是人生理想论。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与坚守便是一种人生境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儒、道互补,不同历史时期,此消彼长,知识分子之人生理想不可避免地受到二者影响。儒家以“仁”、“礼”为核心,建立的人生观,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视为己任,对外维持封建礼教之统治秩序,对内加强心性修养,对家国、人生有很强的责任感。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入仕精神。然而,在现实世界中,知识分子的满腔热忱往往受到统治阶级的残酷打压,在报国无门的沉痛哀怨中转向山野、园林,寻求精神的超越与解脱。此时,道家虚静、柔弱、处下、自然、无为的价值理念成为了知识分子心灵的安抚剂,他们往往不自觉地走向了寻求精神自由的解脱之路。
王国维所处的时代环境比较特殊。古老的中国闭关自守,封建统治走到尽头,国门被西方列强用尖船利炮轰开,举国一片混乱。从他青年时期算起到离开人世(1927年),短短的三十年,在中国大地上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八国联军入侵、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等等,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在这样的急剧变动时期,传统的封建道德理想和人生价值观趋于崩溃,王国维选择了一条治学之路,极少参加社会政治活动,表现出一种超然的、与世无争的社会态度。所以,他的人生境界观,更偏重于道家的社会人生观。因此表现于词学评论中的“境界说”,更多的是在道家思想影响下的一种人生境界观。
在道家人生境界观的影响下,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和文学批评受到了深刻影响,学者聂振斌把这种影响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求审美主体超尘脱俗,保持“赤子之心”,抒写纯真性情,反对欲望、利害上的追求;二是艺术创作推崇天然成趣,自然浑成,反对人工雕琢的伪饰;三是追求以心化物,物我不分的审美境界;四是推崇道家的天地之大美,追求自由与无限,反对用道德政治限制美与艺术,反对因袭模拟。[4]这几方面的影响经浓缩,可以概括为:纯真性情、自然而然、自由与无限。这几个特征可用来概括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同样也可用来概括他所提倡的人生境界观。在社会生活急剧变动,新旧思想强烈冲突的时代背景下,王国维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在历史、哲学、美学、文学、戏曲、文字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在其思想中,儒家的人生境界观暂时“悬搁”,道家人生境界观对其产生了深刻影响。他提倡“真性情”,比如他认为李后主“不失其赤子之心”(第十六则)“性情真”(第十七则)“词以血书者”(第十八则)。“真”是道德和艺术的最高标准,“真”意味着“诚”,但却不是“诚”,它吸取了“诚”之为人意义上的精华而更偏重于自由化的心灵。心中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性情之自然流露便是“真”。李后主不是一个称职的君主,但确是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他把握到了艺术创造中最本质的东西,故能有真挚感人的词作。王国维推崇李后主,意味着他也认识到了道德和艺术创作的最高标准“真”,但是要能充分实践这个标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王国维遨游于学术和艺术的海洋,不断感悟着生命和艺术之真,但同时也不断痛苦着。因为“真”是一颗艺术化的心灵所能拥有的东西,但却不是现实生活所能广泛实践的道德原则。王国维在现实的痛苦中得不到解脱,于是转而寻求学术世界中的心灵慰藉。在词话里,他标举了为学的三种境界:“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第二十六则)这三种境界描述了一个痛苦追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达到为学和为人的最高境界,须投入全部身心,甚至于不为人理解。尽管如此,却须无怨无悔,因为在找寻“真理”、追寻自由的过程中,主体经过种种考验,得到了心中的渴望及真知,这时的快乐无法言语。这就是一种境界,在这种境界中,物我合一,主体经历了这样一个痛苦求索的过程,体味到了人生和艺术,这就是一种化境,也是王国维所努力标举和追寻的人生境界。所以,在此意义上,“境界”是王国维所倡导的一种作家的人生修养论。
通过以上对“境界”两个层面的分析,辨析了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境界”和“意境”两个概念,认为:“境界”美学内涵大于“意境”,“境界”一方面等同于“意境”,指的是一种美学范畴,它的艺术特征包括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境生象外,在《人间词话》一书中,可从“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造境”与“写境”,“隔”与“不隔”三方面得到体现;另一方面,“境界”的内涵还包括人生境界论,王国维的人生观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表现出儒道互补的思想特征,在特定时期,即近代社会中西文化互相冲击的情况下以道家思想为主,同时不失其“赤子之心”,这可从《人间词话》中对李煜的评价中得到体现。最后,王国维在为学的三种境界中得到心灵的净化。
注释:
①本文依据的版本为《人间词话人间词》王国维著,谭汝为校注,群言出版社 1997年版。此版本《人间词话》部分分为上卷、下卷和附录,共152则。此处对“境界”的分析且选择上卷部分,即前64则。
[1]中国词学大词典•概念术语•境界[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23.
[2]许央儿.论王国维境界说之“真”[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5,30(3):6-8.
[3]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4]聂振宾.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M].大连: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
[5]潘知常.王国维——独上高楼[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6]程相占.王国维的意境论与境界说[J].文史哲,2003 (3):70-74.
[7]王国维.人间词话人间词[M].谭汝为校注,北京:群言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