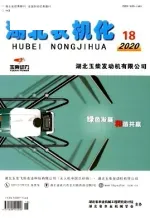农机结缘60载 梦想成真二代人
崇阳县农机局 刘陈辉 黄本良
1954年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改变了我父亲的命运,使我父子俩与农机结下了不解之缘。
6月15日,境内降雨量达243mm,受灾农田为10 383亩(1hm2=15亩)。区公所为了尽快恢复农田,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抗洪救灾,购进了2台抽水机,2台宁波7.4kW柴油机,成立了农机站,把我年仅17岁的父亲调来当机手,通宵达旦在一片汪洋的农田中排水。事后,区公所领导见我父亲能吃苦耐劳,就任命他为农机站站长,但领导的兵只有一个。我父亲当了“官”,就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因为手上有了“动力”(当时柴油机叫动力),不能让这个千斤万两的铁砣睡觉,要它响起来,于是我父亲就和他的“部下”合计,上下求援,四方游说,又找农业生产合作社借款,在汉口购买了扎花机、磨面机、脱米机等。当这些机器运回后,前来看稀奇的群众挤破门庭,人们奔走相告,父亲更是神气十足,机器安装好后,专门为老百姓廉价加工,收取极少的“油钱”,偿还借款。每脱粒50kg大米,收2角钱,很受群众欢迎,来农机站脱米的、磨面的、弹花的门庭若市,热闹非凡,一天到晚,机声隆隆。我的父亲日日夜夜笑容挂满脸,汗水遍身流。四乡八村的老百姓都亲切称我父亲为“机官”。
毛主席说:“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我父亲想,不能长期在机房咚咚咚咚,还是应该到田野中去,为老百姓减轻更大的劳动强度。1970年,农机站发展到5人,添置了3台手扶拖拉机、扎滚机、湖北73型插秧机等农业机械,我的父亲心喜若狂,因为自己的农机梦圆了一半。每当春耕时节,农机站全体“官兵”奋战在希望的田野上,打田、犁田、扎田、耙田、插秧,道道工序,我的父亲总是一马当先。若需要人下水,他首先自己先脱鞋。在那“农业学大寨”的火红年代,在那“春耕如救火”的特殊季节,我的父亲不知有多少个不眠之夜、数以千计的风餐露宿啊!在田埂的草跺上打盹是我父亲最好的享受,因为人歇机不停。一年又一年,泥水和汗水浸泡了我父亲全身,常常只见眼睛眨动,纯属一个活泥人。我母亲见到我父亲说:“你整个人全身泥巴气”我父亲笑着说:“这就是泥土的芬香……”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境内肥沃的土地都洒下我父亲的汗水,万顷良田都留下了我父亲的足迹,夜幕之下都闪过我父亲的身影。1979年,崇阳广播电台以《万水千山总是情》的长篇通讯对我父亲作了专门报道。我的父亲在我的心中是一座伟大的丰碑!
我的父亲在几十年的农机生涯中,总是这山望见那山高,从不知足。特别是看到老百姓在双抢大会战中,面朝黄土背朝天,飞镰割谷,挥汗如雨,尤其是在抢收抢晒中更要争分夺秒,父亲心痛万分。常常看到电视里的联合收割机,羡慕不已,夜不能寐。终身难忘的是1982年,我村一位老大爷为了抢收抢晒,中午不歇,竟然中暑,晕倒在稻田里,当人们闻讯赶到,大爷已经停止呼吸,镰刀死死紧握手中。父亲见到,泣不成声,跪在田里,大声疾呼:“老哥呀,这是我们农机人的罪过啊!”从此,我父亲就做起了收割机的梦。因为已经分田到户,加上国家没有农机补贴,我家经济也不宽裕,要买联合收割机谈何容易。转眼到了1983年,由于父亲长期手扶拖拉机的把手,特别是重复着弯腰换挡的机械动作,父亲的腰弯了、背驼了、患上了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加之长期的泥水浸泡,积劳成疾,于同年9月病退。我接过了父亲的把手,继续帮他来圆农机梦。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伢崽,不管你采取什么手段,不管你想什么办法,都要拥有自己的收割机啊!不仅在电视上能看到,要在本乡本土的田里看到,因为这是我的梦。”我按照父亲的重托,一干就是30年。
如今,国家昌盛,人们富裕,我这个农机站长也好当了。现在我负责着2个乡镇的农机服务工作,机手们戏谑我是“一官两印”。现在,我的农机队伍共有307人,拥有福田、沃得、龙舟等大型联合收割机51台。小型收割机4台,井关高速插秧机1台,小型插秧机22台,大、中型拖拉机72台,手扶拖拉机203台。每年举办两次以上的机手培训班和讲座,增强机手们的安全意识,提高职业道德,熟练业务技能。如今,每当收割季节,我这只领头雁,领着我的农机队伍插上红旗、拉起横幅、浩浩荡荡南征北战,跨区作业:广东的稻田里有我农机人的喜悦;河南的小麦片地里留下了我们农机人的笑声;江西洒下了我们的汗水;江苏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每当我们离开时,当地的老百姓都依依不舍,说我们的机手任劳任怨,要我们来年再来畅饮丰收酒。当我驾驶联合收割机安全回家时,老父亲总要弯着腰爬上高高的驾驶座,紧握方向盘,眼睛眯成一条线说:“这不是收割机,这是我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