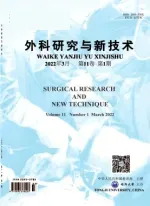关于提高肝癌外科疗效的途径
汤钊猷
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上海 200032
近几十年来,通过肝癌的规则性切除,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突破,经导管动脉内化疗栓塞的应用,射频消融等局部治疗的问世,肝癌肝移植的开展,以及分子靶向治疗的合用等,使肝癌外科的疗效日益提高。然而,肝癌的总疗效仍强差人意,为进一步提高肝癌外科的疗效,仍有大量工作要做,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1 早期诊断和早期切除仍是提高肝癌外科疗效的最主要途径
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以下简称本所)的资料表明,肝癌手术切除从群体的角度,生存率与肿瘤直径呈负相关,即直径越小,切除后的生存率越高,肝癌住院病人的5年生存率已从20 世纪50 至60年代的2.8%,逐步提高到近10年的44.0%,这个提高基本上与小肝癌切除比例由0.9% 提高到50.9%相一致。文献中美国和意大利两个大系列分析,也认为肝癌生存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Altekruse 等Hepatology 2012;Santi 等J Hepatol 2012)。本所早期肝癌病人的比例明显提高,主要来源于单位开展的年度体检发现,也有部分是肝癌高危险人群的定期监测所发现。对外科医生而言,关键是根据乙型和丙型肝炎背景、肿瘤标记和影像医学结果能早期作出正确诊断并及时进行手术。在早期诊断指标中,甲胎蛋白仍被认为对肝癌监测有用(Giannini 等Hepatology 2011);荟萃分析提示,高尔基蛋白73 诊断肝癌的准确性与甲胎蛋白相仿(Zhou 等BMC-Cancer 2012);有报道骨桥蛋白(Shang 等Hepatology 2012)和血微小RNA-21(Tomimaru 等J Hepatol 2012)优于甲胎蛋白。本所小肝癌(直径≤5 cm)的5年生存率:肝移植(米兰标准n=163)为76.9%,切除(n=6510)为58.2%,射频消融(RFA,n=482)为47.9%。对比小肝癌切除和射频消融,文献认为二者总生存率相仿,但切除的无瘤生存率较好。
2 综合治疗是提高肝癌外科疗效的长远方向
由于肝癌是多种因素引起、多基因参与、多阶段形成的全身性疾病,为此综合治疗是长远方向。过去外科医生大多满足于肿瘤被切除,而很少考虑术前术后为提高疗效的相应治疗。如上所述,即使小肝癌切除,其5年生存率也没有超过60%,即5年内仍有近半数出现肿瘤复发转移。过去综合治疗模式主要是“消灭+消灭”,例如手术前后合并放疗、化疗或经导管动脉内化疗栓塞(TACE),其中多种消灭肝癌的疗法合用,待肿瘤缩小后行“降期后切除”是综合治疗提高疗效的典型模式。本所过去资料显示,“不能切除肝癌的缩小(降期)后切除”,由于获得二期切除的肝癌已属于小肝癌,其5年生存率也仅略低于小肝癌切除。近年TACE 的广泛开展,已使不少原先不能切除的肝癌转变为能切除者,但可惜这些病人中仅少数转到外科做二期切除,从而失去可能的根治希望,这也是为什么近年主张多学科联合治疗的原因。通过二联或三联的综合治疗,使肿瘤明显缩小的比例明显多于单一的治疗。本所资料提示单纯TACE 的5年生存率为27.6%,而TACE+RFA 则为44.5%。文献中“消灭+消灭”模式的报道不少,如健择+奥铂使部分晚期肝癌转变为可治(Zaana 等J Hepatol 2013)。但值得关注的是“消灭+改造”模式,如本所早已发现干扰素α 有助预防肝癌术后的复发转移(Wang 等Hepatology 2000),并在临床随机对照研究中证实干扰素组的中位生存期为63.8月,而对照组仅为38.8月(Sun 等J Cancer Res Clin Oncol 2006),荟萃分析也证明其效果。2013年的文献也证实“切除+干扰素α+利巴韦林”减少术后复发(Hsu 等Hepatology 2013)。所谓“改造”,即不以直接杀灭肿瘤为目的的疗法,近年已出现一系列有潜在价值的“改造”疗法,“切除+免疫治疗剂”、“切除+抗炎剂”、“切除+分化诱导剂”、“切除+中医中药”等,将是值得关注的综合治疗模式。
3 研究及防治癌转移是提高肝癌外科疗效的关键
本所过去40年小肝癌切除的5年生存率没有进一步提高,提示如不研究转移复发,则生存率难以进一步提高。近年癌转移的观念已有改变,如:癌转移是全身性问题,癌转移不是晚期现象(Ye 等Nat Med 2003),癌转移与免疫炎症微环境关系密切(Budhu 等Cancer Cell 2006),肝癌干细胞与转移关系密切,癌转移潜能可双向变等。关于肝癌转移/预后的评估有不少指标,如白介素2 与白介素15(Zhou 等Gut 2010)、骨桥蛋白(Zhang 等Int J Cancer 2011)、角 蛋 白 19 (Kim 等 Hepatology 2011)、乙酰胆碱酯酶(Zhao 等Hepatology 2011)、HTPAP(Ren 等Cancer Res 2011)等。甚至常用的中性白细胞/淋巴细胞比例也有预测价值(Motomura 等J Hepatol 2013)。癌转移研究重在干预,全身性干预可从神经、免疫、内分泌、代谢等方面考虑。抗CTLA-4 抗体Tremelimumab 的问世使“肝癌免疫治疗曙光在望”(Sprinzl和Galle.J Hepatol 2013),但这种单抗也有诸多严重不良反应。代谢干预已日益受到重视,如全身PTEN 水平升高,可导致抑制肿瘤的代谢状态(Garcia-Cao 等Cell 2012)。炎症干预已有众多报道,藏红花可抑制炎症、诱导凋亡,为潜在抗肝癌药(Amin 等Hepatology 2011),清理肠道菌群有助预防肝癌进展(Darnaud 等J Hepatol 2013)。中医中药是防治肝癌转移研究中值得探索的方面。本所发现小复方中药“松友饮”可降低肝癌“干性”(Jia 等Evid-Based Compliment Alternat Med 2012),下调肝星状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改善微环境抑制转移(Jia 等BMC-Cancer 2013)。改变生活方式如适度运动,也值得重视(Willyard.Nature 2011)。
4 研究杀癌疗法的负面问题及其干预是提高肝癌外科疗效的一条捷径
本所多年实验研究发现,消灭肿瘤疗法(包括手术、放疗、化疗、肝动脉阻断、抗血管生成等)通过乏氧、炎症和抑制免疫等,导致上皮-间质转化(EMT),促进残癌转移,并伴有分子水平的改变。一些临床常用的无关药物,如阿司匹林、苦参素、唑来膦酸、干扰素α、万特普安、含5 味中药的小复方“松友饮”、丹参酮等,有助减轻消灭肿瘤疗法的这种负面作用,从而提高疗效。这些药物的作用机制不同,如阿司匹林和唑来膦酸主要通过抗炎作用,中药小复方“松友饮”则可降低肝癌“干性”和通过下调活化的肝星状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改善微环境,丹参酮IIA 有使血管内皮正常化的作用等。本所还发现,用于治疗晚期肝癌的索拉菲尼,虽抑制肿瘤延长生存,但下调HTATIP2 而促残癌转移(Zhang 等Gastroenterology 2012);而阿司匹林则可上调HTATIP2 这个分子,抑制转移和延长生存期(Lu 等PLOS ONE 2013)。索拉菲尼的促残癌转移作用还与抑制白介素12b 有关(Zhu 等Angiogenesis 2013)。放射治疗通过凋亡机制可产生很强的生长刺激信号使残癌再增殖,活化的Caspase 3 越多,病人复发死亡概率越大(Huang 等Nat Med 2011)。
由于分子生物学研究的进展,对包括肝癌在内的癌症防治出现了一系列新思路、新途径,例如小RNA、针对信号传导、针对肿瘤干细胞、针对微环境、抗有丝分裂、抗端粒酶、针对异倍体、血管内皮正常化,以及使用“无关药物”等,都值得肝癌外科治疗过程中给予关注。相信在不久将来,肝癌外科治疗将出现新的格局,使疗效得到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