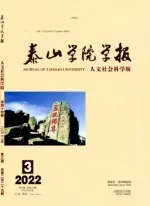天灾与革命:辛亥革命前后常熟千人会的抗租斗争
金 坡,张 超
(1.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5;2.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辛亥革命前十年,全国各地爆发了各种形式的群众斗争,下层民众的“抗租”、“抗粮”、“抗捐”、“抢米”更是此起彼伏。据不完全统计,宣统元年(1909年)全国“下层群众的自发斗争约149次”,第二年“陡然上升到266 次”[1](P229)。各种各样的群众斗争几乎都与自然灾害密不可分。从宣统元年到三年,江苏省每年均有60 个州县受水灾[2](P722)。频繁多发的自然灾害加剧了下层民众的反抗斗争。自宣统元年至宣统三年江苏省发生的各类饥民闹荒达79 次之多[3](P151-154)。在接二连三的饥民斗争中,以辛亥革命前后,发生在常熟、无锡、江阴三县边界的千人会抗租斗争规模最大。本文即探讨辛亥年常熟千人会抗租问题,并借以阐释辛亥革命反封建斗争的不彻底性。
一、辛亥年常熟社会的基本面貌
宣统三年(1911年)即农历辛亥年,常熟社会的基本面貌是:高度集中的土地和高昂的地租率导致农民与地主尖锐对立;夏秋两季频繁多发的自然灾害导致下层民众抢米不断;受武昌首义的影响,常熟社会动荡不安。
辛亥革命前夕,常熟绝大部分土地被极少数的地主占据,广大农民处于少地或无地的地步。当时常熟“耕地约有一百五十万亩,其中百分之六十掌握在一千多户的地主手中,单是孙思敬、邵松年以及翁、庞、杨、蒋等几家官僚地主,即各霸占了几千亩甚至上万亩的土地”[4](P197-198)。他们对农民的压榨也非常严重,“地租率一般高达二分之一左右”[4](P198),年岁荒歉的时候,广大农民把“一年所得全部缴给地主还是不够”[5](P89),交不起租的农民只能忍受“打伽”、“臀刑”之苦,甚至因此家破人亡。严重的土地集中和高昂的地租率导致了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民众与少数地主豪绅的尖锐对立。
宣统三年七月江苏遭受特大暴风雨灾害,“初四、五、六三日大雨,复继以初七、八、九之大风,江潮顶托,湖河满溢”[6](P37)。常熟亦未能幸免,“三年七月,淫雨浃旬”[7](卷七P25),初四到初六“风狂雨大,水涨潮涌,合境平地水高四五六尺”[8](P90),“城区河水过岸……水深及腹,可以行舟。城外几成泽国”[9](P140)。常熟“灾区方圆30 公里,殃及27 乡镇,有20 余万人遭灾,生活无着”[9](P140)。受灾人口达到当时全县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
持续数天的暴风雨,破坏力是相当大的。首先是对农村的破坏,导致农田被毁、房屋倒塌。早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常熟境内的水利设施就“失于浚治,各浦浸以淹塞”[10](卷九P1),大水后,“所植各物,大受侵损”[11](P221),“乡间茅屋草庐多半坍塌,农具器物恒多漂失,房屋之幸存者,亦已浸在水中”[12](P6),大量农民破产;其次是对城市的破坏:大水导致城墙倒塌“西南隅复坍十余丈”[13](P670),道路淹没,“河水过岸高尺余,道门场、寺前街等处均积有尺许”[14](P135),“登高四望,人家宛在水中央”[15](P112);再次是对百姓生命的威胁,“田庐淹没,兼毙人口”[6](P37),以致“大潦之后,民多饿殍”[16](卷三P18)。
水灾导致农业严重歉收,大米价格飞涨。1911年江苏全省“农产品收获只有1 ∕4 至1 ∕5”[11](P101),常熟亦是如此。1910年当地的物价水平已经很高,与1902年相比“米每石由4.10 元涨至7 元”[11](P106)。到1911年夏“每石可售九元四角”[11](P221),苏抚程德全也不得不承认“米重于银,不独急于筹款,更急于购米”[6](P37)。
面对汹涌的自然灾害,农民走投无路时选择了“抢米”这一传统的斗争方式。七月八日,进城报荒的百姓砸毁自治局、洗劫了当地名绅邵松年的住宅,“外自大门,内至上房,均极蹂躏不堪”[14](P136),常熟城内乱成一团,县令魁福躲避;防兵的枪亦被百姓毁掉;地主绅富异常惶恐。第二天,数千农民涌入城内抢劫,抢掠“计八十余户(四乡大户尚不在内),丧失不下五十余万”[15](P112)。初十,“难民已聚众约十万人”[17](P69);十一日,常熟东塘乡民“聚众抢米,将自治公所、从善公局、亭林学堂、米业学堂、耶稣教堂皆被毁,典铺、米行被抢者共六十余家”[14](P139);十二日,梅李、徐市等乡航道被阻,商船多被劫掠;十三日,梅李、塘桥等地织布厂被洗劫,损失“米十六石、布匹若干,约值洋四百余元”[14](P139)。这次饥民抢米持续五六天,各乡均有发生。
对于饥民抢米,常熟士绅及官府采取了一系列剿抚兼施的手段,他们一方面购米赈灾,一方面严厉镇压劫掠者。七月初九程德全令常昭两县“除饬司委勘并拨款赈济,一面饬派王道督率师船,星夜前往弹压外,务即妥筹抚恤,解散胁从,严拿滋事首要禀办”[14](P136-137)。全省最高长官的表态为常熟地方处理饥民抢米事件定下了基调。
七月初八,常昭两令电省请派兵弹压。初九日,苏抚电令“弹压不服,准予格杀”[14](P137)。十日,防兵毙杀灾民首领俞大根,逮捕陶根根等多人“送县枷示”[14](P137)。十一日,程德全重申其立场“乱民肇事,法无可逭……如敢不服及有持械拒捕情事,准其当场格杀”。同时他还分化瓦解饥民,“饥民乱民宜分清:安分待赈者为饥民,必须赈抚;乘间抢掠者为乱民,必须严拿”[14](P138)。常昭两令,十一日枪毙陶根根,强制驱散饥民。当地富绅“一律罢市”[15](P112),组织武装团体“商团、民团、预团一时成立,城内外约有六七百人,彻夜梭巡,枪声不绝”[14](P139)。到十六日,抢米风潮“大局已近敉平”但是“所有原派师船营队仍应专驻该二县境内,以资镇摄”[18](P620)。
除了武力镇压以外,各级政权亦曾办赈救灾。具体措施为募集捐款,发放救灾银两、开仓放米办理平粜、派兵船保护往来商船、开展以工代赈等。常昭两县令“捐钱一千五百千文充用”,江苏义赈会助银二千四百四十二元五角;常熟城区绅民“集捐钱五千八百七十三千六百五十文”[7](卷七P25);常熟水灾超出了地方的承受能力,大水停后常熟士绅就登报乞赈,程德全亦在七月初九请求两江总督“颁发帑银”,以资“广皇仁、遏乱荫”。十日,程电请盛宣怀购米,同时拨银二千两急赈,而后又请求政府免除外粮内运的通关厘税。抢米风潮一起,米行不敢开张,常昭两令分劝米行平价开张。十七日常熟米行开市“每升百文,每人以三升为限。城内各米铺由各行发给或一石或二石,每升售钱一百零六文”[14](P140)。二十一日,清政府江南查赈大臣冯梦华派严国钧携款一万两,到常熟放赈。八月初四,苏省又下拨铜元四万千文,在老庙设义赈局。从八月十一日开始办理平粜,四门各设一局,以孺寡局为总局,“定五日一期,共发十期,每升七十文”[14](P141)。
程德全等亦曾派师船,分驻青墩、梅李两塘镇摄护送,以通航路。常熟县署“代募公债银七千五百圆,专办低区九乡筑圩以工代赈”[7](卷七P25),“修复圩堤百六十有六图”[16](卷三P18),同时开浚白茆塘等久淤水道。在当地地主和各级政权剿抚兼施的瓦解下,这一阶段的饥民抢米风波持续数天便瓦解。
正当常熟各界忙于赈灾时武昌起义爆发,江苏亦受其影响。程德全在奏报中称“人人有思乱之机,处处有蠢动之势,危急存亡,事机甚迫”[6](P48)。在“势已燎原”的情况下,程于九月十五日(公历11月5日)宣布江苏独立。
受武昌起义的波及,常熟社会动荡,市场混乱,“东乡花业,每届八月异常拥挤,今亦大半停止交易”[19](P142),典当业、布业、米行等大多停业;谣言纷传,加剧了群众的恐慌。二十八日,常熟城内多处“拾得匿名揭帖,各学校均有投函,略言九月初四日大兵过境”[19](P143)。受此影响百姓纷纷兑换金条,准备逃避。谣言的传播加剧了市场的动荡,“各典铺异常拥挤,而所质之物,以脚炉等铜铁笨重之件最多”[19](P144);案件频发,治安趋于失控。“后梅李黄姓全家杀害……又有大河、王庄连及金匮、江阴县界,一群不逞之徒约数千人,到处抢劫,几如异军之特起,村镇皆空”[19](P146),治安状况的下降加剧了社会动荡。受苏州独立的影响,十七日晚,常熟绅民推举原县令翁有成为县长,丁祖荫为民政长。十八日县署各局所、城门、店铺、大街小巷皆挂白旗以示光复。突如其来的武昌首义又一次把渐趋稳定的常熟社会推到历史的十字路口。
二、千人会的概况
千人会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秘密组织,是在辛亥大水后饥民抢米过程中成立的,它以传帖聚众,歃血结盟的方式组织群众。主要活动在无锡、江阴、常熟三县的交界处,具体来讲主要是“无锡东北乡的怀上市、蠡漍、戴店、黄土塘,江阴东南乡的北漍,顾山、长泾,无锡东乡的港下、陈墅,常熟西乡的王庄等地”[20](P183)方圆约有20 里。辛亥革命前千人会组织已经在无锡、江阴出现,辛亥革命的爆发促进了它的发展,使其迅速扩展到常熟境内。
千人会的领袖都是下层群众,无锡境内为孙二、孙三和樊文涛,常熟境内是周天宝和杜海云等。孙二、孙三是兄弟,农民兼做裁缝,樊文涛是穷塾师,周天宝是常熟王庄人,“因入赘王庄尤巷周姓,遂改姓。魁伟好武,擅农事,性豪侠”[9](P1090),杜海云也是普通农民。千人会群众基础广泛,无锡、江阴、常熟“三县边区方圆约二十里范围内的农民都纷纷参加了这个组织”[4](P203)。
千人会以抗击地主的高额地租为目标,以“同抗租同得福”、“皇帝没有了,租米也可以不交了”为口号发动群众。喝血酒结盟立誓即为入会,盟约的主要内容是“武装自卫,同心抗租,临阵退缩者,当众处罚”[21](P247),这也是千人会的纪律和宗旨。每个入会者只需写下姓名,出酒饭钱三百文,表示同心抗租就算入会了。
孙二、孙三、樊文涛等在无锡港下一个破庙里,组织百姓喝血酒结盟立誓。江阴农民在沈舍里的周神庙内吃会酒盟誓。周天宝、杜海云、周耀明等人于常熟光复半月后集合农民在名叫福林庵的庙里宰猪盟酒,号召当地农民不要向地主王品南、须纪常等交租。吃会酒时,周耀明登记入会人员姓名,当天“入会的人数约有二、三百人”[22](P131)。
三、千人会抗租斗争的经过及结果
武昌起义后常熟和平光复,但是去掉的仅仅是前清政权的外壳,很多立宪派、旧官僚继续留在新政权里,他们坚决捍卫旧的秩序不允许百姓触动。“广大农村除了换上民国的招牌以外,封建的土地制度和社会秩序依然如故”[23](P459)。独立伊始,程德全即以中华民国苏军都督的名义发布通告:各州县照常办事,“如有大帮匪徒乘机骚扰,妨害安宁,立即报告本都督府,当随时派拨兵队前往剿办”[24](P62)。程亦多次胁迫全省农民交租“如抗租不还……准由各业户禀经该管衙门,按户提案押追,以凭照例严办。如有聚众抗租或竟持械横行,既属有意破坏治安,必非安分良民,本都督惟有按照军律从事”[25](P 74)。常熟新政权成立后,立宪派旧官僚积极进行武装以维护被革命冲击的旧秩序,在他们看来原有的社会秩序,“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基础,打乱了旧时的社会秩序,就等于打掉了他们的上等社会地位”[23](P471);同时积极联合地主富绅对付农民的抢米风潮和抗租运动。
丁祖荫组织常熟新政权后首先编练团防,从城区到各乡镇,普遍建立了民团、商团。“不到一个月,先后近二十个乡成立团防,纷纷请领枪械弹药”[22](P131)。据其所编的《常熟民政署报告》[26]记载,从辛亥年十月初一至十一月初一短短一个月内,为成立团防请领枪械弹药的乡镇,就有东乡的任阳、白茆、徐市、梅李、浒浦,西乡的塘桥、三塘、鹿苑、唐市,南乡的耿泾,北乡的沙洲市等十余处;其次支持地主对农民的榨取,不断催租。十月初三开始就“晓谕各佃赶紧还租”[26](P5),到千人会结盟抗租时丁多次以政府名义向各乡农民催租。
辛亥年九月底,常熟地主开始收租。起初,农民与地主富绅谈判,希望他们能考虑荒歉稍减地租。而占有六七千亩土地的大地主须纪常并不理会农民诉求,他所掌管的须义庄仍按原额九折收租,其族人须寿芝亦按原额收租,其它地主竟相效尤。
千人会看到非武力抗租不可能争取到农民的活路就开始进行准备。而地主王品南等亦到县城报官。新政权将王庄尤巷地保沈效民抓去,沈供出周天宝、杜海云为常熟千人会的首领。就在周天宝领导农民歃血结盟后第三天,常熟新政府即派军警趁夜逮捕了他,连夜押到县城。以此为导火线,常熟王庄千人会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租斗争,随即无锡、江阴等地千人会分赴王庄加入斗争。
周天宝被捕的第二天,常熟千人会的周耀明就派人给无锡、江阴等处千人会报信,请求支援;同时鸣锣聚众,号召千人会成员集会。接着大量农民拿着鸟枪、鱼叉、锄头、大刀、钉耙、鸭舌枪等武器冲向王庄。千人会成员在奔赴王庄的路上,捉了王品南的外甥程老敬作人质。在王庄,千人会成员捣毁了王品南的住宅、宋济生和宋昌先的店铺,同时也捣毁了“地主豪绅的住宅,义仓、仓房等”[21](P247)。不久,无锡、江阴千人会成员赶到,他们打着“‘仁义农局’、‘千人大会’等黄底红字的旗帜”[22](P132)。当天,千人会成员就在王庄城隍庙组织临时领导机构,孙二、孙三为左右都督,樊文涛为军师,同时还将“参加打王庄的千人会人员分为三个营,推好拳棒的无锡鱼炳荣为统领”[22](P131)。他们到处张贴布告,“宣布他们起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抗租”[4](P204)。第二天千人会又捣毁了须义庄。
千人会纪律严明,禁止抢夺财物。当他们捣毁宋济生和宋昌先的店铺时“凡是家俱和细软什物,或抛在河中,或掷于街头,让贫苦群众拣去,而参加打王庄的千人会人员一律不准占有”[22](P132)。千人会斗争目标明确,他们仅打击残酷欺压百姓的恶霸地主,一般地主不在他们打击之列。“恶霸须纪常的哥哥须纪棠,平时对农民不像须纪常那样厉害,千人会在打烂须纪常家的时候,没有触犯连墙隔壁的须纪棠家”[4](P205)。千人会注意发动群众,“王庄的手工业工人、贫苦知识分子、小商人都和千人会水乳交融,打成一片”[4](P204)。千人会以抗租为目的,在充分吸取光复前抢米风潮的教训后广泛发动下层民众,把这次武装抗租以及反抗地主豪绅的斗争推到了最高潮。
千人会的武力抗租,引起了地主富绅和江苏各级新政权的恐慌。地主坚决镇压千人会的抗租斗争,王品南、须纪常他们一方面假托释放周天宝,一方面紧急向常熟、无锡新政权求救。江苏各级政权亦不允许农民入会抗租,十一月初六,程德全电丁祖荫“莠民持械抗租,应会同军队拿惩”[26](P11),同时张贴“严禁同盟抗租”的告示;初九日,“都督电王庄聚众违抗,准照军法从事”[26](P12)。初八到初十,丁祖荫多次电请程德全暨无锡、江阴民政长“派兵会拿王庄乱民”[26](P18-19)。在程德全的统一部署下初九、初十两天无锡、江阴新政权分别电复丁祖荫“已派兵协缉王庄乱民”[26](P13-14)。接着丁祖荫令钱老三率枪船到王庄;江阴也派兵前往王庄;就连同盟会出身的无锡军政分府秦毓鎏也派军队到了王庄张泾桥。此时常熟地主王品南等以及旧官僚程德全、丁祖荫甚至同盟会出身的秦毓鎏完全勾结在一起,他们命令军警在王庄镇梢的大松坟,向正在集会的千人会开枪。千人会奋起反抗,但因无险可守、武器落后,加之没有临阵经验,“双方战斗持续两小时左右,‘千人会’会员终因火力不敌,死伤30余人”[9](P689),“敌人遂乘隙攻入,大肆搜杀”[4](P206)。
在地主富绅与光复后新政权的联合剿杀下,千人会抗租斗争失败。不久周天宝被杀,三县军警联合追捕孙二、孙三、樊文涛等首领。而后常熟各乡如董沈、练塘等不断发生饥民零星抗租、索食等现象。为防止百姓继续抗租,常熟军警在王庄附近驻扎达两月之久。
四、结语
辛亥革命后常熟千人会抗租斗争,是与常熟光复前饥民抢米风潮一脉相承的,“抢米”和“抗租”一直是辛亥革命前后常熟灾民闹荒的主要方式,而以后者影响更为剧烈。在不断斗争中,农民开始认识到只有联合起来武装反抗才可能取得胜利。受当时条件影响,他们只能采取歃血结盟的形式以聚会抗租为出路。千人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担负起领导灾民斗争的历史任务的,受其历史局限,他们不可能提出更为明确的斗争方案,最终在三县地主富绅和新政权的联合剿杀下以失败告终。
常熟土地的高度集中和高昂的地租率引发下层民众与地主豪绅的矛盾是千人会抗租的根本原因;突如其来的暴雨灾害和武昌起义的突然爆发加剧了千人会的抗租斗争。下层民众本想趁着革命光复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境遇,他们认为“政局翻新,须免赋三载”[11](P220)。然而常熟、无锡、江阴三县“新政权的老爷们和豪绅地主串通一气,对起义农民进行镇压、拿办,和旧衙门简直毫无区别;尽心尽力地帮助地主向农民追索租粮,和前清时期也是一脉相承”[27](P121)。辛亥革命前后,“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28](P17),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无视千人会普遍发动农民群众的这种力量,不仅不能很好地引导、利用这种力量,却与旧势力联合剿杀了农民群众这种自发的反抗封建地租的斗争。
千人会组织农民抗租时,三县新政权的领导人分别是立宪派(常熟的丁祖荫),旧官僚(江阴的刘敬焕),同盟会员(无锡的秦毓鎏),他们在镇压农民问题上取得了惊人的一致。就连同盟会出身的秦毓鎏亦把农民的自发斗争看成是异己的敌对力量甚至担当起镇压农民斗争的急先锋。革命党人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则必将失去农民的支持,而失去农民的支持,则意味着改革和革命必然以失败而告终”[23](P458),常熟光复后力量薄弱的资产阶级及其革命党人应迅速与已经自发组织的贫苦农民结成联盟,依靠农民、教育农民、领导农民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他们理应“立即掀起一个以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中心的农村大变动,建立起农村中的各级政权”[23](P458)。然而他们却严厉镇压农民的抗租斗争,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严重脱离下层农民群众以及辛亥革命在反封建上的不彻底。
三县新政权联合剿杀千人会起义,作为旧秩序的既得利益者立宪派出身的富绅丁祖荫最为积极,以其为首的常熟新政权对封建旧势力具有严重依附性,他们内心深处倾向于以程德全为代表的旧官僚,因此常熟新政权在镇压饥民抗租中最为迫不及待。作为封建统治者的清末常熟县政权在平息农民抗租、闹荒以及米荒等风潮过程中,采用的多半是威慑、恫吓、剿抚结合的方式。辛亥革命后,作为新政权的主持者丁祖荫在处理饥民闹荒抗租时,完全撕下了温情脉脉的面纱,他联合附近各县动用军队武装镇压,这说明所谓的新政权与晚清封建政府在处理饥民闹荒等突发事件上,没有什么根本不同。甚至,他们比晚清政府更彻底,对待下层贫民的手段更残忍。辛亥革命的快速胜利,使革命党人在某些方面丧失了革命的自觉,被某些表面的胜利所迷惑。革命后的新政权应该团结与组织广大的下层贫苦农民,不断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同时应该不断加强新政权的建设,最为重要的就是不断清除混进革命阵营与政权队伍中的守旧势力,只有这样辛亥革命后的政权才能巩固。
[1]李文海,周源.灾荒与饥馑1840—1919[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2]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840—1911)(第一辑)[M].北京:三联书店,1957.
[3]王树槐.清末民初江苏省的灾害[J].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1,(10).
[4]祁龙威.千人会起义调查记[A].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C].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80.
[5]陆孟芙,沈芳畦.常熟的封建地租[J].常熟政协文史资料辑存,1961,(1).
[6]程德全.抚吴文牍[A].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C].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80.
[7]丁祖荫.重修常昭合志[M].1946年刊本.
[8]佚名.风雨大作 田庐被淹[N].申报,1911-07-14.
[9]江苏省常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熟市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10]庞鸿文.常昭合志稿[M].光绪三十年刊本.
[11]陈允昌.苏州洋关史料[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12]佚名.东塘市报告水灾[N].申报,1911-07-09.
[13]王国平,唐力行.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
[14]佚名.常昭水灾闹荒日记[A].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C].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80.
[15]佚名.常熟闹荒始末纪[N].申报,1911-07-15.
[16]张一麐.心太平室集[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
[17]廖志豪,李茂高.辛亥革命时期的苏州“千人会”起义[J].社会科学,1985,(7).
[18]佚名.常、昭善后计划[N].申报,1911-08-15.
[19]佚名.常昭光复纪事[A].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C].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80.
[20]陆元同.回忆千人会起义[A].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C].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80.
[21]江苏社会科学院《江苏史纲》课题组.江苏史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22]周文晓.王庄千人会起义始末[J].常熟政协文史资料辑存,1985,(12).
[23]李侃.从江苏、湖北两省若干州县的光复看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兼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与农民的关系[A].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C].北京:中华书局,1983.
[24]程德全.中华民国苏军都督府通令[A].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C].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80.
[25]佚名.程都督劝民完粮纳租之示谕[N].申报,1911-11-18.
[26]丁祖荫.常熟民政署报告[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
[27]吴讱.江苏辛亥光复后的政权剖析[J].近代史研究,1996,(5).
[2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