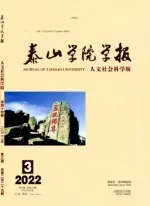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之动机探微
张日元
(泰山学院 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泰安 271021)
4 世纪初,“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这一事件不仅是基督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P17-18)。因为自此之后,基督教不但在罗马帝国获得合法宗教地位,在4 世纪末成为惟一的国教;而且基督教文化逐渐发展为中世纪欧洲的主流文化,成为西方文化的源头之一。
而在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之前,基督教还是一个小而默默无闻的教派,基本上处于一种“地下状态”,且不时地受到罗马帝国的迫害。4世纪初,基督教在遭受到最后一次、且是最严厉的迫害时,却突然戏剧性地得到了获胜的新皇帝君士坦丁大帝本人的支持。所以,对于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及其支持基督教的动机,历来是罗马史学者们研究的一个热点,直至当今,仍存争议。在本文中,笔者拟对学者们关于上述问题所提出的主要观点作一梳理,同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
国外学者对于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的原因主要提出了两种观点:一为政治动机论;二为信仰动机论。
政治动机论是学者提出较早、且现在仍为一些学者所坚持的观点。著名学者雅各布·布克哈特认为,君士坦丁是一个不为任何宗教情感所动的冷酷政客,他所考虑的是如何利用基督教为其世俗目标服务。[2]教会史学者威利斯顿·沃尔克同样认为:“君士坦丁一世基本上从政治上着眼考虑问题,认为只有靠基督教才能完成久已在进行中的统一帝国的进程。罗马帝国只有一个皇帝,一部法律,一切自由民只有一种公民身份,因此也应该只有一种宗教。”[3](P130)社会史学者罗德尼·斯塔克也认为,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敕令》是对当时处境的一个敏感反应,因为基督教经过快速增长已经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4](P2)查尔斯·诺里斯·科克伦更是尖锐地指出:“作为军人政治家的君士坦丁一世,完全是其所处时代的典型产物。”[5](P180)“他在基督教中看到的只是一个护身符,古罗马理想将通过它确保国力昌盛,而官方的异教信仰无法做到这一点。当一系列连续的成功似乎证明了这一希望时,他日益将福音书和帝国以及自己家族的希望等同。”[5](P215)
信仰动机论则是近些年来国外学者非常盛行的一种观点。提摩太·巴恩斯在其著作《君士坦丁与尤西比乌斯》这本迄今为止关于君士坦丁最细致、全面的研究中宣称,君士坦丁大帝从312年起一直忠于基督教信仰,真诚地相信自己肩负着上帝赋予的特殊使命——把罗马帝国基督教化;至于他那些明显暧昧的宗教态度,其实反映了他的小心谨慎,而非内心的怀疑或犹豫。[6]麦克穆伦也否认君士坦丁大帝对基督教的皈依含有政治因素,认为从312年到4 世纪60年代的帝国政治史与基督教并没有什么联系。[7](P44-48)
甚至,有的国外学者认为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的动机永远是一个谜,如J.W.巴尔克认为:“对于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这个问题,我们将永远不可能完全理解这位有争议的统治者的心理。我们也不能准确地了解他为什么会决心与当时占帝国人口百分比很小的教派共命运。”[1](P18)
对于该专题的研究,近些年来也是我国世界史学者所关注的一个热点。到目前为止,已有10多篇专题文章论及这个问题。总体上讲,我国学者对该问题的观点主要倾向于政治动因论。如在代表作《君士坦丁基督教政策的政治分析》一文中,作者认为,君士坦丁大帝在推行其各项政策时必然首先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必然以是否对其统治有利为取舍的原则,其基督教政策也不例外,必然为其政治目的服务。[8]
二
显然,上述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但也有失偏颇。纵观当时基督教对人们信仰、及其在现实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影响,笔者认为上述两种因素都对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大帝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信仰方面,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前的基督教虽然从人数上来看只是一个小教派,4 世纪初时罗马帝国内基督徒人数为5,000,000[7](P32),仅占帝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并被帝国视为非法宗教信仰;但在当时,与异教相比基督教的信仰对罗马人有着更大的潜在吸引力。
在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之前的3 世纪,罗马帝国陷入了政治动荡、经济崩溃、道德沦丧的“3 世纪危机”,广大民众处于一种极度的精神焦虑中,渴望一种精神上的安慰,但当时的异教信仰对此却无能为力,它们既不能为现世的苦难提供一种宗教上的解释,也不能为民众提供一种来世的幻想。于是基督教以其独特的教义填补了这一“精神空白”,为当时的民众提供了一根“精神稻草”。基督教会告诉人们,所有的不幸和灾难都是魔鬼制造的,天灾人祸、疾病痛苦都是魔鬼施展魔力的结果[9](P220);同时,教会又为人们提供了一付制剂——基督来了,他来摧毁魔鬼所做的一切。显然,基督教是在告诫人们,如果你是一位基督徒,在现世中就会得到上帝的保护,制造现世苦难的魔鬼就不敢靠近你;反之,你将会陷入不断的苦难中。除对现世的苦难作出解释外,基督教还阐述了自己的来世观思想。基督教会告诉人们:人死之后,在将来的某一天还会复活,要接受上帝的审判,信上帝者上天堂,而不信者下地狱。这样,基督教也为人的来世指明了两条路——上天堂或下地狱。并且在4 世纪后,教士的布道常常包括有关幸福的天堂永生和可怕的地狱磨难的描述,“堕落的灵魂被带入地狱之中,那儿燃烧着永不熄灭的熊熊烈火,堕落者的肉体死而复生,被投入到火焰之中,发出哀鸣,遭受着永久的折磨——恨不得再马上死去,以避免这永不停息的酷刑”[10](P11)。
在一个宗教信仰盛行的时代,基督教的上述教义必然会对当时的民众产生重要影响。如果一个人不皈依基督教,在得知上述教义后其心理必定会产生一种“恐惧”感。笔者认为,身处那个时代的君士坦丁大帝也不可能完全脱离这种“恐惧”的影响。如果我们看到反基督教者皇帝加勒里乌斯在311年临终前的表现,就会更深刻地理解这一点。
当反基督教者皇帝加勒里乌斯(Galerius)在311年处于痛苦的临终之际,他认为自己可能受到了基督教上帝的惩罚。因310年他患上了一种疾病,这疾病使其生殖器溃烂,并扩展到肠子。它长出了蛆,并发出可怕的恶臭——气味如此强烈,以致很多医生在给他看病时都无法忍受。于是在其临终之时,加勒里乌斯废除了迫害基督徒的敕令,释放了关押的基督徒,并请求他们为其临终祈祷。[11](P397-399)
此外,基督教信仰与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前的宗教信仰具有一些“相近”性,这自然会使得君士坦丁大帝对基督教信仰产生一种亲切感。在皈依基督教前,君士坦丁大帝曾经将太阳神(sol Invictus)尊为自己的庇护神,他的父亲君士坦提乌也崇拜太阳神。而太阳崇拜与基督教信仰具有某些表面上的相似之处,如礼拜日的崇拜活动与耶稣诞生日前后的庆祝等。[12](P31)而且,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12](P31)这必然也会对君士坦丁大帝的宗教信仰产生一定的影响。
所以,笔者认为从信仰这个角度来看,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是一“自然之事”。正如爱德华·吉本所言:
今天的信奉新教的勤于思索的读者,或许会倾向于相信,君士坦丁在讲述自己改变宗教信仰的过程中,一定曾通过一次慎重其事的、有意作出的伪证,以求把虚假说成真实。他们还可能不加思索地断言,他在考虑选择自己的宗教信仰时完全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并(根据一位不信上帝的诗人) 相信他是利用教堂的祭坛作为阶梯登上帝国的宝座的。然而这一严酷而绝对化的结论从我们对人性的理解看来,是难以成立的。在一个宗教热十分流行的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最有手腕的政治家也不免在某种程度上为自己所挑起的狂热所动。[13](P450-451)
在政治方面,皈依基督教对君士坦丁大帝来说更是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首先,虽然基督教徒人数在4 世纪初只占帝国总人口数的十分之一左右,相对于整个异教群体来说还是一个“小教派”,但我们不应忘记所有异教徒形成的只是一个个涣散的群体,他们没有统一的崇拜神灵、统一的教义,更不用说统一的异教组织;所以,教义统一、组织严密、并且具有排他性的基督教团体在实力上应是一个绝对强有力的“大教派”。
因此,在君士坦丁大帝与李锡尼斗争的关键时期,“君士坦丁大帝一直留心观察基督教怎样可以为一个聪明的统治者所用。当他确信这个群体已经显著成长、已经清晰发展出教阶制的特点,当他确信其宗教会议组织的奇特形式以及整个当代基督教的特点可以为支持王权提供巨大的力量——他必须及时为它提供保证,因为这股力量已经开始要求皇帝提供保证了——的时候,他意识到,一个反对李锡尼的可靠平台找到了。”[2](P230)
其次,在当时的统治体制中,基督教已经形成了一个潜在的重要政治力量。到戴克里先统治时期,皇宫、法院、甚至军队中,都隐藏着大批的基督教徒,他们都试图把现世利益同未来生活的利益协调起来。[13](P300)例如,到286年时,基督徒士兵已经构成帝国东部西班牙兵团的主要成分[14](P78);马克西米安在执行迫害基督教徒法令时,仅在其塞比安人军团中就处死6,000 名基督教士兵,几乎引发大规模兵变[15](P80)。而且“在当时,主要由笃信基督教的蛮族人组成的近卫军兴废君主的事变时有发生,军队在皇帝的废立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5](P80)。
303年,戴克里先迫害基督教敕令的颁布,部分原因是他似乎受到了加勒里乌斯反基督教观点的影响,而更大的原因是他逐渐认识到基督教已经成为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12](P25)该敕令内容包括在帝国内禁止举行基督教仪式,以及毁坏基督教堂和礼拜仪式书等。但这次迫害并没有使绝大多数基督徒屈服,而且在当时似乎并不受欢迎,甚至在异教徒当中也是如此。因为,“随着基督徒人数的越来越多,基督教越来越为人们所熟悉,大多数异教徒不再相信基督徒嗜血成性、乱伦及道德败坏等古老传说,反而他们发现基督徒是令人尊敬的市民”[12](P25)。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戴克里先对基督教的这次迫害不但没有削弱基督教会的力量,却反而加强了教会的力量。
最后,正在形成的基督教文化能够为帝国政治上的统一提供一种精神与文化上的统一。政治的统一与宗教的多元化是罗马帝国精神文化的一个内在矛盾;罗马所达到的政治上的统一是以文化上的混乱为代价的。关于这幅画面,著名学者麦克穆伦在其著作中有一段精彩的评述:
这(指罗马帝国,笔者注) 是个名副其实的大熔炉。如果我们能将100年前的大英帝国的各个部分想象为一个整体且相互接壤,而且人们可以不用渡海就能够从兰古恩(Rangoon) 旅行到贝尔法斯特(Belfast),如果我们能因此把其看成是一个在语言、宗教,传统和教育程度上几乎无限多元的统一整体,则(罗马时期) 地中海世界的真正本质将会带给我们更强烈地冲击。[4](P175)
“3 世纪危机”的经历使罗马帝国君主深刻认识到,帝国精神、文化的统一是其政治统一的一个重要前提;而要实现帝国精神与文化上的统一,正在形成中的普世基督教文化为其提供了一个可行性的选择。
同时,教父拉克坦提乌斯(曾为君士坦丁大帝之子克里斯普的老师)的声音必定不时地回荡在君士坦丁大帝的耳边:信仰上帝会消除这些自认为起源于同一祖先的人们之间的战乱和纠纷;福音书的真知灼见会遏制人们所有的不良欲望和敌意或自私的情感,对一个广泛受到真理和虔诚、平等和温顺、和谐和博爱思想激励的民族,她的统治者是可以不用刀剑来维持正义的。[13](P439)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信仰与政治因素构成了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动机中的两个必要条件,二者缺一不可。如果我们只是片面强调信仰或政治因素,将会人为地把历史割裂为“精神史”与“现实史”两个孤立的部分,这显然有违历史事实。因为任何一个生活在历史现实中的人,他的行为不但要受到“现实条件”的影响,而且还要受到当时“精神文化”的影响。所以,对于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动机的分析,我们应遵循历史唯物史观的历史合力论,而不是片面地强调某一因素,更不要走向不可知论。
[1]John W.Barker,Justinian and the Later Roman Empire,Wisconsi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7.
[2]雅各布·布克哈特.君士坦丁大帝时代[M].宋立宏,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3]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会史[M].孙善玲,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4]罗德尼·斯塔克.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M].黄剑波,高民贵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5]Charles N.Cochrane,Christianity and Classical Culture:A Study of Thought and Action from Augustus to Augustin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
[6]Timothy D.Barnes,Constantine and Eusebius,London and 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
[7]Ramsay MacMullen,Christianizing the Roman Empire (A.D.100-400),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
[8]陈志强,马巍.君士坦丁基督教政策的政治分析[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6).
[9]王亚平.基督教的神秘主义[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10]Ramsay MacMullen,Christianity and Paganism in the Fourth to Eighth Centuries,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7.
[11]优西比乌.教会史[M].瞿旭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12]Warren T.Treadgold,A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and Society,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13]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上)[M].黄宜思,黄雨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4]杨真.基督教史纲(上)[M].北京:三联书店,1979.
[15]陈志强.拜占廷帝国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