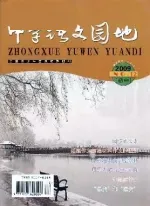语文教学的“虚”与“实”
毕泗建
课堂教学上:反对虚假,提倡真实
先让我们看一则教学案例。《飞船即将坠毁的时候》,记叙了前苏联宇航员科马洛夫,在飞船即将坠毁时冷静地向上级汇报工作,然后与女儿诀别,告诉女儿要认真对待学习的事。不少老师在上公开课时愿意选择这篇课文,并把文中主人公的英雄形象渲染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师:在飞船即将坠毁的时候,科马洛夫做了什么事情?
生:他用大部分时间向上级汇报了工作,用剩下的一点时间和家人诀别。
师:在文章中,最让你感动的是什么?
生:他知道飞船马上就要坠毁了,一点儿也没有紧张,也不是急着和家人告别,而是首先向上级汇报工作。这儿很令人感动。
生:而且他汇报工作的时候是很从容的。
师:是啊,他明知道自己的生命马上就要结束了,可是还表现得那么从容不迫,而且把工作放在了第一位,这是多么令人感动啊。
生:还有他在和家人诀别时,还问女儿将来想干什么。女儿说想当宇航员,他很高兴。说明他很热爱航天工作。这里很感人。
师:他很快就要因为航天事故而牺牲了,但他希望自己的女儿继续自己没有完成的事业。
生:他还教育自己的女儿和别的小朋友要好好学习,认真对待每个小数点。
师:读到这儿你有什么想法?
生:他虽然马上就要牺牲了,但他心里还想着女儿和别的小朋友的学习。他很了不起。
生:他对工作很认真。他要求女儿也认真地对待学习,不要让这样的事故再发生。
师:是的。这是一位对工作尽职的好宇航员,是一位对女儿尽责的好父亲。他在牺牲前的所作所为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个人。
……
首先,已经有不少人对这一文本的真实性产生了强烈的质疑。比如,宇宙飞船“联盟一号”在返回途中发生了故障,科马洛夫怎么会那么肯定地知道问题出在“地面检查时漏了一个小数点”,还要女儿“转告所有的小朋友认真对待学习”?这在科学上是说不通的。除此之外,本文在人文性上同样说不通——面对与亲人的生离死别,科马洛夫与女儿的交谈居然显得这样 “崇高”,没有撕心裂肺的痛楚,没有依依不舍的留恋,怎么看都是反人性的矫情之笔。
不过这样的文本并非不可解读,事实上,如果能站在真实的立场上,对它进行批判性、重构性的阅读,学生或许可以得到更大的收获——第一,帮助学生打破“文本神圣论”的观念,建立起唯物辩证的阅读观;第二,相对于理解文本,批判和重构文本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更高的水平,因而也更有利于学生阅读能力的提高。可是遗憾的是,我们在现实课堂中却很少看到这样的解读。更多的语文教师,还是抱着这样的文本顶礼膜拜,极尽煽情,用虚假的文本换取幼稚的感动。而在这种所谓的“感动”中,失去的则是语文教学最基本的对“真”的追求。
如果教师的解释把学生引向了一种规范化的理解,如果教师的表演、煽情对学生形成了温和的情感强制,如果学生的真实的情感体验被教师的教学情感所代替,那么,这样的语文教学就是一种过度的教学强制,教师的教学的演绎淹没了或者代替了学生自己的真实理解,学生放弃了自己的感受,而迎合权威的标准化的诠释。语文教师过多地对课文进行分解,过度地对意义进行阐发,过分地对情感进行渲染。这些都是对学生的真实的心灵的一种臆测、甚至是扭曲,而不是激发。
学生的自我意识或者说情感、精神当然是需要激发的,因为学生的人性是处于生长过程之中的。学生的人性是质朴的,正是这种质朴的人性需要深化和升华,因此语文教学是一种赋予,但是这种赋予不是简单地给予,更不是诱惑式地导向,而是应当建立在激发儿童的自我意识上,使儿童能够自主地理解世界,理解人,理解自己。他们自己具有充分的理性和能力,具有积极的情感与意志,理解他们的学习内容(特别是人文的材料),我们不能低估学生的智慧和情感,而试图把我们设计好的对文章的解释以及情感的感悟,以某种温和或者强加的方式给予学生。我们语文教师不要以成年人的自大和狂妄,给他们的心灵套上框框,哪怕你认为你的框框是他需要的。我们应该清楚地知道,我们教学的框框可能会限制他们心灵的翅膀,可能会扼杀他们心智的独特性,扼杀他们对于世界的独特感受与领悟,他们也许就在我们语文教学的过度诠释和虚假煽情中,成为某种同质化的人。
作文教学上:反对虚伪,提倡诚实
作文教学可以说是整个语文教学的薄弱环节。古人云:言为心声。文章是情感的抒发,只有情感真挚丰富,文章才能有血有肉打动人,但为了应试,学生只能把真情实感隐藏起来,与此同时,他们也失去了许多陶冶性情的机会,习惯于写假话空话,想象力和创造力严重萎缩。上海市吴淞中学语文高级教师王根宝认为:“作文的关键是看有没有话要说,根据自己的生活阅历,或褒或贬,或扬或抑。但现在高考是一根指挥棒,教师只要求学生的文章观点明确、论据充分,自圆其说,分数好一点,冲上二类卷就可以了,至于是真话假话、真情假情就都不太关心了。”写作本来是来自生活的需要,是有话要说、有情要抒、有事要叙。而学生为了取得好分数,可以任意拔高、泛泛而谈,真情实感少,虚伪成了写作的通病。
一位中学生坦言:“我们写作文不能写心里话。老师教导我们,你们的作文又不是写给自己看的,而是写给阅卷老师看的,只要写得有技巧,只要让阅卷老师觉得满意就行了。”甚至有些人专门揣摩阅卷老师的心理,从而产生了一门被戏称为“阅卷心理学”的“学问”,使这种虚伪之风愈刮愈烈,“八股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一位家长在《北京文学》撰文批评当今语文教育时指出:“(孩子)按大人的意思谨慎地使用词汇,久而久之,所有的孩子都像录音机一样地说话。更令人不解的是,语文学到这程度,学生的作文反而越来越差。学生的作文几乎是假话、假感想、假故事大全,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写过扶残疾人过街、给老师送伞、借同学橡皮一类的故事,他们快乐地共同编着同一个故事,然后套上时间、地点、人物,到老师那儿领一个好分。”
李镇西在《从批判走向建设——语文教育手记》中曾提到这样一件事:一位小学生写了自己回家路上被街上小流氓打劫的经过,由于是亲身经历,写得生动,但老师却批了五个字:“不真实!重写!”于是,这位小学生只好编他自行车坏了,看自行车的大爷如何热情地帮他修车……第二次作文交上后,居然被老师表扬了一番!写真人真事,说不真实;胡编乱造,却得表扬。这就是现在的作文教学!其实,相当多的学生早已习惯写这样的作文了。
一篇题为《绿叶赞》的“典型”作文,最后歌颂道:“绿叶,不求哗众取宠,不图名利,并且有着顽强的意志,这是多么高尚的品质啊!绿叶,我要赞美你!我更愿意做一个具有绿叶品格的人。”作为一个小学生,能有如此崇高的思想,实在“难能可贵”。思想是“崇高”了,但童真却没有了!童心,正被“崇高”的假话腐蚀。
叶老曾告诫说:“要写出诚实的、自己的话!”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也告诫说:“在学校里,不许讲空话,不许搞空洞的思想!”现在的作文盛行“假大空”话,语言已不是作为负载自己真实思想感情的载体,而成了蒙蔽自己、覆盖自己的一层帷幕,把真实的自己挡在里头,使别人看到的不是自己。如果任其发展,就将永远丧失自己的语言,这是最可怕的。北师大教授王富仁曾对作文评分标准中“思想健康”一条提出自己的看法:这种提法实际上是幼稚的,不合理的,而且会起一种误导作用——就是误导虚伪。
虚伪,使得孩子从小学会迎合别人,不会依照自己真实的感情来说话。这样的语文教育就会加强中国人总体的虚伪程度。反过来说,假如一个人在表达的时候,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才真正培养出健全的人格。对于儿童,乃至对于成人,诚实是最重要的道德标准。李镇西也提到,所有“真实的消极”都比任何的“虚假的积极”珍贵一百倍。对于成长中的学生,出现一些糊涂的认识是正常的、真实的,相反,如果学生作文中全是清一色的“正确思想”“健康思想”,那才是反常的、虚假的。
假话、空话、套话等虚伪化作文的如此“成功”,恰恰宣告了语文教育的真正失败,这样的作文教学难道不应该被彻底抛弃吗?
文风表达上:反对虚浮,提倡朴实
不知什么时候兴起来的,刚刚上高一的学生,文章开头,二话不说,劈头盖脑就是一组排比句。或风花雪月,缠绵悱恻,或激情慷慨,热泪翻滚……为什么会出现滥用排比句的现象呢?“这是中考前老师教的”,学生说。因为考试作文,阅卷教师快速阅卷,不一定会看见“漂亮话”,那就得“把花戴在最显眼的地方”,于是排比句的位置最终调往开头,成了蒙人的“三板斧”了。又因为用了这种方法至少没吃亏,甚或讨了点便宜,于是竞相仿效,流行开去。
有一次作文大赛颁奖大会,学生和作家交流,听到有学生问作家黄蓓佳:“为什么你的作品文字总不太华丽?”——学生的提问令人惊异,没想到一些学生习非成是,竟以为他们从老师那里学来的应试技巧不但可以打通高考之门,也能指导文学创作,认为“华丽”应当是文学追求,这就近乎荒唐了。
常见在一些平淡的作文中来那么一段华丽的铺陈,有如穷街陋巷挂了几只红灯笼,虽然未必和谐,毕竟“亮了”,有“彩”了。这让一些教师心理有些宽慰:毕竟学生作文能夹杂些“文化”了,毕竟有点像读过书的人了。而不知不觉间,虚浮花哨的弊端也就潜伏下来。
文风教育,以质朴为本。质朴的情感,准确富有智慧的表达,应当成为写作教学的基本追求。我们不反对形式,只反对形式主义。教师引导学生追求有创意的表达,注意语言表达的内涵,在立意上下功夫,而不能单纯追求形式。比如,现在很多学生不知从哪里学来一种“题记”,不管三七二十一,总要来个“题记”端居文首。长篇作品二三十万字,写个“题记”或许有必要,中学生作文一般只有七八百字,不少同学偏要写下三五行“题记”,这些“题记”往往与文章主题没有联系,干瘪无味,不知所云,徒增人厌。
有些学生善于遣词造句、修饰、积极修辞,下笔总能有一些精彩华美的语言,教师如果对此作过多的肯定,有可能形成误导,会让另一些学生就此认为自己缺乏文采,失去写作自信。语言的风格是多样的,华丽灿烂是一种美,质朴也是一种美。写作的表达应当有多样性,要引导学生根据个人的能力选择最恰当的表达方式。语言平实无华,没有什么可羞愧的,倒是不自量力地追求形式美,会导致恶俗不堪。孙犁曾告诫青年作者:“你心里有了许多话,你要描写一件事,这件事老在你的心里打转,它一切都准备好了,单等你拿语言把它送出来。那你就把它送出来吧,不要怕你的文字不‘美’,言语不文。用花轿送出姑娘固然好看,初学写作好比穷人,把你的姑娘用牛车拉出去吧。只要文章的内容好,语言笨一些没关系——但记住这是说初写,你千万不要认为这就好了:我可以永远用牛车往外送姑娘了。这样下去,会弄成车上已经不是姑娘而是粪草了。”孙犁这段话,本身也是很好的语言范例,通俗平易,其隽永恰恰在于朴实无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