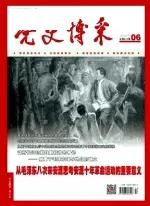正确理解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基于对其独特的语言风格的分析
方闻昊
(清华大学 中国北京 100084)
有的学者抓住毛泽东于1942年2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中关于知识分子的一段话,大做文章,认定毛泽东蔑视知识分子。毛泽东的那段话是这样说的:“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于是有人说:‘哈!你弄颠倒了,乱说一顿。'(笑声)但是,同志,你别着急,我讲的多少有点道理。”基于此语段,一些学者推断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是轻慢、蔑视。
这是典型的断章取义。他们往往没有注意或者故意忘掉了这几句话前面紧挨着的话:“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党中央在两年多以前作过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决定,要争取广大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是革命的,愿意参加抗日的,一概采取欢迎态度。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由此可见,毛泽东像其他领袖人物一样求贤若渴,他喜欢有学问并且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
还有人挖掘出没有载入建国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挖苦教条主义无用的一段话:“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了。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吗,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处呢? (笑声)”“煮饭做菜真正是一门艺术。”而死读书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情”,“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因为“你要捉猪,猪会跑(笑声);杀它,它会叫(笑声)。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笑声),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世界上哪有这样容易的事呀!”毛泽东的挖苦风格和犀利言辞,是极具杀伤力的,往往令一些知识分子如坐针毡。有人这样解读毛泽东的这段话:“毛泽东论及知识分子,他先贬之以煮饭的师傅,再把苦苦钻研理论的行为抑之以屠夫的杀猪,更把抽象的知识(所谓‘教条’)说成‘实在比屎还没有用’。用语真是尖刻恣肆,讽刺真是不留情面。由此观之,在毛泽东的意识形态话语中,知识分子受到了尽情嘲弄,而且是满含了一股怨气的嘲弄。”
其实,毛泽东无非是想表达这样的意思:知识分子不应该以为有了知识而自高自大,应该谦虚一些,应该多了解一些中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农村的情况,应该去掉对工农兵的轻视,要了解他们,和他们交朋友。
诚如毛泽东所言:“我这样说的目的,就是故意挖苦那些把马列主义看成教条的人,使他们大吃一惊,苏醒过来,好拿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他在《反对党八股》中更是把“语出惊人”的语言风格提到方法论的高度来说明:“说理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显然,毛泽东是在着意想要使人们从八股文、教条主义中惊醒过来。
之所以有人从上面的引述中,解读出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满怀恶意,可能与他们没有理解毛泽东的个人语言风格有关。
毛泽东历来主张,一切文章和讲话都要具有生动性。1940年2月7日,毛泽东为《中国工人》撰写的发刊词中,他希望这本杂志“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 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在《反对党八股》中,他把“语言无味,像个瘪三”,列为党八股中的第四条罪状加以讨伐。他的语言,原则性极强,但灵活而不呆板;以说理为主,却又洋溢着浓烈的情感。一般来说,一个人的语言具有了准确性和鲜明性,算是达到了起码的要求。毛泽东的语言超越了准确性和鲜明性,同时具有了感人的生动性,一语中的,耐人回味,具有艺术欣赏的价值。他的讲话,有时一针见血,言辞尖锐,绝句频出,有时举一些极端的例子,如反弹琵琶,出人意料,不落俗套。
著名作家王蒙曾这样评价毛泽东的语言艺术:“有气势,不受约束。他的思想非常自由奔放,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也喜欢说些比较惊人的话,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有时他把一些大事说得很小,‘天塌不下来’这是他喜欢说的,还有‘文革’中也说过的这样的话‘无非是死几个人’。”确实,毛泽东善用夸张手法,如同平地起风雷,可谓笔惊天地,语泣鬼神。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一语,与后来说的如果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没有发挥出来,“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一语,同属此类。
可惜的是,很多人并不熟悉毛泽东“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讲话风格,而只从字面去理解他的话。1957年,毛泽东在上海说出了这样的话:“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有人据此认为毛泽东反对知识分子。对此,切不可望文生义。其实,毛泽东并不认为知识分子是无知的,他是用“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方式,将所要表达的意思讲解透彻,以破除人们长期形成的对没有改造成为劳动阶级的大知识分子的畏惧感,敢于从思想上改造他们;以打击知识分子长期养成的那种高高在上的骄矜心和唯我独尊的优越感,激发他们走出书斋,放下臭架子,以工农兵为师为友,为工农兵服务,再立新功。
在传统理念中,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向来是有高下尊卑之分的,与共产党的工农本位观和平等观相违背。知识分子往往自视清高,认为群众是无知的群氓。岂不知道,共产党正是以这些“群氓”为主干力量打下了天下。毛泽东挖苦那些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翘尾巴,“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个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农民算什么呀?你们就是阿斗,又不认得几个字’。但是,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 知识分子看不起工农兵的优越感来自掌握了知识,而毛泽东在这里偏说“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没有知识的工农最有知识,打掉知识分子自我骄傲的资本,目的还是希望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为工农服务,努力转化为工农阶级的一部分。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人民队伍里,如果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不为人民服务,知识就是没有用的知识,知识分子就是没有知识的知识分子。这才是毛泽东“知识分子无知论”的含义,与反智主义没有任何联系。相反,毛泽东热烈欢迎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人民需要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最有用。
至于为许多论者证明毛泽东蔑视知识分子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一语,其要义实际上在于鼓励人们大胆进取,不要怕权威,要敢想、敢讲、敢做,突破狭小视野的局限,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
1 958年5月8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破除迷信的问题,鼓励人们不要怕“教授”,不要怕“孔夫子”,不要怕“外国人”。毛泽东的讲话中,在谈了“我们大多数同志有些怕资产阶级的教授,整风以后慢慢地不大怕了”以后接着说:还有另外的一种“怕”,即怕无产阶级教授,怕马克思。“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好像高不可攀,要搭很长的梯子才能上去,于是乎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不要怕嘛。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无非是脑子里有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在楼下的人,不一定要怕楼上的人。我们读一部分基本的东西就够了。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列宁说的做的都超过了马克思,如帝国主义论。马克思没有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他在讲话提纲中提出了一些鼓舞人们奋发努力的论点:“从古以来,发明家都是年轻人,卑贱者,被压迫者,文化缺少者,学问不行。”“名家是最无学问的,落后的,很少创造的”,原因是“名人学问多保守落后了”,“世界是青年的,长江后浪催前浪,譬如积薪,后来居上”。
为了论证这一点,毛泽东兴致昂然,旁征博引,在5月8日的全体会议上,一连举出数十位古今中外的历史、神话和现实中的人物。在5月20日的全体会议上,他还提到没有上过大学自学成才的中国数学家华罗庚,以及苏联最早提出火箭飞行理论和航天理论的科学家齐奥尔科夫斯基。毛泽东说:“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说明青年人是要战胜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为大学问家所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种束手束脚的现象不好,要从这种现象里解放出来。而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来是很丰富的。过去是在旧制度的压抑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
5 月18日,毛泽东以“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为题,为印发大会各同志阅读的一份文件写批示:“请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收集材料,编印一本近三百年来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家、技术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如果能够有系统地证明这一点,那就将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他的着眼点还是破除迷信,鼓舞士气,造就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
显然,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实际上就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通俗形象的表达,而并不是鄙视知识,更不是蔑视知识分子,这一思想和逻辑就在于鼓舞群众排除迷信,力争上游的精神武器。
抛开那些恶意中伤毛泽东的情形不谈,对于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的误读,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有正确认识毛泽东独特的语言风格。毛泽东是一位极具语言天赋的领袖。他的话语不仅准确,而且生动。他善用夸张等修辞手法,惯于以犀利的言词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所面对的人或事物的问题。
在具体地分析了他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语言风格后,不难把握其话语背后的真实意思。虽然他在论述知识分子问题时总是带有挖苦讽刺的意味,但是绝不可将其简单地看作是对知识分子的轻慢和蔑视,而要正确地理解其内在的含义,即他希望以此来引起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注意,使知识分子能够成长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人。
[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重印),1991: 815、833、837、1031.
[2]毛泽东选集第六卷 [M].哈尔滨: 东北书店, 1948年: 944、947.
[3]袁盛勇.延安文人的真诚与说谎 [J].粤海风 , 2005(4): 42.
[4]毛泽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二月一日在党校开学典礼的演说)[N].解放日报, 1942- 4-27.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166-167.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编.话说毛泽东——知情者访谈录[M].北京 : 中央文献出版社 , 2000: 105.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M].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114.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9: 89.
[9]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7: 452.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M].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 1992: 195、206、236、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