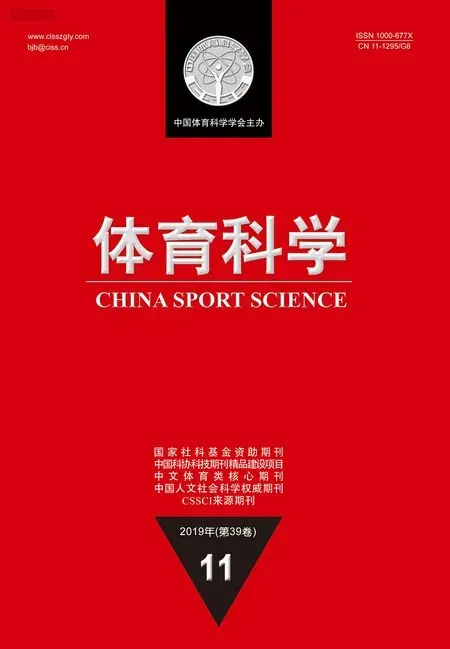体育人类学方法论
胡小明
一门学科的研究方法,是理论形成的出发点,同时,理论又是方法应用的前提,二者相互联系紧密。以方法体系强化科学,对科学方法系统地进行研究,是英国学者培根首倡的[15]。把方法作为研究对象的基本理论与学说,可以称为方法论,它是体育人类学学科发展的重要基础。
对方法的认识和了解涉及研究方法的理论层面,并非本土原创,以至于过去我们对舶来之物深信不疑。西方学者认为,体育人类学的理论模型一般可以分为:解释(explanatory)模型和说明(interpretive)模型两大类型。前者是一种明确提出因果关系的“科学”模型,包括进化论(Evolutionism)、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functionalism)、冲突理论(Conflict theory);而后者只为观察者理解事件或行为提供了不同的视点,包括象征人类学 (Symbolic anthropology)、文 化 相 对 论 (Cultural relativism)、整体观(Holism)等[4]。西方体育人类学现有的两大类理论模型是否能够对体育活动进行有效地解释和说明?这门学科的作用难道仅仅只能进行解释和说明吗?应该遵循怎样的具体方法和技术路线进入具体研究?没有答案。中国学者经过长期的多次实践检验,认为诸如进化论、文化相对论等部分虽具合理性但需要重新梳理和认识,而对其他部分诸如冲突理论、象征人类学等,因其并不能对体育进行有效的解释和说明而提出质疑。同时,针对体育广袤的应用领域,还需要增加更符合体育研究需要的具体有效的方法,在创新中寻找到解决实践问题的真实路径,使这门学科焕发活力。
方法论如果存在缺陷,一门学科早晚也会失去生命力。既然现有的体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存在不足,就需要从认识论的角度重新审视,否则,势必影响到这门学科的发展。像改革开放初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许多新兴学科而现今所剩无几,体育学科一度繁荣竟成过眼烟云,实在是难忘的教训。
1 形成具有体育研究特色的田野调查方法
对体育研究来说,人类学是理论和方法的宝库。很少有学科像人类学这样,有如此丰富的理论和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并不是可以全部照搬应用的,而是要根据不同的具体对象加以选择。当前,最需要引进和倡导的方法,是针对停滞不前的体育理论中虚浮的部分,借鉴具有人类学实证研究之传统的田野调查(田野工作)方法。“方法论是学科发展的基础,人类学学科又是靠田野调查起家的,国内外学术大师有价值的著作、有影响的观点都是对田野工作经验的提炼、概括与升华。于是,研究方法在人类学学科中的位置与其他许多学科相比似乎更重要一些,而方法论更成为人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3]
田野工作(field work),又称实地调查(field research)或田野研究(field study),作为一个学术词汇最初是被博物学家所使用,动物学、生物学、地质学等学科的发展初期曾广泛进行“野外作业”,之后才逐渐专业化,形成各自独立的学科。20世纪以来,田野调查逐渐成为人类学家直接进入社会文化环境调查以搜集资料和建立通则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在美国,最先由博厄斯在巴芬岛开始田野工作;不久,英国剑桥大学的哈登于1898年率队在太平洋的托雷斯海峡做田野调查;尔后,马林诺斯基将其推至巅峰。至此,田野调查越来越成为人类学独特的专业研究,田野经验被认为是训练人类学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田野工作是人类学家的必备训练,远远超出了作为一种具体方法的意义,成为人类学知识体系的基本构成部分。
在西方人类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由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与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主导,先后发行六个版本的田野手册《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凝结了几代人类学家的集体智慧,即便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这本手册中设定的许多调查项目和方法仍是理论与方法结合的最佳典范。书中有关技术工具的部分内容,现今看来已经过时。21世纪数码技术飞速发展,田野工作者拥有的数码相机、录音笔和DV可谓今非昔比。尽管如此,这本书附录提供对资料和田野中采集的样品进行分类的基本方法仍然具有指导性价值,它揭示出人类学研究的对象不是文物、文字、文献中的玄理奥义,而是寻常百姓的现实生活中的日用常行之道。[20]
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的根基,是人类学家获取研究资料的最基本途径。可以说,田野工作的独特方法,建立了学科的基本知识框架,因而成为人类学最重要的方法。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一种方法论(methodology),一是指一种具体研究方法(method)。在人类学的实际研究中,田野工作是指经过专门训练的研究者亲自进入某一社区,通过直接观察、访谈、住居体验等参与方式获得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体育人类学借鉴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在实践应用中加以创新性改进,形成以身体动作分析法与体育效果测量及生态测评、多学科集中介入的短周期专题性田野调查的特色,构建体育人类学的标志性方法。
对于处于发展初期的体育人类学而言,田野工作的现实目标,主要是为撰写民族体育志提供大量有用的资料。田野工作的结果,最直接的是形成一部以真实调查报告为基本框架的民族志,在此基础上运用跨文化比较、文化相对论和整体观,完成新的理论观点生成。
田野调查的方法论意义,首先是对选题学术价值的衡量,重点是提出假设并加以实证的理论意义以及社会效应和可操作的实际意义。在每一次具体的研究中,项目(田野点、社区、对象等)的选择——主题要符合自己长期以来的学术经历和兴趣点,有前期积累的研究基础,研究结果具有学术价值或指导实践的意义。对于在学术上已经有过很多讨论但仍然似是而非的理论假设,可以进一步用田野调查材料加以证明,或者颠覆传统理论、观点和前人做过的研究,也可以提出新的理论的假设来进行实地验证和说明。对体育研究而言,田野调查以真实数据的记录分析作为判断其体育性质的出发点,这是体育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基础。因此,体育人类学不是照搬人类学的一般方法研究体育问题,而是需要采用体育的其他学科及其他应用人类学分支所无法替代的专业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
1.1 深入实地的参与观察
科学研究首先需要从观察入手,观察结果经归纳得到假设,再加以证实其真伪。“科学方法的七个特征是:观察(经验主义)、目的性、系统性、可重复性、可交流性、自我修正(通过学科群)以及积累性。……当个体作为一名科学家发挥其影响时,他需要利用科学的认识方法去鉴别正确性或真实性。在科学方法范围内,必须通过观察证明知识的正确性。在科学中,某个论断要想有用,就必须与一些能够证实/或证伪的经验陈述相关联。事实上,根据科学方法的认识论,如果不能通过观察来证实某个论断,那么,这个论断在科学中就确实没有任何用处或价值。”[1]体育理论特别是体育文化的研究,判断其有无价值的首要标准,也应该是能否正确地观察与证实。
人类知识建立在仔细观察的基础上,不被表面联系的假象所迷惑,需要寻找足够的经验和事实证据使观察符合逻辑并系统化,这是一种跨学科、跨领域的规范。体育现象是动态变化的,人们身体活动行为的意义因时因地而不同,所以,有必要采用人类学田野工作的特色路径——参与观察法。这种观察需要研究者几天、十几天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成为所研究的真实背景的一部分,系统观察所见所闻,探索某种身体运动在特殊社会关系与环境中的本质。参与观察与旅游观光有本质区别,体育人类学在这个期间所做的深度访谈、动作分析、体质测量及其他环境数据收集等,都是参与观察的重要内容。
从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上半叶,受科学方法的影响,人类学家将研究场所搬到了人们生活的实地进行田野工作,开创出与研究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和深度访谈(depth interview)的方法。这种与研究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参与观察方法,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发展了不同时期的学派,形成文化人类学的独特理论体系和方法论。
欲了解某种陌生的文化,接触新的观念和习俗,需了解当地人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表现在外的行为,最好的办法是与他们密切相处。但是,人们对自己从事的活动之主观描述,往往不一定正确或不足以解释其行为。一名受访者在描述某个事件时,常常有意识或潜意识地加以筛选和曲解。所以,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参与到他们的正常生活状态中直接观察他们的行为。从研究体育活动的情况看,参与观察可分为“参与”和“观察”,前者是主动介入到活动之中的并融入其中进行体验、学习以原住民的观点了解事物,可能在面对社会事实时如何创造自己和他者会感到困难;而后者相对是客观的、保持一定距离、不涉入的状态,这在记录素材时尤其重要。按自己的主观疑团乱发问卷,或是按想象视角摆拍照片,都是不可取的。
采用参与观察方式进行的研究,使被研究者不会因研究者的出现而改变其行为,可以在身体运动现场得到直接的和详细的真实资料,以便正确理解和分析。参与观察者不能把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强加于研究对象,把“先入为主”的心态消减到最低程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体育界在社会学的影响下出现以问卷为主甚至“问卷第一”的趋势,对直接观察相对忽略,以至于很难形成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里需要强调:当一般的问卷无法反映真实情况时,尤其是当需要用行为的连续性来解释现象的意义时,除采用参与观察法,几乎别无他法。
作为人类学的学科特色,田野调查的概括、提炼和升华影响到人类学的理论、著作及其他成果。由于马林诺斯基的杰出示范,参与观察法成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式,社会学、医学、教育学等研究领域的学者也有所采用,但也出现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参与观察的方法长期没有进入到体育研究之类的研究中,可能与学者们看法不一致有关。譬如,对参与观察的理解,因为具有跨领域的研究特质,其定义各有差异。E.Babbie(1989)则认为,观察者对于所欲观察的事情并不是事事皆参与,应该以“实地研究”来取代。Lindemann则将观察者分为两种:一为客观的观察者(objective observer),另一为参与观察者(participant observer)。Lofland(1984)则认为,参与观察是一种实地观察或是直接观察,研究者为了对一个团体有所谓的科学了解,而与该团体建立和维持多面向和长期性关系。Raymond Gold(1969)则依照参与程度的不同分为四种观察角色:完全参与者、参与者、观察者、完全观察者。Patton(1990)则认为,参与观察是一种完全浸入(complete immersion)的研究情境,与研究者和研究情境完全脱离之间的一种延续状态。法国学者布厄迪提出,传统参与观察法最大的困境是人如何能够既是行动者,又同时观察自己的行动?这些问题,其实对于本土化的体育研究的影响并不明显,多数情况下,原生态民族体育的田野调查往往是主客位融为一体的。人类学者向来以“他者”,即异己社会文化为研究对象,在观察异己社会文化时有意无意地与自己所处的社会文化相比较,这成为田野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角度。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是一门通过 “他者”的研究来达到跨文化理解和沟通目标的学问,它要求研究者要深入具有异文化性质的“田野”中去做艰苦的调查,并利用所获资料和亲身经历来解说文化与人性[7]。体育人类学研究者面对很多陌生异己社会的身体文化,主要采用主客观统一的比较方法。
人类学的观察方法,一般有主位(emic)与客位(etic)的研究视角。前者是从当地人的视角去理解文化,对研究对象深入了解,通过参与观察,听取原住民对事物的认识和观点,尽量像本地人那样去思考和行动,并依此作为最终的判断进行整理和分析的研究方法。后者是研究者从文化外来观察者的角度,以经典理论和方法对其观察结果进行解释的研究方法。主位研究是站在被调查对象的角度,用研究对象自己的方式和观点去描述和解释他们的文化;而客位研究是站在局外立场,用研究者所持的观点去描述和解释所研究的文化[16]。体育人类学的研究中,一般主位与客位研究并不互相排斥,而是保持互补与融通的“主客位统一”的立场。
无论主位或客位,参与观察者都需要进入实地直接观察,身临其境地研究其文化。这是一个“先融入”、“再跳出”的过程,是研究者直接参与被研究者的生活以及直接观察来搜集数据的方式。体育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并非百科全书式的铺开,而是相对简单地针对某一项活动,其主要目的是从人类日常身体运动的事实中,发掘有利于体育发展的新理论。对体育现象而言,它是一种深度个案的独特研究方法,投入较大、成本较高,选择最有价值的典型对象非常重要,否则如“高射炮打蚊子”,得不偿失。
参与观察并非走马观花,而是一种以深度直接观察进行搜集资料的个案研究方法。体育人类学研究者必需深入到原生态的背景中,在不干扰研究对象自身轨迹的行为过程中,进行与身体活动相关的专题性观察。这种观察比通常的全面立体观察大为缩减,集中于与体育运动相关的对象。在撰写民族体育志前,尤其需要通过直接参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以了解他们进行身体运动的文化行为和技术。以往没有出现真正的民族体育志而使民族体育的研究工作如无根之木,与研究者没有采用规范的参与观察有关。
生活意义的多样性,要求人类学对习俗性身体活动做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解释,参与式观察法在人类学调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并不一定在各种体育现象的研究中都具有普适性。如果研究者出现被当作外来陌生的入侵者,或参与观察遭遇到伦理困境(如黄、赌、毒等现象)时,研究场域的利益完全是秘密的(如服用兴奋剂、不雅的身体活动等),被研究者的观点和研究者的观点严重冲突时,难以获得真实材料,不适于参与观察。
1.2 体育活动的深度访谈
在体育界过去的“田野调查”中,不少人往往忘记了自己的参与观察者身份,仅是找到所谓知情人进行匆忙的询问及发问卷,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到活动现场转一圈拍拍照就回家写论文。尽管短瞬间记录下来的信息也可以作为关于某一身体运动现象的第一手材料,但这种粗糙而单薄的类似自上而下的行政调研方式,并不能完整而深入地反映某种丰富多彩的身体文化现象,何况还会出现许多经过被访谈人过滤、加工后难以证实的误导信息。体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并非大样本的社会调查,也不是一定要把经过统计学处理的数据上交以供参考。因此,不能让访谈超脱于观察之外,而是要利用深度访谈的内容充分佐证参与观察的结果,形成能经得起反复检验的材料,尊重科学实证的重要环节。
简单访谈如今已成为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常用的方法,不仅在研究生论文和各类纵向课题里大量使用,甚至在一些民族体育“田野调查”里也变成了惟一的方法,这里面潜伏的隐患很容易被忽略。中国考古人类学的开拓者李济先生曾提及,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克鲁伯曾调查加州一个只有8千人的印第安人博莫支系,在75个村落中选取了16个,各找出一、二位老人来进行民俗的访谈,每人都是讯问同样的1094个问题,答案只能有“是”与“非”;即便是已经精简到如此程度的两万多个答案,克鲁伯教授仍然因“这些人的知识、准确的习惯、合作的精神及受暗示影响的能力而各不一样”而质疑其可靠性。于是,他进行了其他标准的测验,得到的结论是:有的老人只有说“是”的习惯,并不管事实的是与非;而有些老人则只习惯于说“不是”,一切皆被否定。李济感叹访谈结果有限的真实可靠性,还进行了重要的补充:“有一个限制是为当事人所感觉不到的。这个限制就是无论哪里研究的民族文化,低到什么程度,凡是不刺激那民族的意识与感情的一类材料,大约可靠性比较的高。反过来,凡是活材料,尤其是靠土人口上供给的,那可靠性就难讲了。”他甚至做出了这样较为极端的判断:“一个民族学家,研究另一个民族,就是学会了他的语言,能听、能讲也不见得就能搜集完全可靠的材料。”[13]这样的教训,值得我们汲取。
所幸,体育研究需要抓住的专业特点,是身体和运动;没有身体运动的相关内容,很难被认为是体育研究;而身体运动看得见摸得着,是很实在的现实具象。一般情况下,越接近于较单纯的身体运动内容,涉及到敏感地影响访谈结果可靠性的民族意识形态的障碍就越少。围绕身体运动为核心,一切相关信息都需要以事实的观察为印证。那么,站在学科已有知识体系的角度的“主位”观察,可以进行公认的科学判断;但站在活动者传统文化习俗的承袭心态来进行“客位”的参与性体验,可以获得特殊行为模式“地方性知识”的合理解析。二者往往交织转换,在体育人类学的研究过程中和谐统一,在整体观的统摄下获得更全面的认识。
由于参与观察的主要对象是身体运动,那么,深度访谈的内容也应该以此为轴心。然而,包括体育界,许多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需要进行社会调查,习惯于闭门造车,在调查之前凭空设计调查问卷和表格,臆想问题和调查项目,然后下去找人问答,把填好的表格拿回来分析,才发现有许多遗憾——最大的遗憾是与体育运动几乎没有关系。体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者的素质和能力对于工作的顺利开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仔细选择具有理论价值的研究主题,再把焦点集中于最能够对理论假说具有实证价值的地方。在决定研究领域后,先要踩点,亲自到准备调查的地方了解情况,做简单的预先准备,才能有效提高研究的科学性。
在取得同意进入研究场域之前,研究者需要为自己准备充足的理由——自己为何而来,对有疑问的当地人如何进行某种方式的解释。与研究对象建立良好关系,一定要尊重对方,谨慎而不突出表现自己,尤其不能多管与外来者身份不符的家庭闲事,与当地人坦诚相待。对观察对象的表现不做预设,而是甘当一个反思的听众和忠实的记录者。
在田野调查中,访问与参与观察交融一体。深度访谈首先要取得接受访问者的同意,然后,再根据资料的隐密性决定有无匿名的需要。访谈一般有非结构式访谈和结构式访谈两种形式,一般在调查之初宜多用非结构式访谈,而在与当地人民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后可以使用结构式访谈,两者是互补的。
无论是进行何种访谈,都要注意:
第一,开始调查阶段,应集中访问一些不会引起误会的问题,最好集中在身体运动的内容方面,涉及传统文化需要注意禁忌习俗。
第二,体育人类学的专题调查因时间较短,需要事先制订相关表格。把访问调查提纲中的问题设计出表格,如果太多则应分解为若干个具体的问题。一次访问时间不宜过长,提问要简单明确。注意控制时间。身体运动方面的问题大多集中在几分钟至半小时以内完成。除非是农闲或晚饭后,一般不做长时间的开放式访谈。当被访谈人用自己的概念和术语来描述时,应充分进行记录。结合PRA填表,会大为节省时间。
第三,涉及到价值判断的调查内容,原则上应当让被调查人凭习惯做出判断,以被调查人的直接反应为依据,尽量避免主观介入。在整个调查中,调查人必须随时注意避免用自己熟悉的价值观干扰被调查人的思维,特别是不能用现代体育活动去规制或诱导之。
最后,做好采用各种技术手段记录的准备,在工作的每一天都要记田野日志。
1.3 及时处理田野调查的材料
体育人类学主张用客观的观察角度进行客位的科学理性调查,又有主位的参与体验,是人类学带给体育研究的新视角。这种主客位的同一性往往贯穿整个参与观察的过程,但是,回到研究室,通常需要采用比较来分析判断诸种多元文化,得到新的判断来印证自己的假说。这一切的基础,在于是否获得了足够的真实材料。
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的每一天的记录是田野笔记,其真实性是其具有价值的基础。对于体育活动而言,深度访谈其实也是一种重点观察,其目的是了解通过直接观察无法获得的材料:研究者的问题可以用被研究者的语言形式询问时,透过较长时间对少数对象的访谈,试图透过开放性的问题,引导受访者说出对特定事件、情事或人物的观点。田野调查正式进行时记录当天的笔记,是积累和整理真实数据的最重要的步骤。如果当时没有记录,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补充记录或整理录音。田野笔记是研究者在实地进行观察后,才将所搜集到的数据整理成笔记。而深度访谈则是可以在访谈的时候一面做着记录,但是,由于时间紧迫往往只能以“摘要”的形式来做记录,配备一支录音笔是很必要的,充足了电的手机也可以录音。否则,摘要地写下发生的事件,过于精简且通常只是包含关键词。准备好每天撰写田野日记及时间表,即使当天再累也不要放弃。
体育人类学由于需要研究身体运动的特点,往往需要借助必要的影像记录材料(实况笔记Full field notes)进行分析,事先准备好摄录器材十分重要。对研究体育活动而言,这是一种采集数据的最重要途径,以实况录音和录像进行,然后,根据需要誊写为编号式的笔录稿件。
田野笔记的基本内容应包含:时间与地点、活动主题及内容、参与者或行动者、行为或事件过程、达到目标的效果和感受。深度访谈的内容和田野笔记类型、形式和内容取决于个人的喜好和风格、研究的主题、观察现场与环境以及所运用的技术。为了提高效率、缩短时间,访谈有必要事先准备提纲甚至表格,先印上姓名、民族名(本族的称呼)、性别、年龄、身份、访谈时间、所居住村寨、记录人等空格,完整记录相关真实资料,但应尽可能剔除与身体运动无关的内容。2012年在丽江“东巴跳”的田野调查中,一次东巴集中的法会上调查者在短短几小时就完成了几十份表格式问卷,可见集中的群体活动获取第一手材料的优势。
一份实地笔记或是深度访谈的数据是未来分析的数据来源。“详尽”与“准确”是基本原则。撰写完成前不与他人讨论以免影响观察结果;找不受干扰的安静地方撰写;安排充足的时间撰写;切忌一面撰写,一面编辑。记录下来的材料要进行核实并立即纠正错误。调查材料的整理公布后,各种原始记录应按科学方法存档,以备日后查考 或 研 究 。[5,6]
体育人类学的深度访谈不是像通常问卷调查那样简单分发、填写和回收,而是亲自面谈,要求当天完成访谈笔记,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保存最原始的真实资料。近年来,我国体育界已出现研究者利用多次深度访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竞技游戏个案进行精心分析的博士论文,得到学界广泛认可[12]。
2 针对身体运动的测量及生态环境现状记录
在过去对民族体育的挖掘、整理及研究中,包括笔者在内的研究者习惯于深入实地看看,拍几张照片、访问几位老者,回来就该项目进行文字描述,归纳几个问题提出几条建议就算完成一篇论文。那么,实地走访真就是田野调查吗?没有获得自己亲手采集的素材可以算是田野调查吗?在当今交通便利的条件下,到许多地方进行简单的走马观花远不如网上看驴友的游记精彩;如果没有有价值的假说,有分量的选点,就不会去进行田野调查收集必需获得的宝贵资料和数据。为什么近年来体育界越来越多的“田野调查”越来越没有学术含量?反省的结果:简单的实地走访并非真正的田野调查,尤其不是符合体育研究需要的田野调查。
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大多是有限地域中某一人群的原生态习俗事件,“走马观花”式的调查,缺乏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定性研究,更缺乏有关身体运动的量化分析。资料收集的粗糙和简略,将导致对地方性历史文化基本事实的遗漏,也容易滋生后期编造材料的假冒伪劣之风。因此,主要目的在于“定性”的深度访谈十分必要,不定性就展开量化研究容易南辕北辙,而定量分析作为辅助手段以证实定性的准确,这在原生态文化研究中往往成为重要的基础和轴心。
矫枉过正,近年来体育界又掀起一股宣扬“质性研究”的风潮,弄得有些玄虚,似乎在倡导新的研究方法,其实不过是拉回来重视定性研究的呼声,并未解决实际问题。人类学队伍中出现把田野调查视为质性研究的观点,在体育界也得到附和。然而,体育人类学不宜与所谓“质性研究”划上等号,准确的观察与客观描述,都需要尽可能使用量化工具对资料进行精确统计。体质测量,对体育人类学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进行田野调查工作中,有条件的情况下要尽可能采用。其实,这也是早期人类学家的基本功,如费孝通在大瑶山调查时从1935年9月18日到10月底的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对各地原住民进行的人体测量就达5次之多。体育文化的载体是身体运动,如果研究的内容最终与身体的发展无关,那无疑是在搭建空中楼阁,辛辛苦苦完成的研究成果的价值将大打折扣。
是否亲手获取真实素材,是衡量田野调查成效的基本标尺。体育人类学除了遵循一般的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的要求,还特别需要对人们进行身体活动的生态环境做客观记录。因为体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工作大多针对某些萌生于特殊条件下的原生态身体活动,对其产生的周边环境需要认真采集客观数据,以便分析其成因及生存要素。要避免单纯地就活动本身论活动价值的“刻舟求剑”式的研究,以及将大量民族传统体育的改造成现代运动竞赛过程中出现的“拔苗助长”的后果。譬如,在“抢花炮”成为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竞赛项目后,屡屡发生骨折伤害、打架斗殴乃至伤残至植物人的惨剧,这就是没有充分进行体育人类学的科学研究,缺乏对科学采集的原始数据进行分析,就匆匆搬上现代竞技场的结果。
体育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数据资料收集一般分为体质测量、环境器物、历史文化几部分。从调查过程看,体质测量涉及到测试对象配合等人际关系,需要事先协调。有一些仪器携带不便、指标换算、语言沟通等问题,没有经过体质人类学训练的一般文史工作者难以完成,但由学习过体育专业的师生参与却显得相对简单;环境和器物的调查数据通过网络、书籍、论文等资料检索可在出发前获得粗略概况,田野归来后与实地采集的数据一并处理。调查人员在实地采集数据需要克服交通、气候等艰苦条件,工作量较大,需要有吃苦耐劳的心理准备;最难的是有关历史文化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研究人员需具备深厚的文史哲基础,还要经过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的基本训练,否则在实地获取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后,难以进行理论生成,更难 凝 练 为 创 新 性 观 点 。[5,6]
文理融通,把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与自然科学结合起来是人类身体运动文化的真实需求,这是因为体育研究整体上属于应用性范畴,而且,基本上处于终端,与哲学、理学等基础理论距离较远。体育人类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们的身体活动,成熟的人体测量与评价技术可以在很短时间里获得真实的客观数据,一目了然地判断某种身体活动对人体的影响,从而方便地评估其客观的体育效果。身体活动、身体运动、身体动作的测量与数据分析,是体育人类学特有的独到优势,可以解决与体育相关的具体问题。
体育人类学尊重生物学科成熟的科学方法,并乐于将其尝试用于原生态文化事项的实证过程中。中国的体育人类学团队在研究滇西北“东巴跳”与“东巴文”的田野调查中,首次创造性地采用了“从身体动作到图画文字”、再“从图画文字到身体动作”的身体动作分析法的“双向实证”技术路线,为研究原生态的身体运动对古文字形成的作用开拓出科学的新路径[11]。这是根据原生态身体运动研究的实际需要而进行的原创技术方法,受到美国人类学领军者博厄斯的语言结构理论的启迪,把本是常用于运动生物力学的动作分析法转换改造为身体动作文化符号分析法。
2013年在对广西民族传统体育节庆的评估和跟踪中,体育人类学团队再次采用身体动作分析法,根据新的研究对象重新设计调查表格,把一些藏在深山人未识的巫术仪式表演(如“抬官人”)等进行“巫术、舞蹈、武术”等不同性质的分类,再进行数理统计以寻求相互关系的确切证据,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证实原始宗教对体育运动形式(如武术套路)及艺术表演形式的萌芽催生作用。
在上述两次田野调查中,还尝试运用来自影视人类学全方位展示形象材料技术的启迪,试用类似3D打印的双机位动作拍摄法,具体的规范操作尚在试验阶段。体育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有关身体运动的文化,需要创造满足自身研究独特需要的工具和技术。
在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中,田野调查既是资料的搜集过程,也是特殊的理论生成活动。人类在广袤地球上生存方式的多样性,决定了人类学调查者应该采用不同的方法,对不同地方传统身体活动的田野工作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尽管运动人体科学等学科在运动医学和保健等领域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可靠知识,但科学方法的使用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科、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甚至体育教育训练学等领域却举步维艰,这是因为涉及到以“人”为研究对象,其动机、态度、价值等因素往往受到深层的内外环境影响,个体与群体、民族与文化、传统与变迁、动机与原因千差万别,变量复杂而难以掌控,很难普遍化、形式化和精确化。对人类万分复杂的本性、思维、技巧、智能、交际等若干方面,缺少公认的精确测量工具,导致某一人群常用的体育行为模式难以简单复制与移植到另一群体。因此,对于动态演变的集体性传统体育活动态势,最好引入发展人类学的新理论加以引导。
3 经过田野调查的民族志
为何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学学科建设停滞不前甚至奄奄一息?主要是田野调查的缺欠,导致研究方法和基础路径的迷失。
体育人类学对研究民族体育始终抱有强烈兴趣,这是因为它的理论和方法最适合在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特殊风貌中寻求人类文化的潜在价值。人类学田野调查作为其标志性的研究方法,是获取研究资料的最基本途径,是撰写“民族志”的源泉——这也是民族体育研究的基础。人类学家所使用的“田野工作”独特方法,是判定一项研究是否属于人类学区别其他学科的关键标准,它甚至成为整合整个学科的资源和依靠。倘若一个声称在做体育人类学研究的人却无任何田野工作经历,那么,他作为人类学者的身份在同行圈内会受到严重质疑。同样,一本没有经过田野调查编出来的“民族体育志”,难免不为学界质疑。
人类学最核心的理论和方法建立在扎实的田野工作的基础上,其直接成果是民族志。民族志,一般是指研究者对某一社区、族群或民族的文化所做的描述或解释的文本,而我国的民族体育研究中最为匮乏的就是这种由作者直接观察后获得第一手材料对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系统描述。“就人类学的大部分历史来说,人类学家依靠印刷出版的资源以共享信息,特别是依靠白描型的民族志,偶尔辅之以照片,在很少的情况中,辅之以影片和类似的记录。民族志特别反映出西方人对学术工作的态度,是我们学科的基础。”[17]一般的民族志中并没有记载多少身体运动的内容,因此,通过田野调查再编写民族体育志这样的基础工作,还得由民族体育研究者来完成。
文化人类学早期对于文化的研究,往往基于民族志;而真正的民族志,既是研究方法也是研究产物。民族志(Ethnography)即“记述民族学”(Descriptive Ethnology),是对一个人类群体进行客观的调查结果的全面详尽描述;对民族体育进行专业性研究,准备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新事实、形成新观点,阅读民族志是最基础的工作。反观我国的民族体育研究,严重忽视学术研究中这一具有出发点性质的重要环节,几乎找不到一部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较为规范的民族体育志,遑论把民族志作为研究的导航仪了。其明显的结果,就是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用于搭建沙滩上的大厦,数不清的宏观叙事沦为文字垃圾。
完成民族志需要依赖大量参与观察的实地田野调查,强调长期对文化脉络的深度检视。以民族体育中占主体的武术研究为例,过去往往过于依赖并不详实的史料记载,理论依据则多在传统文化哲理中寻觅附会。然而,中国古代的正史记载历来注重典章文物而不屑于雕虫小技的传统,难免遇到丝毫不见具体武艺内容蛛丝马迹的窘境,也常因牵拉阴阳五行、周易八卦古代名人为源头被学界质疑。其实,对于大量在明清以后才逐渐成形并流传至今的拳种,老老实实做田野调查,参与观察一招一式,深度访谈来龙去脉,认认真真写民族志,才是研究的基础和正途。近年来,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中,仅从编造传承谱系的角度而不从动作特色进行分析去辨识真伪,也难免涌现假冒伪劣的“古董”。
人类学作为研究民族传统体育最适宜的方法,在大量阅读经典尤其是民族志的基础上,田野中的感性体验才能激发灵感。但由于缺乏专门技能训练和浮躁心态导致的急功近利,一般体育研究者很难去阅读自认为与己无关的民族志。即使民族体育活动的研究者认真仔细阅读了相关研究对象的民族志,往往也得不到自己所需的直接描述材料。因为,身体运动并非记载重点,一般的民族志并不一定把该民族的传统身体游戏统统记录在案,即使有零星记录,也不一定详尽。民族体育研究者大多需要前往实地考察,通过自己亲自投入田野调查获取真实经验,对于书本知识重新进行理性过滤,再撰写专门的民族体育志。
当前,民族体育研究工作中最缺乏的是真正、完整的、详细的民族体育志。西方体育进入中国是一种文化传播和文化变迁,但同时也是对中华民族原有的养生保健体系的破坏。东方文明中的养生保健精髓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要使其现代价值重现或博采众长建立新的体系,就需要还原传统的真实风貌以作为参照系。完成描述传统身体运动文化的民族志,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基石。
过去在不了解人类学的情况下,把看到或听到的传统身体活动形式记录下来,再通过访谈相关人员了解来龙去脉等背景材料,拍几张照片或录像,最后回到书斋查阅相关历史记载归纳成文,是体育文史工作者挖掘整理工作的常见模式,虽接近田野调查,却并不规范。这种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直至90年代初,国家体委文史委员会开展全国性民族体育挖掘整理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成立了体育文史办公室,自办刊物,印刷材料,轰轰烈烈工作了十余年,最终成果是编了一本《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这本代表官方民族体育研究的最高成果,付出了千百人的数年辛勤劳动,是对全国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活动的最全面的空前规模的总结;但从学术价值的角度来看,它仅仅是一本对各种项目汇总的花名册及简略描述的资料集,并没有多少“田野调查”的研究成分,更谈不上理论的生成,更像是一部可以按图索骥的目录。
在这之后,许多单位和个人的民族体育研究成果大都只停留在某些项目整理与活动描述的表层,与真正的民族志相距甚远;部分研究者仅从历史的角度或贴上文化的标签来解析民族体育活动,但悬浮于现实生活之上;仅有少数研究者注意到把民族体育研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结合起来,开始注意到田野调查的重要。
实际上,每一项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民族志”,就是一份详细的综合性调查报告。这是在搜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分类整理,认真分析而形成的田野调查成果,以叙述为主,文字要求朴实无华,准确无误。做好田野调查,在此基础上写好调查报告,是完成民族体育志的起点,也是体育人类学研究的起步。
对一项传统项目,如果迈过像民族志那样的详尽调查,盲目进行加工改造,其灾难性的后果往往是难以逆转的。“当前,我国大部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都是从综合仪式系统中分解出来的独立个体,他们的发展路径是从综合走向分化,也就是说,这个自组织结构系统已经瓦解,价值标准当然也随之瓦解。我们不得不忧虑民族传统体育的未来发展,路在何方?……为什么从民间分离出来的项目在新鲜了两天之后,人们就觉得它不好玩了,没有意义了呢?调查结果显示,发挥解析后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破坏了系统的目标达成、适应、相互整合和潜在维持的模式,更确切地说,就是分化解析后的民族传统体育变成了一个纯粹的身体活动或竞赛,不符合村民的审美习惯。”[22]当然,研究成果不能止步于民族志,如果仅仅是资料堆积,或是对本土知识的过度解释,对所研究项目的未来发展并没有提供具体路径,这是虎头蛇尾的结果。这样的缺陷,需要在对特殊现象的系统观察与概括的基础上引出结论,并拓展为参与式发展的后续规划来弥补。
4 文化相对论与体育文化的比较
田野调查在体育研究中的主要目的并非仅仅是撰写民族志,而是验证假说形成理论并固化为知识。“严格地说起来,用比较法作推动一种知识前进的工具,虽是最有效用却是一件最吃力的事。从第一步说起,所用的材料必需要同样的可靠。”[13]田野调查中的参与观察带来的主客位互换的“他者”研究视角,带来真实的第一手材料,而在反复的比较中,文化相对论的萌生是水到渠成之事。人类学家们多年的田野工作成果积淀为大量的可靠的调查资料,文化相对论使长期处于边缘的非主流文化五彩斑斓地呈现于人们的眼前,引导人们用客观的价值判断来验证假说,最终获得正确的认识。
4.1 文化相对论与体育文化研究
美国人类学大师博厄斯反对用进化论简单的单一进化模式来解释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提出历史特殊论与文化相对论的观念,认为世界各地许多相似的文化现象实际上都有其各自发展的历史线索,各民族的文化价值是平等的。因为,衡量文化没有绝对的评判标准,任何一个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人们不应该用自己的一套标准来衡量其他民族的文化。这种观点批判了那种将各族文化按某个进化序列排队并侮辱嘲笑所谓不发达种族或民族的做法,有力反击了以欧洲为中心的种族主义,为倡导体育文化的多元,尤其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和价值评估提供了方法论利器。文化相对论作为一种研究文化的态度,促使人类学形成了关注和同情边缘群体、立足本土文化的学科特色,成为整个人类学的学科理念。这在对待相对弱势的民族文化,特别是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时尤为重要。不同体育民族志的诞生,让我们不能不面对文化多样性的现实,接受文化相对论的合理解释。
文化相对论用平等的视线看待陌生文化,对于认识不同民族的身体运动很有价值。例如,现代奥林匹克竞技项目几乎都是西方文化的结晶,如何挖掘东方,特别是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的潜在价值,需要用同是人类文化组成部分的客观态度来评价东西方文化。这样的研究需要文化比较。
毋庸置疑,文化要素中最有活力的部分是精神文化,其中,最重要的是被社会全体成员共同接受和遵循的核心价值观。人类身处于这个核心价值观引领的文化环境之中继承和积淀传统文化,体育事业的发展也依赖这样的积累和创新。人类历史上的各文明古国,只有中华文明作为文化主体保留至今,其核心价值观必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体育人类学必需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国体育的影响,必需以此精神文化的观念层面作为体育文化的基础和重点。
在体育人类学看来,体育文化的研究对象理应以民族身体文化为基础。文化是一种借助内聚力来维护社会、团体和个人本体身份的连续过程,包括传统的身体运动,其基础单位是民族。现代进化论者已经超越了达尔文把个体作为生物进化基本单位的观点,把群体作为进化的基本单位。因此,对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以民族为单位,即研究民族的文化,包括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按照北美的学术传统,狭义的文化人类学几乎可以等同于民族学。体育文化研究,主要应指向民族文化对体育运动的关系。文化相对论要求研究者客观地看待被研究的对象,从被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待被研究者的文化,这对于研究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恰如余秋雨先生所言,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以及与此相呼应的生活方式,它的最终成果是集体人格。何谓中华民族体育活动中的集体人格?这或可成为我国体育文化研究的聚焦点。
以往的体育文史研究,大多站在各自民族文化的立场,从整理历史文献资料的角度来揭示文化差异;当体育史研究成熟到探索的触角几乎穷尽到所有角落时,从“文史”转移到“文化”,其注意力必然集中到国民性格对开展体育活动的影响上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中国特色的体育道路,这个“特色”从本质上讲,应该是中华民族自身文化的特色。当代体育往往由西方文化强势主体的一元垄断,需要改善成一元为主的多元共存状态,以主流文化为平台对各种文化进行吸纳与整合。现实里,中华民族的身体文化在那屈辱的年代早已被西方体育文化碾轧得七零八落,体育文化研究者必须花很大的力气加以凝练重构,才能使其进入到中国体育的核心价值观层面,成为多元中的一元。[3]
在文化理论的演变中,普世性和相对性始终交织穿插。如果说,文化相对论隐含的不足,主要在于忽视了历史进步的标准,认为诸文化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无前后之别,容易导致否定人类诸文化的统一性和发展的大趋势。不过,这在民族体育的基础研究中尚无明确显现。
4.2 体育的文化比较是为了展示差异与多样性
人类学源自对于“异文化”的研究,既是“透过了解别人来了解自己”,也是“离开自己以便更了解自己”。在西方体育文化传入中国一个多世纪后,中华民族自己的传统身体文化甚至对大多数国人而言也成为了一种“异文化”。
按照人类学的观念,文化常常指一个民族的特定生活方式,它需要多样性,也应该多元。人类学往往通过带有丰富想象力的“他者的眼光”去阐释历史、文化和社会,跳出了固有“科学知识”的束缚而提倡跨文化语境下的“地方性知识”。当今的文化人类学主张平等对待所谓“先进文明社会”与“落后原始部落”,视两者为仅是形态之别,非性质之别;努力了解个别社群的特殊性,但目的却是在于增进对人类普同性的掌握;即使以研究个别社群的共时性(synchronic)结构为主,也并不会忽略殖民化和全球化所引起的历时性(diachronic)变迁。这提示我们,人类的身体运动实际上也在文化上呈现多样性,对于自己不了解的身体文化切不可简单否定。
文化比较的方法的使用,其目的是通过不同文化的民族志资料的对比和交叉分析,来探讨人类包括体育在内的各行为模式的相似性和差异性。通过这种比较分析,可以建立并检验假说。这有些类似关系研究(relational research)揭示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间的关系,往往需要采用统计学的技术,特点是获取素材后并不操作控制可变因素。
文化比较研究,是利用不同文化为样本,用真实的资料做比较研究,以便验证对人类各种行为的假设。文化比较研究可以使研究者发现更多的人类行为,以免去身处单一文化狭窄范围的局限。在中国本土的体育研究中,人文学者尤其不能苟同体育文化的单一性和同质化,在接受伟大的奥林匹克文化的普世价值的同时,却不能眼睛只盯着奥运会把整个国家的体育发展目标孤注一掷于“奥运争光”,更不能被那几枚金牌死死绑住而放任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持续下滑,而应该以文化多元的目光维护体育在不同领域开展的多样性。体育文化比较需要努力了解不同的体育模式并加以对比,特别要珍视自己传统文化尚未发掘的普世价值,避免“灯下黑”,在厚重积淀的隐秘深处挖掘宝藏,作为素材在未来创造出更适应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兴体育模式。
文化比较研究的基础来自于民族志调查的资料,人类学家通过背景构架来进行分析解释,如马林诺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岛调查时,把该岛的生活和文化当作整体的和相互联系的单位来考察。
文化比较研究的型态,第一种是不同案例的差异比较研究;第二种是针对同一个衍生现象的各种不同变异型态而进行的可控比较;第三种则是跨文化研究,即在一组案例之中,进行抽样比较。前两种方法常用且好理解,而第三种方法在我国体育界屡屡提及却很少使用。
文化相对主义的局限性,需要通过跨文化比较加以评估,使其真正价值得以充分认识。跨文化研究并非仅是通过一般的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中检视在某些社会之中的相似特征,而是运用一组充足的样本,因此可以运用统计分析,针对需要探讨的问题,分析在几个特质之间究竟是具有关联性或欠缺关联性。
4.3 证明假说的跨文化比较
体育人类学在提出假说、分析资料并建构体育文化理论时,涉及到人类学研究的另一个传统或精髓——跨文化比较研究。跨文化研究是两个或更多的社会间的比较,也称泛文化比较或全文化研究,是人类学及其姐妹学科(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的一项专门方法,运用来自许多社会的实地研究资料,检视关于人类行为及文化的假设。跨文化原来是通过比较世界上各种不同文化样本来验证人类心理和行为特征的心理学研究方法。例如,以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劳动方式等均不相同的民族为样本,搜集资料,进行文化间的比较,研究他们之间在心理和行为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称跨文化心理学。近年来,这种方法的主要进展是联合使用两种类型的统计分析方法:一种以文化特质为分析单位,一种以社会或部落为分析单位。目前,跨文化比较法的局限性是还没有明确可分析历时材料的统计方法,也就是说,还无法将历史内容与统计模型结合起来[18]。
可以说,希罗多德是最早的跨文化研究者,他在名著《历史》中比较和分析了古希腊的文化。英国人类学家泰勒1889年发表的《制度发展的调查方法》是先驱性的跨文化研究报告。后来,在摩尔根的著作《古代社会》里,跨文化比较被进化论用来排列社会阶段。但这样的比较是依据偶然的选择而非样本,结论不能在统计意义上被广泛验证。20世纪初,跨文化研究被研究文化的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所广泛采用,代表性的研究如英国心理学家 W.H.R.里弗斯对印度和南太平洋居民的感觉和知觉所作的定量分析;美国社会学家W.G.萨姆纳对个人或团体满足需要的功能起源于风俗习惯的研究等。
跨文化的研究方法曾遇到一些波折。这就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对泰勒的跨文化比较表示的质疑。高尔顿认为,广泛分布的跨文化样本单位之间的相关关系可能反映功能关系,也可能是文化的传播和继承关系,共享历史的社会可能存在历史渊源关系,因而不能比较。这个争论后来成为著名的“高尔顿氏问题”,导致系统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踟蹰停滞了大半个世纪,直至默多克(George P.Murdock,1949)恢复这项工作。[9]
当代的跨文化研究始于默多克,他在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关系研究所设立了许多个基本数据库,从事民族志资料的广泛搜集和分类,包括1949年建立的《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与《民族志地图》(Ethnographic Atlas)。他携手道格拉斯·怀特(Douglas R.White)发展广为学界所用的《标准跨文化样本》(Standard Cross-Cultural Sample),目前系由开放获取的电子期刊《世界文化》(World Cultures)负责维护。以前虽然利用背景材料进行有限比较,但存在分析结果缺少广泛代表性的不足,导致大规模的统计比较样本资料库的建立,特别是“人类关系区域档案”建立后,系统的交叉文化分析更加普及[25]。当时,从事文化与人格相关的跨文化研究的学者还有B.马林诺斯基、M.米德、E.萨皮尔、R.林顿、C.克拉克洪等。20世纪60~70年代,跨文化研究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为:一是,将电子计算机用于跨文化研究,因而能处理大量的数和复杂的统计分析,C.E.奥斯古德等人的《感情意义的跨文化普遍性》(1975)一书就是一个代表;二是,跨文化研究方法水平的提高,这可以R.布里斯林等人的《跨文化研究方法》(1973)为代表。20世纪70年代以后,有不少文化分类研究,并根据这种划分进行跨文化研究,主要目的是对与文化相关联的心理和行为特征作假设检验,以揭示其相互作用。尔后,研究者更多地使用精密的统计方法,以控制“高尔顿氏问题”以及宗教多样性和群体意义等问题的产生。目前,华南师范大学的体育学博士生已经使用《人类关系区域档案》这样的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以丰富自己的学位论文。
跨文化比较通常是在一个地区的几个群体之间的有限比较,比较对象具有以下特点:有许多文化和社会的共同特征;少量的差异;保持大量背景材料。
典型的跨文化比较案例是纳德尔对非洲巫术的研究。他在四个非洲社会中做了田野调查:两个在西非的尼日利亚,两个在东非的苏丹共和国。其目的是要建构和检验关于巫术的意义的假说的基础。这一假说就是“失败-攻击”假说[8]。
对体育研究而言,选择的跨文化比较方法主要是为了证明某种身体运动文化演变的假说,材料多来自于民族的习俗,尤其是文化心理部分,自己亲身做田野调查的材料更加弥足珍贵。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是跨文化比较的研究目的应该明确。换言之,事先需要设定一个有价值的假说,跨文化比较之后的结果是检验这个假说的真伪。例如,黔东南独木龙舟与其他龙舟对待“龙”不同心态的跨文化比较结果,成为印证“竞技的起源早于体育”这一理论假设的实证过程的组成部分。
5 具有“类”意识的参与式发展评估
康德认为,人类学如果仅仅包含广泛知识还不能真正称为实用的,“而只有当它包含作为世界公民的人的知识才能如此”[10]。面对体育研究文化,绝不仅是为了哲学思考本身,也不能从概念到概念,而是为了用体育运动来提高生活质量,是为了造福人类的应用。文化相对论有助于体育文化的比较评判,但最终要触及人的“类”意识。这是因为人类需要做出行动上的共同选择,就得从文化目的出发,即考虑某种文化类型是否有利于人类的发展,从这样的角度来进行思考和价值判定。尽管存在诸种差异,但人类毕竟是同一物种,有和谐相处的共同价值观,因此,在理论生成中,需要倡导尊重普世价值的“类”意识,把积极向善的人文精神融入理论构建。这样,才能弥补文化相对主义的欠缺。
5.1 理论生成——从结构、功能到深描、解释
田野调查的重要结果是理论生成。在初期的研究中,体育人类学受到功能学派的影响,发现大量田野调查结果表明许多原生态身体游乐活动并无体育意识与健身功能,将其视为“传统体育活动”系无依据的随意判定。中国研究者实证了“竞技早于体育”的假说;提出新世纪体育的社会功能“从生产到生活、从群体到个体、从工具到玩具”转变的观点;对“举国体制”的剖析,采用了“结构-功能主义”的范式。大量“体育文化”研究,也多是从器物、制度、观念的框架模式,从横向平面的结构层面来梳理相互联系的方式,这是很多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研究者所熟悉的。功能学派领军人物马林诺斯基在中国的影响持续至今,体育界不乏推崇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者。
20世纪60年代末,马林诺斯基的日记在他逝世后被发表了,似乎给人类学界带来了一场地震。这位人类学家私下对当地土著民族的歧视语言里充满了愤懑与牢骚,与他生前发表的民族志中表达的田野工作中的愉快和对土著民族生活的赞扬形成鲜明对比。这就使人类学民族志的真实性和田野工作的可靠性均受到了来自学界内外的质疑。人类学研究要往何处去?人类学究竟应该把自己定位为有一套明确评价标准的社会科学,还是因为达不到纯粹的客观性而变成一种观察和描写的艺术?方法的革命开始了,各种新的民族志写作方式如雨后春笋,人类学者纷纷在其研究中探索着不同以往的新路。格尔茨的著名论文《深描:迈向文化的阐释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格尔茨的论文是对人类学研究方法思考的新成果。他借用了赖尔用于心理学的“深描”一词,来表达对民族志的写作新要求。格尔茨尝试借助于自然科学模式建立一门人类学解释科学:“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的民族学。”对文化的真正解释工作,或者说民族志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深描。格尔茨对各领域学术界产生广泛深远影响的《地方性知识》一文,是对人类学创造性贡献的一大亮点。它使研究者可以把社会文化现象纳入到地方性框架中去解释,得出了与所谓的主流观点不一致或者说是大相径庭的结论。
在当代人类学研究中,“深描”作为一种阐释人类学理论产生广泛影响,使得被研究者的观念世界、研究者自身的观念世界、阅读者的观念世界在此间达成一种“视界融合”,生成一种“不同理解”,创造性地抵达被解释事物的本质深处[24]。格尔茨建构了文化解释理论,他在明确文化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分析文化是对文化行为进行深描,最基本的特征就是解释,这种民族志有能力揭示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2]。“深描”使文化研究方法获得创新,成为与跨文化研究一样与心理学有密切联系的视角与方法。
体育人类学可以学习和尝试采用这种理论,但要注意到其缺陷和不足。“既然深描是一种对文化的解释,那么,深描和浅描的分界点在哪里?何以评估一个民族志是深描还是不是?深描会不会变成作者的主观想象而与实际分离?对一个以解释为己任的科学,这些问题也许并不一定要回答,因为,它们都是格尔茨所否定的实证科学模式下的问题。但是,格尔茨在其文本中认为,解释人类学是可以成为一个有标准、可以检验的科学的。然而,遗憾的是,格尔茨在文中只是不断地否定各种可能的检验标准,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他的检验标准具体内容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不知道一个具体的文本是否达到抑或超过了深描。”[11]笔者根据在印尼巴厘岛的亲身体验,认为格尔茨描写的著名的“巴厘岛斗鸡”并非体育活动,是一种动物竞技的游戏,与当地男性在热带慵懒悠闲的自然环境与生活方式有关;没有发呆亭,可能也就没有斗鸡。在原生态体育活动的研究中,忽略其环境等基础物质条件而对其传统文化习俗心理的过度“深描”,可能难以获得准确的价值判断。
当前,体育人类学研究大多属于基础层面的资料采集工作,更高阶段的研究尚未成熟和展开,大多只需要展现真实全貌,往往还涉及不到太深奥的理论,因而,实证在现阶段更加重要。对理论的借鉴,首先应该是以真实情况的田野调查资料的实证分析为基础,尽量客观呈现研究对象的文化现象,然后才谈得上阐释。譬如,对体育运动形式的萌芽和凝聚,原始宗教尤其是巫术仪式如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等,还没有多少达到真正民族志水准的现成资料,尚需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去实证,单靠在书斋里冥思苦想拼凑资料,是难以得到令人信服的结果的。
5.2 从古典进化论到发展人类学
以往人类学的主流为古典进化论左右,体育界受“落后就要挨打”观念影响,对高水平竞技尤为倚重。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其诞生之初作为一种假说被提出,从19世纪以来时至今日,几乎变成一个公理,只能无条件接受。进化论的伟大在于:揭示了地球上的生物是在适应生存环境变迁的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异的,尤其是生命进化的前期,如果不能随着环境的变迁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则将遭到“优胜劣汰”的灭绝。不过,达尔文的进化论强调生命的进化的同时却忽视了在演化中的衰退方面。况且,进化这种针对自然的说法,似乎不宜照搬于需要人文关怀的社会文化领域。
一个多世纪科学研究的新发现,暴露了古典进化论自身的缺陷。在自然科学方面,现代基因学和遗传学诞生后,对生物的基因及分子水平有了崭新的认识,简单观察的同源器官的相同形态可能对应于完全不同的基因。生命物质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被进化论者回避了。古生物学凌乱的化石证据至今并未显示有物种间过渡类型的存在,人为按进化论组成的单线性谱系漏洞百出,得不到一个统一的结论。寒武纪生物大爆炸在短短的几万年内,几乎现在所有生物的门同时出现在地球上的现象是进化论不能解释的。在《物种起源》发表之际,达尔文自己也曾说:“只有人类的进化,怎么都不可能用我的进化论来说明。”的确,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人类的进化太快了,从20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到5千年前的现代人类,人脑容量迅速膨大;而现代人类产生后,进化又仿佛突然消失了,人的脑容量几千年来基本未变。这个考古学的证据也动摇了进化论。
达尔文的进化论在生物学科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斯宾塞提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忽略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差异,把生物学中概念引进社会学,进而认为寻求到社会发展的规律就是生存竞争,这直接干扰了人类对包括体育在内的很多社会行为的人文判断。与斯宾塞同时代的赫胥黎提出“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被广泛推崇为社会发展甚至暴力革命的理论依据。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以上升时期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时代风潮作为支撑点的,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转型,人们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虔诚信仰开始产生动摇与狐疑[14]。这是一种持强凌弱的“社会伦理”。近代受到侵略和奴役的弱国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以激励自己奋起反抗,无可厚非。中国体育作为“强国强种”的工具从西方学来,又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的熏陶,使体育等于竞技、强健是为了争斗、金牌代替健康的观念风行于社会,产生出“奥运争光计划”作为改革开放的体育旗帜,有其理论根源和历史的必然性。
古典进化论遭到一些学者的批判,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种理论将世界上各种文化按照某种等级进行高低贵贱的划分;而人类学的文化相对论则认为文化没有高低之分,各种文化都是平等的。问题是,文化固然不分高级与低级,但文化对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不同人群的作用是有差异的。以运动技术水平的高低彰显意识形态优劣,以金牌多少暗示民族贵贱,这不能不说是古典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体育观念带来的负面后果。古典进化论只是片面强调前进演化,没有看到进化中存在着衰退;科技进步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的便利的同时也存在负面影响;人类在经济的繁荣中忍受环境的恶化,在金牌的争夺中忽略了大众的健康;人类社会各群体的交替发展,现实与达尔文学说的“优胜劣汰”的直线竞争发展相悖,当代具有后发展优势的“金砖国家”各领风骚的现状已颠覆了“优胜劣汰”的单线进化观。就连体育竞技领域的胜负,也不能成为用来嘲笑弱者的工具。
今天,中国已把发展生态文明提升为国家目标,体育转变发展方式,应该进入生态文明的行进轨道。因此,展开对民族体育活动原生态环境的数据采集,对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意义重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必也不可能在所有的竞技运动项目的比赛中拿金牌;退一步假设,即使拿光所有的金牌又怎样?对中国体育文化的研究,应该立足于文化如何促进中华民族身心的全面可持续发展;更多地接受生态人类学的理论来推行当代体育的生态化,就是利大于弊的途径。
近代中国比西方落后得太多,这是历史事实,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得比任何国家都快,这也举世皆知。中国人不会在西方的道路上亦步亦趋,在政治、经济、文化甚至体育上都可能有自己的发展道路。我们接受西方体育中具有的科学价值,是为了更好地走自己的路。对中国体育而言,发展也是硬道理。体育人类学从进化论中汲取了营养,把自己学科进展的视野转向发展人类学。
发展人类学 (Development anthropology)是将国际发展与国际援助视为主要研究课题的应用人类学的一个主干分支。发展人类学家同样以田野工作为主要手段,在此基础上获取地方性知识和经验,分析判断不同文化与发展的关联程度,从而提供可资决策的信息和建议。人类是大自然中的同一个物种,不同的国家需要互相帮助以求共同发展,体育人类学研究者更清楚这一点。体育人类学的研究主张认真分析人类的身体在自然界发生的不可逆转的变化,在有了“劳动”以前两足直立行走人体的结构形态已经不同于任何动物,由此产生了任何动物都没有的体育萌芽。体育人类学从劳动方式的变化中分析经济发展与体育成熟的关系,得出“从生产到生活”的结论,也是纵向研究当代体育社会功能转变的结果。难怪发展人类学家纳什将田野工作重新定义为“参与观察和广泛发动的结合”[26]。无数个体联合成家庭,再构成不同的民族和社会形态;在遥远的未来,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趋势,将实现全球化的整体联合。而未来的体育方式,倡导生态化户外运动休闲的参与式发展,为了人类的美好梦想,必然是全球性、整体性发展生态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5.3 借鉴发展人类学的PRA方法
体育学从整体看是一门应用学科,其理论生成的依据,必须是基本的事实。适用于所有人的体育规律解析,是最有普遍意义的体育理论。如何掌握必需的技术手段,动手获得体育研究的新成果,是每一位真正的研究人员面临的头等大事。
20世纪70年代,人类学理论已经有相当的积淀,如结构主义主张任意的开放式采访;文化唯物主义的主客位研究法强调了研究对象和研究者的两种视角的不同;解释人类学注重地方性知识与当地人意见;情感人类学强调了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相互理解和相互交流的重要性等。面对世界各群体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日益严重,发展人类学家提出了“参与式发展”理论,随之,人类学便进入了促进人类共同进步的新年代。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一些主要的国际援助机构的援助重心和发展重点的转移,参与式发展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真正蓬勃兴旺起来。国际组织在中国所资助的项目,也通过参与式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从而也就引起了人类学研究方法从参与观察到参与发展的转变与认同。
参与式农村评估(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简称PRA),作为针对某一特定区域的微观方法,强调共同参与、尊重当地人和互相分享知识的工作态度,增强了当地人的参与意识,用当地多数人的标准来评判事物,说明获取信息不只是研究人员单方面的事情。PRA弥补了传统的调查方法(如参与观察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等)的不足,被调查者不再处于被动的地位,而是研究的合作者和实施者,焕发了被调查者的积极性和自信心。PRA方法为被调查者提供了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交谈的途径,非常有助于建立调查双方的良好关系。[23]
PRA作为一种快速收集农村信息资料的新方法,在世界范围被广泛应用于农村发展项目当中。20世纪90年代,参与式农村评估被引入中国,主要应用在一些国际发展援助项目的规划、设计及实施中。实践证明,较之传统方法,参与式农村评估具有难以比拟的优势,因而逐渐被广泛认可。目前,我国几乎所有的国际发展项目,尤其是农村发展项目中,都要求应用参与式方法。体育人类学学习这种方法,可以使过去对研究对象“是什么”的简单外表描述,转向“这么办”的发展方向性的应用路径设计,而且,在形式上的最大获益,是快速完成调查以缩短周期。
大多数情况下,参与式农村评估(PRA)的采用往往是由外来的工作人员发起的。但运用得当时,能促使当地人自己担当起评价、分析、实施、监督和评估的工作。PRA工作的核心,全过程都强调当地人的参与,需要真诚和广泛地听取农民的意见;在工作中注意尊重社区成员,对社区成员的表现感兴趣;谦虚而热情地鼓励社区成员的表达,耐心听取意见,忌用自己的观点诱导或打断对方,从而使结果更易于被接受并具可操作性[21]。这一点,使体育人类学在研究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时得到重要启迪,对于东方文明原生态身体活动的研究,尤其是身体运动的非物质文化保护与传承尤为实用。
体育人类学学习PRA工作的基本流程:应该根据项目计划确定工作目标,然后,组建包括项目相关各学科专家的工作团队,出发至目的地深入田野,与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以及原住民一起展开调查,了解原住民需求并根据这些需求确定项目计划,经原住民确认后加以修订,最终确定项目计划。实施项目并确保原住民继续参与并分享利益,一段时间后,再根据需要回访确认。
这种方法在体育人类学中的应用,形式上最大的好处是快速高效,而实质上不仅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保护,还能与原住民一起对民族身体文化的传承共谋发展,更有利于体现民族体育的多样性的人文价值。不过,PRA方法主要用于基层的经济发展,而体育人类学面对的往往是原生态的文化传承,不能完全照搬,尚需改良创新才可以在实践中发挥最佳作用。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体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尚处于探索阶段。在准备充分的体育人类学大规模综合性研究中,有些案例已经开始把多种方法聚合在一起加以尝试。譬如,研究身体运动对原始文化形成的影响,选择的最佳对象是居住在中国西南横断山脉“氐羌——藏彝走廊”上的各族人群,采用生态人类学的观点,以进化论的视角从体育与宗教的萌芽中纵向探讨身体运动在原始文化中的作用,通过巫师的“东巴跳”到东巴舞谱记录再到对东巴文字构建将产生一系列研究结果;按结构学派的技术路线,对邻近的类似图画象形文字如达巴文、沙巴文、古彝文、巴蜀图语及至甲骨文的比较,可以使用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而创新的动作分析法对于其中典型身体动作进行文化符号的“深描”,有望揭示人类日常的身体运动在特殊的生态环境中对原始文化的形成的作用。如果体育人类学的身体运动对原始文化形成的研究案例延续和扩展,其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难以估量,甚至可以延伸到世界范围的原始巫术形成、艺术萌芽、古文字起源等重大研究领域。这是体育研究对外辐射的创举,不仅超越了某一个群体的局限而倡导“类”意识,并且,把理论构建的触角伸到为人类探索共同文化财富的创新领域,其成果的学术价值可以升华到以往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无法企及的另一个无限宽广的层面。
6 结语
体育人类学不是一种漂浮玄虚的元理论,也不是一种局限于狭隘变量分析的单纯技术工具。它集中融合了自然科学与社会学科、定性与定量研究并重的综合优势,强调在特定真实的背景下了解各种身体运动文化现象,采用亲临实地收集第一手资料的研究范式,并预设假说进行严格的实证设计,按预定程序采集数据以验证研究结果,最终面向可以应用的实践领域。
体育人类学的研究针对具有重要价值的真实对象,认识客观事实,给人们提供实在、有用、确定、精确的知识,揭示客观现象的内在构成因素及相互之间的普遍联系,所得出的结论具有客观性,并根据经验和事实进行检验,追寻具有科学分析过程的理论生成。
相对于其他研究体育的方法而言,体育人类学的基本方法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个方面是秉承人类学深入实地的田野调查传统,根据体育研究的需要认真采用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的形式,因体质与文化相结合的多学科集中介入身体运动的专题调查而使周期大为缩短。
第二个方面是对身体运动效果及生态环境的测评,在文理融通的综合应用中选择符合体育研究的特色技术路线,进行具体方法手段的创新。譬如根据原生态身体运动研究的实际需要,在人类学的语言结构理论启迪下,把本是运动生物力学的动作分析法改造为身体动作文化符号分析法、拓展来自影视人类学的双机位动作拍摄技术等。
第三个方面是倡导在实证的基础上构建民族体育志,通过文化比较与体育活动的参与式发展的结合,推动不同民族的体育事业更好发展。借鉴发展人类学的精髓,促进人类身体文化的多元和谐共生,构建通过分享运动的新型体育发展方式。
21世纪是东方文明崛起的世纪。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释、道均以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最高价值的精髓,可以为发展人类学拓展更高的境界。古老的东方文明或许是克服愈演愈烈的社会问题和生态危机的良方,也可能为人类发展身体运动提供更明亮的航标。中国的体育人类学研究者正试图用生态和科学的和谐发展方式,为人类的体育事业谋求一条和谐发展的正确道路。
[1][美]理查德·M·勒纳(Richard M.Lerner).人类发展的概念与理论[M].张文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570,568.
[2][美]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3]胡小明.胡说体育文化[J].体育学刊,2010,17(3):1-6.
[4]胡小明,陈华.体育人类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
[5]胡小明,杨世如,夏五四,等.黔东南独木龙舟的田野调查——体育人类学的实证研究(一)[J].体育学刊,2009,16(12):1-8.
[6]胡小明,杨世如.独木龙舟的文化解析——体育人类学的实证研究(二)[J].体育学刊,2010,17(1):1-9.
[7]黄平,罗红光,许宝强.社会学人类学新词典[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8][英]J·D·Y·皮尔.历史·文化与比较法——西非之谜[J].颜勇译.贵州民族研究,2001,21(2):162-178.
[9]金龙云,董小川.西方文化史研究的视角与方法[J].历史教学问题,2008,(1):23-27.
[10]康德.实用人类学[M].邓晓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
[11]澜清.深描与人类学田野调查[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46-49.
[12]李志清.乡土中国的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13]凌纯生,林耀华,李济,等.20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2,75-80,81.
[14]罗秋立.历史唯物主义人类学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批判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5]培根.新工具[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8.
[16]滕星,巴战龙.从书斋到田野——谈教育研究的人类学范式[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2(1):19-22.
[17]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3.
[18]吴泽霖总纂.人类学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156.
[19]向有明,向勇,韩海军,等.身体动作与文字形成的双向实证研究[J]体育科学,2013,33(8):57-63.
[20]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M].周云水等译.香港: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9.
[21]张实.参与性农村评估在民族调查中的意义及运用——以云南中甸形朵村为例[J].思想战线,2001,27(3):88-90,100.
[22]郑国华,何元春.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沉浸的影响模型[J].体育科学,2011,31(10):56-57.
[23]周大鸣.人类学田野调查实习(第四章)快速了解调查点概况——PRA[EB/OL].http://resource.jingpinke.com/de-tails?uuid=ff808081-22c93527-0122-c9360e8c-4922&objectId=oid:ff808081-22c93527-0122-c9360e8c-4923.
[24]GEERTZ CLIFFORD.Thick Description: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C.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M].New York:Basic Books,1973:6-10,18.
[25]MURDOCK GEORGE P,DOUGLAS R WHITE.Standard Cross-Cultural Sample[J].Ethnology,1969,8:329-369.
[26]NASH J.In the Eyes of the Ancestors[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