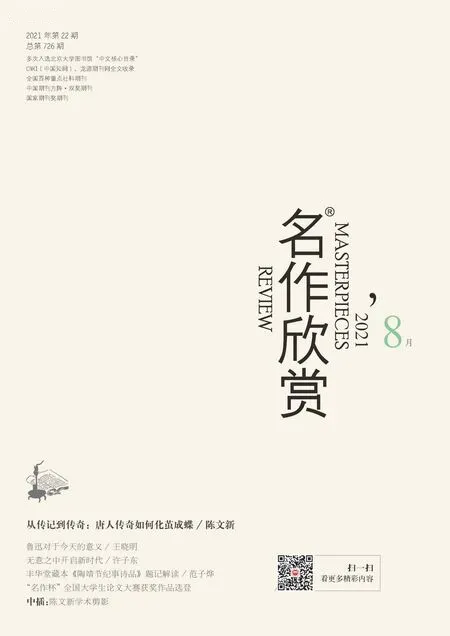历史与文学的错位与对视:李锐1970年代、1980年代的知青故事
/ 江苏_李旺
1988年李锐因发表《厚土》系列小说获得文学界广泛认可,这距离他发表第一篇作品已经十四年,1974年,李锐发表了革命故事《杨树庄的风波》,文首标明作者是蒲县插队知识青年。这是北京知青李锐插队山西吕梁地区的第五个年头,距离“文革”结束还有两年时间。《杨树庄的风波》讲述新上任的队长、年轻的共产党员李大海与前任队长、“阶级敌人”于得荣的斗争故事。在故事中,于得荣来自阎锡山的保安队,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反革命分子”,在更换队长之际,于得荣借穿中农张老满的一双大鞋偷盗队里的麦子,偷麦之后又将麦子藏匿在张老满家中,以此要挟张老满站在自己一边,与李大海作对。于得荣的反革命履历、调包计故事与革命样板戏《海港》钱守维的故事基本一致,这是当时主流文学评论号召文艺创作全面移植、学习革命样板戏的结果。故事的后半部,李大海营救张老满的儿子而置自己儿子于不顾,这让张老满幡然悔悟,这是当时争取中农政策的文学化图解,李大海勇战飞车的经历则显然有《欧阳海之歌》故事模式的遗传。不论是故事模式还是人物形象,都可以看出李锐受到1949年后党文学传统的深刻影响。这篇作品拥有李锐自己特点的方面在于,故事以山西农村妇女的对骂开始,李大海妻子和于得荣妻子你来我往,语言泼辣,新一任队长妻子没有沾上队长的党气,还可以拥有一些个性,这在“文革”文学中是较为少见的。
知识青年李锐不论他彼时的内心是否对这一运动——知青上山下乡,对于自己的经历——插队干旱贫瘠的吕梁山区有过反思,就当时他呈现的作品来看,他在“文革”文学的主流叙述中开始练笔,并以自己的作品论证了“文革”、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合法性。他的彻底反思需要再等十多年以后才得以发生。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从此,掀起了长达十余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①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贫下中农是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的好老师,一切有革命志气的下乡知识青年,都应当下定决心在农村扎根一辈子,革命一辈子,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②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知识青年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纷纷到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安家落户,踊跃地走上了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康庄大道。”③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股滚滚的革命洪流,猛烈地冲击了几千年来剥削阶级轻视农民、轻视劳动的旧思想和旧习惯,起了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巨大作用,密切了城乡关系,加强了工农联盟,对我国的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等领域,已经并将继续产生深刻的影响。”④
这是1970年代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高潮时期官方的论述,知青李锐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态度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与主流意识保持一致,包括“文革”结束后。
《杨树庄的风波》之后,李锐与王子硕合作发表了《东风吹来百花开——欢呼党的“十一大”胜利召开》,文章赞颂华国锋剿灭“四人帮”的功绩,以极其热烈的政治期待热情歌颂了“十一大”,并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繁荣兴旺的前景表达了乐观祝愿。此后的作品是《幸福的时刻》,文章缅怀周恩来去世,回忆1966年周恩来指挥中学生演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情景,文末以周恩来精神永存和以粉碎“四人帮”这一消息告慰周恩来结尾。《北京的来信》以一封被装裱在墙上的信引出故事。1972年,抗日战争时期民兵英雄马开旺丢失了残疾证明,于是给华国锋写信求助,希望当年的民兵队长华国锋给他写封证明信。华国锋回信后,全村人一片欢呼回忆起华国锋吃苦在前的光荣故事。文中有这样的描写:“打开信封,一股中南海的暖风,沁肺腑!摸摸信纸,华政委留在纸上的温暖,传遍全身!看看字迹,每一个有力的字体,每一个清晰的标点,如细针密线,把华政委和老根据地的人民紧紧相连!”这十分符合“四人帮”被抓之后,华国锋作为毛泽东接班人被全民崇拜的政治语境。其时,刊物封面、扉页、插页的画作和书写华国锋革命事迹的特写、通讯、散文蜂拥而至。这些颂歌作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方式:第一,“你办事,我放心。”主题重复出现,表达毛泽东“托孤”于全国人民的政治宣示。第二,关于华国锋的画作全部克隆毛泽东的着衣风格和手势动作、表情。第三,叙述华国锋在山西和湖南时期的革命事迹以及在全国各地的亲民故事,表现他已经经历革命的风吹雨打和为人民服务的忠诚。显然,作为插队山西的知青李锐也融入了这条政治洪流。
《脉搏》以女护士陈小娟的口吻讲述卫校毕业生在上班第一天遭遇的奇迹:钢铁英雄牛福海倒用体温计,佯装健康逃出医院回到厂里进行技术革新。牛师傅虽因急性肾炎双腿双脚浮肿,但技术革新终于成功。这类所谓土专家攻克高科技,排斥知识分子、工人至上的技术革新故事是“文革”期间大搞三大革命运动⑤、工业学大庆的产物。小说中护士长的一段话也体现了“文革”文学中最流行的修辞,以具体事物来象征宏大的主流话语:“我说的是一个老工人对革命工作的热心,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心!这是体温计永远也量不出的!你知道吗?”“文革”结束后,李锐并没有很快地走出“文革”文学的话语模式。
李锐与张石山共同署名的《两闯苍鹰峰》表现出较高的艺术品质。小说讲述太行机车厂车间主任孙亮顶住“四人帮”压力,公开招考司机的故事。在准女婿玉海的考试过程中,他严肃认真,用技术说话。在小说中,老孙与玉海在苍鹰峰上的对话生动传神,特别是老孙的语言表现出老司机坦荡勇敢的个性。老孙的女儿孙玉秀置身于父亲和男朋友之间,且又面临政治压力,小说对孙玉秀焦急的心情也刻画得丰富细腻。此后,李锐尝试过较多题材的文学创作,在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之后,他才开始摆脱主流意识形态的束缚。
在1970年代,可以代表李锐对于上山下乡运动、对于知青的态度的作品当属《扎根》,小说讲述知识青年杨新满腔阶级仇恨、立志一辈子扎根农村的故事。小说表现了杨新与贫下中农之间的深厚情谊,以及地主分子赵源财的万恶不赦。小说对知识青年与贫下中农深厚情谊的描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知识青年对农村的热爱与奉献;二是贫下中农对于来自城市的知识青年的重视,特别是对于来自北京的知识青年的格外信任与崇拜。1970年代李锐反复书写的这一切在1980年代被他完全颠倒过来,他在1970年代讲述的知青故事在1980年代遭遇彻底瓦解,上山下乡运动的神圣性化为齑粉。在《扎根》中,知识青年是为共产主义献身的一群:
咱革命青年图的不是上大城市,不是为名为利,而是跟着毛主席,一辈子干革命,扎根山区,把青春献给共产主义事业!
你听我说完。你听我说完,你想我能离开山区吗?现在我能放下贫下中农的印把子离开赵家沟这场激烈的斗争去上大学吗?这里的斗争都需要咱这些年轻人呀!六年了,贫下中农不光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亲人,我能甩开他们吗?
贫下中农对知识青年满是信任:
散会以后,老李留下杨新嘱咐了几句:“新娃,你是个新党员,又是个知识青年,往后办事多向贫下中农请教,只要跟群众拧成一股绳,啥事也好办。”
地主则是万恶不赦,所谓满肚子变天账:
土改以后,地主赵源财除了留给他家住的两间房子外,其余的财产被分光了,他恨得咬破了舌头。就在土改这一年,他在自家院子里栽了一棵小杨树,他给这树起了个名字,叫“记仇树”。从此以后,每天早起他都要把这树看两眼,遇到不称心的事,就拿斧子在树干上砍上一道,当做记仇记号。他想呀,盼呀,梦想有一天,这些翻身户们再倒下来,赵家沟再变成他耀武扬威的天下!
然而在1988年,在李锐的叙述中,这些都发生了巨大的逆转:
老以前,锄玉茭邸家给吃饸饹,山药蛋熬粉条子,管够。现在没有饸饹,也没有粉条子,只有队长豹子样的吼骂。
1949年后,由高玉宝小说《高玉宝》塑造的地主形象周扒皮、泥塑《收租院》塑造的地主形象刘文采、拥有各种文学体裁的《白毛女》塑造的地主形象黄世仁和《红色娘子军》(同样拥有各种文学体裁)塑造的地主形象南霸天,形塑了1949年后地主的存在肖像。这些地主形象完全颠覆了传统社会中乡绅在维持地方经济、文化统一方面发挥的独特作用。李锐在《扎根》中塑造的赵源财就是周扒皮形象谱系中的一个,但《锄禾》中的邸家则并非如此。地主时代有饸饹和山药蛋熬粉条子吃,消灭了地主的时代则肚腹空空。判断历史的对错是非并不简单,自此,李锐跃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压抑。
学生娃从队长手里接过那个旧纸筒筒,弄不大明白为什么新报纸总是被剪了鞋样子或是糊了墙;也弄不大明白,既是专门“开”给学生的语录,为什么总要由他这学生娃念给众人听。可是有那一分工管着,他还是要念: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算逑了吧,你也歇歇嘴。”
可以说,这声贫下中农的断喝不仅喝止了《锄禾》中的学生娃,也喝止了整个1970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十年青春在农民眼里无非是纸上谈兵。李锐1980年代的小说不再以一个知青的视角对上山下乡运动进行回顾,而是或以一个农民的视角进行感受性的讲述,这感受关乎饥饱、性欲(《眼石》《好汉》《假婚》),或以一个夹杂着审视者的冷静和在场者的热度的混合视角进行描述加分析式的叙述。这类混合式叙述是内心独白与全知分析,关乎苦中煎熬、关乎痛苦中的怜惜,甚至是一份有些畸形的温情(《青石涧》《二龙戏珠》)。那些隐忍者的悲喜歌哭都有着黄土的颜色,不是具名的,而是历史的子孙(《秋语》《看山》)。李锐1980年代反思历史最突出的思想贡献,是他写出了历史作为一种遗产对置身其间的人的影响力。
《厚土》系列中的《合坟》,讲述了原知青点的乡亲为一位牺牲了的女知青“合坟”的故事。这位为了学大寨而牺牲的女知青可以看做是殉情于时代的象征,农业学大寨是“文革”期间喊得山响的口号。然而昔日的政治口号远遁,纪念她的只有当地的风俗。牺牲的知青是历史政治的恶果,而祭奠她的却是历史的遗存,在小说中,历史的遗存与时代政治相遇时,虽有摩擦发生,老村长既口口声声反对迷信但又无不一一照办就是明证,但结果却是长久的历史抚慰了时代的牺牲者。小说中最为诡异的是《毛主席语录》在墓地中的留存,毛时代如同那本阴森森的墓地语录,在当代中国历史中留下烙印。李锐既看到了时代强权的疲软,同时也看到时代强权日渐作为一种新的历史的可怕。
李锐从1970年代到1980年代遭遇了剧烈的思想转变。1970年代李锐的知青故事完全复制主流话语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表述,与现实生活中知青的悲惨命运完全不符,是属于历史错位的文学写作。1980年代,李锐开始正视知青下乡,包括对自己下乡生活的自审,终于开始获得历史与文学的对视契机,完成了对自己1970年代的超越,也完成了一次对整个知青下乡运动的检视。《厚土》系列作品是李锐1980年代最富有思想深度的作品,同时也是整个1980年代文学重要的思想收获之一。
①1950年代中期开始,已经有城市青年学生被号召落户农村,但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从1968年开始。
②③《抓好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人民日报》社论,1970年7月9日。
④《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人民日报》社论,1973年8月7日。
⑤三大革命运动是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