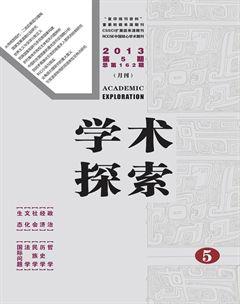世界主义与全球分配正义
刘明
摘要:在最近几十年里,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诸如全球贫困、世界环境、国际移民、儿童和妇女的国际人权等问题也日益受到学界关注。其中的一个主要反映就是,在政治哲学中,全球正义或国际正义问题日益成为焦点问题,并引起了激烈的分歧和争论。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世界主义作为一个实践哲学流派在当代得到了复兴。本文简要介绍了世界主义在政治哲学中的一些基本主张,并在此基础上批判性地考察世界主义者是如何辩护人权和分配正义的。
关键词:世界主义;绝对贫困;生计维持权;全球分配正义
中图分类号:D8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5-0020-06
“国际正义”问题自古有之,它是伴随着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跨国交往而出现的,“国际正义”关注的焦点首先放在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战争、和平、宽容等问题是其首要主题。而“全球正义”则是随着二战之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而提出来的,它将首要的关注点放在了全球范围内的每个个体那里,认为,全球范围内的每一个人,不论出身、国家、种族,在道德上都应该得到平等的尊重,都应该享有作为人的基本尊严。这正是世界主义者的基本主张。在这种意义上讲,全球正义问题与当代世界主义的复兴是相伴而生的。
一、世界主义的基本观念
称当代世界主义流派的出现是一种复兴现象,意味着,世界主义是有一个古代渊源的。世界主义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斯多葛学派提出来的,其核心主张是,每个人都是生活在世界共同体中的世界公民,相互之间应该平等地尊重和彼此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1](P39~45)。进入近代的启蒙时期,康德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永久和平论”以及“重提这个问题:人类是在不断朝着改善前进吗”[2]等论文中,较为详实地阐释了世界公民和世界共同体的观念,并认为,某种类型的国家联盟(staatskrper)以及世界公民观念是人类历史发展当中所隐藏的一个自然目的。[2](P15~21)康德在一种跨国界的全球共同体意义上来讨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国际人权问题,在这种意义上,康德实践哲学是当代世界主义的一个主要渊源。
不过,与斯多葛学派和康德这种一般性的哲学论述不同,当代的世界主义有着较多的现实针对性。正如上面所提到的,世界主义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就是全球化背景下仍然存在的大量绝对贫困问题,这使得当代的世界主义者尤为重视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互动模式对道德辩护的构成性作用,以及重视相关的制度问题和可行性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涛慕思·博格对世界主义的一个分类来进一步了解当代世界主义的特征。
在“世界主义”这篇文章中,博格根据正义原则评价对象的不同,区分了四种类型的世界主义:伦理世界主义、法律世界主义、社会正义的世界主义和一元论的世界主义[3]。简单地讲,伦理世界主义认为,正义原则的首要评价对象应该是个体行动者、集体行动者以及他们的相关行为,也就是说,全球正义原则的首要评价对象是个人、跨国企业以及国家这些行动者及其行为。伦理世界主义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它要求世界上的每个人和每个国家都关注全球正义问题和世界上每个人的平等问题,这是不现实的。
比伦理世界主义更激进的一种形式则是博格所提到的一元论的世界主义。简单地讲,一元论的世界主义将所有的对象纳入到对社会正义状态这一单一目标的促进之中,例如,它不仅要求世界上的每个人、所有企业和国家都关注全球正义这一目标的推进,而且还要求全球范围内的基本制度以及文化和风气都能够关注和参与到全球贫困的解决及全球正义问题中来。[4](P113~147)在博格看来,这种类型的世界主义很难在效率与公正之间实现协调,更为重要的是,它没有为我们偏爱自己的家庭、朋友和个人事业留下任何空间。
上面所提到康德的世界主义和斯多葛主义的世界主义实际上都在主张某种类型的伦理世界主义或一元论的世界主义。受到罗尔斯的影响,像博格和查尔斯·贝茨这些当代世界主义者则主张了一种相对节制的世界主义形式,即博格所提到的社会正义的世界主义。在“正义论”中,罗尔斯将社会正义的首要评价对象应用于社会基本制度和基本结构,受到罗尔斯的影响,博格也认为,世界主义的全球正义原则的首要评价对象应该是全球范围内的基本制度。不过,罗尔斯所提到的社会基本制度是一国内部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而全球范围内并不存在一个类似于国家的基本结构和基本制度。于是针对全球正义是否要求一个世界国家体制这一问题,博格区分了法律世界主义和社会正义的世界主义。法律世界主义直接要求通过世界范围内的制度设计来实现世界主义的核心理念,因此,法律世界主义有这样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它要求社会制度在全球层面有一个类似于国家制度的框架;第二,这种全球层面的社会制度所施加的利益和负担平等地应用于世界范围内的所有人。
由于意识到全球范围内并不存在一种类似于国家体制的世界政府,因此,像博格和贝茨这些当代主要的世界主义者都不赞同这种法律世界主义,而是主张社会正义的世界主义。与法律世界主义不同,社会正义的世界主义并不直接要求制度应该怎样设计,相反,它仅仅提供一种评价不同制度设计之优劣的道德标准,一种社会正义观是世界主义的,当且仅当这种正义观的评价将所有人的利益纳入到平等的考虑之中。由此,社会正义的世界主义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它并不认为世界政府是全球分配正义得以存在的前提,而是认为,如果一项全球性的制度将世界上每个人的利益都平等地考虑进来,与之相关的正义原则就是世界主义的。
博格所作出的这些区分和澄清,实际上已经表明了当代主要的世界主义者不再像康德和斯多葛主义那样仅仅提供一个一般性的哲学论证,而是添加了更多制度性和现实性的考虑,这类考虑尤其体现在他们对全球范围内人权和分配正义的辩护当中。在考察世界主义者对人权和分配正义的看法之前,我们先简要介绍一下当代世界主义在道德辩护中所具有的几个根本特征:(1)规范的个人主义:道德关怀的终极单位是个人,而不是家庭、部落、种族或国家这类群体;(2)不偏不倚(Impartiality):必须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人类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家庭、肤色、族群或国籍;(3)完全包容性(All-Inclusiveness):作为道德终极关怀的每一个人类个体,都必须被世界主义的道德标准考虑在内;(4)普遍适用性(Generality):世界主义的道德标准和规则对所有的个体行动者和集体行动者都是适用的,进而具有效力。
二、世界主义对基本生计维持权的辩护
我们提到,当代的世界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反思全球贫困这一现象的过程中而复兴的。因此,如何看待全球贫困和与之相关的人权问题就构成了当代世界主义的一个核心任务。他们的这一关切与《世界人权宣言》的第25条具有直接的相关性,《宣言》在这一条中指出:“人人有权享有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平,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世界人权宣言》,1948)。不过,世界主义作为一种哲学话语,并没有直接接受这些法律性的(或宣言性的)条款,大部分的世界主义者对《宣言》以及随后的几个主要国际人权公约都持有一种批判性的反思态度。比如,针对全球贫困现象,大部分的世界主义者并没有像《宣言》那样去辩护某种健康权或福利权,而是仅仅辩护了一种基本的生计维持权。所谓的生计维持权所说的是,在缺乏一些基本生存资源的情况下,一个人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由于这种权利又是与一些基本的物质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也被称之为“最低程度的经济安全权”,它的具体内容包括“未受污染的空气、未受污染的水、适当的食物、适当的衣着、适当的藏身之所以及最低程度上的预防性公共保健”。[5](P23)如果一个人不能够享有这些生存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经济安全权”,那么,他就处于一种绝对贫困或绝对剥夺的状态。
我们这里没有必要去深究如何确立这个经济安全权的最低标准,而是要关注如何为这样一个权利提供公共的辩护。与世界主义者一样,当前大部分的社群主义者以及民族主义者也都赞同这类基本的生计维持权能够成为一种普遍人权,他们的分歧在于,如何为这样一种权利提供道德辩护以及如何去辩护与之相关的责任或义务。
首先,世界主义者是如何辩护生计维持权这类普遍人权的呢?在这一问题上,大部分的世界主义者是介于启蒙思想家和当代的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主要指罗尔斯)之间的。大部分的启蒙思想家主张,人权是独立于人类社会现有的法律制度、政治制度以及相关的认知力和执行力的,因此,人权是天然存在的,是不受人类历史和地域的不同所制约的,是人性(humanity)本身使得人权成为权利。[6](P185)这种辩护在哲学上的最主要体现便是近代兴起的自然法传统。这种传统可以在洛克和康德那里找到影子。在洛克那里,自然权利被表征为一种自我所有权,在此基础上所确立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等自然权利被认为是基于人性而天然存在的,即这些权利的存在是不依赖于权利主体以及相应的政治共同体是否具有能力去实现这些权利,因此,自然权利在洛克那里就是一种脱离历史语境和空间语境的存在。与洛克不同,康德的自然权利是一个不以经验为基础的理性观念,即自然权利被认为是道德主体普遍立法的结果,因此,康德的自然权利理论似乎可以被认为是他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延伸。
像博格、贝茨、舒伊(Henry Shue)这些当代的世界主义者,一方面继承了康德的一些传统资源,认为是人性和人的尊严赋予了权利以基础,例如,舒伊明确提到,“基本权利是每一个人对自己的人性的最低程度的合乎情理的要求”。[5](P19)但另一方面,与自然法传统不同,他们并不主张构成权利之基础的尊严或人性是植根于直觉和理智当中的,进而是不证自明的;而是给予人性和尊严一个经验主义的解释。这个解释产生于这样一个逻辑当中,即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他的尊严和人格产生于他慎思和追求自身目标以及有效地参与社会合作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而这一过程的实现需要一些基本的“能动性”(agency)条件。这个能动性的条件在森(Amartya Sen)和纳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这些世界主义者看来主要指的是一些基本的能力及其行使[7]。人们要想行使这些基本的能力,进而追求自身目的和参与社会合作,一个根本的前提就是基本的生存必须得到保障,因此,基本的生计维持权就构成了一个普遍的人权,说它是普遍的,指这一权利有一个普遍的人性基础。而且,它也是基本的,因为,缺乏了生计维持权,其他类型的权利也就无从谈起。
另外,尽管当代大部分的世界主义者也认为世界主义的道德原则应该是适用于世界上每一个人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像康德等启蒙思想家那样认为道德原则和人权原则是前制度的。在这一方面,当代的大部分世界主义者可以说是受到了罗尔斯的影响。罗尔斯不仅将正义问题设想为是制度的基本属性,而且也将人权问题放在一种制度框架中来解释。在罗尔斯讨论“国际正义”问题的“万民法”中,罗尔斯并没有将人权问题建立在普遍人性基础之上,因为在罗尔斯看来,不存在一个共享的人的观念,能够作为万民社会的公共推理的基础。在这一方面,罗尔斯是与启蒙思想家和世界主义者有所不同的。那么,在罗尔斯那里,基本人权的根基到底是什么呢? 在“万民法”中,罗尔斯提到了这一点,“只有那些构成任何社会合作体系之必要条件的权利,才可被称之为人权,如果这些人权遭受经常性的破坏,那么,我们就处于强制和奴役体制的命令之中,并且不能有效地参与任何类型的合作”。[8](P68)按照罗尔斯的逻辑,只有在社会合作体系内部,我们才能够合理地理解人权以及相应的分配正义问题,而这个社会合作体系,在罗尔斯那里主要指国家。
大部分的世界主义者并不赞同罗尔斯对人权的辩护,而是认为,基本人权是立基于人的人性当中的,是人之为人所具有的基本资格,并不能够从外在于人之外的因素中去寻求人权的根源。在普遍人性的意义上,基本的生计维持权之所以能够被认为是普遍的权利,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基本的生存需要,如果一个人的基本生计维持权得不到保障,即缺乏生存所必要的那些基本资源和手段,那么,他的生命权就会受到威胁,在这种意义上,基本的生计维持权是与生命权直接相关的。称基本的生计维持权是基本的,是因为如果缺乏这种权利,那么,人的生命就无从保障,进而其他类型的权利也就难以实现。因此,大部分的世界主义者实际上是将人权建立在人类个体所共享的某些人性特征上,这些人性特征可以是某些共享的生理结构、心理结构和理智结构。比如,在纳斯鲍姆看来,道德原则的辩护需要依赖于一些“基本经验”,而这些基本经验存在于我们对人类个体所共享的某些特征的理解当中,它们可以被称之为经验内核,这些经验内核包括:某些基本的生理构造和心理结构,具有类似的认知能力和实践理性,等等。[9](P242~267)
因此,与康德等启蒙思想家不同,当今大部分的世界主义者并不主张基本人权是自然法的一部分,是产生于理性立法当中的,而是赋予了基本人权以更多经验主义的辩护元素。但另一方面,当今的大部分世界主义者却与启蒙思想家的理性主义抱负保持了一种一致性,即他们都认为,基本人权原则是一种普遍的道德原则,应该适用于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这一主张本身并不存在多大的争议,争议的根源在于,如何实现这一道德理想?或者说,争议的根源在于,我们应该如何辩护与基本人权相关的义务问题和正义问题?
三、分配正义的边界
基本的生计维持权是每个人都应该享有的一种基本人权,这是大部分的理论家都不会反对的。他们的分歧在于,当面对某些国家和地区大规模的饥荒或贫困时,谁应该承担起相关的责任或义务?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在开始区分世界主义的类型时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回答,即当前主要的直接主义者都坚持一种社会正义的世界主义,因此,他们并没有直接说这个责任应该由富裕国家或大的跨国公司这类主体来承担,而是说,首先应该通过某种公平的程序在全球建立起相关的基本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针对全球贫困问题的全球分配正义制度。
是否应该存在全球性的分配正义呢?这引出了当前全球正义理论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即分配正义的边界问题。具体而言,这个问题所说的是,分配正义应该仅仅是国家内部的事情还是应该扩展至全球?大部分的社群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都坚持认为,分配正义应该仅仅是国家内部的事情,例如,沃尔泽就论证道,分配正义应该仅仅在那些拥有凝聚力的社会群体内来实施,例如,那些因为具有相同的成员身份而具有共同认同感的群体或国家。[10](P31~63)民族主义者戴维·米勒则认为,分配正义只有在那些共享着共同的领土、文化、历史和民族情感的国家或群体内实施才是合理的。[11](P27)米勒实际上是主张,正是共同的领土、文化和民族情感这样一些价值赋予了这一民族或国家以自决权,因此,分配正义也仅仅是国家或民族针对其内部成员的事情。
针对社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论证,像博格和贝茨这些世界主义者则坚持完全不同的看法。在他们看来,像分配正义这样的道德原则或人权原则,首先关注的对象应该是个人,而不是文化或族群,社群主义或民族主义实际上是将某种集体性的价值或凌驾于人权之上,这是世界主义者多不能赞同的。而且,在大部分世界主义者看来,像沃尔泽和米勒所辩护的领土属性、成员身份或民族情感等因素在道德上是具有任意性的,因为,从一种历史视角上看,国家的领土往往是随着战争等因素而不断变化的;随着人口流动和全球化的进程,成员身份也呈现出流动和变化的特征。通过民族情感来辩护分配正义的界限更是不合适的,因为,当前大部分的国家都是多民族的国家,而分配正义在国家边界内部的合理性已经得到较大程度的承认,这说明,民族情感并不是确立分配正义之边界的必要因素。例如,贝茨就论证到,民族群体的成员身份及其相应的自决权因为多民族国家的特征而削弱了,而且,多个民族共同生活在一个政治制度下的事实使得他们并没有发展出足够的忠诚感。[12](P114~115)
世界主义者同社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这些争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种经验性的考察,而且,分配正义同成员身份或民族情感之间的关联到底是何种意义上的,并不是在理论上可以简单说清的。与沃尔泽和米勒不同,罗尔斯则从理论上系统论证了国家边界作为分配正义之界限的合理性。在罗尔斯看来,某种以互惠观念为基础的社会合作体系构成了思考分配正义的一个背景条件。简单地讲,在罗尔斯看来,在社会合作体系中,行动者的动机是以互惠(reciprocity)为主的,互惠是公民之间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通过规约社会的正义原则获得表达,在此一社会中每个人所得的利益都依照该社会所界定的适当的平等标准而得到判断。[13](P15~18)另外,罗尔斯也提到公平正义原则的一些基本特征,首先,它是从某一政治传统内部开始的;其次,罗尔斯认为,作为公平的正义是一种政治观念,它是适用于社会基本结构的,而社会的基本结构主要指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以及在这些制度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世代相传的社会合作体系;最后,在罗尔斯那里,社会基本结构是自足的、封闭的,例如,罗尔斯提到,基本结构是一个封闭的社会结构,也就是说,它是自我包容的、与其他社会没有任何关联的社会,它的成员只能由生而入其中、由死而出其外。[13](P11~15)
在罗尔斯看来,这些适用于社会合作体系或国家内部的正义的背景条件,在全球层面上并没有出现。例如,在全球层面并没有一个“公平的正义”得以存在,并被各个行为主体(主要指各个国家或人民)所认同的公共政治文化传统;其次,作为行为主体的国家或人民各自享有着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在全球层面,并没有出现一种类似国家内部的那种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再次,即便在全球层面已经存在广泛的互动,但是,与一国内部的体制对其成员的影响相比,全球层面的互动和体制仅仅处于一个极其次要的位置;最后,支持社会合作的那种互惠观念在全球层面能否形成还是存在争议的。
罗尔斯所提到的社会合作体系在现实世界中的主要体现就是国家,因此,罗尔斯实际上主张,分配正义仅仅是国家内部的事情,并不应该存在适用于全球范围内的分配正义原则。针对某些落后国家的普遍贫困问题,罗尔斯仅仅主张了一种“援助性的责任”。[8](P116)罗尔斯试图说明,确保人权、满足基本需要,是一种“援助性的责任”,而不是“正义的责任”。在应对全球贫困问题上,尽管罗尔斯试图说明,“援助性的责任”同样可以解决全球贫困问题,但它与“正义的责任”还是有所不同的。例如,“正义的责任”要比“援助的责任”具有更强的约束力,如在制度上,它要求将全球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如有可能会要求某种全球税收制度的存在,如类似博格所提到的“全球资源红利”:而“援助的责任”则并没有在一种全球制度的框架内来处理人权问题,而是在一种国与国之间的国际关系的框架内实现的,它依赖于富裕国家的道德自律。
另外,与米勒相似,罗尔斯认为,国家边界具有道德上的重要意义,而这在世界主义者看来是难以接受的。正如罗尔斯的建构论社会合作体系所暗示的,某一国家或人民并不仅仅是国界本身而被称为具有特殊道德意义的,而是因为在国界内部,其成员共享着源自于独特政治文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并形成了某种互惠的机制和理念。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在罗尔斯看来,即便国家边界在其产生和起源的意义上具有道德任意性,但是,经过世代相传,由国家边界所确立的国家或人民已经内含了其成员的智力和劳动,因此,就具有了重要的道德意义。因此,罗尔斯暗示,至少在现有的历史条件下,国家边界确定了分配正义的范围。
受到罗尔斯的影响,像博格、贝茨和巴里这些世界主义者,也将分配正义的范围与一些制度框架联系在一起,即承认,分配正义之边界的确立是与某种类型的社会合作体系的假定直接相关的。但是,与罗尔斯不同,世界主义者认为,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已然存在了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之类的全球制度和结构,这些制度和机构深刻影响着全球范围内的每一个国家甚至个人。而且,全球经济已然处于一种相互依赖的状态,在这种情形下,利益和负担在全球范围内的运作和转移就是一个基本事实,某个国家或跨国公司的行动能够直接地影响到其他的国家及其公民。因此,世界主义者试图论证,全球层面所出现的这种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相互依赖能够表明已经存在了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合作体系,因此,国家边界在确立分配正义的范围方面并不具有绝对的道德意义。[14](P128~132)
在社会合作体系的框架内,支持分配正义的第二个主要理由是“运气均等主义”。在“正义论”中,罗尔斯提到,没有人应得其(较好的)自然天赋,也没有人应得其因出身之故所处的社会处境。[15](P12)罗尔斯的这一论据被世界主义者所发掘和拓展,认为运气均等主义恰恰支持的是全球层面的分配正义。他们依次提出了两个层面的主张:首先,如果没有人应得其因出身之故所具有的天赋和境况,那么,相应的情况也应该是,没有任何国家或人民应得较少或较多的自然资源。如贝茨提到,“如同一个人的天赋一样,国家所占有的自然资源在道德上也是具有任意性的,因此是不应得的”,[12](P139)因此,应该存在一个针对全球自然资源的再分配政策。其次,世界主义者认为,不仅仅每个人的天赋、出身家庭在道德上是任意的,而且每个人所出生的国家在道德上也是任意的, 因此,应该存在一种统一的全球经济再分配原则。
总体而言,在对人权和正义的辩护中,当代的世界主义一方面继承了启蒙传统的一些普遍主义特质,但却否弃了启蒙思想家那种绝对主义和基础主义的辩护策略,而是将人权放在了现有的历史语境和制度语境中来思考。另一方面,与社群主义者和米勒及罗尔斯这样的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不同,当代的世界主义者认为,某些道德原则或人权原则是能够在全球共同体这样一个背景中得到辩护的,因此,他们试图在全球范围内辩护某种普遍平等主义的人权原则。
小结
可以说,与全球贫困相关的大规模死亡仍然是当今人类最大的灾难,也是整个人类所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当代的世界主义者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才在民族主义思潮占主导的环境中复兴起来,而且,在英语世界的实践哲学界,世界主义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流派之一,甚至是具有了压倒性的力量。在具体的学术主张上,一方面他们批判性地继承了自然法传统的一些基本主张;另一方面,在经历了最近三四十年的发展和完善之后,又逐步与社群主义和民族主义形成了分庭抗礼之势。世界主义者对人类灾难的深切悲泣和对普遍人权的大力呼吁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尤其是在当今全球化趋势日趋加速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很难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普遍灾难置若罔闻。因此,无论是政治实践还是理论关切,一种全球视域和全球关怀的呼吁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1]Derek Heater, “ Origins of Cosmopolitan Ideas”, in Gerard Delanty and David Inglis(eds.), Cosmopolitanism: Vol 1(Routledge, 2011).
[2]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Thomas Pogge,“Cosmopolitanism”, in Philip Pettit and Thomas Pogge (eds.),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Political Philosophy (Oxford: Blackwell, 2007), pp312-331.
[4]这种一元论的正义观在当代的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对罗尔斯的批评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最著名的代表就是G.A.Cohen 和Liam Murphy,可见他们的论文:G.A.Cohen,“Where the action is:On the site of distribute Justice”,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26,no.1 (Winter 1997):pp3-30;Liam Murphy, ‘Institutions and the Demands of Justice,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33 (2005).
[5]Henry Shue, “Basic Rights: Subsistence, Affluence, and U.S.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6]A.John Simmons, “Human Rights and World Citizenship: The Universality of Human Rights in Kant and Locke”, in Justification and Legitimacy: Essays Rights and Obliga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7]Amartya Sen, “The Idea of Justic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Martha C. Nussbaum,“Frontiers of Justic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8]John Rawls,“The law of Peopl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9]Martha C. Nussbaum,“Non-Relative Virtues: An Aristotelian Approach”, in Martha Nussbaum and Amartya Sen(eds.):The Quality of Life (Clarendon Press, 1993).
[10]Michael Walzer,“Spheres of Justice”,(Basic Book, 1983).
[11]David Miller, “On Nationality”, ( Clarendon Press,1995).
[12]Charles Beitz, “Pol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
[13]John 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14]Charles Beitz, “Pol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pp143-153;Brian Barry, “The Liberal Theory of Justice”,(Clarendon Press, 1973).
[15]John Rawls,“Theory of Justi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Cosmopolitanism and Global Distributive Justice
〔责任编辑:左安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