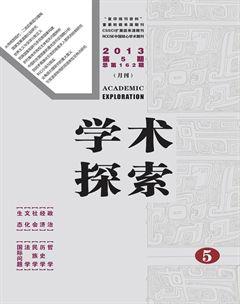跛足:作为此在与大地关联的隐喻
和丽春
摘要:东西方神话传说中普遍存在过“跛足”这一神话原型,表示着生命从弱小开始的原始具象思维。本文从“跛足”的此在进入,探寻“跛足”以非正常态的“身体”凸显“大地”存在的内蕴转换,进而建构“身体”与“大地”的交流空间——意义联系的生命初始场域,两者在行动过程中去体验、掌握实际生命与精神思索的统一。“大地”的力量使这一欠缺成为不断消除对立与矛盾,既而肯定生命的过程。将“跛足”作为“身体”复归“大地”的美学意象,将概念化的“身体”引回“大地”。
关键词:跛足;此在;大地;美学意象
中图分类号:B83-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5-0011-04
从人类的本性而言,难以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人类中心主义难以克服。人自恃有洞悉万物本质的理性精神,自诩“人是万物的尺度”,通过不断从大自然中获取的各种资源来对世界进行对象化的改造,从而认为自己就是宇宙中的主宰者。这样的观点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和欺骗性,使人不能更好地认识到人何以产生及如何实现的本初之义,以至于“人,认识你自己”都无法真正做到。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要转向“非我”的角度,而是要复归“身体—大地”的联系场域之中,重新找到存在的实质与意义。本文试图通过“跛足”这一身体显像去重新理解“身体—大地”的本质内在联系,建构“身体”与“大地”的交流空间,把跛足作为“此在”走向“大地”的启示,寻找生命的动力源。
一、“身体”—“大地”:问题的起源
“大地”具有惰性的、不透明的、坚实的等物质特性,以在场性的方式保障、完善身体的存在。“大地”这一缄默的存在,在现象无限繁衍的世界中好像从未出场,我们却须臾未曾离开过它,在它的怀抱中,历史的车轮载着一切生老病死滚滚向前。
(一) 作为哲学范畴的“大地”
对“大地”的哲学化思考古已有之,从古代到现代、从实践到哲学,“大地”不断进入人们的各种领域中,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模式,这不仅是人类思想的发展,也展示着人类实践的无限可能性。
希腊文明是西方文化的源头之一,古希腊的哲学家从朴素的唯物主义物质观出发去探索现象背后的“本原”,企图找到一个对世界具有决定性的元素,找出是什么东西作为万物生长、消失变化的起始因素。米利都学派创始人泰勒斯认为水是万物的“本原”;阿拉克西米尼认为气是万物的“本原”;赫拉克利特则认为火是万物的“本原”;而德谟克利特则将原子作为万物的“本原”;在爱丽亚学派的赛诺芬尼的观念中,“一切都从土中生,一切最后又归于土”。东方同样存在着对“大地”的思索,在古印度时期就有哲人提出“地身、水身、火身、风身、乐、苦、命”[1](P44)等各种关于世界起源的看法。这里的“地身”指的就是大地的物质性存在。而在中国的传统认识中,人由女娲抟土而创造出来,这是基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而生发出来的认识。“大地”作为无数自然现象发生的“场域”,万物在其中产生,也在其中消失,也就自然把“大地”作为万物的“本原”之一,祭天地仪式是这种哲学思索的外化形式。
而在现代哲学视野中,海德格尔对“大地”的思索尤为突出,在他的哲学范畴中,“大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核心概念。在他的观念中“大地”是“生存空间”的建构因素,“大地”与“世界”是艺术作品的承受者与体现者。
从古代对“大地”朴素唯物主义的本体论观点到近代的认识论转向,是哲学家对“大地”存在范式思考的转向,这是人类意识变化发展的一个主题,也是因为人类一直都在意识到“大地”自始至终都在与人的生存密切相关,人类存在从“大地”的存在中找寻到“身体”存在的意义。
(二)身体——大地的互动存在
生命的持续是身体真正存在的状态,一切意识活动和实践活动都从中生发。但“大地”恰恰是最被忽略的存在,只有在我们体验的反思中,“大地”才被启示出来,它处于一种隐匿与缄默的状态,但无疑其真实性与深刻性,在特定的时刻通过某种方式启示出来,通过身体“这种实际的,实现历史性的生命,亦即在自身的有所关心的自身具有之方式这个难题所具有的实际方式中的实际生命,寓于实际的‘我是我在的意义”[2](P40~41)。
“身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存在,在与“大地”不停的质疑与解构中,发现彼此间在物质性与意义形态方面存在着相互呼应的部分,却渴求超越,但在超越中却又背负着无法否定的实存。因为身体所无法否认的是肉身的存在,对“大地”就有物质的依赖,如果只是被动地实现生存就会将“身体”降为物的存在,所以必须在这种依赖中展现出自为性,一种“自我”的存在,但也不是努力摆脱地心引力去实现完全的超越,这将会使认识趋于孱弱,对“大地—身体”的观照走向偏颇。我们以一种可能性的方式而不是绝对的强制去重新观照“大地”,走向“大地”的反思的复归,回到“身体”与“大地”生命初始场域去完成实际生命与精神思索的统一。
(三)跛足:以非正常身体与“大地”对话
“大地”是缄默着的状态,在特定时候才被启示出来,透过“身体”展现为与生命有意义联系的初始场域。完整的“身体”往往忽略“大地”的存在,而当生命出现困境,“身体”处于“欠缺”状态时,“大地”才被凸显出来。
1.神话中的“跛足原型”
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奥尼索斯,称其为狄奥尼索斯即“瘸腿的人”之意。是好客的酒与狂欢之神,他代表着非理性的形象。还有就是火神赫菲斯托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火神与匠神,宙斯把他从奥林匹斯山上抛到勒姆诺斯岛上,使他摔成跛足。在特比亚传、塔木德神话、所罗门遗训中都有对阿斯摩蒂尔斯跛足的描绘,被十九世纪基督徒认为是冥界王。
在中国的神话传说关于跛足原型最著名的就是大禹,相传帝尧时,黄河之水经常泛滥,百姓苦不堪言,大禹以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精神,经过多年治理终于治水成功,而腿因为长期浸泡在水中,患上腿疾,走路时一瘸一拐。其他的还有“魁星爷”钟馗,“八仙过海”中的铁拐李、云南纳西族东巴神系中的丁巴什罗等都是神话中的跛足原型。
“人们有理由相信,在神话所揭示的东西背后还隐藏着一种较深刻的意义。”[3](P16)神的形象按说应该是完满的,为何又以欠缺形象出现在现象世界中。这其中涉及艺术手法——以跛足原型这一欠缺的方式凸显出“大地”。
2.“跛足”与“大地”的启示关系
当熟悉到可以被忽略的、占优势的动作被障碍打破时,流畅被撕开一个裂口,“大地”的场域就被开启,用观照的方式把掩盖在其上的浮尘去除,把目光从克服障碍的迟滞行为中引向现象的背后,引向“大地”的存在。而跛足这一欠缺的显像具有了一种可能性,一种在切近生命本真的意义层面上突破障碍的可能性。因为“机体的各种反应,甚至某些基本的反应,都不能根据它们借以实现的各种器官,而应根据它们的生命意义来分类。”[4](P225)只要生命还是持续的,那这障碍就不是无法跨越的界限,是一具有可能性的“契机”。
对跛足原型的观照如果仅停留在看与被看的层面,那就只是一个“他者的”、与己无关的形象。把他放在哲学与美学视域下来看,他就成为了一个关于全人类都有共感的对于生命的生长与疼痛的启示,“古希腊人对风行世界的‘跛行舞称之为‘双膝拐弯处的舞蹈,这种舞蹈意味着‘弱小和开始,常在春天萌芽,新生儿洗礼和婚礼时跳,属于生殖神话母题,表示由弱小而开始长大。”[5](P115)原始社会自然条件恶劣,使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种种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焦虑与畏惧常相伴。只有保障生命的繁殖与延续,才能确保人的种族。而“大地”是生命持续的源泉,“跛行舞”以模仿的方式,暗示着生命的成长与遭遇的阵痛,以巫术的方式企求庇护。
正常的行走是身体内部一系列神经系统、肌腱组织的完满适应,形成足部前后交替等分频率的常规行动。这是最简单、最自然的行为,“不是因为行为是简便的,所以行为是占优势的,相反,因为它是占优势的,所以我们觉得它是简便的。”[4](P222)而所以是占优势的是因为在消耗最少的能量情况下实现行动。而跛足使这完满的适应出现不协调,使身体重心发生偏移。身体的动力平衡被打破之后,人体主观能动性为确保向前的行动力会对身体做出相应的调整,这一身体局部——足部的正常状态被打破后,取而代之的是跛足的行走方式。 它表现为一种新的运动状态,实现对问题的解决。但犹如一面完整的镜子裂了一条缝,我们调整视线去重新适应它,但关注点就会发生转移。同样,跛足在确保向前的行动力时,对它的关注会转移到它与“大地”的联系上,与先验中存在的行为的理想状态进行比较。就如疾病让我们意识到身体的健康存在,从而激发免疫力保障生命力。跛足的欠缺建立起了“身体”与 “大地”的互动的空间。而“大地”也在这一契机所打开的空间中,让其所包含的力量运作起来。“身体”借助这股力量也实现着生命的完整。
在跛足行走中,主体的能动性在不断地参与到过程中,否则就会使“身体”完全依附于“大地”的质料中,成为无法摆脱的奴役状态,而“大地”也成为使其消逝的物质性存在。跛足行走在位置与距离的推进变化中,使“大地”的力量消散在身后,表现出“人在途中”的美学意象。因为跛足这一“身体”行动状态的欠缺,使行走发生迟滞,但也因为如此异于常态的异己感,引起心理观照倾向,以一种局部有异的意象形成持续性的诱导,从而进行“身体”与“大地”之间有效沟通。我们能更好地关照“大地”的存在,明确到它是作为生命存在的初始场域与我们之间的意义关联,而不是一味去挣脱“大地”的束缚以求超越存在。
当然,在对跛足与“大地”进行观察时,也是由具体的、行动的特殊现象超越到对其的哲学观照。“身体”现象具有“多”和“差异”的特征,表现出无数身体行为的繁衍,“这种繁衍编织出数量繁多、错综复杂、丰富多彩的关系,以致除非用奥秘的知识便无法理解它们。”[6](P145)面对着这“多”与“差异”时,继续沉浸在不断繁衍的众多显像无法自拔;要么就是试图超越,找到统摄“多”与“差异”的全能法则。前一种会让我们迷惘,找不到出口,迷失在现象之中,而后一种会让我们越过行为的充实而走向形而上意义的超越,而失去与“大地”的有效沟通,引起相互间的排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回归到原初的物我不辩、主客同一的状态才能把握住“身体—大地”。我们要建立超越—复归间的有效机制,在自我意识能确定的状态中、让“身体”在肯定—否定的辩证中把超越的无羇复归于“大地”。而生命也必然地运动在超越—复归之间,始终停留在超越点或复归点,生命都不能得到确证,是消逝的状态 。使超越不再仅仅是形而上的而是从有机体内部发生的,成为对“身体”能进行确切把握的内在意识。
二、作为一种身体美学意象的“跛足”
“身体”在我们去实现“自我”以达到掌握世界的过程中起了一种“介质”的作用,它把我们保持在一个物质性的界限中,在生命确保持续的行动中,利用机体的整体生命意义创造出意义的世界。而跛足让“身体”成为欠缺的存在,这个欠缺身体把在先验之中存在的完整意义上的、封锁的“身体”“空间建构”打开了一个裂缝,强调地表达着足这一紧贴“大地”的部位,通过这一部位,“身体—大地”建立起互动的联系:“大地”通过跛足得以凸现,身体由于欠缺成为不圆满的、不断生成的、在与“大地”的依赖中渴求超越的“身体”,具有发展的可能性。
(一)失衡——复衡的动觉效应
这是借鉴现代舞蹈家多丽丝·韩芙丽跌倒—复起的动作理念。生命从开始到结束不是从生到死一条笔直的线所能概括的。为了生存得不断地斗争,又渴望平稳,身体会遭遇疾病、心情也会此起彼伏,以复杂的步伐逐渐走向死亡——这一人类的最终归属。由于能思,所以注定了人类存在的复杂性,在生——死之间蕴含着行动的无限性和可能性,正如尼采所说,“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总是代表了人渴望向前又渴望平衡的斗争过程,这些不仅是希腊悲剧的基础,也是所有戏剧化动作——舞蹈的基础。”[7](P162)而在生与死之间就是在将矛盾的双方不断拉回平衡主轴的努力过程,是在失衡与复衡的力的摇摆之中完成生命的存在。不断处于失衡与复衡之中求得平衡是宇宙中最基本的本质。跛足的形成原因多种多样,可能是外源性因素导致的,也可能是内源性导致的,在行动力平衡打破之后,改变了人体原有的运动模式,让双足等分频率交错前行的步伐变为拖延迟滞,这是生理意义上的跛足,看似平常无意义,但在古希腊神话、所罗门遗训、中国远古神话中陆续出现“跛足神”的踪迹,以及在许多部落中出现的“跛行舞”让我们意识到,这个直接感官所知的身体显像形式背后所具有的哲学美学意义。
远古的人类在意识中已体验到“大地”与生命之间的本质联系,在无法用逻辑的思维表达这一联系时,就采用巫术的方式实现与“大地”的沟通,而巫舞中的肢体模仿就是他们思索的载体。艺术是以感性呈现的方式把思索的东西表达出来,正是这思索与特殊显像的统一成就了美的创造。“身体”与“大地”之间的沟通是通过生命企求完善的努力中得到实现的,这一沟通以跛足的身体显像为入口,通过舞蹈美学的努力成为“人在途中”的美学意象。非正常身体表现把人从神拉回到尘世之中,让人从高高在上的、征服者的态度上跌落。用一种非常态的方式重新审视人与“大地”的终极关系。
(二)提取——变异的美学形态
“运动”是万物存在的基本法则,“动作的内在质量和外在形态紧密结合,共同构成具有丰富表现力的充满内在含义的动作符号。”[7](P102) 跛足在失衡与复衡中“运动”,完全的失衡就把自身完全依附进“大地”的质料中,只有“外在的肉体的显现,作为个体的直接存在,在它遭否定的痛苦中须显出它自己是否定面”,[3](P298) 在主体能动的表现之中,“生命是向否定以及否定的痛苦前进的,只有通过消除对立和矛盾,生命才变成对它本身是肯定的。如果它停留在单纯的矛盾上面,它就会在这矛盾上遭到毁灭。”[8](P124)跛足在否定的身体形态上通过向着“大地”的复归消除这一否定,通过异于常态的身体显像提取—变异后强化了知觉的感受,达到深层情感的观照。变异是为着弱化表现的次要特征,强化“身体—大地”间跛足的美学意象,把这一显像的特征提取出来,以变异的方式强化局部,使这一局部特征占据支配权。在自主性的运动本能推动下实现对时间、空间的通过,与“大地”形成共生。“大地”作为这一与生命意义联系的初始场域之中,将跛足作为复归的入口,在变异的美学形态中显出生气灌注的、圆满的美学意象并在这个美学意象中,揭示出“大地”的存在。
三、结语
“跛足”作为一个蹒跚行走在荒漠大地的美学意象,让我们看到一个切近生命本真的存在,在自我向“大地”寻求支撑、在失衡与复衡的矛盾运动中、在复归“大地”的行动中,建构着 “身体—大地”沟通的空间,成为揭示“大地”的入口。通过“跛足”进入“大地”,视其所见、听其所闻、触其所感,以介入的方式,将“大地”的缄默转向表述,拂去其上的尘埃,重新观照日常经验遮蔽下“身体”与“大地”的关于生命初始场域的意义联系,以非正常身体将人从虚妄的“神”拉回到尘世中。肯定生命是要以偶然性的痛苦与毁灭为必然,并在与之冲突的失衡与复衡中,获得悲剧式的审美。在被理性覆盖的“钢筋水泥地”上寻找到重归“大地”的入口,把概念化的“身体”引回“大地”,并在其中找到原始动力,回到本原。使趋向彼岸的“身体”回到“大地”。让“身体”在科学理性高速运行的列车上,避免“脱轨”。
[参考文献][1]孙鼎国.世界人学史(第一卷)[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2][德]海德格尔.路标[M].孙周兴,译.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0.
[3][德]黑格尔.美学(第二卷)[M] .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4][法]莫里斯.梅洛-庞蒂.行为的结构[M].杨大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5]刘建,孙龙奎.宗教与舞蹈[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
[6]福柯.疯癫与文明[M].刘北成,等译.北京:三联出版社,1999.
[7]刘青弋.现代舞蹈的身体语言[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
[8][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责任编辑:李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