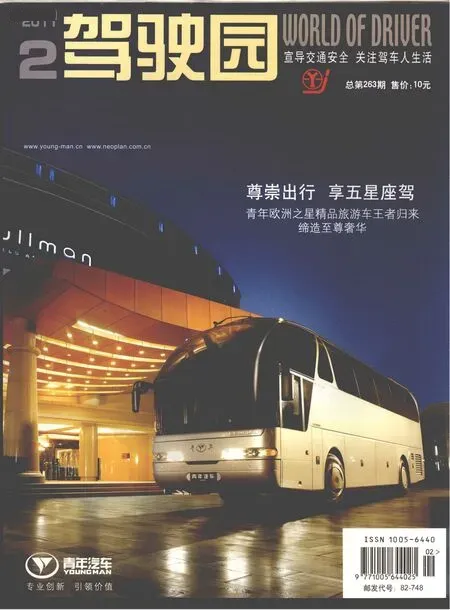“年”的诱惑
■文/马保才
临近年关,一则新闻颇引人关注:据统计,在今年除夕之前的半个月时间内,全国道路旅客运输量将超过12 亿人次。考虑到换乘等问题,春节前夕,约有3 亿人将参与到春运大潮之中,接近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为什么春运场面会如此恢弘?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集体迁徙?恐怕原因只有一个:回家过年。春运大潮中,所有的旅客都是游子,所有的旅途都是归途,所有的终点站都是那个叫“家”的地方。对于中国人来说,“年”的诱惑是任何诱惑都不能替代的。
由此,笔者不由回忆起关于“年”的一些往事——小时候,总觉得日子过得太慢,一天又一天总也过不到新年那一天。那时候盼过年,因为过年能穿新衣,吃饺子。
70年代,物资匮乏。新衣服,那可只有到了过年才能穿上的。那时候,一年到头穿的都是打补丁衣服,只有过年,母亲才会买上一块儿新布料,为孩子们做上一身新衣,虽然并无任何款式可言,但当孩子们穿上新衣时,激动的心情是难以言表的。听着大人们啧啧赞叹,心中会有无限满足感,以至于在过完年后很长一段时间,这身衣服都会是我每天的首选,直到有一天也被母亲打上补丁,我那份固执的坚持才会告一段落。
饺子,在平日里也难得一见的。一日三餐几乎都是粗粮,偶尔吃上一顿馒头,母亲也会在面中掺上些玉米面或山药面。于是,过年吃饺子就成了一年中最真切的期盼,那可是真正的白面饺子呀!每逢过年,帮母亲剁馅、包饺子都是最开心的,等饺子包好,母亲把一盖帘一盖帘的饺子下到锅中,看着水饺在锅里上下翻滚,如同一只只银色的小鱼,嘴馋的我不停地问:“熟了么? 熟了么?”那时候认为白面饺子便是天底下最美味的了。
80年代,日子不再那么紧巴巴了,一年当中也能穿上一两身新衣服了,但仍是手工做的。而过年那身新衣服却开始了由做向买的过度。而在饭桌上,也常能看到白面了。记忆中,那时的面粉分成三个等级:90 粉、85 粉和72 粉。日常吃的多是90 粉和85 粉,72 粉是很少吃到的。记得有一次去舅舅家赶庙会,母亲蒸了一锅72 粉的馒头,当那白白的馒头冒着热气出锅时,我竟然惊诧于世上怎会有如雪一般白的馒头。白白的馒头进入口中,竟还带着甜甜的味道,从此后我总是要求母亲用72 粉蒸馒头,而母亲总是说:“等过年就能吃上了”。
90年代,已经成家的我通过打拼,手中渐渐有了节余,开始置办电器,彩电、冰箱、洗衣机都在那时购买的。新衣服和饺子不再是过年的期盼,因为吃穿已不再是一种奢求。我开始觉得年味越来越淡,也越来越没意思了。
进入21世纪,尤其是人过三十后,我突然觉得一年又一年,日子过的是如此之快,好象只是眨眼的功夫,时间就已从指缝间滑逝而过,新的一年又来了,我开始体味“大人怕过年”的内涵。父母一年比一年老,孩子却一年比一年长高,上要养老,下要养小,我知道,在这样角色里自己一定要坚实!虽然这时包饺子仍是家里过年的主打,但早已与吃无关,那里面包住的,更多的是对过去岁月的怀念和对未来的畅想。
到如今,“年”其实更多地是一种亲情的交融和团聚,不然,你去看看每至岁末,那壮观的春运场景,那些只为买一张车票能够回家过年,而焦急忙碌、脚步匆匆的人们,或许就能找到我们的“年”能够生生不息,任何节日也无法取代的原因。应该说,那种父母、儿孙团聚一堂,其乐融融的氛围和家人发自内心的笑容,就是“年”的诱惑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