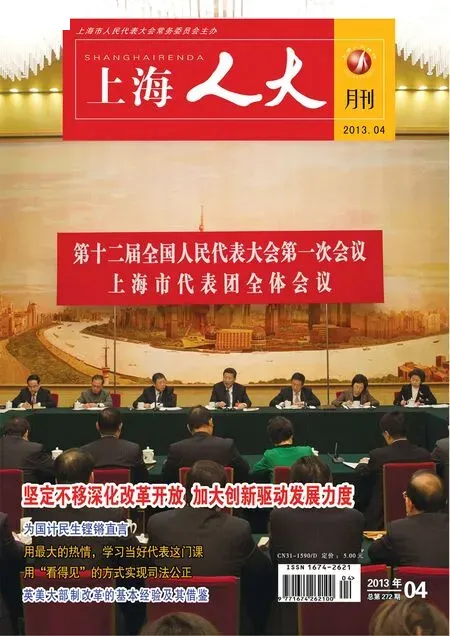从“造城市长”离任说开去
文/孙霄隽
从“造城市长”离任说开去
文/孙霄隽
春节前后,关于大同市原市长耿彦波调任太原的消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其即将离任履新之际,上千大同市民上街打出横幅、签名请愿,甚至有民众当街下跪,挽留“大同历史上最干事的市长”。一时间,这位以“造城市长”闻名全国的“明星官员”再次成为舆论热议焦点,围绕耿彦波的报道见诸各大报端网络,对其评价也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对耿市长的功过是非,笔者不敢妄加评论。市长离任,百姓不舍,甚至不惜以下跪方式挽留的现象,在当下中国可谓鲜见。想必耿市长在当地是干出过一番事业、有扎实的群众基础,报道中诸如“在工地多过在办公室”、“见市长比见局长容易”等一系列亲民务实之举,更是赢得了百姓的赞誉。市民挽留市长,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这位充满激情、愿干事、能干事官员的肯定。同时,在报道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当地群众对耿市长突然离任的失落之情,以及对大同旧城改造政策能否延续、城市拆建形成的财政赤字如何偿还、动迁遗留矛盾如何化解等众多问题的种种担忧。后续报道称,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大同市主要党政领导都郑重表态:向人民的承诺一定要兑现,并表示要做到“五个凡是”。一句话,政府工作是连续的,新官要理旧账。这样的结果,也许能舒缓大同市民的忧虑与不安,但也折射出一个不争的事实:当前一些城市发展中的重大决策,仍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领导的个人意志,缺乏科学化、民主化的规范和保障。
有些地方官员往往留给人们这样的印象:个性鲜明、充满魄力、政绩突出、百姓拥戴,散发着迷人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以“一己之力”推动地方建设发展突飞猛进、一日千里。但这种“强人式”的治理模式,往往带有人治色彩弊端。正所谓“三年五年做规划,不及领导一句话”,在他们的主政之下,城市建设发展也许能在短时间内产生立竿见影的、“跨越式”的成效,但一旦离任,诸多长期因片面追求发展速度而引发的深层次矛盾和社会问题就逐渐暴露出来,并蚕食或抵消已有的发展成果。
城市的发展不应随着一个人的离任而陷入迷茫,即使有人离开,整座城市的运行应当仍然是健康的、有序的。城市的规划建设和长远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和自身的特点;城市发展重大决策的制定,也不能单靠个别地方官员的铁腕政治,而是要靠科学规划、公众参与、民主监督的方式,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历史一再证明,一个国家也好,一个城市也罢,如果其发展仅仅是维系于一人之上,发展的连续性和有效性就容易受到损害。在现有体制下,地方行政长官应当在城市发展中起到关键的作用,但是城市发展决策、方案、计划的出台和执行,必须经过反复的科学研究、缜密的专家论证、严格的公民听证、法定的程序认可。只有这样的决策,百姓的认同度才是最高的,带来的负面效应才是最少的,执行起来的可持续性才是最佳的。
城市建设应当选择怎样的发展模式,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逐步改变城市面貌?还是把未来的钱拿到现在花,通过多干快上来个快刀斩乱麻?这个选择权,还是应该还给值得依赖的制度规范。试想,如果一项公共决策在出台之前,其主要内容、重点项目和关键环节都能向社会公开,与公众进行充分的沟通,在听取和整合各方不同利益诉求的基础上,不断修改和完善;如果当地的国家权力机关能通过法定程序,对决策文本予以审议和认可,将达成一致的民意上升为决定决议等,并严格加以监督执行,也许下一次,市民们需要关心的,应当是决策内容是否依法得到贯彻,而非主要官员的“去”还是“留”。
张德江委员长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得出一条重要结论,就是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城市发展重大决策亦如是,一座城市发展的整体进程,不能因个别领导的变化而变化,不能因个别官员思路的改变而改变,这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一方百姓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