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的人
文/安庆 [短篇小说]
安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文学院签约作家。小说多次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转载,短篇小说《加油站》《扎民出门》两度入选《小说选刊》年度排行榜。
一
刀子正响着不响了。不响了,就不对了,原因是什么呢?他觉得不是问的时候。他就任刀子停着,停着,灯泡晃着,身边的墙上是她手握着刀凝神的影子。他没有催,觉得现在不是催的时候。他闭上眼,不行,就先眯上一会儿。在午后或洗过澡后,小眠是一种享受,今天他就是洗澡后过来的。刚才,小栾还说,你差不多都是洗了澡后过来刮脸。不好吗?好!小栾说,这样的男人讲究,有味道。
在他又盯了盯墙上的影子时,小栾的手机合上了。
刀子又沙沙地响起来。
第一次,第一次他和小栾交谈,那次喝了点酒,有一种兴奋。他问小栾,说,你叫雪儿吗?
雪儿?
这理发店不是写着雪儿理发店吗?
哦,哦,是!
雪儿呢?你是吗?
小栾眨了眨眼。摇摇头,不是。
不是?谁是雪儿?
小栾朝外看了看,好像在找着雪儿,说,我是小栾!她一边把洗得白净的毛巾捂在他的脸上,小手触过他的面颊,温度适中的毛巾在他的面部铺好,轻轻地拍了拍。
她说,我,怎么说呢,我也叫雪儿。她仰起头,下意识地朝外看看,说,一个雪天,一个女人在雪中漫步,雪天清爽,却让她迷茫;因为这一天,她在一个厂子里被炒了,她是冤枉的。还有,她的男人在很远很远的外地不再属于她了。她就在雪中走,雪中走,一直走!雪下着,一张白幔把大地铺严,路边的树成了雪人。她拿出手机给远方的男人打电话,可能还是想和他说说话,争吵也行,只要还有一种声音,有个说话的人。电话忙音,她骂了一句,抓起一把雪,抓在手里团成雪泥,又捂在脸上,在脸蛋上搓!最后她走到了北干道上,路过一片小树林,她找着一棵树,使劲摇,树上的雪纷纷落下,她变成一个满头白发的人。
大雪弥漫中,她看到一个向外出租的房子,她打了门上的电话,赌气似的把房租下,开了间理发店,理发店因雪天而名:“雪儿”。
这个故事对多少人讲过!
不,我不会轻易对人讲!我不会那样贱,那是揭我自己的伤疤。
第二次,林宽躺在松软的小床上。小床干干净净,薄被子被小栾或者“雪儿”轻轻地盖到身上,软软和和的。他说,我要去外地了。
每次来刮脸,都是因为要去外地或参加活动,平常都是用电动刀。小栾把热水端来,一个粉色的塑料盆,毛巾泡在水里,热气朝外冒,一小片雾在房间蒸腾。小栾的小手在他的脸上摸,脸俯在他的脸上方,说,你胡子远看不多,近看却不少呢。
毛巾拧干,慢慢搭在脸上,小栾在床头换刀片。帘子被人掀动了一下,有进来的脚步声,问,人呢?小栾站起来,在呢!对方问,忙呢?小栾答,哦,有客人刮脸。就你一人啊?我,还有一个,她请假了,家里有事!那不还是你一人吗?是,你要不等一会儿?来人犹豫一下,回身又掀帘子,说,那你忙吧。
毛巾揭下来,又蘸水、拧干,搭在脸上。小栾起身,林宽听见了钢刀的声音,啪啪啪,在刀布上使劲地擦刀,像滑在磨石上。小栾在床头坐下,林宽听见泡沫的声音,毛巾拿下来,皂粉抹在脸上。毛巾又在水里蘸,这一次热毛巾搭在了额头上。刀子开始接近,这会儿一般是没有话的,只闻见持刀人的鼻息和刮刀的响声,沙沙沙,像风刮在沙滩上。往往,开始说话是从刀子离开嘴唇上下开始的,那一片先收拾过了。
小栾说到了他的皮肤,在他皮肤上摸一遍。小栾说,你属于比较干性的肤质,干性皮肤要使用保湿和含些油性的化妆品,对皮肤是一种湿润……
第二次,或者是第三次,小栾讲到一个客人,那人是一个画家。小栾说,一个画家你认识吗?
画家?
他经常来这里刮脸,尤其是酒后。
林宽知道他说的画家是谁,是莫森。林宽没有说认识他,听小栾继续娓娓讲下去,画家每次来都不是很老实地躺在床上,酒气在房间里弥漫,她用热毛巾把画家捂睡,温水蘸了皂粉,一点一点抹在脸上,再把热毛巾搭在额头,开始刮脸。往往一觉醒来,酒也醒了,画家摸着变光的脸,说,哦,对不起。坐在镜子前,任小栾把头梳规矩了离开。有时,画家会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兴许是酒后太兴奋了。小栾说,那一次画家在他的刀子下说着说着,竟然流泪了。他说,小栾,我这一次刮脸是要去办一件事,就在明天的上午,画家说,我要离婚了。
小栾说,她去看了画家离婚的过程。小栾是无意来的,第二天她去民政局附近见一个朋友,忽然想起画家离婚的事,好奇地等在民政局门外的小树林里。她真的看到画家和一个女人出来了,女人出来后上了门口的一辆小车。画家呆呆地看着小车走远,发疯般地跑进小树林。他用手一棵一棵地拍打着树,从兜里掏出一小瓶酒,咕噜咕噜地喝,搂着树吧嗒吧嗒掉泪。小栾从树林里闪出来,递过去一张纸巾。说,我是路过,想起你说过离婚的事,真碰着了。画家抬起头,捋捋长发,说,我只是一下子过不去。
林宽问,后来呢?
小栾说,画家还是隔一段时间来一次。还是常常带着酒意,只是常和她谈起他又画了什么画儿,说自己的心反而静了。
林宽知道画家的老婆,画家的老婆曾经是画家的一个模特,比他小几岁,现在已经嫁给一个老板。老板原来和画家关系好,经常淘画家的画儿,给画家提供过一个画室,现在画家已经不在那个画室了。
小栾说,我有画家的一幅画。你想看吗?
在这儿吗?
没有,在家里,我裱了挂起来了。
那找机会吧!林宽说。
二
他看过小栾转钢刀的样子,小身架拂动,小臀部前后摇动,风姿绰约。那一次,他说,我要去外地。小栾接上他的话,刮干净看上去精神,也是对别人的尊重。他在刀子下笑了,笑得想抓住小栾的手,不想让小栾刮得太快,和小栾多聊一会儿。刮了脸,小栾问,掏耳朵吗?你已经几次没掏耳朵了。掏吧,他说。她就掏了。他舒服地躺着,侧着身,耳朵里痒痒的,好舒服,尤其是用那种硬硬的头发在耳朵里搅时,痒痒的感觉很过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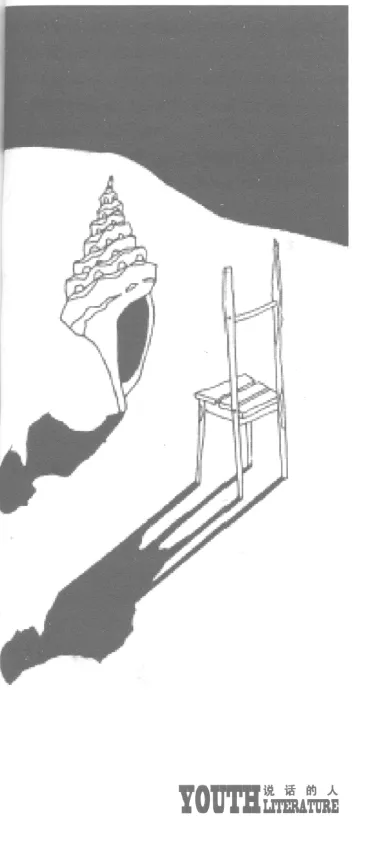
没有想到小栾半似开玩笑地说,小声点,你怎么舒服舒服地叫,臊不臊啊!他一愣。小栾的手还在他的耳朵旁运动,搅动着耳蜗。他闭着眼,没有看小栾,说,小栾,我不是说不文、明的话啊,掏耳朵的感觉真好。他还在绕着弯子,不好意思地说出后边的话。
什么好?你说什么好?小栾的手小心翼翼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射进耳蜗里。
他说,像,像……
不说了,要说的话题意会了,就不用说了。而且林宽是郑重的,没有一点调情和戏谑的样子。
停顿。
停顿后小栾咯咯地笑了。这一笑,他松弛下来。小栾也停下来,说,你说什么,你是说,我被你想成了什么,我和你,是在……
不,不,是感觉。林宽好像生怕小栾误会。
哈哈哈,小栾又笑了。
下一次刮完了脸,小栾问,还要那感觉吗?
她不是挑逗,她是真问。
他说,过一阵吧,耳朵不能掏得太勤。
这一次,小栾又开始讲她的经历。
有一回快关门时,一个男人畏怯地推开了理发店的门。她一眼看出来,是理发店曾经的老主顾,只是很少见他了,她刚开理发店时他常过来理发或者刮脸。
外边的雪被他带了进来。
脚底下的雪留在了店里,电暖气在烤化着他身上和他带进来的雪。门外的雪还在弥漫,弥漫出一种厚厚的雪雾。窗玻璃上蒙得看不清窗外的景致。她站起来,男人去掉了遮住了脸部的围脖,露出一双带着抑郁的眼。这样的目光是让人心疼的,她递过毛巾,让他把身上的雪掸掉,想了想,自己过去帮客人把雪掸了。她说,你等等,先在电暖气上烤一烤吧。
他告诉小栾,他劳改了两年刚出来,胡子该好好地刮一刮了。她没有问他是什么原因,之前在他突然不见了踪影之后隐隐约约地听说过他被判刑了。他静静地躺下让小栾刮脸。老板,你的手艺更成熟。他叫她老板,言谈举止更显慎重。我以后还会过来。他没叫她小栾,也没叫她雪儿。小栾曾经对之前的顾客说,她就叫雪儿。刮着脸,那个人静静地睡着了,像个婴儿,只是眼角在睡眠中悄然地淌出了泪水,小栾轻轻地给他擦去。
林宽听小栾讲述着。
小栾说,他醒来时,我快靠着沙发睡着了,外边的雪还在下,愈发大起来。一直没有再来客人,这样的鬼天气也不会来客人的。男人醒来,对小栾有些抱歉地说,我该走了。小栾没有让他马上走,说,你看,你的头发长了,我再给你理理。那个雪天,小栾和他找到了一家羊肉汤的小店,一起喝羊肉汤,小栾不但没收他的理发钱,还请他喝了羊肉汤。小栾说,算我给你接风。
男人说,接风,接什么风,我又不是旅行归来,更不是衣锦还乡。
小栾说,是,其实就是一场旅行。
旅什么行?
小栾说,人生有很多次很多种的旅行。小栾想起刚开了这家叫“雪儿”的门面,她的确想改名叫雪儿的,开始的一段时间她干脆就以雪儿自称,任别人喊,她应。过了一段日子,一切被时光冲淡了,她才告诉顾客,她的名字叫小栾。理发店静下来的时候她看一些杂志,在一本书里她记住了一句话:人生其实就是无数次的旅行。今天,她又说给这个同样是在雪天的不速之客。
林宽听小栾说着。
现在呢?那个男人?
小栾的刀子停了停。小栾说,他还来理发、刮脸,也掏耳朵,都在我这儿。
林宽说,一个理发店,遇着这么多故事、有故事的人,你的生活真丰富。
小栾停了停,说,这不算什么。
活儿已经做完了,刮脸、包括掏了一次耳朵。林宽说,小栾,你再给我按按吧,我想听你讲,不然,我回去也睡不踏实。
小栾说,好吧!难得有你这样喜欢听我说话的人。
那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本来早该关门了,可我在理发店打了个盹,那个盹太长了,蓦然醒来,眼前站着一个男人。夜很静,但那个男人像一片树叶飘进了理发店。我努力地镇静,慌乱地站好,使劲地揉眼,看到闯进的人胡子拉碴,头发蓬乱,像刚从什么地方拱出来,一种草稞味。我捂住鼻子,男人在打量我的理发店,大镜子里是一个蓬头垢面的人,意识到是自己时他慌乱地躲开。他拽了拽头发,说,给我,给我理发。我还没有愣过神来,我想说太晚了不干了,刚才都睡着了。可我没敢说,夜已经很深,街上没了动静。我身子暗暗地抖,无助地斜眼看着对方,我哆嗦着下意识去摸剪刀,摸一条毛巾,实际上心里十分慌乱,拿不定主意。我还是说了,想试着拒绝,终于吐出那句憋在心里的话,太晚了,明天吧。明天?那个人似乎没有听见我说什么,在小声嘀咕,明天,我明天来干什么,我这种人还有白天?我两眼直直地瞅着,对方踌躇了一下,然后说,不行,给我理!他把发干发灰的手指往头上插,头发缝里落下一些很细的细粉,细粉里的味道迅速窜到理发店的角落。我下意识地挪了挪椅子,看见了搁在桌面上的刀,刀脊闪出一层银光。我想如果有什么事,就用这把刀,我手里紧紧地握着那把刀。
洗头时我还一直听着街上是否有动静,哪怕有一个人的脚步声都会让我的胆子大起来,或者有一条狗过来都行。他头上的味道冲鼻,手握住头发像握住一把干柴,见火就着。我把洗头膏打过去,往盆子里续水,水里又掺进了模糊的颜色,一个人的头怎么能脏成这样?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干什么的?正常的人不会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我的身子一阵阵发紧,心头一阵阵发抽:是一个逃犯?不然就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我从镜子里看对方的面目神色,眼里有一种黯然,但不像是不正常的样子。这么说一定是一个逃犯!我紧张起来,停了几秒钟,对方等得不耐烦了,说,洗呀,快给我洗完!等洗完头他一字一顿,快给我剪头,太难受了。理,理啥发型?随便,还什么发型。嚓嚓嚓,我已经按寸头在给他剪了,我在电视上看过,那些人的头发很短,青头皮都能看到。理了几分钟,那个人举了举手让我停下,他站起身,把门狠狠地闩上,又抬头看看头顶的灯,很亮,在转椅旁边还有一个小灯。他说,把灯拉了!他又说了一遍,把灯关了!不行,我理不好的,我说。他说,亮个小灯就行。我没有动。他找到了开关,光线马上暗下来,我差不多是摸索着在给他剪头。手不敢停,一停他就催,你快点,快点行不行!我的手在头发上又动起来,嚓嚓的剪刀在夜里回响,头发楂像落地的细雪,剪过的头看上去有了精神。我习惯地看一下镜子,镜子里是一个模糊的头。他突然把头换了方向,转椅转了个九十度的弯,说就这样,不看镜子,我的头你不是看不见。我想说服他,想对他说这是理发人的习惯,理发店不是剃头挑子,来理发的人得遵守规矩。可我没这样说,我在运剪中忘记了恐惧,从惊悚中镇静下来,我想找一个话题。想了想,我说,大哥,你长得又不丑,为什么不让对着镜子?他低着头,张张口,但没有话出来。大哥,这么晚从哪儿过来?他有些疲惫,理吧,哪儿来的那么多话。又过了几秒钟,问,好了吗?我说,没有。我正吃力地理着他的耳根,这是通常比较讲究的地方,和脸颊在一个方向,要多下工夫。我听见了咽唾沫声,对方的喉咙里咕噜一阵。简单点吧,不用太细。我说,不行,就快好了。我进入了角色,放下剪刀又换成了推子,电推子发出一阵嗡嗡吱吱地响,眼吃力地盯着他的头。大街上又传来了车声,车灯的两柱光扫过窗户,窗户上一阵白。那个人把围裙撩开,站起来挡在门口,盯着窗户上的光,光在一瞬间又消失了,车轮滑过路面渐行渐远。
灯全灭了,人在黑暗里擦身。这是他理完发又想起要做的事情,一步步逼着,炉子上的水激发了他洗身的欲望,他让我给他找一条抹身的毛巾,在把水倒进脸盆时,灯全灭了。他说,你坐下,扭过身,对不起,我得把身上洗洗。说话声变得委婉,有了礼貌,恢复了一个人的常态。我扭过身,没有想到自己在这个夜晚没了自由,想寻找跑出去的机会,但都被他识破了。他说,你要稳当点,我不会伤害你,不然…… 话没有说下去。
男人抱住我是在他洗完身上之后。黑暗里,声音停下来,听见细碎的脚步声,从窗外射来的灯光在墙上映出一个高大的身影,挪动,慢慢地往我的身边来。我躲着,绕着转椅,终于被抱住时镜子里模糊成一团。在湿淋淋的头发拱过来时,我听见他说,对不起,我以前就是这样,洗过了就抱自己的女人。我使劲挣,大喊起来,可我不是…… 嘴被捂住了,我感到一股难以抗拒的蛮力……
眼前是一个赤裸的男人,这个晚上真是太可怕了。被劫持了,不,被控制了,他使劲地抱住我,我害怕、畏惧,浑身筛动,说,你别这样,会遭报应的。他搂得更紧,我怕什么报应?我都成这样了,还有什么害怕的,我迟早会被抓起来。告诉你,我一直躲在青纱帐里,郊区的青纱里,吃烧玉米也饿不死我,我可以穿过大片的青纱,在青纱里呼呼地大睡。可是玉米收了,所以说我快了,快跑不动了。那男人开始解我的衣服,我抖得浑身骨架都散了,我大叫了一声,嘴马上又被捂住。窗户被窗帘遮住,星光、月光、路灯,所有的光线被挡在外边,那些光竟然穿不过一层布。我被那个男人撂在床上,我感到深深的恐惧,紧紧地护住了被角,浑身在被窝里发抖,我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可是,几分钟后我听见了呜呜的哭泣声,像一头老牛。他的眼泪吧嗒吧嗒掉在地上。外边又有几声滑过的车声,夜更静了。我愣住了,眼泪也一刹那在这个陌生人、逃犯的面前倾泻而出。我的屈辱、我的忍受,我被离开了这个城市的男人的遗忘,一下子被调动;我忘记了防线,想反抗,去拿剃须刀的念头松懈下来。不知从哪儿来的胆量,我劝着面前的男人,你这样是罪加一等,别欺负我,自首去吧,也许你还可以早点出来。别跑了,也别觉得窝囊和屈辱;去吧,等出来,家里人一定会接纳你,不要折磨自己了!我的眼泪唰唰地落到地上。
那个男人摇了摇头,说,你不要说了,我告诉你,你不要怕,我不会把你怎样,不会!就是因为女人我动了别人,把别人动残了;那个人太不像话,我回家的时候他竟然让我碰上了,他欺负我老婆好多天。我咽不下这口气,谁能咽下?对不起,大妹子,把你吓着了,对不起,我,我不是要故意吓你!我躲了几个月,玉米唰唰长时我就开始躲,现在玉米都收了,地光秃秃的,我还在躲。我每天惶恐不安,我就是想借你的水洗一洗,借你的手艺把头整整,其实我是挺讲究的一个人,我不想浪荡,我的头上身上都痒。现在好了,谢谢你,有机会我会来补给你理发钱。我记住了,雪儿理发店。那个人说着还是近近地看着我,一双眼离我很近。
我松了一口气,说,不用了,不用了大哥,去自首吧,你迟早得走到那个地方,别拖延,别耽搁自己。
他好像太疲惫了,把眼挪开。从地上站起来,他拨拉着刚理过的头,得寸进尺地说,大妹子,我,我有个想法,我想在床上睡一觉。我,我好长时间都没睡过床了,我就是想在床上好好地睡一宿。大妹子,怎么样啊?
我说,你睡吧,我很少在理发店睡的,今天打过了盹让你赶上了。我起身往床下跳,他一手拽住了,不行,你不能离开我,这样我才能睡着。我说,我不会告发你,你自己去自首,你就安心睡吧!那个人看看床,掀开被子看了看,打了个哈欠,眼里透出对床的渴望。可他没有钻被窝,他目光在屋子里环顾,最后落在一根用来搭毛巾、搭围裙的绳子上。他说,对不起,我想睡个安稳觉,只好委屈你了。我想起了什么,说,你,你先别绑我,我这里有方便面,我给你泡,我知道你饿,你肚子都叫了。他耷着头,打了哈欠,说,我急着理发,急着洗身都把饿忘了……我最后还是被绑上了,被迫坐在床头,头倚着墙听着窗外的夜声,后来我听见了他的鼾声。
黎明前,他醒了。他弯腰深深作了个揖,门哗啦打开,然后又折回身,把我解开,再作个揖,从门外消失了。
小栾说,我后来收到一封信,他记下了我的地址,告诉我,他自首了。
三
这一次,林宽对她说,我要去参加一个研讨会。
林宽躺在小床上。理发店不大,不过二十平方米,里里外外的几盏灯亮着,一台电视搁在进门的地方,开着。也许,还是他用过的毛巾,沾了水,热气冒着,外边的风在刮,门帘被风掀动。
刮过脸后,小栾看看表,说,今天有风,我领你去看一个人。
什么?
小栾径自地朝前走,两条长腿带动着一个女人苗条的身段,一个鼓鼓的小臀部,走到了一个路边的广告牌旁边。小栾停住,广告牌下正站着一个女人。
女人直直地朝头顶看。广告的霓虹正在闪烁,色彩不断地变幻,画面是一个幸福的女人,满脸溢笑。小栾不说话,不知什么时候她挽住了林宽的一只胳膊,似让身边的男人给她壮胆。风一阵比一阵大,林宽看着仰脸看广告牌的女人。小栾又把他朝前拽了拽,这一次他听见女人的念叨,在骂广告牌,你个没良心的广告牌,你怎么不把我砸死……女人看着看着,搂着线杆摇晃起来,太粗的线杆纹丝不动……
小栾和他躲在路边的两棵树后。没人看,路过的人偶然有人停下来,看不懂或许是麻木了,又走了。接着,女人坐在了路边,从衣袋里掏出了火机,从提包里掏出了纸钱,开始烧。风大,她从包里带出一个什么避风的东西,纸钱点燃了,一缕缕飘起来,飘到半空,驾着风吹远了。
女人在看着飘飞的纸钱。
小栾说,你等着。
小栾走近女人,弯下腰把她从地上拽起来,拎起她的包,挎到她的肩上,拍打她的衣服,拉着手,在说什么。女人走了,风还在刮,线杆上霓虹闪烁,回头看,广告上的女人有些孤独。
两个人去了一家小酒馆。
小酒馆快打烊了,很静。
小栾说,这个女人叫姚角。你可能不知道,去年,就在这个地方出了一次意外的事故:一天晚上,一男一女两个人出来散步,线杆上的广告牌忽然从天而降,砸到了男人的身上,男的当时看着没事,可送往医院的过程中伤情越发严重,他的内脏被砸伤了,在医院没抢救过来。姚角是第二天听说的,她哭得比谁都痛。后来每一次遇到大风天,她都会来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男人出事的地方。她骂着广告牌,在线杆下呜呜地哭,又每次都跪下来祭奠死去的男人。
那个人是姚角的恩人。姚角原来是一个乡下姑娘,有画画儿的天赋,出事的人原来是一个县里文化局的局长,一次活动上见到了姚角,他看出了她的天赋,问了她的情况。姚角因为家境困难,耽误了考试,没有再继续上学。局长帮了她,让她回到学校,毕业之后她到了县里的文化馆。姚角的画儿一直很好,局长后来升到了副县长、县长,又调到市里,姚角在他的帮助下调到了市文化局。姚角一直感恩,所以局长的意外离世让她接受不了。
还有,你知道她每次点着的是什么吗?
什么?
是画儿!每一次她都把自己最新创作的几幅画拿过来,在风中点燃,告诉老局长,这是她的新画作。
我能见见姚角吗?别让她把画儿烧了,怀念一个人可以用很多种方式。
小栾说,你说的用另外的方式纪念我不同意,姚角用她的画儿祭奠是最合适的。
林宽说,喝酒。
林宽没有对她说明白,林宽懂画儿,而且是兼搞评论的,他每次听小栾叙述,并没有把自己分内的工作说清过。他准备等见过了姚角再对小栾说。小栾呢,实际上已经从他的谈话里听到了不少信息。喝了几杯,小栾说,林宽,老实说,接触这么多顾客,你是最让我愿意说话的人,今天,我也借着机会敬你一杯。
出了酒馆,小栾拽着林宽往理发店走。小栾说,不行,林宽,我今天要再给你掏一次耳朵,让你有,有你说的那种感觉。
林宽想笑,一扭头又走到了线杆下,看见了线杆上的广告,他把笑打住了。
四
林宽是一年以后调到省里的,调往省城前他又一次去了“雪儿”。
“雪儿”还是那么一字一板地坐落路边。又是冬天,门帘换成了棉的,中间留了一个白色塑料的小窗口。一个大风天,林宽自己去了广告牌下,那一天小栾回了娘家,“雪儿”的门关着,把风也关到了门外。林宽不是一个人去的,林宽邀了人,他邀的人是很主要的,有那个局长的妻子、女儿,还有一个是他们的亲戚。先远远地看着,直到姚角又走向广告牌,在广告牌下滔滔地叙述,叙述了一个段落,林宽和他们出现在了姚角的面前。姚角一仰头,抹一把眼泪,吃惊地看着眼前的几个人。说什么呢?姚角语塞了,有些不知所措。广告牌在风中被牢牢地绑着,她等待着来的人说话。
局长的妻子说,姚角,你不要这样了。他的灵魂早不在这儿了,他去了天堂,那儿有人等他,有他住的地方、能干的事儿。
几个人过来拉住姚角。那个孩子挽住了姚角一只胳膊,说,阿姨,再不要这样了,我爸他真的去了天堂。再说我们也给他安置了灵位,他怎么能天天在这个冰冷的地方,不要再遇风天来这儿了。
姚角还是沉默着。
局长的妻子走过来拉住姚角,说,你不要这样,这样对你不好,对你不安全。我们商量好了,他每年的忌日,我们邀你一起去祭拜,好吗?两个女人拉着手,我们知道你是记恩的人,难得有你这样的人,我们也很感动。说着说着,两个人都眼泪哗哗的……
后来,他们离开了广告牌,离开不远,广告牌上的灯光暗淡了。
林宽躺在那张小床上,热毛巾煨过了他的脸,刀子在慢滑过他整个面颊,沙沙声,像雨打在沙滩。林宽说,其实我认识那一家人,和他们家共过事,那个局长也做过我的领导,他真的是一个好人。只是我不知道姚角,不知道姚角会这样。我去找那一家人,告诉他们姚角的事,我觉得应该劝阻姚角走出来。一个人惦念恩人没错,这个世界需要更多人懂得感恩,一个感恩的世界会更好;但感恩需要干好自己的事,这才是最好的感恩!这个世界有更多这样的人才会更好。那一次大风天,我和他们一家约好,遗憾的是你不在理发店。还有,小栾,我告诉你,他们和姚角去找了心理医师,我告诉姚角,我是在“雪儿”理发店知道了她的事。她答应我,有一天来和你好好聊聊。
小栾的刀还在运,运得缓慢下来。小栾说,你真要走了吗?
林宽说,对。
小栾叹一口气,说,你还会来这儿刮脸吗?
会!
那我等你,理发店还一直叫“雪儿”,不搬迁。
不过,我怕来得更少了。
不怕,只要你来!
我来!
刮完了脸,小栾用手抚摸着寻找着还扎手的地方,抚过来抚过去,分明是拖延时间。
小栾有些迟疑和忐忑,静静地看着他,还是犹豫着说出了那句话,抱抱我吧,林宽!
林宽稍一迟疑,还是伸手出来。他坐起来,他们就那样温馨地抱着,抱着……小栾说,林宽,就算我这样为你送行了。声音很低,似一缕气息,林宽,记住,记住这儿有一个雪儿理发店。你再来,我还给你刮脸,给你掏耳朵……小栾说不下去了。
林宽,你是个好心人,有心人,细心人。
林宽没有想到会在省城和小栾邂逅。
那个牧城不是不可爱,那个“雪儿”不是不可眷恋,那些牧城的朋友,牧城的风俗,牧城的小吃,牧城的林荫大道,牧城的湖,这里的环境都是让他留恋、让他眷恋、让他敬慕的。问题是有了这么一个机会,他就来了省城;不是敬慕省城的大,是省城可能更适合拓展一个人的事业。想当时他每一次来省城参加活动都要认真地对待,即便穿着不讲究,但精气神得足;比如每一次去“雪儿”刮脸也是为了一分精气神,正如他对小栾所说,要在平常的外表上对人尊重。老实说,人挪动一个地方是喜悦的,但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一种孤独。不奇怪,总得有个适应的过程,或者说,有的人就是为了体验孤独才挪动才更有动力,生存得更好;尤其是对于做学问的人,比如,林宽。
他差一点喊出了一声“雪儿”。他刚参加完一个活动出来,这已经是第二年的春天,草长莺飞,万物回生。他站在春天里,就在这时看见了小栾,是小栾吗?是小栾:瘦瘦清朗的身体,美丽的眼睛,透明的嘴唇,像春天的一棵树站着。她怎么会找到了这里?他看见了小栾向他挥手,举起的手有些畏怯。他挺了挺身,正面地迎了过去。
小栾说,我知道你在这儿有一场讲座,我在窗外听了。
窗外?为什么不进去?
他们不让。小栾朝楼道的方向努努嘴。
两个人已经站到一棵返青的梧桐树下。小栾举举手里的包,找着了话题,我带了刀子,我,我想再给你刮一次脸……
她打开包,把东西一件一件地掏出来:毛巾(蓝色的)、刀子、刀片(包装着的),一个小盒的化妆品,一个……
可是,我今天……
你几点结束,我都等你!她固执地看着他。
他看看表。
你知道吗?我每一次来省城,都带着刮脸掏耳朵的工具,在你单位的门口等过你,我想在省城给你刮一次脸,怕你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有一次你下楼匆匆地钻进了小车,那次你的胡子长,远远地看着,我心里不舒服……
我现在很少刮脸,找了几个地方都不舒服,也很少掏耳朵……
我,今天给你刮一次吧?她甚至有些乞求,怕他拒绝。
手机响了。他说着话,他往身边看看,仰头看着返青的树枝,一只鸟儿穿过树枝的乱缝,飞进了楼层,从树上落下些细碎的东西,裹着一根羽毛。他看到一张等待的脸,他稍一迟疑,对对方说,你等我一个小时,对,一个小时后我过去!就这样定……
他摸了摸脸,朝前边走。小栾跟着,林宽,不,哦,林,林宽……她边走边滔滔不绝地说,我,我有很多话想跟你说说……
装着工具的小包在小栾的手里晃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