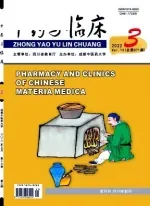非处方药品说明书【用法用量】项的警示缺陷及责任主体分析
王欣,宋民宪
近年来,随着《侵权责任法》的建立,公众越来越关注药品侵权责任相关问题的研究,由产品责任制度中产品缺陷结合药品特性得出的药品缺陷应运而生。据统计,我国约有4亿儿童,其中患病儿童的比例约占患病人口总数的20%[1],表明儿童用药需求量巨大。近年来儿童用药安全越来越受到重视,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指出,全球的患者有1/3是死于不合理用药,而不是疾病本身[2]。目前,对于儿科的研究仅着眼于现状的探讨、处方点评、说明书分析等方式,而对于药品说明书存在问题的研究少之甚少,而儿童非处方药品说明书存在较多的不合理之处,“用法用量”就是其中较为严重的问题之一。因此,笔者在此仅针对非处方药药品说明书【用法用量】项下的部分问题进行简单分析研究。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06年颁布的《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指出,药品说明书是指药品生产企业印制并提供的,包含药理学、毒理学、药效学、医学等药品安全性、有效性的重要科学数据、结论和信息,用以指导临床正确使用药品的技术性资料。药品说明书是医师在选择用药时重要的参考依据,是指导药师审方发药的参考依据,是患者使用药品的依据。《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非处方药”(简称OTC)是指由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公布的,不需要凭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处方,消费者可以自行判断、购买和使用的药品。而《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办法》也有规定,“消费者有权自主选购非处方药,并须按非处方药标签和说明书所示内容使用”。非处方药虽然是经过医药学专家的严格遴选,并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较为安全的药品,但它们仍然是药品,安全也是相对而言的,其作用对象大多不具备专业医学知识,因此,正确撰写非处方药品说明书对公众健康和指导正确合理用药具有重要意义。
“用法”就是指药物的给药方式或方法,如口服、直肠给药、滴鼻等。“用量”就是指药物的给药剂量,或用药的多少。儿科非处方药品说明书中的【用法用量】就是指导患儿用药的方法和剂量,是决定药品安全、合理、有效使用的关键之一。
1 数据分析
笔者利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网站数据查询栏下搜索出的儿科非处方药药品说明书333个(169个化学药和164个中成药)中存在的不合理之处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探讨。
1.1 用法
1.1.1 顿服 阿苯达唑相关剂型的药品说明书中【用法用量】项下均标注了“顿服”这一服药频率词,就专业医药学人员而言,尚且理解“顿服”的含义,那对于没有医药专业常识的消费者,是否清楚?
调查研究发现,有的消费者认为“顿服”就是“吃饭的时候服用,这样药效果好,容易和饭一起消化。”还有的消费者认为“只要吃饭了,就要吃药,一天三顿每顿都要吃。”也有认为是“一顿服用量”,绝大多数的消费者对其含义一知半解。
“顿服”一词来源于中医,语出汉•张仲景《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右六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顿服之,老小再服,取汗。”《简明中医辞典》谓“顿服”是“指一次较快地将药物服完。”而在西医中所说的顿服则是指将一天的药量一次服下,以达到最佳的效果。通常只有突发疾患,病情危急的情况下,需要集中药力,速挽残局来遏制病情的蔓延与发展时,才采用顿服药物的方式,但此举只能起到急挫病势的作用,如若要治愈此病,用药后应依据病情追加药力并酌情减量。儿童生理特点主要表现为脏腑娇嫩、形气未充、生机蓬勃、发育迅速,病理特点为易发病、易变化、易康复,就是说,儿科治疗与成人相比,更要强调及时、正确和谨慎。儿童对药物剂量差异反应灵敏,用药时必须根据儿童个体体质和疾病轻重区别对待,且中病即止。阿苯达唑作为非处方药,患儿在首次服药后的用药情况仍主要是由其监护人决定,而其监护人在该药药品说明书的指导下极有可能连续两次或两次以上服用同等剂量,就此是否会因用药过猛对患儿产生不良反应或副作用不得而知。
1.1.2 服药方式 在333个药品中,除开33个外用制剂,仅有79个药品(占口服制剂26.33%)的用法描述为“咀嚼后服用或用温水溶解后服用”、“服药时可倒出药粉加入少量温开水或奶液服用”、“将软囊滴嘴开口后,内容物滴入婴儿口中;有吞服能力的儿童、孕妇及乳母可直接吞服”、“婴幼儿可直接嚼服,或碾碎后溶于温热牛奶中冲服”、“用刻度吸管吸取后滴入口中,或放入温开水、牛奶、果汁等饮料中摇匀后服用”、“用40℃以下温开水或牛奶冲服,也可直接服用。”等语言,而其余73.67%的口服制剂均简单描述为“口服”。试问,“口服”是直接将药干咽服下,还是用凉开水、温水、开水送服。对于没有吞咽能力的儿童,诸如片剂、胶囊剂型,儿童的服药顺应性极差,通常监护人都会将其碾碎、咀嚼后服下,或将胶囊内容物取出服下,除此之外,对于药味稍重的药,监护人会让儿童将药用牛奶、果汁、汽水等饮料送服,其服药方式亦是口服,但其药的吸收作用部位、代谢途径、药品成分与饮料间的相互作用等因素是否会影响药效,甚至是发生不良反应就不得而知。
卫生部办公厅2011年8月《关于加强孕产妇及儿童临床用药管理的通知》中规定儿童药物治疗药严格掌握适应证,除成人用药原则外,必须严格掌握儿童用药的药物选择、给药方法、剂量计算、药物不良反应及禁忌证等,避免或减少不良反应和药源性损害。
1.2 用量
1.2.1 生长期 小儿维生素咀嚼片的药品说明书中【用法用量】为:“生长期儿童一日1片,咀嚼后咽下。”何为“生长期”?
中医儿科学中,将整个小儿时期划分为7个阶段,分别是胎儿期(男女生殖之精相合而受孕,直至分娩断脐)、新生儿期(出生后脐带结扎开始至生后满28天)、婴儿期(出生28天后至1周岁)、幼儿期(1周岁后至3周岁)、学龄前期(3周岁到7周岁,也称幼童期)、学龄期(女为7周岁到12岁,男为7周岁到13岁)、青春期(女12岁到18岁,男13岁到18岁)。《WHO儿童标准处方集》规定新生儿为0~28天,婴儿为1~12个月,儿童为1~12岁;《儿童药代动力学研究基本要点》规定新生儿为0~1个月,婴儿为1个月~2岁,儿童为2~12岁。
然而,无论基于何种划分标准,均无从得知“生长期”这一词所概述的具体年龄段,词典里解释“生长期”为作物可能生长的时期或作物从播种到成熟的时期。那对于人而言,“生长期”就应该是指受精卵生长到儿童成熟时期或小儿出生后到成熟时期。传统儿科服务的对象限于14岁以下的儿童。2002年在北京召开的第23届国际儿科大会,明确将儿科服务的对象认定为18岁以下的儿童,明确儿科学的研究对象为自胎儿到青春期的儿童。那是否可以就此认定“生长期”即是指胎儿到青春期的儿童。
以上对于儿童年龄段的划分均是专业知识限定,当药品说明书的对象为非医药专业患者或患儿监护人时,怎能使其准确掌握用药剂量。通常儿童药品说明书上是用“1~3岁、4~6岁、7~9岁、10~12岁”这一简单明了的表述来区分年龄段,方便患者或患儿监护人针对不同年龄儿童用药剂量的理解。
1.2.2 服药量划分依据 在样本333个药品中,占68.47%的药品(其中化学药品占64.50%,中成药占72.56%)是依据年龄段结合体重来划分用药剂量,如“1~3岁,10~15 kg;4~6岁,16~21 kg;7~9岁,22~27 kg;10~12岁,28~32 kg”,将年龄和体重并放一起,是为了更好的规范用药剂量,但当患者或患儿监护人面对病人的实际情况与年龄分段的体重不符合时,应该遵循何者?
而根据儿科教材及相关用药指导得知,儿童用药剂量的确定方法主要是四种:根据体重、年龄、体表面积或者由成人剂量折算计算。但根据体重计算剂量,对于体重过重儿,剂量会偏大;根据年龄计算的方法计算过程太过复杂,很少被采用;按照体表面积计算方式不适宜大于30公斤以上的小儿,因为对于10岁以上的儿童,每增加体重5公斤,增加体表面积0.1 m2,如30公斤=1.15 m2,35公斤=1.25 m2,50公斤=1.55 m2,70公斤=1.73 m2,如此算来,体重超过50公斤时,则每增加体重10公斤,增加体表面积0.1 m2;而按成人剂量表(表1)折算可能剂量会偏小,但相对较安全,可供参考。

表1 成人剂量折算表
1.2.3 疗程 在收集的333个非处方药品中,仅健儿糖浆、儿脾醒颗粒、儿泻康贴膜、儿泻停颗粒、小儿厌食口服液、小儿秘通口服液、小儿健脾口服液、小儿宣肺止咳颗粒、儿康宁糖浆(2)共10个药品品种有叙述服用疗程。
对于其余非处方药品,在久服不愈后,应当采取换药服用还是及时就医?对于含有特殊毒性药味的药品,久服是否会产生蓄积性毒性,损害患者机体健康。
我国药品说明书相关规定指出,应当详细列出该药品的用药方法,准确列出用药的剂量、计量方法、用药次数以及疗程期限,并应当特别注意与规格的关系。
2 药品缺陷
我国《产品质量法》第41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民法通则》第106条第3款及第122条的规定,产品责任属于法律有规定的需要承担无过错责任的特殊情况之一,即产品生产者应对产品缺陷对他人造成的损害承担无过错责任。药品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在其生产过程及销售和使用过程中都必须确保药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因此,药品缺陷责任同样是一种无过错责任。
警示缺陷是指药品生产者、销售者未对药品的危险性和正确使用作出适当警告和说明,导致药品使用中存在不合理危险[3],是药品缺陷的类型之一。药品的警示具有两方面的基本作用:一是指示用途,即通过说明药品的基本情况,包括成分、适应症、用法用量等,指导患者合理用药;二是警告用途,即告知药品存在的危险、不当使用时可能招致的损害以及危险的防免。警示事项不全或有误,均属警示缺陷[3]。而【用法用量】项下内容与指示用途相关。
儿科OTC药品说明书的作用对象除了是医师、药师及医药相关人员外,还有患者或患儿监护人等,而“顿服”、“生长期”等词专业性较强或意思模糊,让公众如何正确理解其含义并合理用药。我国《新药审批办法》和《药品管理法》对药品说明书的撰写都有相关规定,但均不曾提到专业性较强、词义模糊的词语不能用,因此,上述用语并不违反相关使用规定。但《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及《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办法》中均有规定,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的文字表述应当科学、规范、准确,非处方药说明书还应当使用容易理解的文字表述,以便患者自行判断、选择和使用。在美国Suter v.San Angelo Foundry & Mach.Co.案中,法院认为,“一个产品会由于指示不充分而成为不安全产品”。“制造者对其所销售的产品负有一些说明的义务。只有一件产品附带有适当的能够使得消费者在使用该产品时具有合理的安全性的信息‘软件’,才能认为该产品是‘合理’安全(或非‘缺陷’)的。”儿科OTC药是为大众所消费、使用的,由于没有专业中间人士的指导,对其标签和说明书的要求相对于处方药来说,应该更加严格,其说明书中的警示内容应为社会上不具专业知识的一般人所能引起注意、知晓、理解。因此,上述“顿服”“生长期”等专业用语模糊不清是相关药品说明书存在警示缺陷的不合理危险。
3 警示缺陷相关责任主体
3.1 药品生产企业
2006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修订的《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开始施行,要求药品生产企业要对说明书的正确性与准确性负责,为因安全性、有效性导致的不良后果承担法律责任。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一条、第五十九条规定,因药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药品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0条至第42条,明确规定了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造成消费者人身伤害、死亡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药品生产者位居药品产销流程的首位,是药品说明书用法用量制定控制源,况且,药品生产者在药品经营过程中有获得利益,应当承担该药品造成的损害责任,因此,只要药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除了法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责任事由外,药品生产者都应当为该药品侵权的主要责任主体。然而药品监管部门批准的药品说明书内容,只是为药品生产者设定一个最低强制披露义务的下限,出于保护公众健康和指导正确合理用药的目的,药品生产者可以主动提出在药品说明书加注监管机构批准内容之外的警示语。美国非那根案例中,最高院根据FDA的“有效改变规则”(简称CBE规则)——“允许药品制造商在得到FDA预先的批准前改变其产品标签以增加或加强产品的警示,只要其事后提交修改的警示以供审查或批准”——判定惠氏公司获得FDA批准的药品标签违反了药品的警示义务,存在过失,不得对抗原告的诉请。MacDonald v.Ortho Pharmaceutical Corporation案中,马萨诸塞高等法院在上诉审中判决原告胜诉的理由之一,认为Ortho制药公司虽然依照FDA法规对其药品作出了警示,但其警示语中缺少通俗易懂的“中风”一词,而是使用“脑细胞组织受到非正常血液凝结损害”的说法,无疑会减轻对使用者的警觉力度,也会让普通消费者无法清楚了解危险的性质[4]。药品说明书的印制内容获得药品监管部门的批准,并不能作为诉讼中不构成警示缺陷的抗辩事由。依照《侵权责任法》按照产品责任承担侵权责任,符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药品生产监管规定的只能免除行政责任。如【用法用量】项警示内容的用语本应在药品生产者的能力范围内被控制的缺陷,造成受害人损害事实的,应当适用无过错责任。
3.2 药品销售者
药品销售者(指药品生产者以外的其他药品销售者)属于制造与行销完整事业体系的组成部分,具有盈利行为,其药师对处方的审核、销售者对非处方药的销售含有对药品用法用量的掌控或嘱咐行为。《药品管理法》第十九条指出,“药品经营企业销售药品必须准确无误,并正确说明用法、用量和注意事项。”因此,消费者通过药房(店)购买药品时,店员(或驻店药师)有责任主动向消费者解释该药品说明书上的专业术语并告之准确的用法用量,否则,受害人因此造成损害,可以向药品经营企业要求赔偿。司法实践“亮菌甲素注射液受害人诉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广东医药保健品有限公司、广州金蘅源医药贸易有限公司损害赔偿案”、“王小华诉翁牛特旗医药支公司龙胆泻肝丸致害案”中,法院均判决药品销售者对受害人承担无过错责任[3]。我国《产品质量法》与《侵权责任法》第43条均有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属于产品的生产者的责任,产品的销售者赔偿的,产品的销售者有权向产品的生产者追偿。属于产品的销售者的责任,产品的生产者赔偿的,产品的生产者有权向产品的销售者追偿。因此,药品经营者对受害人承担无过错责任,而药品生产者与经营者之间存在不真正连带责任。此法条增强了经营者维护消费者用药安全的意识;使受害人能够及时、有效的获得赔偿;同时也保障了生产者与经营者中,无责任方的权益。
3.3 医疗机构
医疗机构在药品的流动过程中,扮演了同时包含有销售者和使用者的重要角色。《医疗机构药事管理规定》指出,医疗机构的药学专业技术人员严格按照《药品管理法》、《处方管理办法》等法律规章制度审核、调剂处方,并告知患者用法用量和注意事项。医疗机构除了向患者提供药品(包括处方药和非处方药),也指导药品的使用,其中就包括非处方药用法用量的解释与指导。《药品管理法》93条将医疗机构与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一并列入药品致害的赔偿责任主体;《侵权责任法》59条亦明确规定了医疗机构对于药品致害的赔偿责任,因药品缺陷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的,医疗机构赔偿后,有权向负有责任的生产者追偿。在医疗机构与药品相关的业务多、可能存在用药医疗事故因素的影响下,医疗机构不同性质的侵权行为所承担的赔偿责任不同。但笔者认为,医疗机构对患者承担的义务应比销售者对消费者承担的义务更重。因为,在消费者选择购买非处方药的过程中,消费者的主要行为是收款供货,而在医疗活动中,由于医学知识的缺乏,患者在选择使用医疗产品时,是无法行使其选择权的,而是有医疗机构代为行使的,医疗机构凭借其专业知识、职业道德和临床经验为患者选取使用医疗产品,医疗机构应有义务保障患者在使用其选择的医疗产品后不会出现生命健康的损害。而法律尚且对销售者追究无过错责任,对医疗机构则更应追求其无过错责任。
《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及《中成药非处方药说明书规范细则》中明确规定,药品说明书是经过国家行政管理部门审批核准的,药品说明书的具体格式、内容和书写要求由国家行政管理部门制定并发布。若药品说明书中的警示内容存在缺陷,国家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在其职责范围内予以纠正或禁止。然而,该行政部门制定的药品说明书内容不合理,长时间未发现、纠正缺陷,导致依此标准制定的药品存在不合理危险,而该药品对受害人造成损害事实时,应承担行政不作为责任(行政不作为就是指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有积极实施行政行为的职责和义务,应当履行而未履行或拖延履行其法定职责的状态)。药品相关监管部门怠于行使职权使得缺陷药品流通与市场并导致社会个体利益损害的,根据《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民法通则》等法律的规定,受害人有权主张赔偿。外国在这方面已经产生了一些判例,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日本亚急性脊椎视觉神经症系列案判决。9个地方法院对此案的判决结果都承认了国家的相关责任[5],如金泽地方法院的依据:1)医药品本质具有危险性,厚生省与药品和准时,须对其安全性及有效性进行审核,而本案中,厚生大臣在批准药品制造后,懈怠对Chinoform进行安全确认[6];2)药品收载后,国家的安全确保义务,并不因此而削减,该案中,厚生省对该药物安全存有疑问,但未立即为药局方之变更,从而应承担不作为责任。目前,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就产品侵权案件对药品监管部门的失职或违法行驶职权的行为,只规定了相关的刑事、行政责任,而没有明确国家赔偿责任。国外的成功案例即可成为今后相关案件判决的有力依据。
4 结语
我国对药品实行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制度,处方药的使用尚有医生、药师的特别指导,而非处方用药的普及,使得患儿监护人给患儿自用药物的现象比较普遍,而患儿监护人的医药专业知识有限,以及现有儿科药物剂型的缺乏或规格不合理,加之患儿监护人治病心切,盲目加大剂量或延长疗程,往往导致用药不当,对患儿造成损害。因此,与药品相关的部门或企业均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严格履行义务,减少或避免患儿用药损害的发生。
药品生产者,作为药品专家,履行警示行为应该充分、持续和及时。警示缺陷的存在,不仅仅可能危害到患者,也可能给药品生产者自己带来不可预计的财产和名誉损失。药品生产者科学、正确的撰写药品说明书,尽可能的保障了患者的用药安全,同时,合理规避了相关侵权责任。
然而对于非处方药品的使用,患者本人或患儿监护人的主观意识也是安全用药的关键因素之一,如我国首例因服用药物致人窒息死亡案例——成都市温江区一女子因服用“桂枝茯苓丸”致咽喉部堵塞引起窒息死亡案中,法院认为受害人李秋华服用被告杨文水制药公司生产的“坤舒”牌“桂枝茯苓丸”时已满34周岁,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直径约为1.6 厘米,外形呈软性状的大蜜丸进行服用时,应当预见到服用药丸方法不当可能存在的危险,并且这种危险是其自身可以轻易克服和排除的,受害人李秋华对药丸服食方法的不当是导致药品存在的潜在的不合理危险转化为窒息死亡损害后果的主要原因,据此,受害人李秋华存在主要过错,应当自行承担主要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不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的规定,综合全案的具体情况,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认定本案因人身损害产生的损失,由原告自行承担 80% 的责任,被告杨文水制药公司承担 20%的赔偿责任。此案例充分说明了患者或患儿监护人对于无医生指导的非处方药品的使用应随时具备安全用药意识,否则也会对造成的损害负相应的责任。
关于对用法用量的规定是中成药与化学药相比,中成药药品标准增加的内容之一。药品说明书标准是基于临床试验或长期经验归纳得出的,而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可能在新技术、新方法的指导下发现药物新作用或新不良反应而使得药品说明书具有滞后性;不良反应相关监测部门的不良反应报告上报的不及时又使得药品说明书具有信息有限性,建议对【用法用量】项的内容不作限制性规定,依药品生产者根据研发药物当时的实际科学技术研究所得信息为准,促进药物研究人员对药物的不断研发和改进,为患者提供更安全、可靠、有效的药品。
药品监管部门行政人员切实履行职责义务,增强责任心和为人民服务意识,完善药品法律体系中尚不健全的条款,使我国的医药事业稳定、健康发展。
[1] 冯红云,刘翠丽,侯永芳.浅析我国儿童药品不良反应/事件现状[J].中国药物警戒,2011,(8):483.
[2] 魏令敏.儿科合理用药的探讨[J].中外医疗,2011,(22):186.
[3] 陈璐.药品侵权责任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152.
[4] MacDona v.Ortho Pharmaceutical Corp.394Mass.131 ,475N.E.2d65,cert,denied, 4744U.S.920,106S.ct.250,88L.E.Ed.2d 258(1985).
[5] 植木折[日].医疗法律学[M].冷罗生,陶芸,江涛,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6] 于敏.日本侵权行为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