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兵为“弑母”道歉背后
姜浩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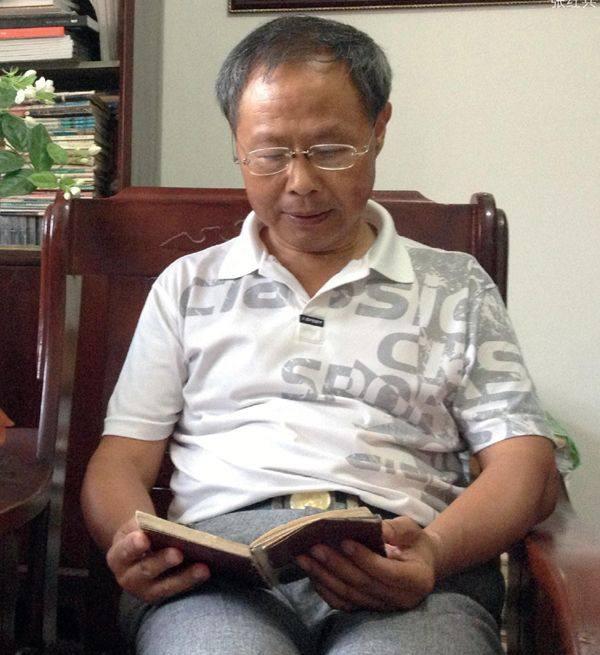


“我为自己有一位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母亲而感到骄傲。我愿在大庭广众之下,解剖自己卑微的灵魂,公开地对被我告发而冤死的妈妈进行忏悔;同时我还要声明:属于包括我在内的家庭成员的责任归我们自己,属于社会的责任归社会,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以前者取代后者。希望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探讨和争论,促进人们思考:在中国大陆,为什么会出现丈夫揭发妻子、儿子把母亲送去赴死的惨绝人寰的悲剧?怎样才能避免悲剧重演?”
2012年8月3日,在固镇县举行的方忠谋墓(遇难地)认定不可移动文物听证会上,方忠谋的长子、也是她“罪行”的告发者之一——张红兵,当众向母亲方忠谋忏悔、道歉。
1970年4月11日,安徽省固镇县人民医院门诊部副主任方忠谋女士,因替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鸣不平,并毁坏了毛泽东画像,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而枪决。后经宿县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复查,于1980年8月14日平反昭雪。
2009年,张红兵状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 固镇县志》(以下称《固镇县志》)编委会和相关出版社,称该县志中《〈方忠谋“现行反革命案”复查平反〉案例》(以下称《案例》)“内容严重失实”、“涉嫌侵害死者及其家人、近亲隐私”;2011年又申请安徽省文物局、固镇县有关部门将方忠谋墓(遇难地)认定为安徽省省级不可移动文物,未果。
在过去的这一个夏天,为“文革”亲历的荒唐事道歉者接踵而至。
他们道歉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他们为当年的所作所为付出了怎样的代价?这又是怎样的一种心结呢?
道歉接踵而至
怀胎十月,一朝分娩。1953年9月,伴随母亲生产的阵痛,他呱呱坠地。父母给他起名张铁夫。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还不满13岁。那一年,张铁夫亲自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张红兵”。
2005年12月,张红兵开了几个博客,其中在凤凰网上的博客以“方张铁夫”为名。当时,他早已是一名资深律师。博客内容诸如——“‘末代皇后案出现罕见一幕”或者“山东农民徐某状告无门”等,大多是他替人打官司的案例。而“方张铁夫”之“方”,来自其母亲方忠谋。
2009年11月16日,张红兵律师来到北京海淀区法院。这次,他是要为自己打官司。他以《固镇县志》的《案例》涉嫌侵害自己和父母隐私为由,将该书作者安徽省固镇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出版发行者中国城市出版社告上法庭,“请求依法判令两被告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抚慰金人民币5万元”。海淀区法院未予受理。
2011年8月,张红兵又向安徽省固镇县有关部门提出,希望将母亲方忠谋的墓(遇难地)认定为文物,未成功;其后,他将有关部门告上法庭,今年4月初,二审终审判决:败诉。
2012年8月,在张红兵申请文物认定期间,固镇县文广局曾对方忠谋墓(遇难地)是否为不可移动文物举行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张红兵陈述道:“我应该成为反面教材,希望历史的悲剧不要被遗忘。”
不仅是张红兵,今年夏天,不断有为“文革”往事出面道歉者——
6月,《炎黄春秋》杂志刊登了一则广告,称:“本人刘伯勤,‘文革初为山东省济南一中学生,时因年幼无知……参与批斗学校校长、老师等。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但是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特向以上师生,诚恳道歉。”刘伯勤,今年61岁,退休前系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处长。
山东蓬莱卢嘉善、河北邯郸退休干部宋继超、湖南退休教师温庆福等人,通过不同渠道,纷纷向在“文革”中被自己迫害的人公开道歉。
同样的行为还来自陈小鲁——陈毅元帅的儿子、粟裕将军的女婿。8月18日,《陈小鲁反思“文革”真诚道歉》一文见诸其本人博客,称:“我作为当时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陈小鲁在文末写道:“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的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与其他道歉者相比,今年60岁的张红兵,因为当年的所作所为遭遇到极致的心灵震撼,背负了更深重的心灵枷锁。他当年做的,除了分别贴过母校固镇县实验小学校长刘祥祯、“固镇县卫生系统头号走资派”——自己的父亲张月升各一张大字报,1970年,由于他和父亲分别向县革委会人保组、固镇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军代表揭发母亲的“反动言论”,导致母亲方忠谋被枪决。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因为“想逃却无处可逃,必须面对”。
1970年2月14日,张红兵的父亲张月升向方忠谋提出离婚。当年4月8日,固镇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做出《离婚书》准予离婚。张月升于2003年1月9日去世。
那个“弑母”的黑夜
8月下旬,张红兵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讲述了自己在“文革”中“弑母”的经过。
“事情发生在1970年2月13日夜晚,我们家人在一块辩论‘文化大革命,母亲说:‘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毛泽东为什么搞个人崇拜,到处都是他的像!作为毛泽东的忠实红卫兵,我立即投入了对母亲的批判斗争,这个时候我父亲张月升说:‘从现在起,我们就坚决和你这个坚持反动立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你就是敌人,我们斗争你!你把你刚放的毒,全部写出来!母亲写完一张纸以后,父亲就拿着这张纸,出了家门,他没有告诉我出去干什么,我意识到:父亲可能去县有关部门报案。”
张红兵回忆说,当时听到母亲说这样的话,他非常震惊。“在我的印象中,一贯紧跟党走、工作积极、待人亲切的母亲竟能说出这些话!顿时,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改变——她不是我的母亲,而是一个张着血盆大口、青面獠牙的阶级敌人!”张红兵说,“在我的脑海里、融化到我的血液中、落实到我的行动上的是红歌——‘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这是一种条件反射。我担心父亲没有真的去报案,作为毛泽东的一名忠实的红卫兵,为了证明自己在与母亲这个‘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站稳了无产阶级革命立场,我马上写了封检举信,当晚就把信和我的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和我家同住县卫生科大院的军代表宿舍的门缝里。”
那一个晚上,天气特别冷,冰天雪地。因为激愤、恐惧和寒冷,不满17岁的张红兵不由自主地上牙“的的”打着下牙,浑身颤抖。
张红兵当时写的揭发材料名为——《检举揭发罪恶滔天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罪行》,他在文末写道:“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
接着,张红兵回到家里。在他发给《新民周刊》记者的电子邮件中如此写道:“在母亲将我们孩子住的东屋门头上的一张毛泽东画像、她和父亲住的西头卧室里墙上的一张毛泽东画像、镜框里的一张《毛主席去安源》邮票等焚烧后,父亲和县公检法军管组负责人、军代表张排长等人进入卧室,对着我母亲的腿就踹了一脚,她一下就跪地了,然后就像捆粽子一样,用带来的绳子把她五花大绑捆了个结结实实。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捆人,现在都能记得:母亲被捆时,肩关节发出‘喀喀的声音,我的心一阵紧缩。”
说起母亲的案件刚发生时的感觉,张红兵说:“我的头‘轰的一声,似乎像爆炸、被掏空,整个身体也仿佛不是自己的。这是我生来第一次从来没有过的极其奇特、极端痛苦、无法忍受的感觉。我的这种痛苦持续了一个月左右,是最糟糕、最令我无法承受、甚至想去死的感觉。”
4月11日,是宣判的日子。那一天,张红兵到了公判大会现场。
“看母亲跪在台上,一个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男军人揪住她的头发,把她的脑袋硬往下按——要她向广大革命群众低头认罪;但是,按着她的手一松,她的脖子一拧,立刻就昂起头。宣判结束,她被人拖上停在主席台旁边的解放牌大卡车车厢时,掉下了一只脚上穿着的黑色平跟带襻皮鞋。”
方忠谋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至于枪决现场,张红兵当时已不愿前往。
记者问张红兵:“是否听说过‘亲亲相隐的古训?对父亲举报母亲你怎么想?”张红兵说:“我在此案发生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作用:当晚父亲离家外出时,并未直接告诉我说他出去报案。当时,我怀疑父亲不是真的去报案,于是自己写了检举信。如果当时父亲坚持不报案,按照我的坚决态度,极有可能将父亲、母亲一起告发,父亲就会因‘包庇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罪名被抓,父亲、母亲将会一道被审判。”
张红兵坦承:“我还要向父亲道歉,因我的告发使他失去妻子,‘文革中我还贴过父亲大字报,作为儿子的我不应当这样做。”
“大义灭亲”的好处
张红兵认为,《固镇县志》的《案例》涉及其父母和本人的文字严重失实,于2009年状告编委会和出版社。
《新民周刊》查阅了《案例》,其中写道:“方忠谋,女,民国15年(1926)生于枞阳县一个地主家庭……”
张红兵认为,母亲对家庭出身被划为地主成分有异议。他说:“早在1953年,母亲就对父亲说过,土改时全家6口人只有2间草房、5.3亩田、半套农具;外公方雪吾一直教书;田地依靠自家的部分劳动、亲戚帮忙和农忙时雇请零工来经营,全家以农业收入和外公的教书收入为生。按当时政策规定只应当划为中农,而不该划为地主。只因为参军前家里为母亲与他人订过婚,对方要求结婚,母亲不同意并提出解除婚约,造成对方精神失常。这时,男方的一个堂兄弟被派到母亲家乡任土改工作队长,借划分农村阶级成分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之机,不但利用职权把我外公方雪吾划为地主成分,而且莫须有地以‘恶霸地主、‘国民党中统中心组长、‘反革命杀人等罪名,将方雪吾判处极刑,褫夺政治权利终身并立即执行。”1980年6月26日、27日,固镇县县委常委召开民主生活会,就方忠谋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对方忠谋的父亲方雪吾的罪恶和地主成分发现有疑点,尚需进一步弄清,请(宿县)地委考虑决定。”
同时,张红兵认为,《案例》叙述案情与事实不符。《案例》载明:“(1970年)2月13日晚饭后,方忠谋对正在刷碗的大儿子铁夫说:‘我活一天,还要劳动一天,不像你们天天高谈阔论,不做实际工作;天天在毛主席像前请示、问安,那是假的。我是相信、拥护共产党的。铁夫反驳说:‘你反动!她义正词严地说:‘我就是反动,我看刘、邓、陶、彭德怀他们是正确的!铁夫说:‘你敢为刘、邓、陶翻案,我就用盆砸烂你的狗头!正在内室看报的张月升赶忙出来喝令:‘打现行反革命分子!铁夫就拿起扁担与张月升一起撕打方忠谋,无意中砸烂墙上的毛主席像。张月升遂即故意激方忠谋:‘你敢撕毛主席像,罪该万死!有种的,你敢讲,还敢写吗?……当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派人去拘捕她时,发现其又把陈伯达、江青等人的画像也烧了。”
“即使翻遍当年为方忠谋定案的全部材料,也找不到上述任何事实和情节,特别是不知道哪儿冒出来的陈伯达、江青画像。”张红兵告诉《新民周刊》,“1980年8月14日,宿县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认定:‘经查,方忠谋参加革命后,工作积极负责,政治上要求进步,在部队曾荣立三等功,出席过安庆军分区英模大会,1950年11月转业后,曾出席省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案例》却对上述生效判决认定的死者方忠谋的一贯政治表现只字不提。”
同时,《新民周刊》也了解到,尽管自参加革命后,方忠谋工作积极负责,政治上要求进步,1956年参加安徽省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多次递交入党申请书,但由于其家庭地主成分和父亲 因“匪特”身份被镇压,她长期不能入党。凡此种种,让她对“文革”的态度经历了从积极拥护、产生怀疑到坚决反对的一个过程。
1970年方忠谋被枪决后,张红兵回固镇中学初二年级上课。有一天,老师喊他到校革委会旁边的一间空屋里,一位中年男子对他说,为了办固镇县教育革命展览,要画一幅肖像。“他让我左手拿着《毛选》,右手朝前方指着,意思是指着我的母亲进行批判。”张红兵说,后来,“大义灭亲——固中学生张红兵和反革命母亲坚决斗争的事迹”就被做成展板,放到固镇中学一排教室中的“固镇县教育革命展览室”。
然而,张红兵和他的父亲并未因“大义灭亲”获得更多“名利”。方忠谋案发后,张月升曾多次向有关方面提交了《关于提出要求给我们结论的请示报告》,要求在方忠谋没有处理之前给自己和孩子“做出结论或证明,防止在今后政治运动中对遗留问题扯皮不清;要求组织上、领导上承认孩子的革命行动,和他们坚决要求脱离母子一切关系,要求今后在政治上不依现行反革命子女称呼和看待,对他们今后报名参军上学等方面问题在政治审查时,不因此问题受到限制,也不因此问题而增加他们的思想包袱”。固镇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县人民医院革委会、公安局、法院专为此事写过证明,至今张红兵还保存着上述文件。
张红兵告诉《新民周刊》,在母亲方忠谋被执行死刑后不久,自己和弟弟就被下放到当地农村劳动。“当时根红苗正的人或是进了工厂,或是升学,或是进部队当兵,我们作为‘黑五类子女,又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只能去农村。父亲自从军队转业到地方工作之后,一直是正科级干部。但在母亲的冤案发生后,他离开固镇县卫生科调动到五河县商业局工作,行政职务从科级变成了副科级,就是降级使用,直到他退休。受母亲冤案株连,我的小姨母方佩兰、舅父方梅开都下放农村劳动,遭受了太多、太多的苦难。”
改革开放以后,张红兵通过中华全国律师函授中心法律专业等函授学习,离开工厂调入五河县司法局、法律顾问处从事律师等工作,先后任安徽省第三经济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建元律师事务所广州分所、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现在北京市博圣律师事务所执业。
2010年,固镇县一居民在方忠谋墓地东侧建房,堵住了通往墓地的通道。经张红兵举报,该房屋被认定为非法建筑,须自行拆除,但该户一直未履行,相关部门也未予强拆。为此张红兵曾向政府申请过行政复议,还向法院提起过行政诉讼。在官司对抗中,固镇县政府提出,方忠谋的墓也是有问题的。根据《安徽省殡葬管理办法》:“禁止在城市公园、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区以及水库、河流堤坝两侧建造坟墓。上述区域内现有的坟墓,除受国家保护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墓地予以保留外,应当限期迁移或者深埋,不留坟头。”因此,方忠谋墓不在保留范围。这一认定猛然提醒了张红兵:“我要以申请文物保护作为切入点,争取把母亲的墓地保留下来,把非法变成合法!”为此,张红兵认真地钻研《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等规定,潜心编撰方忠谋墓资料,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就“文革”受害者墓认定不可移动文物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书面申请。
“关于母亲墓认定文物一案,我将选择适当时机依法申诉。”他对《新民周刊》表示,“1980年此案平反时,方忠谋曾被誉为‘安徽的张志新。根据固镇县有关部门电报通知,我姨母方佩兰专程赶到固镇县写出材料,书面提出了为方忠谋彻底平反昭雪、修建烈士墓等5项要求。当时固镇县委赴五河县调查组也与父亲和我谈话。”
方忠谋冤案发生时,只比张红兵大4岁的舅舅方梅开当晚也在现场。他说:“我大姐被判死刑,是张红兵和他父亲要求的!”
方梅开谈到大姐方忠谋在“文革”后遭遇的一系列变故:1966年,方忠谋的女儿也就是张红兵的姐姐,到北京接受毛泽东第八次接见革命师生活动,感染脑炎回固镇家里几天就去世了;1967年,丈夫张月升被固镇县卫生系统造反派揪出来,戴高帽游街批斗挨打尿血;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方忠谋自己也因“地主分子”、“特务嫌疑”被单位隔离审查、交代、劳动,限制人身自由长达2年。
方忠谋被枪决后,方梅开有近10年没有与张家父子来往,直到1979年前后,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方梅开与自己的小姐姐方佩兰,主动催促张红兵父子为母亲的案件写申诉。当时,他们父子还认为时机不成熟。直到张志新事迹被报道后,张红兵才积极行动起来。如今,方梅开非常支持外甥张红兵将方忠谋的墓申请认定为文物。
我为什么会卖母求荣
在方忠谋冤案的发生地固镇县和知道此案的人群里,到现在都有许多人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丈夫和一个儿子,这么绝情地要求判处妻子和母亲死刑?
有多种说法——也许是为了自保,求得撇清与方忠谋的关系?也许是为了自己理想的纯洁,宗教般的虔诚,不惜奉上最贵重的祭品?也许是知重刑为获轻判而教训一下方忠谋?
而张红兵并不避讳地告诉《新民周刊》:“确实有自保的念头。”
自保后的张红兵,并没有因此而平静生活,这一段往事的影响,伴随其一生。“1998年,我已经做了多年律师,在担任一起刑事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时,一次,与被告人熟悉的一位村民对被害人丈夫说:‘任何人说张红兵,他都不愿意调解。他妈妈都被他告死了,他是什么人都敢告的。你还是同意调解吧!”张红兵告诉《新民周刊》。这样的刺激并不鲜见。“2001年,我曾经的一位同事,也是律师,在法庭上,我们代理双方,激烈辩论。休庭后,他在楼梯口拦住我,高声地向过路人宣扬我检举母亲的事情,说《固镇县志》里都提了,大家都去看!”
母亲被枪决,对张红兵的人生影响,远不是多年后才发生的。
从方忠谋案发那一刻,张红兵就感受无穷压力。他称自己1976年10月至1977年8月发生严重的精神抑郁症。在此期间,他停止了记日记,当然也无医生可看,无药可服,硬是自己扛了过来。“造成抑郁症的原因是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让我忧心忡忡:广播、报纸上宣传的所谓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是真的吗?这是不是一次军事政变?是不是毛主席曾经预言过的‘资本主义复辟?我不敢再想下去:外公被镇压影响到母亲的一生;母亲被枪毙也会影响到我的一生——也许有一天我也会被送上刑场枪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越来越表现出严重的精神抑郁症状,比如我与父亲、弟弟通过语言交流思想已经困难。我在心里揣摩着要说的每句话,考虑说出来是否正确。有时候竟无法准确地用词语表达。我想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不与他人接触,避免可能发生的恐惧。抑郁最严重时,我甚至想过自杀,逃避现实社会。”
从1979年11月开始,张红兵常常梦到母亲。他告诉《新民周刊》:“有很多、很多次,在睡梦中,经过我在无数次寻觅,在不知道母亲为了什么原因离家多年以后,她忽然从我不知道的一个地方回到家里——她没有死,还像临刑前那样年轻。我跪在地上,紧紧地拉着母亲的双手,有一肚子的话想述说,但又害怕她再次消失,只能说出最要紧的几句话。我大声地说,妈妈!不孝儿我给您下跪道歉了!儿子我真的对不起您!您别走,我们这个家庭真的离不开您啊!但是,妈妈没有回答我。在与母亲相会的许多梦境里,她从来不和我说话。我相信,这是她对我的一种惩罚。不知什么时候,她真的又悄然离我而去;我所能做的,只是孤立无援、绝望无助地捶胸顿足、嚎啕大哭。这时,我才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哽咽,泪流满面……”
而张红兵的父亲,在儿子面前则一直小心翼翼地回避。直到父亲退休后,有一次张红兵陪伴父亲回老家,在去刚修建的桐城火车站的路上,他和张红兵谈起这起冤案的责任问题。张月升说:“我们家出了这个事,我应该要负主要责任,因为我是一个成年人和家长。”
“为什么我会卖母求荣,表现自己‘站稳了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如今,张红兵认为,“对此,几十年来,我一直处于困惑、学习、反思、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当时我没有把造成母亲冤案的责任全部推给时代和政客,现在也没有类似的心理过程。”
张红兵还说:“只是在自己和亲人们经历过无数的艰难和坎坷,付出了一次又一次血和泪的代价,并且在我自己娶妻生子之后,原本不懂任何人情世故的我才大彻大悟了:什么虚幻的景象,动听的说教,人造的偶像,神圣的祭坛……全是愚弄别人、自欺欺人的骗人鬼话,是毒害青少年和儿童的精神鸦片,是杀人不见血的锋利刀子!不管是谁,永远都离不开自然规律——吃饭、穿衣,生老病死;世界上最伟大是母爱,最崇高的是人性!”
今年以来为“文革”致歉的个人
王冀豫
一场红卫兵武斗中,16岁的王冀豫挥舞大棒打死了一位19岁的青年。43年来,他常在暗夜中醒来,问自己:“我打死人这事儿该怎么算呢?”2011年1月,62岁的北京商人王冀豫选择站出来向世人说出自己的罪。“忏悔太虚了,我不求原谅,我认账,活该受折磨,遭报应。说出来,是为历史留下证据。”
刘伯勤
这位济南市文化局前文物处处长,自己花钱在《炎黄春秋》今年6月号刊登广告,向“文革”期间被自己参与批斗的师生诚恳道歉。
忏悔者
今年6月,《快乐老人报》发起“文革忏悔录”征文,有不少读者为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道歉。
湖南退休教师温庆福写道:“回忆起‘文革岁月,我至今觉得愧对的一个人是原来在湖南益阳三中任数学教师的张琼英女士。她如今已是耄耋老人,听说她过得很好,我深感欣慰,很想去看望她。”
福建泰宁68岁的雷英郎对于自己戏辱“走资派”的行为,写道:“多年后,通过反思,认识到我的作为很卑鄙,侮辱了他人人格,追悔莫及。”
山东蓬莱的卢嘉善先生写道, 1984年参加工作后,偶遇“文革”期间被自己批斗过的迟老师。“他又老又瘦,早已退休,推着自行车卖雪糕贴补点家用。我要掏钱给他,他硬是不要。当我提起‘文革那段往事时,他摇摇头说:‘老了,什么事都不记得了,那时你们都是毛头孩子,谁还没有点脾气?关键是现在你们长大了,能挣钱养家糊口,很不错了。我还能说什么,只有退后两步,对着恩师深深地鞠了一躬。”
河北省邯郸市退休干部宋继超写道,一直想找机会给老师道个歉。第一次,话到嘴边没说出口;第二次,写了篇文章投给报社,没能发表。如今,老师早已去世,宋继超也退休了,可64岁的他依然放不下这件事。
陈小鲁
陈毅元帅的儿子、粟裕将军的女婿陈小鲁,8月18日发表博客《陈小鲁反思“文革”真诚道歉》一文称:“我作为当时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陈小鲁在文末写道:“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的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
亲亲相隐的理念,最早见之于《论语》。孔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后来这成为我国古代刑律的一项原则——亲属间有罪应当互相隐瞒,不告发和不作证皆不论罪,反之要论罪。亲亲相隐客观上维护了宗族伦常。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亲亲相隐原则进一步得到确认。唐律对亲亲相隐原则作了具体规定,以后各朝的规定大体上与唐相同,其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亲属有罪相隐的,不论罪或减刑;控告应相隐的亲属,要处刑;有两类罪不适用亲亲相隐原则而须大义灭亲:一类是谋反、谋大逆、谋叛及其他某些重罪,另一类是某些亲属互相侵害罪。
2011年第17期《人民论坛》文章《“亲亲相隐”与现代法治精神》提到:“新中国成立后,‘亲亲相隐作为封建糟粕被废除。但是,重新审视‘亲亲相隐制度,不难发现,其有存在的合理性,与现代法治精神并不违背。”我国在1998年10月5日签署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该公约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会单元,并应受社会和国家的保护。”有学者认为,“这就要求我们的现行法律,应和保护人权的具体条款相一致而不能违背。同时,当代 ‘亲亲相隐的亲属范围界定应为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姊妹、(外)祖父母及(外)孙子女以及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与丧偶女婿较为合理,不应过分扩大。同时要严格限制亲属免证权的案件范围。对重大犯罪,如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及利用亲属关系的职务犯罪、亲属之间的相互伤害的犯罪就不应容隐。”
“文革”心理遗伤研究
长期从事“文革”心理遗伤研究的武汉市心理卫生研究所所长施琪嘉认为,“文革”的心理创伤不仅持续影响亲历者,还对其子女乃至后世数代人产生了代际传递。这种影响,最明显的后果是损伤后代的思考及记忆能力。施琪嘉说:“‘文革是一个民族的集体创伤,它至今仍在生疼、化脓。这段记忆需要获得治疗性的处理。这是大多数‘文革亲历者未曾意识却始终承担着的梦魇。痛苦的回忆会反复以各种形式——画面、声音、味道、皮肤感觉的闪回,一直存在于受害者的头脑中。”
在施琪嘉掌握的材料里,绝大多数的受访者甚至将自己的父母描述为“专横、严格、充满仇恨”,教育的恶果则会在多年后凸显而出:少年们仇恨并背叛自己的父辈,随着时间的推移,“弑父者”却变得越来越像他们的父母。暴力在悄然间传递。一种无法说明的恐惧笼罩着他们,以至于他们特别“害怕成功”,总会将一些事情刻意弄得糟糕,比如升迁,比如婚姻。
施琪嘉尝试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文革”心理创伤及其代际传递。神经科学的理论基础帮助了他,大量研究后他发现,它会如一个深藏在体内的发炎脓肿一样,不断地影响着机体:创伤记忆,带着强烈的负性情感片断,会储留、堵滞在脑子的杏仁核内,不能正常上传到负责记忆整合的海马,并进一步处理到皮质。(根据公开报道整理)
“文革”遗存欠保存
张红兵想让自己母亲的坟墓成为文物。在有些人眼里,这不“科学”——“文革”岁月过去不到半个世纪,对于有着五千年历史、十数个专制王朝的中华文明来说,“文革”遗物要想列为文物,简直无从谈起。
“文革”后,一些当年的红卫兵、革命小将,由于种种机缘,身居高位者有之,发达致富者有之,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最好“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几度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放在心底……”难得有陈小鲁这样出面致歉者。
“文革”的受难者也选择性遗忘。几年前,我曾经采访过清华大学的韩家鳌教授。“文革”期间,他是清华中学的校领导,批斗会上,被红卫兵用皮带头猛抽。韩家鳌并不愿意和我谈及这些往事。“都过去了,不提了。”他就这么摆摆手。
然而,十年浩劫,乃至其之前如何酝酿,之后又如何流毒于我们民族的血脉,难道不需要彻底反思吗?最近,在四川大邑县建川博物馆聚落,馆长樊建川对我说:“‘文革浩劫,灾难性的遗址,得到保存的太少。把历史抹得太干净,中华民族就记不住教训,还会摔跟头。这也是我搞收藏的目的。”
樊建川特别同情张红兵。他对记者说:“不仅是‘文革,建国后几十年的教育,只讲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同志关系。他当时认为他的母亲那些话,对国家不利。我们也都经历过那个荒唐的时代。我现在特别赞赏张红兵这样忏悔的勇气。人到这个年龄,能做出这样的事,不容易。”
樊建川认为,那时候“运动”起来后,夫妻反目、揭发家人的事很多,只不过后果或许没张红兵家那么严重。“摔毛泽东像,在当时也真是够枪毙的。”樊建川说。如果张红兵,哪怕是他父亲不去报案,但凡有人去报案,说不定一家都得搭进去。张红兵的母亲是被枪决的。然而,“文革”时期的暴虐行为,岂止枪决?在建川博物馆的库房里,有比方忠谋案惨得多的“文革”文物,记录了当年的恐怖与荒谬——扒人皮、割耳朵……有些惨烈的东西,樊建川甚至不敢拿出来公开展示。
谈起如今的年轻人对此事的看法,樊建川说:“他们不了解当年的情形。作为张红兵的同龄人,听到这则新闻后,我一直在反思——如果当时是我,我会不会去报案?”
提到“文革”遗存的保护,樊建川表示遗憾。比如重庆红卫兵公墓拆迁的问题,假若这些公墓当年列入文保单位,或许就不会遇到后来的麻烦。“文革”遗存欠保护,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记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新马桥中心小学强亚兵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