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枝败叶:百年孤独前的孤独
文/ shirleysays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那时的马孔多是一个二十户人家的村落,泥巴和芦苇盖成的屋子沿河岸排开,湍急的河水清澈见底,河床里卵石洁白光滑宛如史前巨蛋。”
《百年孤独》开头是与《枯枝败叶》有联系的。一个是以马尔克斯的故乡阿拉卡塔卡为原型的马孔多镇,另外一个就是布恩迪亚上校的名字曾短暂地在《枯枝败叶》里出现过几次。尽管《枯枝败叶》早于《百年孤独》成书十余年,可前者并不是后者的序篇,而是发生在马孔多镇上相对于布恩迪亚百年家族的波澜壮阔而独立出来的一个片断。
或者换句话说,正因为马尔克斯轻车熟路地驾驭了篇幅不长的《枯枝败叶》,在叙事当中有意无意地留下了多处线头,他才意识到有必要再写一部长篇巨著来诠释“枯枝败叶”们给小镇带来的冲击,影射其为拉美世界带来深远影响。马孔多镇是拉美民族文化的代表,那里故事多,神秘多,奇幻多,怪诞多。而马尔克斯将所有的社会动荡、生活震颤、怪异行为都归结于一种宿命的力量,那便是人类本源的孤独。喧闹人群里的每一个人都有着遗世独立的孤独感。所以,可以把这本书看作拉响《百年孤独》的前奏曲。小说家讲故事的办法有很多种,个人觉得马尔克斯是最善于在故事之上构建故事的,就像一位技艺精湛的建筑师。《枯枝败叶》采用复式叙事结构,通过外祖父、母亲以及男孩的三人之口来讲述镇上的大夫死了,在镇上居民的怨恨声中祖孙三人顶起将其下葬的重任。大夫是小镇上一个神秘的符号,没有姓名,没有出身,人人都恨他,而他自己却选择了不留遗言上吊而亡。我总隐隐觉得《百年孤独》里的梅尔基亚德斯的死与大夫的死是相互照应的,至少他们都带走了许多秘密。如果马尔克斯愿意写,马孔多镇上的故事恐怕他一生也写不完。可惜,他的身体状况已经让他辍笔无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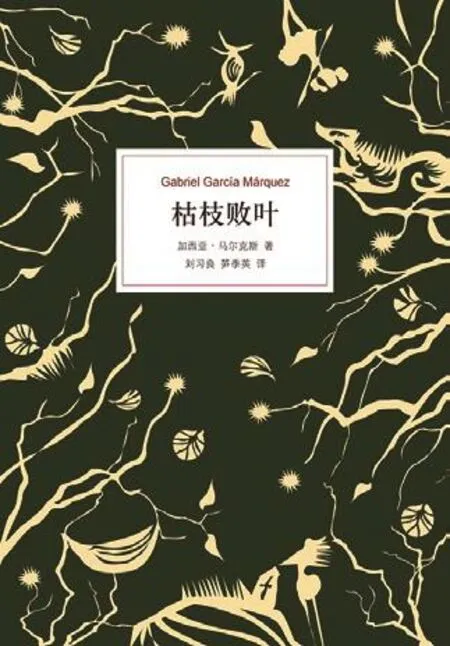
祖孙三人利用碎片式的回忆方式,试图为读者拼凑一个大夫的形象。可其中夹杂的却是他们各自的秘密。男孩少不更事的叙述,令人觉得生活轻巧快乐,一个人死了也不过如此; 妈妈既不能反抗父亲,也不能放弃对大夫的怨。可她的婚姻也不幸福啊,由父亲做主嫁给了一个骗子,为她留下一个孩子。当现代文明不断地入侵贫瘠蒙昧的拉丁美洲时,各村镇里出现的何只是一个叫“马丁”的骗子。这是马尔克斯对“香蕉公司”的控诉,就像他在本书的开篇所言,“枯枝败叶”冷酷无情。
祖父的回忆是本书的重头戏,是他的坚持才让大夫得以魂魄安息。他最后一次与大夫在走廊上谈话时发现,“我看到他忧郁孤寂的脸斜靠在左肩上。我想起了他的生活、他的寂寞和他那可怕的精神创伤,想起了他对生活麻木不仁的态度……”他是读懂了医生的,读懂了他“迷宫般的孤独的秘密”。“枯枝败叶”所设立的职工医院抢走了他谋生的生意,所以他最终已经忘记了医生的技艺。“大夫”成了孤独的代言人,唯有死亡才是摆脱孤独的方式。
《枯枝败叶》的语言冷漠、节制又如行云流水,即使面对死亡时也一样不动声色。你很难理解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青人能在自己的创作初期就显出这样的大家风范,你很难理解一个初涉写作的小伙子能把一个几乎没有故事的故事讲得如此繁复。前些天我在小津书房听雍雅老师关于古希腊悲剧的讲座时,她说:“伟大的艺术家都有一颗火热的心和一个冷静的大脑。”,这句话用在马尔克斯身上显然也非常合适。
早晨的阳光淡淡的、暖暖的。在我们街口,又看见那卖水果的老人、修理水喉的老人。他们各坐在街口的两旁,好像是这小街的守护神。街道很短,只有几幢大厦,而且街道只有一个入口,他们坐在那儿,几乎认得全街的人了。卖水果的老人,穿一件短袖的白內衣,背一个盛钱的蓝布袋,坐在水果箱上,跟我们招呼。有时母亲前一天买了西瓜,他遇见我们就会问:“昨天的西瓜甜吗?”那个修水喉的老伯,一次一次为我们修好脆弱现代的胶制抽水器,有时是小毛病,他很快弄好,就搓着两手,摇头不肯收钱,退出门外去了。
我们街道这边是杂货店,还有新开的汽车修理铺和一爿废纸行,在对面,修水喉的老伯那边的街道,是一列廉租屋。街口那幢最近拆卸,包起布幅和竹席的棚子,黃色的机器车开进去,把地面挖成一个个窟洞。在大厦外面地上堆满了泥和木板,又搭起临时的行人道。那老伯也迫得搬了位置。如果继续拆,不晓得他会搬到那里去。
在街尾的地方,是一个小小的垃圾站。再后面,是一条泊车的小巷,然后就是山边了。风吹起来,山上绿色的竹树都沙沙作响,给人清涼的感觉。青山和垃圾,最美丽和最丑陋的,都全在这里了。
早晨的时候,鸟儿吱吱鸣叫。新开的车行和纸行带来了更多的声音。洗汽车的妇人在大声说话,有时有个车主高叫起来,说人家故意弄坏他的车。从窗子可以看见这些车辆,静静泊在这儿,一辆黃车的车顶有丛丛叶影,旁边一个人不知咯咯地在敲什么。在晚上可以看见驶进来的车灯一闪一闪。有个晚上,下面人声嘈杂,原来是警察在那儿搜白粉。车主、警察和闲人吵作一团。那晚的月亮又圓又白,映在窗玻璃上。记不起是不是十五。在早晨的时候走过,可以看见车位都空了。人们都去了工作,只留下一条静静的街道,仍有人咯咯地敲着一点什么。
我们从街尾转入屋邨的后门,那儿有一幅空地,是散步的好地方。一幢一幢大厦和停泊的汽车之间,有花园般的空地。在一张石凳上,一位朋友和她儿子正在晒太阳。她就住在这儿。儿子八个月大,看起来挺健康。他胖胖的,常常笑;膝盖那儿好像有两个酒窝,也像在笑,她在石凳上铺了一幅白布,让他爬来爬去。她说每天早上带他出来晒太阳,玩一小时左右,然后回去给他洗澡。这孩子动个不停。过一会,他又用双手双脚支着身体,好像在那里做掌上压。他看来健康又快乐,一看就知道是在充分的照料和爱护之下长大的。这屋邨倒是有这个好处。有孩子游玩和晒太阳的空地。
不过,我们的朋友说,这儿我屋宇將会逐渐拆去。街首那幢先拆,建成更高的大厦。然后她们住的街尾那幢,就会拆了。孩子踏在石凳的白布上,身上健康的皮肤反映着阳光的颜色。在他背后,街头那幢大厦蒙着阴郁的屏障,不知要建成怎样的新厦。
大厦间的空间更狭窄了。据说,这儿原来都是游玩的空地,但逐渐的,许多空地都划成车位。在挤迫的汽车占去的地方之间,这母亲和孩子悠闲地在石凳上坐一个早晨,晒这还未被挡去的暖暖的阳光。
我们散步回来,经过街头,看见圆满木板的建筑地盘外,那位修理水喉的守护神已经不在了。街头一半安宁,一半肮脏。街尾我们朋友住的那幢楼宇,仍是安安静静的关着门。过去她姐姐和姐夫在的时候,住在地下,我们常常过去玩,甚至搬了张凳子过去坐在门前叫门。有一次,他们开了罐头豆豉鲮鱼,在面摊那儿买了碟油菜,捧上来我们家吃宵夜。面摊好像已许久沒有开门了。近山边那儿,有人搭了木板,不要连青山也拆去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