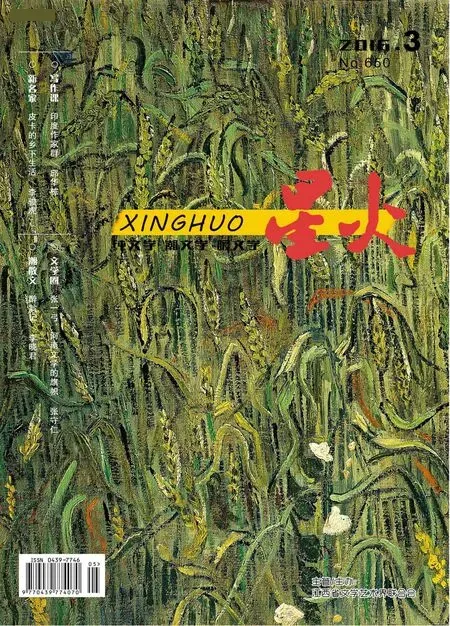摘茶叶
□阮家国

正月间,山里边又下了两回雪,好像还是在过冬天。按说,二月间天总该暖和了,可又下了桃花雪,天好像更冷了。这个老天爷,像是哪个把他得罪了,不是下雨下雪,就是板着个脸,好像不快活,害病了,又像有么子心事。节令倒是到了开春的时候,可山上地上倒像还没发青。
到了三月初,就又是一回事了,天上一连出了好几个大太阳。太阳一出来,天就一点都不冷了。太阳一晒,躲在地皮树皮里边暖被窝儿的嫩叶叶儿嫩草草儿,猛一下子就都拱了出来,一些个一下子叫不出名儿来的小花花儿,也都撵着撵着长出了小花苞苞儿。山里边这才开春,可也有发青发得慢的东西。山上的茅草,好像就还没发青,看上去,茅草还是灰扑扑的,还是去年的老茅草,可实际上新茅草芽芽儿也发出来了,只是叫老茅草遮盖着,还看不出来。
还有一样儿东西,发青也发得慢,就是茶叶,不到时候,太阳不晒够,新茶芽芽儿就发不出来。一进三月,有茶叶的人家心思都在茶叶上边,见天都得看看茶叶发没发青。
时候倒回去一点,杨云香早在二月底就开始看茶叶了。她家的茶叶都在门跟前的菜园里,有二三十蔸茶叶,每一蔸茶叶都像有一根绳绳儿,在拽她的眼睛。可在天冷的时候,茶叶哪儿发得了青,她一连看了好几天,连个小茶芽尖尖儿都看不出来。
天晴了茶叶该得发青了,可这时候好像也好不到哪儿去。晒了两个太阳,茶芽尖尖才冒出来针尖大一点点儿。眼看就要到清明了,也该喝新茶了,可这茶叶就是发不出来。
杨云香家住在车路边上,每天路上都要过不少车不少人。这天早上,她看到有人在买花花绿绿的清明吊儿了。今儿天才三月初五,隔着清明还有七八天,有人都在买给走了的亲人挂青的东西了。清明挂青讲究前三后四,就是清明前三天跟后四天给亲人挂青才妥当,唯独清明当天挂青好像就不吉利。
吃午饭的时候,有一个小货车从乡上跑来了,停在路边上,车上大多堆着清明吊儿。货主司机下车,点了根烟,蹲在路边上吃烟。眨个眼儿,有人就端着饭碗来了,买清明吊儿。那么多清明吊儿,还怕人买光了?杨云香才不端着饭碗去呢,不过,她还是把饭吃得快了一点。一搁下碗,她就去看清明吊儿。她发觉,今年的清明吊儿怪抢眼儿,颜色还怪花哨。这时候,好像就没人来买清明吊儿了。她跟司机说,你这清明吊儿做得还怪好看,多少钱一个?司机说,便宜,十一块。她说,这贵,还便宜?要得发,不离八,八块卖不?司机说,没见过挂青买东西,哪个还讲价。她说,多买几个卖不?好一下子,司机都没吭声儿,末了才说不卖,把车开走了。
杨云香随便朝山上看了一下,发觉树扒(树林)里边的青色好像又多了一点。朝回走时,她拐了一下,朝菜园走去,又看茶叶,先看路边上的一蔸茶叶。这蔸茶叶的芽尖儿才发出一点点儿来,只有一颗米长。她又进菜园里边去,一蔸蔸地看,有一蔸茶叶叫她的眼睛亮了一下,新发出来的茶叶芽尖儿有两颗米长了。
住在她菜园上边的汪翠芳在院坝边上跟她打招呼说,杨云香,茶叶发得咋样?她说,这茶叶发得也太慢了,简直发不出来。汪翠芳说,生娃儿的人不着急,抱腰的人倒急得不得了,看把你急的。她说,我急个屁呢。汪翠芳在院坝边上蹲下来说,我们这儿地势高,茶叶一时发不出来,下边的青龙茶场地势低,茶叶都要开园了。她说,哄人,哪儿有那快?汪翠芳说,哪个哄人?人家那边的人打电话说的,明天我们一路下去摘茶叶。她说,不晓得今年摘茶叶又是好多钱一斤。汪翠芳说,去年就是四十,今年少说也是四五十吧。她走出菜园说,那你明儿早上可莫忘了带我。汪翠芳说,到屋喝口水。她说,要是新茶,我倒想喝一口。汪翠芳说,那就快点去摘茶叶,茶叶不摘哪儿有新茶喝?
开春了,发青了,她们这些年轻女人心里也像在发青,毛毛躁躁的,好像不找点事做做就不安稳。茶叶都发出来了,她们不摘茶叶,就不安稳。
乡上有一个大茶场云峰茶场,云峰茶场下边又有好几个分场,每年清明前后,各个茶场少不了都要摘茶叶。跟针线活儿一样,这摘茶叶是手上的活儿,女人家天生有一双巧手。今年又快到清明了,她们又咋咋呼呼要给茶场摘茶叶。
杨云香记得,青龙茶场去年是清明前八天开的园,汪翠芳说青龙茶场明天开园,她就有点不信。只是她没想到,三月初七早上,汪翠芳比她起得还早,还悄悄跑了。她还指望着汪翠芳带她去摘茶叶,汪翠芳会骑摩托,她不会骑,家里也没买摩托。汪翠芳肯定是带别人走了,她打电话问汪翠芳,是不是在摘茶叶。汪翠芳叫她快去,她差一点点儿就有点动心了,可她还是没去。她看了一下天,天板着个脸,好像又要下雨,她就估摸着青龙茶场今儿天不得开园。
这天气叫她看透了,半早上的时候,天就开始下起毛毛儿雨来,没摘成茶叶的人都回来了。
杨云香心里盘算着,今天就到青龙茶场那边去,省得明天早上还要撵路。
摘茶叶可不是小事,是个秀气活儿,摘茶叶的人总得收拾收拾,穿着也该像一回事。吃过午饭,杨云香就烧水洗头洗澡,拿指甲剪儿剪了指甲。才剪的指甲刮划人,摘茶叶弄不好就会划了嫩茶芽芽儿,她又拿指甲剪压盖上的锉刀面儿把指甲锉了锉。跟着,她换了一身走人家才穿的衣裳,上身穿着桃尖儿领的粉红色羊毛衫儿,外边再穿一件八成新的杂色大花格子的休闲服,裤子是一条新蓝色牛仔裤。把自己收拾利索,她又把换下来的衣裳洗了。要走的时候,她还悄悄照了一下镜子。
屋里有一个板挎箩,每年摘茶叶,她就用这个挎箩。昨天,她把这个挎箩好好洗了洗,今天她又给背带儿上拴上了一截红绸子。她找了一条五块钱一包的烟、两瓶瓶装酒跟两袋点心出来,搁到挎箩里,跟婆子说,妈,我回娘屋去,屋里的事你就多操点心。婆子说,要得,回娘屋看看,就便儿好好摘几天茶叶。她没吭声儿,笑了一下,背上挎箩就走。婆子说,你拿个伞,招呼雨下大了。她想想也是,又回屋拿了个伞。
还亏得婆子叫她拿伞,走到半路上,雨就下大了。
她的娘屋就在青龙茶场那边,娘屋那儿的地势到底低些,嫩鲜鲜的新茶芽儿都发得怪匀净,能做芽茶了。她摸到一蔸茶叶边,摘下一个茶芽儿,搁到嘴里边嚼。新茶茶芽儿有点香,有点苦,还有点涩。
娘屋隔茶场不远,走出茶场的茶园,再朝下边走个两三里路就到了。怪,走出茶场,先头她嚼过的那个茶芽芽儿,嚼碎后却不晓得到底跑到哪儿去了,是吐了还是吞了。
下雨天天黑得早,一走到娘屋,天就要黑了。吃过晚饭,她也看了一下电视,把中央台新闻联播后的天气预报看完就睡下了。想到明儿是摘茶叶的大晴天,她一睡下就睡着了。
天还没亮她就起床了,听见她起来,也要去摘茶叶的舅母子也起来了。舅母子说,看把你急的,天都还没亮。她说,眨个眼儿,天不就亮了?
她们摸黑走到茶园边上,天才麻麻亮,有撵早摘茶叶的人进了茶园。茶场门头上的大灯泡亮着,里边也亮着灯,有人进去,有人出来。炮子在茶场大门口放响了,跟着,花子就在天上开出一朵朵大伞花儿,把天照亮了。茶场每年开园,跟县上机关新年头一天上班一样,都要放炮子放花子,图个吉利。
清明前后,茶场都要做一芽一芽的芽茶,摘茶叶要摘芽叶。每摘一个芽叶,不能拿手指甲掐芽叶叶根儿,手只能轻轻带上点劲儿,拿两个手指头逮住要摘的茶叶,轻轻一拈一拽,一个芽叶就摘下来了。手脚快的人,不拿一只手摘茶叶,拿一双手摘。杨云香就是一双手摘茶叶,两个手刷刷刷地摘。吃午饭前,人家大多只摘了六七两茶叶,她竟摘了一斤多。
今年茶场摘茶叶的工钱比去年长了一点,五十块钱一斤,杨云香在青龙茶场一连摘了三天茶叶,挣了六七百块钱。到第四天,三月初十,天又下起雨来。天气预报说初十跟十一两天都下雨,雨天自然不能摘茶叶。
摘不成茶叶,她就回去。到乡上顺路,她就便儿去买上坟挂青用的东西。清明吊儿七块钱一个,她先拿了四个,跟着又拿了四个,一共拿了八个。卖清明吊儿的店铺边上有人在打芝麻饼子,两块五一个,买的人还不少。一看就晓得,这芝麻饼肯定还好吃。她给了六个芝麻饼的钱,等了好一气才拿到手。才炕熟的热芝麻饼吃起来才香,看见有面的车过来,她就上了车。
婆子见她大早上买了芝麻饼回来,说,要得,省得我做早饭吃。吃两口芝麻饼,婆子说,这芝麻饼倒还怪好吃,又酥又香。她说,原来乡上没人打芝麻饼,先头看见就买了几个,你要是喜欢,我隔一隔就给你买回来吃。婆子笑眯眯地说,那哪儿划得来?人家打饼子总是要赚钱的,我们今天尝尝也就行了。老公公说,今天初十,眨个眼儿就是清明,前三后四,你买了清明吊儿,这两天去挂个青倒也要得。她说,今天也摘不成茶叶,我正准备去呢。老公公说,弯刀我昨儿就磨了,就是不该雨下大了,要不我也去。她说,伯(父亲),你年纪大,腿脚又不行,还是我去。
她把摘茶叶穿的衣裳脱下来,又换上进树扒砍柴的衣裳,穿上胶筒鞋,把挂青要拿的东西用塑料袋包严实,都搁到花挎箩里,把自己要吃的两个芝麻饼拿塑料袋装上,也搁进去,把挎箩背上,打上伞就走。
她从菜园边上过身,看了一下茶叶。几天没看自家茶叶了,茶叶新发出来的头一个芽芽儿都长足了,有的芽根儿又发出了一点小芽芽儿。
祖坟坟场有点远,在上边山上云峰寨的老坟场。云峰寨是早年大户人家躲土匪用的寨子,寨子东边山坡下有个卧凼,卧凼里有个水潭,水潭里的水是浑的,不晓得有好多年了,只是又不得干,又不得清。老坟场就在水潭里边,懂风水的人都说这儿风水好,就有不少人把祖坟朝这儿搁,这儿就变成了一个老坟场。林本树的爷爷、奶奶、太爷、太奶的坟都在这儿,林本树这几年在外边打工,挂青的事就甩给他媳妇杨云香了。清明前,来坟场挂青的人还不多,只有几个坟上挂上了清明吊儿。
祖坟坟堆子上爱长荆棘茅草,去年腊月间,杨云香就来砍过,才过了两个多月,坟上就又长满了草草荆荆的东西。好在有老天爷帮忙,雨又停了下来,她拿上弯刀,先从太爷坟上砍起,一连把四个坟上的茅草荆棘都砍干净了。这时候,她歇了一下,就便儿看了一下别人的祖坟。她看了一眼林本清的四个祖坟,前几年,每回来上坟,她也就便儿帮他收拾过。林本清是林本树的远房兄弟,原来跟林本树家是邻居,从山里搬走八九年了,好像在哪儿做么子生意。他当然没请过她帮忙上坟,只是她见不得熟人的祖坟没人管,一看见熟人的祖坟没人管,她心里就过不得(过不去),她帮他一下也只是就便儿的事。刀快,砍点东西也只是眨个眼儿的事,她就又去帮林本清一下,把他祖坟上的东西也砍了个干净。挂青先要叫先人晓得,跟着就要给祖坟放炮子,烧纸。炮子是两百响的便宜炮子,她给各个祖坟都放了一封,烧了纸,挂上了清明吊儿。她留了一封炮子跟一墩子火纸,在林本清的祖坟前放了炮子,给他的每个祖坟烧了一点纸,又挂了清明吊儿。
离开坟场,她看了一下手机,时间已到下午两点多钟了。她这才觉着肚子饿了,早上她没吃早饭,原本就想把两个芝麻饼当午饭吃。她拿上芝麻饼嚼,手机好像叫唤了一下,是来了一个短信,可这个短信却又叫她不敢相信。短信跟她说,她已交纳五百块钱话费。
说起手机,她大多是用来接电话,轻易不打电话,话费一年也用不了多少,顶多也超不过五百。她的手机话费从来也都是自己去乡上交的,哪个人还会一下子给她交这多话费?肯定是哪个交错了,这才叫她捡了个大便宜。好像是天上猛一下子掉下一捆钱来,就掉到她脚边上,她觉着人家给她交话费这事还真稀奇,也太怪了,就想叫林本树也晓得,给他打电话,可他手机却关了,大概是没电了。
雨又下了起来。嚼又一个芝麻饼时,她又想,这才怪了,哪个交话费又交得错,可哪个又会给她交话费呢。想来想去,她都想不透,哪个还会给她交话费。看来,八成儿是哪个请人交话费,去交话费的人却又交错号了。
晚上,林本树打电话来,问她有事没。她说,我今儿去给祖坟挂青了,给你说一下子。林本树说,今天屋里没下雨?她说,下了,下得还不小。林本树说,那你还去挂青?她说,下雨不去,还大晴天去?天晴好腾空儿摘茶叶。林本树说,你倒会算账,呃,屋里茶叶摘没摘。她说,今年茶叶发得慢,再说又不做芽茶,过了清明再摘,等茶叶做出来,我给你寄一点。林本树说,莫寄,我们这儿人多,你寄来又哪儿喝得成,我能不给人家喝?哎,这说话就是钱,也莫多说了,挂了。她正要跟林本树说,他咋不问一下在乡上中学读初一的儿子学习咋样,还要给他说个稀奇,说说人家给她交话费的事,哪儿晓得他倒把电话挂了。
早上,天又下起毛毛雨来。毛毛雨有一下没一下地下,倒像有么子心事。
这时候,杨云香已到了乡上,她来到手机交费点,看自己的话费还有好多,一看竟然还有五百多块钱。要是有人交错话费,那当天人家不就会找到交费点把交错的话费转走?怪,这才怪了,出稀奇了。
云峰茶场隔云峰寨不远,那儿山高,茶叶定在清明开园。云峰茶场今年搞得怪,摘茶叶还要灵便人。杨云香从乡上一回来,汪翠芳就撵来说,你说稀奇不稀奇,云峰茶场给组长打电话说,上去摘茶叶的人又要长得顺溜,又要穿得顺溜,还要身上没怪味儿。她说,我看人家这样搞也不是要不得,脏手脏脚的人,又哪儿能去摘茶叶?汪翠芳说,你说这话,好像你就是人家茶场的人。她说,我心里还真是这样想的。汪翠芳说,茶叶是个嫩东西,做茶叶又是个细活儿,从摘到做,一顺溜儿的都得过细,不管咋说,人家云峰茶场的人脑壳儿还真灵便。
到云峰茶场有二十里路,杨云香起了个大早,摸黑朝上走,路上遇到撵早进城的面的,她也没搭车。搭个车上去,得花十块钱,她还真舍不得。半路上,汪翠芳骑着摩托来了,屁股后边带着组长的媳妇儿。汪翠芳叫她上车,她嫌挤,叫她们走。
她倒是没想到,眨个眼儿,汪翠芳又回来接她。
云峰茶场今年把开园摘茶叶怪当回事,还给他们看得上的摘茶人发采茶证,拿到采茶证的人才能进茶园摘茶叶,还给隔家远的摘茶人提供吃住,这倒给杨云香省了个事,省得她又要在这儿找歇处。
清明后天气好,杨云香在云峰茶场一连摘了三天茶叶,每天摘茶叶挣的钱比在青龙茶场挣得还要多。第四天早上,有一个小车开进了茶场。汪翠芳说,又是哪个领导来买茶叶。杨云香说,我们只管摘茶叶,还管哪个领导来不来?汪翠芳说,领导该不会来看我们摘茶叶吧。杨云香说,你是在做梦吧。汪翠芳说,要说做梦,还真说不清,一点都不相干的事,可人有时候不还是梦见了?杨云香不吭声儿,反正她没梦见过一点都不相干的事。过一下,汪翠芳就咋呼起来说,杨云香,快看快看,你小叔子林本清回来了,茶场的叶经理陪着来看我们摘茶叶。杨云香就愣了一下,摘茶叶的手有几下就没逮着茶叶。她有好几年没看见林本清了。
叶经理陪林本清来看茶园,看人摘茶叶。来到杨云香她们摘茶叶的点,他们多站了一下。林本清跟老邻居们打招呼,末了儿跟杨云香说,你能不能耽搁一下,跟我去一下云峰寨?杨云香说,我在摘茶叶呢。林本清说,你摘茶叶手可真快,那你先摘茶叶吧。他们开始朝茶场场房走,叶经理跟林本清说,你这个嫂嫂儿可不简单,摘茶叶还数她手快。这边,汪翠芳说,杨云香,叶经理在说你呢。杨云香说,一心无二用,莫管那些,我们只管摘茶叶。汪翠芳说,呃,我记得,林本清比你大两岁,哪怕他是你小叔子。杨云香说,他比我大,还不是我小叔子?你嘴也太多了,咋都说些有油没盐的淡话?
又过一下,茶场的一个副经理来叫杨云香到场房去,说保证一点都不耽搁她摘茶叶。杨云香这才动身,等她走拢,副经理说,你咋要得?一天到晚只晓得挣钱,连亲戚家门都不认了,你小叔子可是市里一个大公司的大老板,他请你帮个忙你都不肯。叶经理说,从今儿天起,给你三天时间,你陪陪林总,你摘茶叶的工钱就按昨天的算。她只陪陪小叔子,每天就能拿摘茶叶的工钱,副经理跟她说这话,她倒还怪喜欢听。
林本清自己开车,他的黑色小车看起来肉乎乎的,杨云香还是头一回坐他的车。车子出了场房,朝云峰寨去,他要先去挂青。车子只能开到寨脚下,他把车靠边停下,从车屁股里拿出挂青的东西。挂青的东西堆了一大堆,有三筒花子,八封一万响的浏阳花炮,十六墩子火纸,还有十六个五颜六色的清明吊儿。这多东西,两个人拿手拎难得拎。杨云香就去一个人家屋里借了一担花箩筐,把东西朝两只箩筐里一匀,拿扁担把箩筐系一绾,躬身就挑。林本清要挑,可他的手机又叫唤起来了。先头在车上,拃把远一截路,他就接了好几个电话。这回他挂了电话说,手机有时候还怪烦人。他干脆把手机关了,去撵挑东西的杨云香。挑东西的挑子重倒不重,可她还是怕小叔子不会挑。他横直要挑,杨云香也只得叫他挑。上云峰寨的小路因走的人少,并不好走,每走几步就有荆棘挡路,可林本清挑挑子并不费劲儿,遇到有东西挡路,挑子一磨就磨过去了,这倒叫她没想到。她说他,我还当你不会挑挑子了呢。他说,笑话,就是挑一挑水上去,我也不得洒一滴出来。
清明过了,老坟场上的清明吊儿都挂满了,看起来怪花哨。
三筒花子,林本清先在老坟场前边点响一筒,跟着在他的祖坟前点响一筒,又在林本树的祖坟前点响一筒。杨云香看着花子在云峰寨的天上炸开一朵朵红红火火的大伞花儿,看得有点出神,她还从没在大白天看过炸花子,更没在云峰寨看过。林本清给他的各个祖坟,放了一封炮子,跪着磕头作揖,烧一墩子火纸,挂上两个清明吊儿。对林本树的祖坟,他也一样对待。每回烧纸,她都帮他烧。给祖坟挂完青,他问她,我回来得少,祖坟亏你招呼着,你是哪天来挂的青?她说,有好几天了,那天是个雨天。他说,雨天你还来挂青,你可真舍得自己。她说,不是雨天,我也不得淋一身湿,晴天要摘茶叶。他说,呃,你屋里头道茶摘了没?她说,这几天都不在屋里,还不晓得茶叶发没发好。他说,那我们就去看看。
等杨云香还了扁担箩筐,林本清又把车朝老家开。杨云香记了时间,从云峰寨回去,车子只跑了十分钟。林本清把车磨到路边,从车屁股里拿出一个袋子跟一盒儿茶叶,拎上。茶叶是云峰茶场的新芽茶,袋子里边是一条烟跟两瓶酒。林本清来看杨云香家两个老的,她的老公公跟婆子咋呼说,本清你来玩就是,咋还拿这多值钱的好东西,要不得要不得。婆子要拿挂在墙上的腊肉弄饭待客,林本清叫莫弄,说有点吃饭,杨云香也说是这回事,婆子这才没动手拿肉。
林本清去看杨云香家的茶叶。几天没看,茶叶芽子都发起来了,大多都发出了两个芽子,有的芽子都快长成叶子了。林本清说,这茶叶再不摘就老了。杨云香说,是得摘了,明儿早上就摘,这头一道芽子正好做毛尖儿茶。他说,唉,你说怪不,我现在倒想喝点手工灶儿茶叶。她说,手工灶儿茶叶哪儿有茶场做的机制茶好喝?他说,你做的茶叶就好喝得不得了,那个时候,我就最喜欢喝你做的茶叶。她说,哪儿晓得你现在还喝得惯不,可我们不喝不行,茶场的茶叶越卖越贵,做的都是机制茶,动不动就是好几百块钱一盒,一盒还只有五六两茶叶。他说,那倒是,卖包装嘛,可我是真想喝手工灶儿茶叶,等你把茶叶做出来,我可要买两斤回去。她说,我算是懒得卖,头道茶也只做得到两三斤,你买去我们还喝不?你哥他就喝不成。他说,那我就跟你换,拿四盒茶场的茶叶换你两斤茶叶。这时候,她的手机叫唤起来,是叶经理打来的电话,说林总关机了,请他们上去吃饭。她跟他说,我就不去了,在屋里准备一下,明天好做茶叶。她是怕人家摘茶叶的人瞎说,说小叔子一回来,她都能跟着沾光吃席面儿了。他说,还是一路去吃,下午我送你回来就是。看来,她只得陪他到云峰茶场去吃午饭。
陪客吃饭,杨云香最怕人家劝她喝酒,好在茶场的人不晓得她的深浅,她不沾酒,只喝饮料,算是躲过去了。林本清就躲不过去,他是主客,尽管挡来挡去,可还是喝了不少酒。饭吃了一个多钟头,饭后,叶经理叫林本清打麻将,说有洗牌快的新麻将机。林本清就要打牌,还要杨云香也打。杨云香说,你在这儿玩,我回去有事,再说你们现在打么子“卡五星儿”麻将,我又不会。他说,看两圈不就会了?不打也行,你就在我手上提成儿。她说,我还是回去。他说,那你骑摩托回去?她说,我没摩托,也不会骑车。他说,我正好有个小木兰,一直闲着,干脆你拿去用,后天你跟我一路出去,我教你骑车,木兰又好学,一学就会,学会了你就把木兰骑回来。她说,那还不好?我就去你那儿把木兰骑回来。看她真在走了,他又去开车,撵上她,叫她上车。她说,你莫送我,人家等你玩呢。他说,你看我喝了酒,不敢坐车吧?放心,我只喝了一点点儿,没事。她上车说,喝酒开车违法,招呼交警扣你的车。他说,这儿山高皇帝远,交警都在城里。
下车,杨云香看着林本清倒车,看见他把脑壳从车里伸出来看了她一下才走。她就愣了好一下子,一直看着他的车,直到看不见了。
她拿手机看了时间,没直接回屋,拐了一下,朝菜园走去,又去看茶叶,一蔸蔸地看。过十几分钟,她给他打电话,问他到了没。他说,早到了,都打一圈儿牌了,呃,你这个电话倒还真打得好,我又是大和自摸。他在打麻将了,她的心这才放下来。
明天得起早摘茶叶,茶叶一摘紧跟着就要做,今天有不少事都先要做出来,摘茶叶、炕茶叶、揉茶叶的东西都要洗干净。杨云香先把摘茶叶的挎箩、篮子、揉茶叶的团笸擦洗干净。她有一个专门用来炕茶叶的锅,她把这口锅找出来,先拿清洁球攒劲儿磨擦,又拿干丝瓜瓤子磨擦,再清洗干净。
晚上,汪翠芳来玩,拿塑料袋给杨云香包了一点新茶,叫她尝新。汪翠芳不会做茶叶,她家的新茶是她婆子今天才做出来的。杨云香就拿个玻璃杯泡了一杯,开水一倒下去,就有碎黑煳末末儿漂起来,一看就晓得,这是炕茶叶的锅没洗干净。头道垢甲二道茶,她把茶水倒掉一半,再把茶水倒起来,茶味儿就出来了。她喝两口茶说,口味儿倒还要得,也有劲儿。汪翠芳说,大平常喝,也就那回事,呃,你明天摘茶叶不?她说,摘呀,再不摘就糟蹋了。汪翠芳说,瞎扯,上不上云峰茶场?她说,后天再去。汪翠芳说,也不陪小叔子了?她说,摘茶叶都忙不过来,哪儿有心思陪他。她晓得,这几天她摘不摘茶叶,云峰茶场都要给她工钱,这事汪翠芳还不晓得,她也懒得说。她怕汪翠芳嘴长,还有,人家给她交话费的事,她原本也想给汪翠芳说一下,可也没说。汪翠芳说,林本清哪天走,你叫他把我带上,我进城有事,手机也坏了,得修一下。她说,你自己给他说就是,又不是认不得他!汪翠芳把她看几眼说,你说怪不,你也是生过娃儿的人,你那个腰咋还细得不得了?她说,汪翠芳,你又在怪嚼(说话)。汪翠芳把杨云香一拽,嘴对着她耳朵说,你那小叔子好像怪喜欢你,一看他看你那个眼神,我就晓得。她不吭声,右手悄悄去掐汪翠芳的肋巴骨,可哪儿来得及,汪翠芳早有防备,跑开了。跑到她家院坝边上,汪翠芳还在说,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这回事。
明天摘茶叶,家里人人都得早睡早起。老公公去上茅厕,杨云香跟婆子说,妈,你叫伯把手拿肥皂好好褪两道,明天早上再拿清水洗两道。婆子说,你不晓得,你伯那手爪子平常就没好好褪过,我还就怕摘茶叶坏事,先头就叫他褪了,褪二道时,水都是浑的,又多褪了一道。
天麻麻亮时,杨云香先下地摘茶叶,她怕婆子他们这时候眼睛看不好,叫他们晚一点再来摘。等他们来摘时,她又说,伯,你摘慢点,可莫把茶叶芽子摘得囫囵半块的。老公公说,我手笨,就是想快都快不起来。
半早上的时候,林本清来了,要摘茶叶。杨云香说,你手干净不?林本清摘茶叶的手就缩回去了。杨云香说,你哪儿摘过茶叶,莫摘。林本清去把手洗了,又来摘茶叶,说,怪不得,这摘茶叶还真是个细活儿,没摘过真摘不好,茶芽芽儿不是摘老了就是摘嫩了。她说,你摘得也怪好的,呃,今儿又是哪儿接你?他说,午饭在青龙茶场吃,乡上也得吃顿饭。她说,今儿要做茶叶,也顾不得招呼你,你莫怪。他说,那你到乡上吃晚饭,到时候我来接你。她说,你可莫来,这做茶叶一做就会做到大半夜。他的手机在叫唤,接过电话,他说,算了,我哪儿都不去,就在这儿看你做茶叶。她说,那有个么子看头,不过就是下锅杀青,揉搓,摊晾,再回锅炕干。他说,说起来简单,真做起来可不简单。她说,客随主便,你赶快走吧。他说,这吃个饭倒还搞得怪烦人的。
茶叶清一色摘的是一大一小两个芽子。茶叶摘完,杨云香拿秤称了一下,一共摘了十三斤双芽茶。手工灶儿做茶叶全靠火候,火候又要看做茶人的心劲儿跟手劲儿用得是不是在点。等把茶叶做完,都到半夜了,她又称了一下,一共做了四斤三两干茶。今年的头道茶总算做出来了,她泡上一杯酽茶,先把茶卤儿泡出来,滗掉一点,再倒开水进去,看茶色。杯里的茶水清清淡淡,茶色怪好。她抿一点,咂咂嘴。清香味儿还在舌头上,口感也怪好,茶也有劲儿。泡茶的玻璃杯是林本清昨天给她的,杯子身上印着字儿,一看就晓得是云峰茶场在人家茶杯工厂定制的杯子。
她喝了一杯酽茶才睡。今天她太累了,哪怕喝了酽茶,可还是眨个眼儿就睡着了。
早上天一亮,林本清就来了。杨云香却不在屋里,他问婶娘,杨云香到哪儿去了,婶娘却不晓得。婶娘见他手上拿着个空玻璃杯,给他泡了一杯酽茶。他给她打电话,她的手机却关机了。婶娘把一袋子茶叶给他,说,媳妇说你好多年不来,给你一斤手工灶茶叶。茶叶拿有封口的塑料袋封了三层,封得严严实实。他把茶叶搁到身边的一把空椅子上,说,我还要换你们两斤茶叶。婶娘说,媳妇儿她没说这个话。
这时候,汪翠芳来搭车,听见这话,说,杨云香也真是的,人家拿机制茶换她的手工灶儿,她都不换。汪翠芳见人自来熟,又说,林本清,你要是看得上我家的手工灶茶叶,我跟你换就是。林本清说,不换就不换,本来就是说着玩的。林本清看看汪翠芳说,你今天穿得还怪顺溜。汪翠芳扭扭身子说,不瞒你,我这可是出门才穿的衣裳,轻易不出门,出一回门儿还不穿好一点?林本清说,你穿得简直都像个新媳妇了。汪翠芳说,你可莫再贬损我了,我脸都红了,你没看见?汪翠芳把林本清搁在椅子上的茶叶跟茶杯拿起来说,我给领导搞服务还不行?今天我就好好给你当一回服务员。
实际上,这时候,杨云香就在屋后边的树扒里,躲在一坨青枝绿叶儿下边,看见林本清的车走远了,她才回来。
不用说,她晓得林本清多她心了。本来,她已答应林本清,今天跟他一路进城,可她又躲了起来。本来,她还想单独问问他,她的五百块钱手机话费,是不是他给她交的。这几天,她一直在想,话费是不是他悄悄交的,要是他交的,咋又不说,到底在搞么子名堂?本来,昨天在他送她回家的车上,她就想问,可她好像有点晕车,有点困,倒打起盹来了。迷迷糊糊时,好像有人就摸了她一下子。她就坐在他边上,这个摸她的人不是他,还是哪个?他这一摸就把她摸醒了。
她又换上干净衣裳,背上昨天摘过自家茶叶的板挎箩,去云峰茶场摘茶叶。一走上车路,就有面的车来,她就上了车。
车走到她恍惚记得的那个点,她又把昨天在车上的事想了起来。
能看见茶场了,她就下了车。茶场里外都没看见林本清的车,她这才朝有人摘茶叶的茶园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