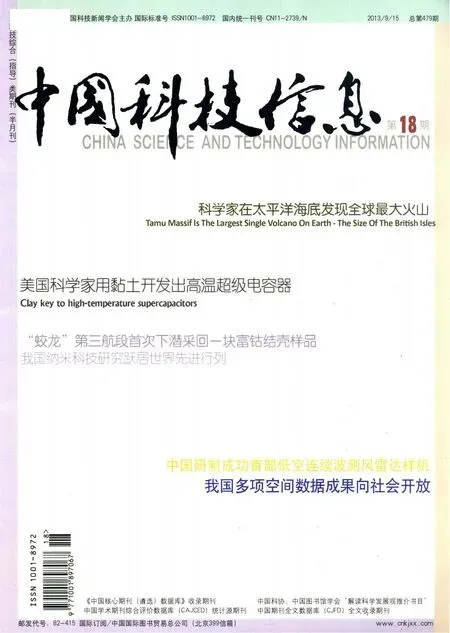未来生物战场上的“杀手锏”——动物生物武器
张建宏 刘颖丽
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兽医研究所
随着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未来战场的战争方式逐步呈现多元化。近年来,各国研制的无人战机、无人履带战车、机器人士兵等一系列新式武器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传统以人类为主体的战场作战模式。可以设想,动物作为生物武器作战将是未来生物战场的趋势所在。
1 什么是动物生物武器
所谓的动物生物武器是指专门针对动物或是通过动物来袭击人类的生物武器。具体来说,它是通过采用现代生物技术手段,改造各种动物源病原体做生物战剂、利用动物作为媒介进行传播病原体以及用生物技术武装的动物本身作为攻击人类武器的总称,从而造成他国重大经济损失、人员伤亡,达到扰乱社会秩序,恐慌人心的目的。
动物生物武器之所以可怕,不仅在于它具有令人胆战心惊的杀伤力,还在于它是一种廉价、方便,且难以预防的“杀人工具”。生物战剂所需的原料一般来自自然界,成本较低,而动物资源丰富,流动性强,因此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同时使用方法简便,隐蔽性强。经过特殊处理之后的细菌、病毒和致病基因组成的多种微生物,可直接用于动物生物武器。由于各种新发、突发人畜共患病和外来病的流行趋势日益增加,且传染病的流行具有潜伏期,早期不易发现,导致大面积爆发。此外,动物生物武器危害时间长,作用面积大。由于动物包括野生动物数量多,可长期保存这些生物战剂,并随着动物的迁徙和活动而将生物恐怖范围扩大。
2 动物生物武器的类型
利用训练有素的动物参战助战,古今中外不乏先例,古天竺国的大象军团在战场上力大无比、势不可当;我国明代曾利用训练有素的猴子火枪队抵制倭寇、消灭敌军;二战时期纳粹的装甲雄师曾横扫西欧、所向披靡……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动物在未来战争中将以全新面貌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动物在生物战中分为以下几种不同的类型:
3 转基因的“动物士兵”
将破译出的可攻击人类的物种基因转接到同类动物体内,其繁育的后代将成为具有攻击性的“动物士兵”,在未来生物战中扮演恐怖杀手。如果将具有攻击性和杀伤力的南美“杀人蜂”、“食人蚁”、“血蛙”、“巨蛙”等新物种的残忍基因转接到普同类物种身上,再不断克隆复制这些带有新基因的动物,它们就可以成为“动物杀手”。也许这样的场景将来不光只能在科幻电影中出现,即利用克隆技术使人类基因与动物基因结合,培育出具有特殊能力的非人非兽的怪物,将这种怪兽投入战场对敌方进行进攻,其作战能力是任何优秀士兵和武器所无法比拟的。
4 袭击动物的生物武器
使用动物作为生物恐怖袭击的对象具有社会道德压力小、隐蔽性强、危害性大的特点,因此针对动物使用的生物武器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大。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军队就试验过用动物鼻疽和炭疽病的病原体感染协约国的军马,使大批军马倒毙。而在2006年到2007年期间,美国35个州的人工养殖蜜蜂不约而同的离奇失踪,使养蜂业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后经调查发现,美国1/3的蜂群受到一种名为“以色列急性麻痹病毒”的袭击,这是以色列用来对付伊朗的基因武器中的一种。
5 人畜共患病类生物战剂
通过人为将染有传染性病人兽共患病病原体释放,使敌方人员染病而减员,是生物恐怖的主要方式之一。随着基因组学的进展,许多人兽共患病病菌的完整基因序列已经发表,意味着这些天然的细菌和病毒不仅可以直接作为生物战剂,而且通过基因重组改造成威力更大的新型生物武器。2006年,美国在普通酵母菌中接入一种在非洲和中东引起“裂谷热”细菌的基因,从而使变异的酵母菌可以传播可怕的裂谷热病。如果将艾滋病毒、炭疽杆菌、鼠疫杆菌,甚至流感病毒等都制作成生物武器,这些“生物原子弹”足以毁灭地球。
6 动物毒素基因武器
动物毒素是有毒动物为了防御和攻击而产生的可引起中毒的物质。河豚鱼的毒素毒性相当于剧毒药品氰化钠的1250倍,只需要0.48毫克就能置人于死地。类似的动物毒素还有蛇毒、石房蛤毒、蜂毒、蝎毒、蜈蚣毒等。毒素的这种剧毒性、快速性、稳定性以及获得的方便性,符合生物武器特点,特别是通过基因技术增强天然毒素毒性,发展新的毒性更强的混合性毒素。俄罗斯已研究剧毒的眼镜蛇毒素基因与流感病毒基因的拼接,试图培育出具有眼镜蛇毒素的新流感病毒,它能使人既出现流感症状,又出现蛇毒中毒症状,导致患者瘫痪和死亡。

7 生物武器中的动物媒介
媒介即在传播人与人之间或人与动物之间的疾病中起作用的有机体。由于动物本体防护弱,流动性强,因此在生物恐怖中,动物作为媒介传播疾病有着得天独厚优势。目前世界上可能用于生物武器的媒介动物主要有节肢动物、鼠类和鸟类等。在抗日战争和朝鲜战争中,日军和美军都曾用带有传染病菌的跳蚤、蜘蛛、蚊子、苍蝇、蚂蚁甚至老鼠等,来传播鼠疫、霍乱、炭疽杆菌及其他传染病病菌,造成中朝军民数万人死亡及传染病流行。美国在2002年曾报道,美国的西尼罗病毒有可能来自古巴生物武器实验室放飞的被感染的鸟儿,然后直接或间接把这种病毒传染给人。人类会不会有一天将生活在见到任何生物都恐慌的时代之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