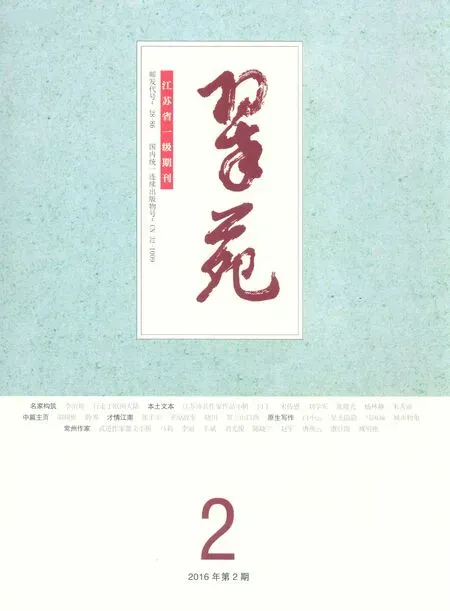旷野书
■赵文珺
空心树
那棵树,就站在小水渠的边上。或许,是它的奇特吸引了我,或许是其它。事实是,还来不及细想,脚步已经过来了。
30年,或是40年前,(这不是一个记得很准确的数字。总之,我离开已经太久了)这里曾是我们的乐园。不远的地方,曾有一个巨大的蓄水池,我们管它叫“涝坝”,或是叫“涝池”。它是供我们全村人吃水的地方。我们这里历来缺水,童年或是少年,关于水波荡漾或是波光鳞鳞之类词语的理解,就全凭这一池蓄水了。
冬天,涝池是我们的游乐场。我和弟弟每天的一项任务,就是去涝池里抬水。看着一寸一寸的水结冰,小鱼、小虾、水草,一点一点地被冻到水底。直到有一天,整个的涝池,冻成了一面光滑如玉的镜子,抬水就不再是痛苦的事情。借此机会,要在冰上尽情地玩一会儿。当然,最主要的项目就是滑冰了。
站在高处,一个俯冲,就能像飞一样地冲出好远。那种感觉,就像在飞。那个年龄,常常梦见自己在飞。在梦中,自己就像一只长着翅膀的大鸟,轻轻地从村子里飞到田野上,再飞到树梢或是小土包上。大人们说,那是孩子在长个子。后来,在某一年看了《泰坦尼克号》时,看到男女主人公站在船头,做飞的动作时,自己就不由地想起,小时候自己滑冰的感觉。不过他们可能还有爱情的感觉在飞,而我,是整个童年在飞。
奶奶在院门口的大树下大声喊我们。弟弟做完了最后一个前后翻飞的滑翔动作,刚想走,却又跌了一个狗吃屎。
这些情景,都被旁边的一棵大柳树,看得一清二楚。它常年守在涝池边上,吸收了水分,总比别的树长得大一些。
春天,它第一个发芽。我们折了它的枝条,拧成柳笛,“呜哩哇啦”,乱吹一气。少年时光转眼之间被吹得没了影踪。
夏天,姑娘媳妇们攒在树下做针线。飞针走线之间,一对漂亮的鸳鸯,悄悄地游进了涝池的水中。
小时候,我有浓密而茂盛的头发,两条辫儿又黑又长。大姑娘的一项工作,就是给我编各种各样的辫子,我则天天顶着她们的佳作,四处招摇。
那时,柳絮飞扬,树婀娜的影子和姐姐们年轻而美丽的脸盘,映在池水之中。有邻家的哥哥在偷偷地向这边张望,姐姐的脸盘若红霞一样的好看。但那时我不知道,世上还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样形容女子的美好词语,否则,我一定要念给她们听。
待我20岁离家的那一年,那棵树已经长得有两人合抱那么壮了。它枝繁叶茂,正处盛年。
后来,各家的地头装上了自流节水井,涝池一天天地干枯了。
柳树,也开始一天天地枯萎起来。起初,只是大片大片地掉叶子。后来,树头悄悄地死了,并在一个大风的夜里,一个跟头栽了下来,扑到了没有了一滴水的涝池里。它和涝池完成了最后一个热情的拥抱。
渐渐地,树干开始腐烂。一些地方,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大窟窿。一些不知名字的虫子乘机衍生出来,树干被它们一口一口啃噬。吃饱了液汁,它们无处可逃,就死在了树杆里。有了臭味,又吸引了苍蝇、蜜蜂等其它各种虫子,它们以相互残杀的方式,开始大块吞食这棵树。
终于有一天,这棵树的树心完全空了。
没有了心的树,如没有了心的人,已无所谓痛或是不痛了。看过电影《胭脂扣》。当如花以鬼的形式,到人间来寻找她分别50年的十二少的时候。她已经感觉不到心痛了,因为她是鬼,没有人的心跳或是痛苦。50年的光阴,她在阴冷的地下等待,原来相约的恋人却根本就没有遵守诺言,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梦而已。
好奇的孩子们,发现了这棵奇怪的老树。不知谁带头,从根部的一个窟窿里把这棵树点着了。
浓烟四起,一股怒火从树杆中间,冲向了树枝,又在分叉处的一个窟窿里愤怒而出。
孩子们吓得一轰而散。树,就这样被烧成了一棵真正的空心树。
此时,它无语地望着我。一些枝条,顽强地伸向天空。
我知道,这棵树,它如这个村子所有的生命一样,只要有一口气,它就会活下来。
远处,我空荡荡的村子,在寒风中静默着。年轻人都外出了,村子也如一个空心的树一样寂寞地疼痛着。
芨芨草
我家的场院里,有大大小小,十几个芨芨编的背篓、提篮。这些物件,有数十年的历史了。大的,可以背草、背粪,小的用来提草、盛菜。
奶奶在世的时候,无论春夏秋冬,只要她走出院门。手里或是背上,总是挎着或是背着它们,它们好似奶奶的标志。
春天,奶奶和她的提篮,一同行走在寒风料峭的田埂上。苣苣菜、猪耳朵、野苜蓿……,在奶奶灵巧的手里,一个又一个跳进提篮里。青嫩无比,漂在我们晚饭时的粗瓷碗里。麦苗长高,奶奶提着小篮子,俯在麦地里薅草。青青麦苗,齐声歌唱。杂草心慌意乱地从风的间隙里逃走。麦地里,留下奶奶走过的长长痕迹。芨芨草迎风而舞,燕子在远处人家的屋檐下呢喃而歌。
秋收时节,收割过的麦田里,总有一些遗失的麦穗。我和奶奶,背着芨芨草小背斗,顶着毒辣的太阳,把一个又一个金黄麦穗捡进背篓。拿回家去,用一根粗粗的木棒捶了。那珠玉一样的麦粒,躺在簸箕里。奶奶用芨芨草烧火,给我们炒青麦子吃。小花狗闻着香味,丢丢地跑过来,悻悻地看一眼,又懒洋洋地走了。
冬天,场院里堆满了麦草。奶奶和妈用一把老铡刀把草细细铡碎,堆在草房里。用一只硕大的芨芨草背斗,背了给另一个院里的老黄牛吃。它正奶着小牛犊呢,小牛犊还不会吃草,就连青青的苜蓿,也引不起它的兴趣。
场院的一角,冬日的阳光暖暖地晒着。村里的老九爷,正在给我们编新的一批芨芨筐。他可是这个冬天里最吃香的人。编的芨芨筐,光滑平正,美观大方。有时还能在边上编一两个花样子。那些芨芨草,都是奶奶和妈在秋后的田埂上拔来的。饱满,平直。水里泡过,使它柔软。然后,就由九爷一根一根编成筐子、背斗、席子、草蓠芭等各种各样的用品。有时,我站在旁边给他捋芨芨。他三下五除二,就会给我编一只小羊或是小狗,还会给我扎个草项圈,让我戴在脖子上玩耍。
夜里,老九爷睡在草房子里。他是老光棍,也无所谓家或不家的,一个简单的手艺,就能使他整个冬天不至于挨饿受冻。冬天的农家,有许多筐子、背斗、篱耙要编,还要扎扫帚。一个村子里忙下来,漫长的冬天也就基本上过去了。但他也从不在人家屋子里睡。夜里,就和那些芨芨们睡在一起。他熟悉那些芨芨的脾性。他知道喷多少水,才能使芨芨变得柔软,使多大的劲,才能使那一根根强劲的芨芨,成为自己手里游刃有余的材料,然后编出富有浪漫气息的筐子或是提篮。
寒冷的夜里,他一遍又一遍地抚摸那些芨芨草,唱一些谁也听不懂的曲儿,“一根竹竿一十二个节,小男子出门一十二个月……”。奶奶说,那叫《小男子出门》。不过,还有一只老黄狗一直陪着他,他到谁家,那只狗就跟到谁家,一声不吭地蹲在九爷脚下。
一家编完了,九爷收拾简单的行头,和他的老黄狗到另一家去了。
那些筐子、背斗,就崭新新地挂在每一个农家的院子里。
农闲时节,人们的一项任务就是上地拔芨芨,没有一根芨芨被闲置着。没有一丛马莲草,不被勤劳的农人收拾到自己的家里。
而如今,那样的日子早已远去。地头上,到处都是荒芜的芨芨草。它们披头散发,任由寒风吹破了它们一个又一个完美的梦想
老一辈人,渐渐地走了。春种夏收都基本机械化。秋天,人们草草地收拾完庄稼之后,就急急地外出打工了。外面的世界,总有太多的诱惑与机会。那里,能捞来比土地多几十倍的财富和梦想。
田埂上,芨芨草、马莲草,连同那些遗失在麦地里的麦穗们,在寂寞的风中,一天天干枯、腐烂。村民们,不再以前辈们固有的方式,做一个认真打理田地的农民了。
一部分人,已经搬到了新的居民点。那些红顶、白墙、绿栏杆的小洋房,很像乡村里打扮洋气的待嫁女子。敲锣打鼓之后,不知道她们到底要远嫁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