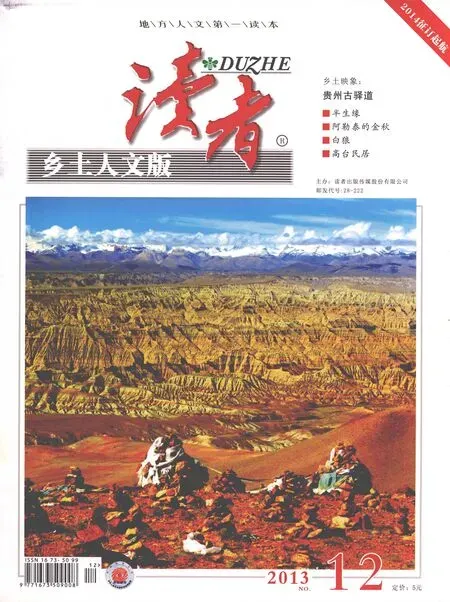山村里的故事
文/郭永明
山村里的故事
文/郭永明

山 风
也许,山风是大山喂养的怪物,没有身影,没有腿脚。安静时,它温顺得像一只小猫,轻轻地吻你,舔你的肌肤,拂你的发丝,柔柔地给你的生命唱歌。你看不见它,只能感受到它的呼吸和凉凉的爱。
夏日的阳光如同刀子一般刺疼了它的个性,加上那一团团肮脏的乌云在它身上滚来滚去,它就张开血盆大口咆哮起来:
“嗬—嗬—”
几百里的森林,也同时一起一伏,“嗬—嗬—”
闭目凝听,仿佛天空失去了颜色,大地绷紧了神经。黄河决堤了,海浪惊天了,树消失了,山消失了,自己也变成了一片浪涛中的枯叶。
它不想吃掉什么,也不想摧毁什么。
它是在展示一种威力,一种气势,一种沉默者心中的怒潮。
蝉 鸣
谁曾想过,一只蝉和一位歌唱家的距离,一声声蝉鸣和海潮的距离。
蝉的的确确微不足道,指头般大的小精灵,薄得几乎看不见的彩衣,要不是两只发光的小眼睛和一张尖细的“嘴”,你简直看不出它们的影子!
它们伏在夏天的树干上,或者竹枝上,伏在人们的记忆里。一只、两只、三只……要是整个家族合起来,那谁也无法估计!
它们也是一个王国,一个紧密团结、同呼吸、共命运的音乐王国。
也许,深山里的阳光就是它们五彩的旗。信号一启动,数万只密密麻麻的小肚子都一起一伏,“吱……”节奏一致,音量一致,情感一致。于是,崇山峻岭,山上山下,山里山外,都一起轰鸣,如同排山倒海一般,“吱……吱……”
这声浪一天连着一天,一月连着一月。整座大山被炒熟了,每片树叶,每棵小草,甚至每粒沉沙,都灌满了清亮亮的音符。
天空的白云停止了飘动,林中的鸟鸣被压成了悲怜的露珠。
没有亲眼目睹这一切的人,还不知有多少乐队在深山里吹拉弹唱,敲锣打鼓。而我们山里的歌手们却没用一支笛、一支箫,没用过人间的任何一种乐器。
这支深山里的乐队太庞大了,简直可以和当代的明星对阵,与任何一个国家的乐队对阵,与大海的潮声对阵……
你们难道不感到自豪吗?我深山里小小的歌手们!
大山里的月亮
月亮跟大山是亲戚,也可以说是邻居。
大山离月亮很近很近,仿佛就在自己的家里。山里的人说话、唱歌,以至炒菜、睡觉,月亮都看得见;月亮里的琴音、舞蹈以及月光丝丝流动的声音,大山也全部听得清。
炎热的夏天,月亮还经常给大山送被子—白色的被子,清香的被子,轻而又轻的被子。一盖上这被子,大山就开始做梦。
有人站在山顶看见,这被子是由人间找不着的特殊材料制作的。盖上它,山上的一切都看不见了,如同无边的银浪,如同天空沉淀的白云。蝉声、鸟鸣都做梦去了,花草、树木全成了大山的梦境。
中秋,是月亮的生日。这一夜,月亮看见山里山外的人,家家户户都在团聚,都在为它轻歌曼舞。它一激动,恨不得把所有的爱、所有的光都倾倒出来……
山上的月亮也喜欢安详、静穆、和平。
山上的月亮最厌恶喧闹、捕杀、战争。
映山红
把性格挂在你的名字上,而你的品性却写在花瓣里。
每当初夏的阳光把你的花瓣点燃的时候,群山都被映红了,山边的云也映红了……
一种大自然的野花走到这一步,需要何等的气魄啊!
而细细地打量你、触摸你,你却是那么温柔、朴实、俊美、多情,你依然不失女儿身。
我们从来没忘记过你的身世和那个“杜鹃啼血”的故事。为了寻找那个普普通通的丈夫,你居然痴情到如此地步?!
时光已经流逝了几千年,你的灵魂已变成了一只孤独的鸟儿。每当你天天飞来飞去,仍在一声一声呼唤着他名字的时候,我的心也一次次地滴血。这血不是滴落在茫茫的空中,而是滴落在某些现代家庭战争的刀剑里,滴落在法庭争执的火星中……
上帝呀,请快快把这些心中僵化了的土地开垦出来吧!全部种播上你爱的种子,情的种子,映山红一般燃烧的种子……
山 路
曲曲折折,袅袅如烟,宛若梦幻中斑驳的记忆。
这就是传说中的天梯吗?
不,这血脉一般的伤痕,是数千年历史结下的血痂。
古猿从这里走过,山鹰和小鹿从这里走过……狩猎者弓箭的速度和猎物的奔跑便成了这里的山风。
脚印的叠加成为历史,历史的风又淹没了多少脚印。
如今,你从这满是脚印的山路上经过,可随处捡拾到一串串现代的青春和浪漫,你还可以把一帧帧绿色的风景、红色的风景捧起来,装入你心中的存储卡。
时代久远了,山路渐渐变成山民心中的箭,直指远方的苍茫……
(梦哲语摘自《散文诗世界》201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