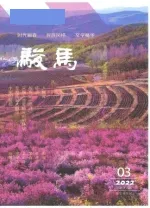阿龙山中蝴蝶会
范培松
苏州大学教授、苏州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江苏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苏州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散文学会顾问。论著有《散文天地》《散文写作教程》《散文了望角》《悬念的技巧》《中国现代散文史》多部及散文集《从姑苏到台北》,长篇散文《南溪水》。主编了《写作教程》《写作艺术示例》《文学写作教程》等。论著多次获国家和省级奖励,并获江苏优秀哲学社会科学专家、苏州优秀哲学社会科学专家称号。
一
我痴迷山。妈妈身材高挑巍峨,在我心中,她就是座山。我的生命是从山里孕育出来的。每次见到山,不管有名无名,总想爬上去,和它亲近一番。登上了山,我也成了山,飘飘欲仙,世界被我踩在脚下。什么是神?山就是神,我在山上,我也成了神。
走遍了无数山山水水,自己都搞不明白,居然会把名山大兴安岭遗忘了。年已古稀,至今还未到过大兴安岭,这是事实。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难道你真把这座名山遗忘了?
谁说遗忘了?大兴安岭在我梦中。
那是杂乱的碎片:茫茫林海雪原里的抗日志士,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伐木工,藏在深山老岭里的东北虎,出没在崇山峻岭里的土匪诸如座山雕、蝴蝶迷……梦中的大兴安岭渺渺茫茫,模糊成一片,神秘而充满诱惑。
不过,内心深处深藏着一个和大兴安岭有关的疙瘩。记得在中学时,我特迷《林海雪原》,少剑波、杨子荣是我心中永不倒的偶像。但是我始终不明白,作者为什么要给一个深山老岭里的土匪婆起个“蝴蝶迷”的绰号?我顽固地认为,蝴蝶是属于我们南方的物种,比如云南大理蝴蝶泉边,每到农历四月十五左右,蝴蝶到此聚会。据说那天蝴蝶满天飞舞,会出现蝴蝶与蝴蝶连须钩足,长长的一串串的悬挂在树枝上的奇景。我被这些描述勾得心痒痒的,约了几个朋友,利用暑假前往大理,实在扫兴,且不说蝴蝶满天飞舞了,真正见到的蝴蝶屈指可数,更没有什么蝴蝶与蝴蝶连须钩足,长长的一串串……又比如我的家乡江南宜兴,那是蝴蝶的乐园,梁山伯与祝英台双双化蝶成仙的美丽传说就诞生在那里。在我看来,冰天雪地的大兴安岭,怎么会有蝴蝶呢?这里的土匪婆的绰号应该是“花狐狸”、“雌老虎”之类,才符合地方特色。我武断地认为,“蝴蝶迷”应该送给南方的“土匪婆”。
大兴安岭实在是一个令人痴迷的梦。
想不到,一个电话把我送进了梦,呼伦贝尔市和根河市的文联向我发出了邀请,到大兴安岭的明珠根河市采风。
欣喜若狂。大兴安岭在召唤我,我要去大兴安岭了。
汽车奔驰在呼伦贝尔的草原上,渐渐地进入了大兴安岭。根河是根河市的标志性的形象代表,它在深山老林中默默地躺着,时隐时现,温情脉脉地紧紧地挨着我们,陪伴着我们向前进发,大家显得特别柔软。其实,我还没有从苏州出发,已经感受到大兴安岭人的特有的温馨。他们不断地来电来信,报告大兴安岭的气候、环境,提醒各种事项,甚至要我的脚的尺码,为我们准备当地的球鞋。更想不到的还帮我们买好保险。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在为我牵肠挂肚。牵挂,牵挂!现在世界什么都有,就是缺少人与人的牵挂。遥远的大兴安岭在真诚牵挂,就像根河温情脉脉地围绕着大兴安岭那样的牵挂。牵挂把我和大兴安岭紧紧融在一起了。
汽车在一片白桦林前停了下来。在许多描写寒冷地带的国内外名著中,常常会出现白桦林,今天我终于见到了它的尊容。这是真正的原始的白桦林,密密的,无边无际的林海。它没有神秘没有恐怖没有杂乱没有交错,有一种整齐洁净感,就像我家边上的大公园里的树林,给人有一种家山家树的感觉。难道这里的每棵树都得到了人们的关爱和呵护?我油然产生一种亲近。正在那里痴想,有两只蝴蝶围绕着我翩翩飞舞。这可把我弄糊涂了,在这中国最冷的地方也有蝴蝶?我瞪大了眼睛,怎么看,它们都是不折不扣的蝴蝶。我将信将疑,不禁又胡思乱想了:或许这两只蝴蝶是我们苏州太湖边的,它们知道我来大兴安岭,怕我寂寞,特地伴随我的。我向它们行注目礼:你好!美丽的天使!自由飞舞吧。
二
这次采访重头戏是阿龙山。它位居大兴安岭中腹西坡北部。
出发前,我们做了充分准备:头戴为我们准备的类似养蜂人戴的可以护颈的绿帽子,脚穿护腿的半筒靴球鞋。大家兴奋地期待着,一是要到中国最冷的“冷极”——金河。那里,冬天要冷到摄氏零下五十多度。二是要去采访鄂温克族,他们已经结束了游牧生活,定居在大兴安岭,以饲养驯鹿为生,目前全国仅存的千余头驯鹿就在此。还要拜访一位90多岁高龄的额吉。
“冷极”充满了冷的各种传说,它是中国的北极。据说冬天在“冷极”户外,一会儿,可以冻掉一层皮,吓死人了。“冷极”现在旅游非常热,一到隆冬,北京有专列把无数想冻掉一身皮的人送到此冷极。我最怕冷。只能在“冷极”最酷暑的时刻来叶公好龙。为了纪念到了“冷极”,决定在“冷极”的标志塑像下拍张集体照。这时,烈日炎炎,阳光刺眼,地皮被太阳烤得像蒸笼似的,大家又是戴防晒帽,又是架好墨镜,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照完相,个个大汗淋漓,众人雀跃,戏称在“冷极”体验热极,快哉!
叶公好龙者们人人都有征服的满足。
冷极人非常文化,在半山坡上,艺术地构筑了逶迤的栈道,我们把它称为爱情栈道。浓浓的树香草香,葱茏的树木,在其中漫步,你不想爱也会发情,你不想浪漫也会疯癫。此刻,我们都疯疯癫颠。又见几只蝴蝶围绕我飞舞,把我的心情舞得直发狂。原来组织者只不过是准备在栈道上小憩一会儿,看到大家如此地赖着粘着,就让大家尽兴。泡了足足一个多小时,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冷极”属金河镇管辖。金河美极,青山绿水,一尘不染。一顶吊桥艺术地架在金河上,站上桥晃悠,晃得心花怒放。山、水、村、桥如画一般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镇里非常整洁,有序,处处可见管理者的精心和艺术。镇书记高大,魁梧,一双眼睛非常有情。他介绍,镇里以养殖狐狸为主。我窃笑,怪不得他那双眼睛有狐气。我到过不少地方,一个有管理经验的主政者,倘若情商高,这个地方就会把山水治理得如天然的画。他的同伴介绍,书记是复员军人,用部队的管理经验管理此镇。金河镇美的答案出来了,原来这里的主政者,既有武的管理经验,又有多情的艺术气质。金河镇被描绘成了一首诗,“诗并不飞翔凌越大地之上以逃避大地的羁绊,盘旋其上。正是诗,首次将人带回大地,使人属于这大地,并因此使他安居”,我想起了海德格尔,他又说——
人充满劳绩,但还
诗意地安居于这块大地之上。
想形容金河冷极吗?关键词无疑是:青山,绿水,蓝天,白云。那么形容我们江南呢,关键词不也是青山,绿水,蓝天,白云吗?我有些混乱了。
眼前的金河却是清晰的,分明是冷极的江南。
悠悠挂着白云的蓝天,倒映在碧绿的金河水里,洁净的空气,你怎么呼吸都让你心醉,这是世界最干净的一块土地。
三
吃完午饭,汽车向阿龙山驶去。或许是在冷极张狂了一点,或许是公路两旁的山林单调,大家都朦朦胧胧打起瞌睡来。也不知走了多少时间,在朦胧中,突然一位同伴叫了起来:
蝴蝶!蝴蝶!蝴蝶!
大家猛然睁开眼,眼前的景色使我大吃一惊。天哪,汽车已经完全被蝴蝶围困,只见它们在车前车后满天飞舞,一片童话世界!没有前奏,没有预兆,一切来得那么突然。大家顿时亢奋起来,乱嚷起来,个个被眼前飞舞的满天的蝴蝶迷住了惊呆了,又担心汽车碾死撞死蝴蝶,本能地连连惊呼停车。
汽车在蝴蝶包围中停了下来。
打开车门,个个大呼小叫,空中飞舞着蝴蝶,公路两旁,居然密密地铺着蝴蝶。极目向公路远方眺望,匍匐公路两旁的蝴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成了两条望不到头的银色的绸带。怪哉,蝴蝶应该栖息在树木上,或花丛中,这里却匍匐在地上,和大地相依。我们脚不敢落地,小心翼翼,怕踩着蝴蝶。谈何容易,一脚踩下去,还是碰到了蝴蝶。细看蝴蝶,似乎仅是一种品种,皆呈银白色。我们家乡的蝴蝶,只只是精灵,总是和花相恋,蝶恋花嘛,它们灵活得很,休想捕捉到它。可是,这里的蝴蝶铺天盖地,肆无忌惮地匍匐着,傻乎乎地飞舞着。察看汽车,上面印满了蝴蝶撞击的印痕,大家不禁有些心痛,个个心中在问:蝴蝶蝴蝶你怎么了?蝴蝶疯狂了!多得让我们绝望。这里人迹罕至,我们闯进了它们的乐园,它们把我们当成了同类,不依不饶地粘着我们,要我们和它们翩翩起舞,嘿!我们个个成了“蝴蝶迷”。
置身在蝴蝶王国中,面对铺天盖地的疯狂的蝴蝶,突然大家安静下来了,我们都痴了!
这是2013年6月25日下午,我们在通往阿龙山的途中,和蝴蝶邂逅了。
来大兴安岭之前,在苏州我翻阅过许多资料,没有任何关于蝴蝶会的介绍。在苏州各报刊上的有关内蒙古、呼伦贝尔和大兴安岭的旅游宣传,也没有蝴蝶会的文字。联想到有些把一个平常的景点吹得天花乱坠的宣传文章,我为阿龙山叫屈。
疯狂的蝴蝶会,在我心中产生了太多的疑惑,不禁问司机:
“这样的蝴蝶会常见吗?”
“我来过几次,也是第一次碰见。”
“它们为什么匍匐在地上?”
他面有难色,想了想说,“也许这里的地干净。”
大概是我的问题触动了他,他突然反问我,“你对我们这里印象如何?”
我正在为蝴蝶会疯着呢,他的问题问到我心坎里,我由衷地说,“这里的旅游资源太丰富了,可以大力开发。”
“啊——”他瞪大了眼睛,不由得把目光移向印满了蝴蝶残翅断臂痕迹的汽车,显然,我的话使他对明天产生了惶恐,自言自语地说,“一天,几十辆车来,用不了多久,蝴蝶就会灭了。”
“啊——”这回轮到我惊讶了。他的眼光告诉我,他想象的开发是一场破坏。
在苏州,我热衷于旅游开发,曾为多个地方出谋划策,有滋有味着呢。从来没有想到旅游者竟是自然的天敌,也没有想到开发者会成为破坏者。我的文化理念受到了挑战,有些手足无措。我一遍遍地叩问自己,难道这次我不应该来圆大兴安岭之梦?
汽车继续在绵延的蝴蝶王国中行驶。“额吉”在等着我们呢。张承志在他的散文中,虔诚地抒写了“额吉”崇拜情结。他笔下的“额吉”是高贵的神。这也感染了我,我虽然没有见过“额吉”,但她们在我的心中,似乎个个成仙。现在我已经踏进了“额吉”和蝴蝶为邻的居住的仙境,实实在在感受到“额吉”的仙气了。不过,此刻我的心情怪怪的,蝴蝶会的仙境被我们骚扰,司机“啊——”的回答中透露着对明天的惶恐,都搅动着我的心灵,我对“额吉”的拜访,会不会干扰她的平静生活?我怯怯的,不断地问自己,我还该不该去拜见这位我心中圣洁的“额吉”?
责任编辑 高颖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