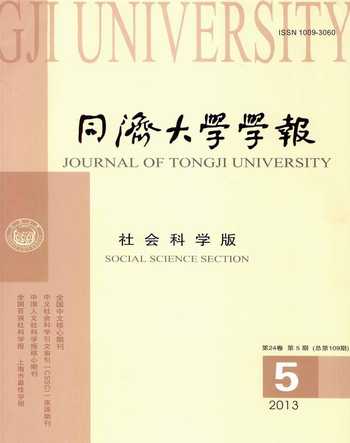行动的理由与行动的原因
陆丁
摘要:行动的理由与行动的原因之间的关系,是近几十年行动理论中颇受关注的议题。其中,有一种特定的进路是试图通过行动的原因来给出行动的理由。文章试图说明的是,采取这一进路的代价是改变“原因”的含义。文章在第一节中对这个情况给予了一个一般说明,并且引入了一个“概念的自由度”的分析工具;在第二节中,以“动机性理由”为例具体地说明了一种因为改变自由度而使得“原因”概念发生改变的情况;在第三节中讨论了这种改变可能会造成的某种负面影响。
关键词:行动理论;行动的理由;行动的原因;动机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3)05—0080—05
当我们对一个行动进行某种评价(是否善、是否正当、是否合理、是否应该、是否可以被允许等等),以便为某种后续讨论提供根据或者出发点的时候,这种评价本身显然也是需要理由来支持的。一般来说,这种理由可以有两种形态。一种是从行动的某个性质出发来支持这个评价,即给出这样的论证:对于一个具体的行动a来说,因为a有性质F,所以如此评价a是正确的。但是,这种形态的理由至少会遇到一种困难,即无穷倒退的问题。事实上,考虑到对a的评价本身也具有或者至少可以看作是具有“a有性质F”这样的形态,所以,从形式上看,这第一种理由只不过是用一种性质判断取代了另一种性质判断而已。
第二种能够为行动评价所提供的理由则是出现在下面这种流程中:我们首先把行动“展开”到某种形态,然后在这个新形态下对行动加以评价,或者依据这个展开形态来对行动加以评价。比如,我们可以把行动按照“有意向的行动”这种结构加以“展开”,然后在这个结构中对行动加以评价。
对于近30年来的道德哲学或者伦理学来说,比较通常的做法是把行动按照“有理由的行动”来进行这种“展开”。但是,行动的理由要想成为这种与评价有关的结构性要素,却需要满足一个前提,即它不能仅仅是行动的理由,它还需要与行动有某种更强的联系。比如,对于一个具体行动a和它的理由来说,a还得是行动者“按这个理由来行动的”(acting on that reason),或者,还得是行动者“出于这个理由而行动的”(acting for that reason)。
事实上,为了使得一个行动的理由不“仅仅”是理由,通常的做法是对理由提出某种额外的要求。同时,这种要求往往被表述在类似于“只有……才是理由”的句式中,而出现在这个额外要求之中的则是行动的原因或者某种准原因,比如动机。但是,问题在于,当一个分析者提出要求,让一个理由能够通过这种中介而达成那种与行动之间的、满足要求的更强联系时,他实际上就对这种中介本身也提出了要求。特别地,满足这种要求——即能够成为理由与行动之间的关系的中介这个要求——实际上也改变了这个中介与行动之间的原本关系。事实上,在我看来,如果说对于行动的评价确实需要以某种对行动的展开为前提进行理由提供的话,那么进行这个“展开”的更好方式,不是把行动展开成“有意向的行动”或者“有理由的行动”,而是展开成“有原因的行动”。换句话说,与其去强化“理由”概念,不如去弱化“原因”概念。不过本文并不奢望论证这一点,它只想说明某个较弱的论点,即,至少(1)把行动展开成“有理由的行动”改变了而且必然改变原因的“原本”含义,(2)这种改变并不是全无负面影响的。
一、理由与原因
为了说明(1),我们先来说明一个相关的论题:
(3)当我们用行动的原因来充当行动的理由的时候,它就不再是原因。
比如说,我忽然嘴馋想吃面,于是跑到厨房给自己煮了一碗面。一方面,此时“我想吃面”是“我去煮面”的原因。另一方面,当我被问到“你为什么煮面”而我回答说“因为我想吃面”的时候,“我想吃面”又变成了“我煮面”的理由。现在的问题在于,当“我想吃面”变成“我去煮面”的理由之后,我显然可以不去煮面。就是说,如果“我想吃面”和“我去煮面”之间的关系“仅仅”是理由与行动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此时“我去煮面”这个行动是否要被实行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即使我没有真正去煮面,“我想吃面”仍然可以是“我去煮面”的理由——只要它符合某种有效的实践推理模式。但除非我确实会去煮面,否则此时甚至谈不上煮面有一个原因。
事实上,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还可以就理由与原因获得更进一步的结论。如果我们按照下面的形式来分别设定关于理由与原因的检验标准,即:
L理由的检验标准]如果p是φ的理由,那么存在某个实践推理模式,使得我们可以从p得到一个类似于“应该φ”的结论。
[原因的检验标准]如果p是φ的原因,那么p让行动者会确实去φ。
那么,我们可以说,如果一个p只满足理由的检验标准,它一定不是原因。换句话说:
(4)如果理由的检验标准是某个p成为理由所唯一要满足的标准,那么p一定不是原因。
因为满足理由的检验标准与“确实会去(φ”无关,而满足原因的检验标准则只依赖于这一点。而这就意味着,当我们用原因的检验标准来加强我们对于某个p成为理由的要求的时候,这种加强一定不能以合取的方式获得,即不能是某种“既满足理由的检验标准,又满足原因的检验标准”这种形式。
可以看出来,(4)已经是(1)的另外一种表达。因为当一个理由被说成是原因的时候,它当然在某种意义上“既是理由,又是原因”。而根据(4),这个“在某种意义上”一定不能包括“理由”和“原因”这两个概念都不改变含义的情况,否则此处的“既是理由,又是原因”就相当于对理由的检验标准和原因的检验标准进行合取。而既然我们现在是在把理由说成是原因——而不是把原因说成是理由——那么这个理由就必须首先按照“理由”的原义成为理由,于是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改变原因的含义。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正面地来考察一下这个“原因”概念是怎么发生变化的。
仍然以吃面为例,不过我们这次从理由开始。假设“想吃面”已经是“去煮面”的理由,就是说,存在着一种有效的推理路径可以让我们从“想吃面”得到某种“应该去煮面”。更具体一点的话,这条有效的推理路径是怎样的,之后得到的那个“应该……”就要有相应的意思。与此同时,现在我们还想让“想吃面”与“去煮面”有一种更强的联系。为得到这一联系,我们要求“想吃面”这个理由能够让行动者会确实去煮面。可是,类似于(4),如果一个理由只满足让行动者会确实去煮面这一个要求,它显然不能支持“应该去煮面”这类的结论。因为,即使一个行动者确实是因为想吃面而去煮面,这里仍然可能存在各种不同的情况,或者也可以这么说,他可能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而想吃面。就这些原因而言,也许有些可以支持“应该去煮面”,但至少未必所有的这些原因都支持这个结论。于是,就必须对使得一个原因成为原因的原因加以限制,才能够保证当一个理由成为原因之后仍然还是理由。而这些限制恰恰改变了原因的“本义”。
事实上,就上述分析来说,也许我们可以引入一个“自由度”的概念来帮助表述此间发生的情况。一个概念的“自由度”,在这里是指某个具体的事物成为这个概念的一个实例时情况的多样性的限度。或者,这个“自由度”也可以理解为,当我们把某个具体的事物判别为属于一个类的时候,所使用的论据在类型上的多样性的限度。具体来说,当我们把某个u判别为“是u”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把“是U”等同于“满足如此这般的一个/组条件”。问题是,如果“u是U”确实是真的,那么未必只有一种理由使得它真,而且这些理由之间未必是等价的。就此而言,一个概念的含义,对应的既不是这个概念的“外延”,即实例的限度,也不是“内涵”,即关于某个实例是否是它的实例的判别标准,而是一个实例成为它的实例时所引用理由的多样性的限度。按照上述观点,“原因”这一概念的含义所发生的改变,恰恰在于这个限度所发生的改变。
下面我们以迈克尔·史密斯对“休谟式的动机理论”的分析和伯纳德·威廉姆斯对“内在理由”的分析为例,具体地说明这种自由度是怎么发生变化的。
二、以动机性理由为例
按照迈克尔·史密斯的分析,一种“休谟式的动机理论”所给出的理由,应该满足下面这个要求:
[强原则]一个理由R在时刻t构成了(constitutes)行动者A去(φ的动机性理由,当且仅当存在一个ψ满足:在时刻t,理由R构成了行动者A对ψ的欲望,并且构成了A的这样一种信念,即要是他去φ的话,他就能ψ。
或者,它至少应该满足下面这个要求:
[弱原则]行动者A在时刻t有去φ的动机性理由,仅当存在一个ψ满足:在时刻t,行动者A有对ψ的欲望,并且A相信要是他去φ的话,他就能ψ。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两个原则中的动机概念,即在“动机性理由”中以“动机性”这种形态出现的动机概念,其意义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以及这种改变是怎么发生的。为此,我们可以先给出一个参照性的动机概念的“原义”。事实上,关于一个动机,我们似乎总可以给出如下的检验标准:
[动机的检验标准]如果行动者A在时刻t有去φ的动机,那么,在时刻t“A会去φ”为真。
可以看到,在这个标准中出现的“A会去φ”,在史密斯给出的两个原则中被弱化到了一个在虚拟语气中的表述,即“摹是A去φ的话”的形态。而且,在这两个原则中,不仅φ是没有原本形态的“会去”,事实上在这两个原则中没有任何行动带有“会去”的原本形态:φ是被变成了虚拟语气,而剩下的ψ根本连“会去”都没有,只剩下了“A对ψ的欲望”。
另外,在动机的检验标准中,我们可以看到“会去”是有时间标记的(“在时刻t”),但是在强弱两个原则中,有时间标记的其实不再是φ或者“A会去φ”,而是ψ以及行动者A对φ与ψ之间的这种手段一目的关系的相信——这也非常自然,因为两个行动之间是否具有手段一目的关系,本来就是一种一旦为真/假就会一直这样下去的、与时间无关的东西。但是,这样一来,在时刻t与行动者状态直接相关的实际上就不再是φ,而是某个与φ处在一种无时间关系中的ψ。换句话说,此时行动者对之“真正”有动机要去做的,与其说是φ,还不如说是ψ。如果放到吃面的例子上就是,本来我们要为“煮面”提供一个动机,但按照史密斯的这两个原则,煮面通过吃面获得了一个动机性的理由:想吃面(对吃面有欲望),而且要是去煮面的话就能吃(上)面。这样一来,原本当我们按照动机的检验标准去为一个行动提供动机的时候,本可以使用各种方式,但现在至少出现了一种对于这些方式的限制,即它必须通过某种中介ψ来进行。而这个限制,恰恰降低了“动机”概念的自由度。
如果说,之所以史密斯版本的“休谟式的动机理论”会导致这种对于“动机”概念的含义变化,是因为它引入了对于理由的额外要求,即能够为行动分析给出一种手段一目的结构的话,那么这种含义变化在威廉姆斯对内在理由的分析中则是出于另外一种原因。威廉姆斯是这么说明一种对于理由的内在主义诠释的:
[理由的内在主义诠释]如果一个人“有理由去φ”,那他一定找到了一个有效的推理路径(sounddeliberative route):这个推理路径从他自己的某个动机集合出发,最后达到的则是“他应该(should)φ”这样的结论。
与史密斯给出的两个原则相比,这里不再有手段一目的结构,而只是要求任何一个得到“他应该φ”的实践推理必须是从行动者的动机集合中的某个成员出发的。就此而言,它是用实践推理的起点去限制实践推理。但是,问题在于,这个限制显然也同时是对动机集合的限制:并不是每一个能够被看成是动机集合的成员的动机,都可以有一个实践推理让它能够有一个“他应该φ”的后承——否则谈不上用动机集合来强化“实践推理”这个概念了。
事实上,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理由动机化方法的一种或许也可以被称为“两难”的处境:一方面,如果不对理由概念进行强化,那么它无法承担行动理论所要求的分析工作;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动机可以被用来强化理由概念,那么它一定是以动机概念的弱化为代价的。而这种弱化所导致的结果,就是被强化的理由概念一定无法达到原本我们想要用动机来强化理由所希望达到的强度。换句话说,当我们试图通过“是动机的理由”这条路径来找到一种比单纯理由更强的理由的时候,我们找到的一定是某种“其实还不是动机的理由”。
三、原因的含义变化的负面影响
这种状况当然不仅在“逻辑”上是有趣的,而且确实会对行动分析产生某种实质性的影响。比如我们来考虑批评问题,特别是批评的“合法性”问题。事实上,关于什么时候才能够对一个行动进行批评,存在着两种虽然各自不同但在实际性的强度上并无差别的考虑。而且,这两种考虑至少在形式上是相互冲突的:
[P1]一个行动,只要它是不如人意的,就可以进行批评——不管它是否有改进的余地。
[P2]一个行动,只要没有改进的余地,就无法进行批评——不管它是否如人意。
彻底解决∞这个冲突,不是本文所能讨论的。这里我们只是考虑这样一个更容易获得答案的问题:如果[P2]不是完全不能成立,那么此时对行动进行分析的话,应该给予一个什么样的框架?或者说,一个行动分析框架应该具有怎样的特性,才能使得[P2]不是完全不成立的?
从这个问题出发就可以看到,要想让[P2]不是完全不成立,至少这个框架应该允许一种与“是否如人意”无关的对行动进行谈论的方式——只有先存在这种谈论行动的方式,才可能去考虑批评是不是出现在这种对行动的谈论中。但是,无论是威廉姆斯对理由所作的限定,即“必须能够从动机出发达到‘他应该φ”这个限定,还是史密斯的两个原则——无论是强的还是弱的——都不满足这个要求。事实上,任何从理由出发而对行动所作的分析都不满足这个要求。因为,即使不能说理由总是从某种是否如人意的角度去分析行动,但至少,当我们给予行动一个理由之后,我们就变得能够谈论这个行动是否如人意,于是行动就变成一种与是否如人意相关的东西。这样一来,在比如像史密斯或者威廉姆斯所提供的这种行动分析中,我们实际上无法谈论这种与是否如人意无关的行动的可能性,即改进行动的可能性。但后者至少是针对行动而给出的批评性话语中的一个有机的部分。就此而言,前面所说的这种意义转换,就其缩减了行动话语表达能力而言,就不再是无足轻重的。
(责任编辑:谢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