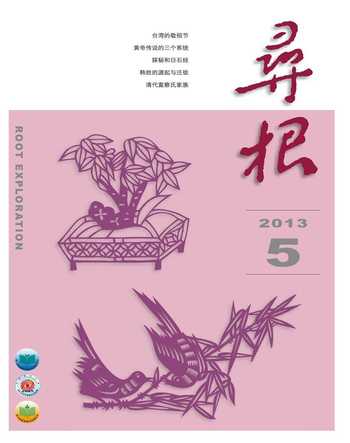钱大昕的《恒言录》与钱大昭的《迩言》
曲彦斌
分别著有《恒言录》和《迩言》的经学家兼训诂考据学家钱大听、钱大昭,是一对著名的乾嘉学派同咆兄弟学者。其《恒言录》和《迩言》,均属中国文献史上重要的汉籍民俗语言珍稀文献,是自周秦以来采风问俗的经典著作。
钱大昕与《恒言录》
五月秧针绿,兼旬雨泽稀。瓯宴干欲坼,布谷暮空飞。
米价频年长,田园生计非。老农占甲子,辛苦候荆扉。
读这首明白晓畅的《五月》,悯农之外还似乎可以给人以田园的意蕴。但是若读其《和竹君戒坛读辽法钧大师碑因吊学士王鼎三十韵》,尤其是那三百余言充满书卷气的考释性自注,则尽显其乾嘉学派学者的本色了。再看钱诗《寄王琴德》的自道“惟余文字癖,欲疗医无案;语辨宋鲁讹,文证豕亥乱”,更犹如一位老学究的自画像矣。在清代诗坛上,钱大听无多大诗名。但在其毕生驰骋其间的经学考据领域,则不容小觑。且莫说《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心录》《音韵问答》《经典文字考异》《唐石经考异》《声类》《潜(研/手)堂文集》等累积其学术地位的诸多传世之作,单就是于其生前未及刊行流传的一部《恒言录》,即非同一般。特别是在研究人书的题材方面,则是以属于“大雅”的传统考据方法,辑录考释生活中的常言俗语。
书名所谓的“恒言”,亦即常言俗语。是书内容、体例略如《通俗编》,性质亦近似,然分类又似较《通俗编》稍为严谨一些。先经乌程张鉴、扬州陈常生补注,后又有陈鳣《恒言广证》六卷,则使其内容益加详密。全书六卷,凡分十九类:卷一为吉语、人身、交际、毁誉四类;卷二为常语、单字、叠字三类;卷三为亲属称谓类;卷四为仕宦、选举、法禁、货财四类;卷五为俗仪、居处器用、饮食衣饰三类;卷六为文翰、方术、成语、俗谚四类。总计凡八百余条,或以内容划分类别,或间以俗语结构形式划分,如“单字类”“叠字类”。皆以考据学方法征引经史子集文献,考证俗语源流,是宋王应麟《困学纪闻》提出“俗语有所本”以来,继《通雅·谚原》《通俗编》之后的又一部考释俗语的力著。现代著名训诂学家杨树达盛赞之:“余少时读钱晓徵《恒言录》,颇喜其翔实。”(《俗语典》序)亦有当代学者评价其“已初具俗语辞典的规模,在编写质量上达到清代俗语研究的最高水平,开创出我国俗语研究的新局面,堪称不朽之作”(赵伯义:《论钱大昕的(恒言录)》,《河北学刊》,1997年第3期。且看书中如下诸例:
重身 《诗》:大任有身。《传》:重身也。《笺》云:重谓怀孕也。《正义》云:以身中复有一身,故云重也。陆德明云:重,直勇反,又直龙反。常生案《素问》:问岐伯日:妇人重身毒之奈何。鉴案:《说苑·修文篇》:取禽不麝卵,不杀孕重者。《汉书·匈奴传》:孕重坠犊。(卷四俗仪类)
打秋风 《七修类稿》:俗以干人云打秋风,累想不得其义。偶于友人处,见米芾札有此二字,乃丰熟之丰。然后知二字有理,而来历亦远。常生案:《野获编》:都城俗亨对偶,以打秋风对撞太岁。盖俗以自远干求曰打秋风,以依托官府赚人钱物日撞太岁也。《暖姝由笔》:靖江郭令辞《谒客》诗,有“秋风切莫过江来”之句。(卷六成语类)
《恒言录》有嘉庆十年(1805年)扬州阮氏刊本(收人《文选楼丛书》),光绪十年(1 884年)长沙龙氏刊《潜妍堂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以商务印书馆1958年排印本(附陈鳣《恒言广证》六卷)为完备。最新版本为,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由陈文和主持点校的《嘉定钱大昕全集》。
钱大昕(1728-1804),字及之,一字晓徵,号梓楣,又号竹汀居士。先世居江苏常熟,其为清江苏嘉定人。生于清雍正六年,卒于嘉庆九年。乾隆十三年(1748年)肄业于苏州紫阳书院。十九年(1754年)举进士,官至詹事府少詹事。三十八年(1773年)以父忧而归,居家凡三十余年,历主钟山、娄东、紫阳三书院,门生数干人,终卒于紫阳书院。大昕博学,平生著述颇富,辑有《潜(研/手)堂文集》等皆传于世。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八一、《清史列传》卷六八、《清代学者像传》等多种史志。
今人赵伯义《论钱大昕的(恒言录)》比较全面地研究之后认为,钱大昕为清代著名学者,博通经史,尤其精于传统小学。在经学盛行的封建社会里,俗语被斥为低级的词语,不能登大雅之堂。而钱氏却独具慧眼,继承东汉服虔《通俗文》的研究传统,在治经史、小学之余留心于俗语的研究,《恒言录》即其在这方面的研究结晶。《恒言录》继承前人的研究传统,钱氏借鉴雅学著作的编写经验,在俗语研究上取得了卓越成就。第一,钱氏博古通今,长于辨析古今异义,释义精微,为后代树立了楷模。第二,求本溯源,启迪后代学者对词语进行分析。钱氏征引书证,尽量选取最早用例,显示词语产生的时代。第三,体例严密,为后代俗语辞典的编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河北学刊》,1997年第3期)
钱大昭与《迩言》
《礼记·中庸》“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郑玄注:“迩,近也。近言而善,易以进人。”朱熹《集注》亦云:“迩言者,浅近之言。”宋刘敞《贤论》:“昔者舜有天下,大圣人也,惟其不欲其身贤而已矣,是以舜好问,好察迩言。”又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卷三:“圣祖仁皇帝西巡,俯察迩言,采及清望,温旨褒奖。”可知《迩言》书名所显示其宗旨,乃辑释通俗常语之作。至于帝舜及清圣祖康熙皇帝“察迩言”,皆在于晋人常璩《华阳国志》中所说“考八方之风雅,通九州之异同,主海内之音韵……知天下风俗也”。
《迩言》六卷,有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原刻本,《啸园丛书》本,1959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与《释谚》《语窦》《常语寻源》《俗说》合订一册,题为《迩言等五种》)。全书凡六卷,卷一辑158条,卷二辑111条,卷三辑52条,卷四辑98条,卷五辑130条,卷六辑58条,计600余条。不分类,举凡饮食起居、言语举止、交际、礼仪、名物、技艺、典制、亲族称谓、习语等,多有涉及。释文一般不释义,只征引经史、笔记等为证,不如《恒言录》《土风录》《证俗文》详备。例如:
不耐烦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云: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事故繁其虑,七不堪也。《宋书·庾登之传》云:弟炳之,为人疆急而不耐烦。宾客于诉非理者,忿詈形于辞色。(卷五)
不中用
《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又《外戚世家》云:武帝择宫人不中用者,斥出归之。《汉书·王尊传》云:助太守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卷五)
张三李四 《朱子语类》云:如这众人,只是一个道理,有张三、有李四,李四不可为张三,张三不可为李四。(卷六)
凡此可见,释文虽简明,却远不如《恒言录》详密,如“张三李四”条唯引《朱子语类》;而陈鳣《恒言广证》已补以《五灯会元》书证,大昭似未见及。征引多注所出,较之唐宋同类著作为精。
由于此书是由张鉴和阮常生各加补注后才刊行的,因此张、阮两人的注释为原作也丰富了不少内容。其中,张鉴和阮常生所作的注释分别标明“鉴案”和“常生案”。
《迩言》与《恒言录》同是辑录常语俗言,虽各有千秋,但在一些条目征引的材料方面却不如《恒言录》更为丰富。
但是,《迩言》有些条目的考释和文献征引,不仅不见于其他同类著作,而且亦很翔实,颇见大昭之学养功底。如“斟酌”一条的释文:
《国语·周语》云:而后王斟酌焉。《荀子·富国篇》云: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汉书·律历志》云:斟酌建指,以齐七政。《扬雄传》云: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叙传》云:斟酌六经,放易象论。《白虎通》云:言周公辅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后汉书·章帝赞》曰:左右艺文,斟酌律礼。《张奋传》云:犹周公斟酌文武之道。《班彪传》云: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班固《两都赋》云:腾酒车而斟酌。又典引云:屡访群儒,咨故老,与之乎斟酌道德之渊源,肴核仁义之林薮。仲长统昌言云:非能斟酌贤愚之分,以开盛衰之数也。《蔡邕传》云:斟酌群言,韪其是而矫其非。《魏志·袁涣传》云:常谈日:世治则礼详,世乱则礼简。全在斟酌之闲耳。《宋书·恩幸传》论:都正俗士,斟酌时宜。(卷一)
钱大昭(1744~1813),字晦之,号竹庐,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钱大听之弟。生于乾隆九年,卒于嘉庆十八年。昭事兄如严师,得昕指授,时有“两苏”之比。大昭淡于仕进,嘉庆元年(1796年)方举孝廉方正,赐六品顶戴。昭学不及其兄,然淹贯群籍,与兄齐名,趣在闭户读书。著有《说文统释》《广雅义疏》《诗古训》《经说》《尔雅释文补》《两汉书辨疑》《三国志辨疑》等。出身于经学之门,亦为经学名家,《迩言》注重考证而疏于释义,亦其学风也。
阮元、陈鳣、张鉴和阮常生
钱氏兄弟的《恒言录》《迩言》两书之所以被视为中国文献史上重要的汉籍民俗语言珍稀文献,除二人自身的才华和学术眼光要素外,特别得益于乾嘉学派纯正的学风,尤其是得益于阮元、陈鳣、张鉴和阮常生诸位的无私相助和他们与两位的深厚情谊。
陈鳣(1753~1817),字仲鱼,号简庄,一号河庄,浙江海宁人。在京师,与钱大昕、王念孙等往来,被阮元称之为“浙中经学最深之士”。著有《说文声系》《说文解字正义》《石径说》以及《续唐书》《论语古义》《简庄文钞》等。如此一位乾嘉学派之大家能够突破“文人相轻”“同行是冤家”陈规陋俗和陈腐观念,以学术为重,以情义为重,对《恒言录》加以补证,深化了钱大听的研究成果,人品高尚,学风端正,实属难能可贵,堪为今人楷模。
张鉴(1768~1850),字春冶,亦字荀鹤,号秋水,清浙江乌程(今吴兴县)人。据《清史·文苑列传》《清史稿》和汪日祯著《南浔镇志》等史志的记载得知,嘉庆五年(1800年),阮元出任浙江巡抚,于西湖“筑诂经精舍”,张鉴和同里“杨凤苞、施国祁皆与焉”,均作为阮元的门生“肄业其中”,并成为阮元的得意门生。受聘担任诂经精舍讲席,成为东南经学名师之一。张鉴在阮元浙江学政和两任浙江巡抚任上一直追随左右,成为阮的重要幕僚。其间,曾协助阮元编纂了《经籍籑诂》《盐法志》《儒林传》等著作。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他被“选授武义(今浙江武义县)教谕”,执掌武义的教育及文庙祭祀诸事,位属正八品官员。著有《古文尚书脞说》《十三经丛说》《西夏纪事本末》等多种,皆传于世。
阮常生,一作长生,字彬甫、寿昌,号小云,原系阮元的族子,后过继为阮元长子,妻为扬州学派重要学者刘台拱长女刘蘩荣。常生为人、做官和做学问,皆秉承家风家学。其一生为官清正廉直,官声政誉颇著,是道光时期的惊天大案宝华峪陵寝工程贪腐案中极少数未受牵连反而获得升迁的官员。同时,也是多才多艺的才子,但不以才地矜物,能嗣家学而又能够独立思考。而且还擅长金石书法,尤其精于擘窠书,《扬州府志》称其“生平研究经术,精钟鼎大小诸篆,得柳诚悬笔意”。所著有《后汉洛阳宫室图考》及《小方吟馆诗抄》。道光《仪征县志》复著录其《团云书屋诗抄》等,皆传世。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云台(或作芸台),又号(研/手)经老人、雷塘庵主等,江苏扬州人,是历官乾隆、嘉庆、道光三朝而始终坚持学术研究的乾嘉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学术泰斗,经学领袖。《清史稿》卷三六四《阮元传》称其“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阮元的学术渊源主要来自戴震,但作为通达有见地的学者,他对钱大昕、汪中、程瑶田、凌廷堪、焦循等人的学问,也很推崇、敬佩,至少是“略其短而著其功,表其长而正其误”(《西河全集·后序》)也。个中,尤其盛赞大昕为学之精博,能兼清初以来诸学之大成。
作者单位辽宁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