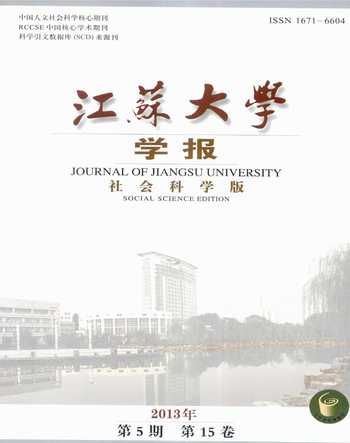西蒙·奥提斯的《反击》:环境正义、变革的生态批评及中间地带
乔尼·亚当森 张玮玮
摘要:“自然”、“地方”和“正义”等概念是正在勃兴的社会和环境正义运动的基石。与倡导“荒野伦理”的美国主流环保主义者相比,美国印第安裔诗人西蒙·奥提斯更关注位于自然与文化的中间地带的园地,并倡导一种“园地伦理”,展现出与前者截然不同的自然观。在此基础上,当代生态批评学者对“中间地带”的探讨将有助于人们思考在特定的地方生态、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的差异是如何产生的,从而推动社会与环境正义运动的进程。
关键词:美国印第安文学;正义;地方;环境正义;中间地带;园地伦理
中图分类号:1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3)05—0034—08
现在,尽管水资源和矿产资源都已经被开采,许多生活在美国西南地区以农业和牧业为生的印第安人仍然奋力争取按传统的生活方式来生活。因为他们的家位于某些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露天开采的煤矿附近,许多人被迫到水源地取水喝并且呼吸充满尘埃的空气。但是,他们并不退缩到“荒野”去寻找更好、更原始的场所,而是留在原地、坚定地用手机和电子邮件等现代而非传统的方式为保卫家园而战斗。
他们当中的许多部落生活在“四角地”(the Four Corners),即美国西南部一个四州交汇的区域。西蒙·奥提斯(Simon Ortiz)在《反击:为了人民、为了土地》中对此做了感人的描写。在此书中,奥提斯指出:截止到1972年,四角地因为原子弹的军事试验及铀和煤的开采而受到了极为严重的毒性污染,以至于尼克松当局曾试图将其指定为“为国家牺牲的地区”。
奥提斯根据他在印第安部落阿科马·普韦布洛(Acoma Pueblo)的成长经历以及20世纪60年代早期在新墨西哥的格朗茨(Grants)附近的铀矿开采和加工业的工作经历,创作了《反击》——一本混合了散文和诗歌的作品集。在书中,他将20世纪美国印第安人的“牺牲”和他们为保护自己的社区和资源而进行的斗争与1680年的普韦布洛起义联系起来。当时,普韦布洛人揭竿而起,反抗西班牙人的民事、宗教和军事统治。在此前一百多年里,西班牙人盗取普韦布洛人的土地和资源、奴役土著居民并且禁止他们信奉自己的宗教。在那场计划周密的武装起义中,一支由受压迫的、一无所有的土著印第安人和贫困的西班牙人组成的组织松散的联盟军将西班牙人驱赶出去。
“自然”、“地方”和“正义”等概念是正在勃兴的社会和环境正义运动的基石。接下来,为了探讨对于它们的一些非主流观点,我将分析奥提斯的《反击》。通过考察阿科马人如何通过他们在园地中的劳作逐渐理解自然世界,我将探讨为什么“荒野”这一概念无助于帮助我们回答这样一些问题,即在一个整个地区和人民群体都为类似于采矿形式的资源开发而牺牲时,人们在伦理上如何生存?我主张,作为生态批评者,如果我们想为最难回答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找到答案,我们必须从荒野中退回来,好好看一下文化从自然中浮现的“中间地带”,这将有助于我们与那些决心为剥削人类和他们生存环境的势力而战斗的人们结为同盟。
一、第一个白人的神话
根据他们的口头文学传统,西蒙·奥提斯的祖先——阿科马·普韦布洛人或者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叫做阿库玛·哈欧(Aacqumeh hanoh)人——来自于大地。他们首先生活在查科峡谷(Chaco Canyon,位于今新墨西哥州),后向北迁移到梅萨维德(Mesa Verde,位于今科罗拉多州)。据他们的长者说,阿库玛·哈欧人后来又向南迁移,经过多次尝试,来到了他们从郁郁葱葱、齐腰高的草丛中拔地而起的、橙红色的平顶山上。他们在山顶建立了新的印第安人部落,称其为“阿库”(Aacqu)或“准备好的”,因为他们的神在预言中告诉他们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一个值得他们守护的平顶山。在那里,他们可以建立他们的城市;在它周围的肥沃的平原地区,他们可以种植玉米、豆类、西瓜和南瓜。
在他的整部作品中,西蒙·奥提斯描写了阿库玛·哈欧人塑造他们有关自然和文化的观点的不同方式。一些贯穿在作品中的经历,都是从他孩童时期在他祖先们历史悠久的土地上的劳作开始的。奥提斯记得,在巨大的砂岩悬崖的阴凉处,他喜欢在他父亲耕作的时候赤脚跑过沙土地。跟随父亲走在家里的犁和马的后面,他每隔一步将玉米种子撒在地上,然后把南瓜和西瓜种撒在地上,再用薄薄的一层软土将它们盖好。阿科马人和他们的祖先已经种了几个世纪的玉米,或许再没有其他东西比玉米更能代表自然和文化难解难分的中间地带。在奥提斯看来,玉米来自于土地并被视为大部分西南部落赖以生存的食物。因此,大地和人之间便有了一种神圣的关系:人恭敬地照料和耕种土地;反过来,当人食用玉米之后土地又重新创造了人的身体。奥提斯写道,玉米只能“被视为生命和土地创造力的神圣的、备受尊敬的产品,以及人对彼此和土地的责任和关系”。
跟世界上数百万通过猎捕动物、采摘果实、开沟播种、消灭害虫和收获作物来深入了解自然的人们一样,奥提斯也是通过操纵自然生产食物获得了他对土地的最初知识。在他的文集《花纹石》(Woven Stone)中一首名为“父亲的歌”的诗中,他生动地回忆了发生在他父亲耕种的土地上的一件事情。这一事件告诉了他一些与自然中生命过程有关的事情,并且让他明白他父亲和他的同胞与人类之外的世界的关系。在一次春耕中,奥提斯像之前许多次一样跟在父亲的犁后面。但是这一天,他的父亲停下来,蹲在地上,让他的儿子来看犁头铲出的老鼠洞。他极其温柔地捧起“渺小的、粉色动物/放在自己掌心”并且让儿子过来抚摸这些弱小的、刚出生的生灵。后来,父亲和儿子将老鼠移到了地边,将它们放在一块松软潮湿的沙地的阴凉处。在奥提斯关于这件事的记忆中。自然与文化、土地和语言融合在一起,“我记得那份柔软/属于凉爽和温暖的沙土和渺小的、活着的/老鼠和我父亲讲述的事情”。
与阿科马人不同,当大多数当代美国白人在思考他们同自然地关系时,他们并未走向园地(即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中间地带),而是走向荒野,把那里想象成人类文化没有触及的地方。许多美国的自然主义者和自然作家为了说明他们与自然的原初关系,总是想象当神话般的“第一批白人”第一次进入新“发现的”地方、俯视一个视野中没有人类文化印记的世界时,这个地区看上去是什么样子。最受欢迎的“第一批白人”通常是刘易斯(I.ewis)和克拉克(Clark),以及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科罗纳多(Coronado)在美国的西南部沿着亚利桑那和犹他的河谷旅行,被认为第一批白人中最受尊敬的人。但事实上,奥提斯着重指出,当16世纪西班牙人抵达阿库时,他们发现它周围已经是小规模的、秩序井然的农业社区。奥提斯和他的父亲或许几个世纪之后仍然种植玉米,这些人也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土地。他们种植和收割各种各样不同的植物,并慷慨地与他们最早碰到的西班牙士兵分享他们的劳动果实。西班牙人钦佩地注意到,阿库玛·哈欧人修建的从河流到农田的灌溉系统,在设计和技术上同墨西哥的十分相似。在日志中,他们对这座城市的干净整洁进行评价的同时,对壮观的平顶山顶部的防御地点也留下了深刻印象。
环境历史学家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评论道,“第一批白人”都是富有同情心的人,但是他们却存在于人类历史之外的某个地方,是用文化建构出来的、自然世界的旁观者。在自然作家的叙述中,他们作为环境原罪的承受者进入景观之中,给变化的开端和历史做上标记。人们认为当地土著人具有某种永恒的“精神的”或“传统的”知识,但却不相信他们有能力做出改变。怀特认为,问题在于环境史学家的研究以及对刘易斯、克拉克等人的日记的更详细的解读并不支持这一说法。跟最早进入阿库的征服者们一样,刘易斯和克拉克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所穿越的景观是已经被人类活动改变了的自然。他们在日记中描写了“印第安人耕种、打猎、捕鱼和放牧”。
基于第一批白人神话的故事不但没有承认第一批来到北美的欧洲探险者经过的景观的历史记录,他们还将自然浪漫化了。麦克·波伦(Mi—chael Pollan)在他的《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一本思索园地和园艺的书)中写道,自19世纪中叶开始,美国人就崇尚一种远离人类世界的嘈杂,到自然中寻求庇护的观念。根据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最后一个谈及园艺的重要美国作家——所谓自然的“更高法则”,他们认为荒野具有某种恒定不变的秩序,是人类世界唯一可以追求的东西。波伦认为,当作为我们文化的一种禁忌及我们统治和破坏自然倾向的一种阻挠时,这一关于一个有秩序的、平衡的生态系统的概念可能是美妙的、强大的和有益的。然而,现在生态学家坦率地承认,甚至生态系统的概念也只是一种理论,是我们行为的一个隐喻,也是强加给一个更为变化多端和不确定的现实的人类构想。自然没有宏大的规划;它或许有一些内在的趋向能够用有关秩序和平衡的理论来描述,但是,偶然事件能够将自然的过程转变为几乎无数个不同的可能。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偶然性在自然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中几乎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
每年在园地中的劳作已经让阿科马人接受了偶然性,无论是他们自身的还是自然的。奥提斯写道,在他们的口头文学传统中,人们并不将自然浪漫化,而是讲述它的危险、变化无常和神秘性。他们明白,有一些时候,汹涌的洪水会淹没农田,让他们的劳动成果化为乌有;也会有一些时候闪电会击中大树或牧场,可能将风景烧毁;也会有连年大旱,庄稼颗粒无收。他们已经接受自然既不总是美好也不总是罪恶这一事实,他们学会与自然的美好和罪恶共存,去理解自然的模式以及在他们的耕作中模仿自然的过程。
尽管是一代代相传而来,但他们并不认为他们自身的耕种活动能够为土地或他们自身提供神秘的保护。他们认为人们偶尔犯下的错误会导致环境危机。阿科马的口头文学暗示,人类对环境的过度使用和错误估计时常要求人们去对抗或者改变传统。从过去的经历中得到的教训被编进了故事和歌曲中,口耳相传,被人铭记。奥提斯解释说,这些有关丰收或者危机时刻的故事经常以“神秘故事”(mythic proportion)的形式讲述,“目的是让听众牢记有许多需要学习的经验、价值和原则”。
阿科马口头文学鼓励人们记住过去并从中学到经验。他们对传统的利用说明尽管因为“自然之死”遭到某些环境主义者和自然作家的谴责,人类文化仍然可以在教会人类观察和记忆、分享经验以及更重要的是在约束自我等方面发挥作用。自然并未召唤奥提斯去犁沟看渺小的老鼠,而是他的父亲。在文化的指引下,老奥提斯通过将老鼠移开犁沟来告诉他的儿子,因为人类依赖于许多其他的生命形式,所以必须在任何可能的时候谦恭地、充满敬意地以及体贴地将其他非人类自然世界的利益考虑在内。然而,他也清楚地意识到人类为了生存必须改变环境。老奥提斯与梭罗不同,他将老鼠移走继续犁地。而后者却曾经将野生自然浪漫化到了如此的地步,他感到“对歧视杂草非常歉疚……以及……不明白为什么他和园地中的居民土拨鼠和鸟儿们一样有权享用花园中收获的东西”。
波伦注意到,梭罗曾经在《瓦尔登湖》(Wal—den)中宣称“他认为最可怕的沼泽也胜过任何园地”,这实质上是将园地从美国有关自然的书写中驱逐了出去。梭罗将已经驯化的领域抛在身后,认为文化是不可救药的,中间地带是堕落的。但是,被抛弃的“自然”又会怎样?当杂草和土拨鼠入侵,或者开发者决定在此设立分部时,豆田又会怎样?仍旧留在这些“堕落”的地方、不能迁往那些更干净明亮的环境中的人民该怎样生活?波伦恰当地证明,我们将荒野视为远离人类和他们的嘈杂历史以及自然是自然法则的纯洁表达的观念无助于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在《反击》中,奥提斯暗示,我们不能从“外在的那里”而是“中间地带”(即人类可以在他们文化的引领下或许能够“往好的方向改变事物”的地方)出发,去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
二、通过劳作理解人类同自然世界的关系
《反击》是通过劳作塑造、磨砺出来的:奥提斯本人早年在阿科马农田中的劳作,后来在铀矿加工厂报酬低廉的劳作,以及终生作为作家的劳作。此书的背景便是在20世纪40到50年代奥提斯成长的村庄附近。奥提斯记得阿科马的老者们讲述那些河水清澈、充沛、湍急的时光:频繁下雨的时候平顶山周围的牧草能够长到齐腰高。但到了19世纪80年代,这一地区开始遭遇长期的旱灾;随着20世纪30年代铁路、一个伐木小镇和深海大坝(the Bluewater Dam)的建设,水资源仅够维持很少的人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因为贫穷,那些不能像他们的祖先一样继续从事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的人被卷入了薪酬经济。他们先是从事修建铁路的工作;后来到20世纪50年代,又在遍布这一区域的铀矿和煤矿上找到工作。
奥提斯上学的20年也是阿科马人经历毁灭性破坏的20年。这就是“印第安人终结”(Indian Termination)和“迁移”(Relocation)的时代——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的两个项目的名称。它们试图终止一切与印第安保留地相关的联邦政府服务项目、与它们的联系和对它们的认可,并且试图将印第安部落的人迁移到达拉斯、芝加哥、圣何塞、洛杉矶和克利夫兰去。由于经济压力,奥提斯的父亲被迫为了微薄的工资从事铺设铁轨的工作。数星期、数月甚至数年远离家人,他感到失落、孤单和无助。在名为“最终方案:工作,离去”(Final Solution:Jobs,Leaving)中,奥提斯用令人心酸的方式描写了周日的下午父亲离开车站的场景。孩子们哭喊道:“再见。再见父亲,/请你归来。请别离开。”但是他们需要钱买生活用品、衣服和房屋。因为河水和泉水不能为农田提供足够的水源,他的父亲也不能再仅仅通过种地来养活家人。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转而从事铁路修筑工作,老奥提斯也随之辗转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堪萨斯和德克萨斯。
尽管经常离家在外,奥提斯的父亲仍然会回到他的田地间,从劳作中找到力量和智慧。他鼓励孩子们去学习能够学会的有关他们身处其中的、迅速变化的世界的一切知识,他告诉他们:“你们这些年轻人/你们拥有机会”。在耕种土地、砍伐木材以及铺设铁轨期间,奥提斯的父亲用跟他祖先同样的方式学到了有关世界的知识:通过劳作。更重要的是,他的劳作将他带入了美利坚人的世界。在那里,他获得了对一种与他自身完全相异的文化的见解,一种“倾向于总体的、不可阻止的毁灭和阿科马似乎不能掌控的”文化。
所以,当奥提斯的父亲为自己的家园歌唱的时候也鼓励他的孩子们“去战斗/以劳作的方式”,他没有简单地哀悼一个逝去的时代;他敦促他们遵循着他们的传统、通过劳作去学习他们这个区域自然和文化难解难分的历史,并且通过记住和创造能够让他们反抗不公正压迫的练习去“反击”。
三、走向园地伦理
奥提斯从来没有忘却父亲的话语和歌声,他写作的视角能够彰显出许多美国印第安作家的文学文本和那些美国自然作家最显著的差异。奥提斯从在家里的田地和在铀矿的工作经历中获得了对人类和自然关系的理解。在这些地方,他不但开始注意到他的人民遭受的压迫、他们的土地遭受的破坏,更力图去理解和写出这一破坏背后的原因。
父亲曾经期望奥提斯能够不要从事像修建铁路那样摧残人的体力工作来展开反击,所以他鼓励儿子上学。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教授印第安人的老师主要是白人,他们很少鼓励印第安人考入大学或进入专业领域。作为一名曾获得奖学金的高中生,奥提斯贪婪地阅读、写诗,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并且清楚自己想成为一名作家,但他却从来没有考虑过上大学。19岁那年,奥提斯在他家附近的铀加工厂做了一名工人。“我得到了一份工作,”他回忆道,“对于受教育程度不高、没有技术、失业率高的穷人来说,这是一件大事”。在他工作的那些年间,他碾压、沥滤、制作黄饼,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并且将他富有创造性和专业性的见解运用于他的观察中。后来,一场工人罢工导致矿工们无所事事,给了奥提斯一个进入大学的理由。
20年之后,奥提斯早已完成了学业并且成为一名诗人。在《反击》中,他充满诗意地考察了采煤和采铀业对四角区的企业殖民,他的结论是历史正在复制自身。1680年的普韦布洛起义是反抗对土地和资源的盗窃、对劳动力的奴役以及宗教迫害。300年之后,许多相同的状况又再次显现。而这一次,是由跨国公司的活动导致的。“往好的方向转变”是根据他作为铀矿矿工的经历创作的诗歌中的一首。奥提斯在诗中有力地证明面临危险的不仅是阿科马人的存亡,而是“这个国家所有人”的存亡,亦即整个美国。通过一对印第安夫妇皮特和玛丽和一对来自俄克拉荷马的白人夫妇比尔和艾达的友谊,奥提斯表明如果我们为“环境”而进行的斗争中不考虑到所有贫困和边缘人群的生活质量,那么任何人的生活质量都得不到保证,我们是否保护“自然荒野和文化公园”也将没有任何意义。
对这一对印第安人、一对白人夫妇的描写中,奥提斯看到矿山是为了富有的经营者们而开立的。他们经营矿山所遵循的伦理道德并不认为“人和大地以及他们的延续是头等重要的事”。正如在1680年,贫困和压迫迫使来自不同部落的土著人彼此结盟推翻了西班牙人,20世纪的低工资和不安全的工作条件也让白人和印第安人在矿区结下了友谊。在20世纪50年代种族关系紧张的美国,在工作场所之外的地方很可能不会发生。因为自身的背景和经历,奥提斯对所有工人的状况都非常敏感,无论他们的种族。他观察到印第安和盎格鲁的矿工存在许多相似和相异之处。他注意到许多刚从西弗吉尼亚和俄克拉荷马移居四角区的工人阶级白人本身“没有远离以土地为基础的背景”,也就是说他们也是农民。跟阿科马人一样,他们也被干旱和贫困剥夺了他们的耕地,并且由于经济需要被迫来到四角区的矿上工作。20世纪50年代,奥提斯在矿上的确在某些同事那里遭遇到种族歧视,但是在多数情况下,他发现工人阶级的白人都是“勤奋、诚恳、忠于团体,即使他们在语言上是排外、武断和生硬的”。奥提斯在诗中创造了“比尔”这一形象——一个同印第安土著矿工皮特一起工作的电气工程师的助手。
诗中,比尔和他的妻子艾达(Ida)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离开俄克拉荷马来到铀矿工作。他们住在很小的家中。每天早上,比尔和皮特开同一辆汽车去上班从而结为朋友。下班之后,皮特喂羊,并且,在他祖先曾经种过玉米的同一小块地上耕作。比尔尽管已经在矿上工作了20年,他也跟皮特一样,生命之根仍然与养育他的俄克拉荷马的土地连在一起。他梦想能够赚到足够的钱返回家乡买一片地。奥提斯写道:“皮特,你有点儿土地可真幸运,/比尔会说。/尽管不多但是它是点儿土地,/皮特会赞同”。后来,两位妻子在杂货店相遇,然后一起到艾达的小屋喝苏打水。艾达将玛丽带到她的园地,承认她对新墨西哥的土地很不熟悉,它跟俄克拉荷马的大不一样。她让玛丽看了她枯萎的生菜、萝卜和长在坚硬红土中的并不繁茂的玉米。玛丽告诉艾达她的土壤需要“其中的某样东西”将沉重的、结块的红土弄散。过后,玛丽给艾达带来一些羊粪撒到土壤中让它更加肥沃。来年春天,艾达得意地在她的园地中种出了玉米、生菜、胡萝卜和西红柿。
艾达的园地表明了《反击》中最经常出现的主题之一:为了生存,人类必须意识到同大地的相互关系。人类必然要改变的环境,即他们在其中生活、建造房屋、种植园地、饲养牲口以及从为供养自己从土地中获取其他原料的地方。正如威廉·克莱农(William Cronon)所说,“称呼一个地方为家必然意味着我们会使用在其中所发现的自然,因为除了操纵、运用,甚至毁灭自然地某些部分来建造家园之外,我们别无选择”。既然每一种使用的行为都不可避免地改变自然,人类的持续生存意味着人同园丁一样,必须认真地、负责任地去思考他们如何使用土地。正如奥提斯在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所说,只有当人们懂得“善待土地从而不会浪费或毁灭它”时,土地才会丰饶并善待人类。玛丽一生都在善待她的土地,她清楚地意识到艾达的土壤缺乏什么,并且告诉了她这一情况。因此,她帮助她和这个特定的地方、她的园地里独一无二的新墨西哥州的土壤、长在那里的各种植物以及干燥气候之间产生更多的共鸣。在用羊粪令土地更肥沃和疏松之后,艾伦和土地也建立了互惠关系。她向土地倾注了更多的时间和关爱,因此它也将变得更加丰饶。她证明并非所有使用土地的行为都是破坏性的,有些行为能够“往好的方向”改变土地。
通过将比尔和艾达的园地和铀矿相对照,奥提斯直面那些企图解释和证明剥削“自然”和“他者”(即非欧洲裔以外的人、底层阶级的人和人类以外的物种)的行为合理性的伦理。比尔20多年来为了仅能够维持生活的工资,在危险的环境中工作。尽管承认这一事实非常痛苦,比尔的经历还是让他意识到为数不多的活得“先进和安全”的美国人是那些在经济萧条的印第安社区中经营高利润的矿井的人。通过比尔的见解,奥提斯说明假如贫困的工人阶级不能更深刻地理解为什么土著印第安人在为“土地、水和人权”斗争,压榨印第安的土地和社区的同样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势力“将必然摧毁其他人”。
奥提斯说明要求在神圣的、荒芜的“新大陆”周围画上保护线的势力跟将其他地方描写为“堕落的”、并将它们——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民——交给自由市场经济裁决的是同样的势力。因此,荒野伦理和企业伦理尽管乍看上去格格不入,但实际上却异曲同工。迈克尔·波伦认为,这两种伦理都提出“让一种准神圣的力量——自然及市场——自生自灭,它知道怎样对一个地方最好”。这两种观点的真正威力以及它们能够吸引这么多拥趸的原因在于它们的抽象性。波伦认为,在美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地理条件多样的地方,我们不可避免地倾向于那些抽象的观点,它们具有简化和统一的力量(如网格、单一栽培、荒野、供给经济学),因为它们“能够被全面地推行,甚至在全国范围内立法实施”。
当面临自然和“堕落”为市场的地方两种选择时,美国人选择了自然。但当被问及更为棘手的问题,诸如如何对付毁掉了他们最珍视的古老森林的酸雨,或者如何处理导致边缘地区人口死亡的有毒的地下水时,他们却不知如何回答。他们将世界视为“荒野”或者“牺牲地区”等这些过于简化的概念让他们表现得好像跟“自然”没有关系,并且让他们忽略了他们在中间地带的生存方式跟酸雨以及不安全的工作场所息息相关。波伦主张,如果我们想要解决最为紧迫的环境问题。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跟自然之间的关系,构筑一种既能教会我们利用自然又能告诉我们不利用自然的伦理。他提倡一种“园地伦理”,尽管它永远不会像荒野伦理一样有着清晰的表述,但是它的意义恰恰在于它建议“不同地方、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解决方式”,并且对于当地的问题在当地寻找答案。
在“回归,你将前进”中,奥提斯解释了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能够考虑地方差异的环境伦理或者“园地伦理”。他再一次对比了一块普韦布洛的园地和企业的景象。石油和采矿企业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展开了运营,开始开采矿产资源卖给遥远的电力公司,丝毫没有顾忌当地环境和当地人民的健康状况。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和企业一样,对于这些行为的正确与否以及人类的存亡都漠不关心。如果让人类自己选择,他们可能为了利益破坏大地、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剥削无权无势的人,甚至会增加自然的负担让它变得不适合人类生存。奥提斯写道,“大地”将“听凭你便”。但是对于印第安土著农民来说,这种不可逆转的破坏行为是不可思议的。就像奥提斯诗歌中的玛丽,一边看着生长的植物一边温柔地对它们唱歌。她也收获了农产品来养育她的孩子。她用她的呵护、规划、“怜惜和爱”来善待她的土地,因此来年也可以得到土地的回报。由于在实践中遵循“园地伦理”,她意识到将一种更适合其他地方的抽象行为或者最好避免的行为强加给一个特定的地方,这个地方则会遭殃。只有用这样的关注和关爱来关照这片土地,只有通过回馈它某些东西,这片土地才会生生不息、“生命才会继续”。
奥提斯认识到“园地伦理”教会我们要在我们栖居的地方更负责任地生活、要意识到我们在自然世界中的化身、要尊重我们周围的荒野。正如奥提斯的父亲屈身向卑微的老鼠表示尊重,正如他明白我们为了生存必须“往好的方向”改变事物,人类也可以通过思考他们和“自然”以及包括人类和非人类的、各种各样的“他者”之间的关系来尊重他们在中间地带发现的荒野性。威廉·克莱农写道,“学会尊重野生物——也就是学着记住和承认他者的自主性——意味着争取在我们所有的行为中都拥有一种批判的自我意识。它意味着每一个使用的行为中都必须伴随着深刻的反思和尊重,也意味着我们必须时常思考不使用的可能性。它表示当我们注视着我们打算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的那一部分自然时,要问一下我们能否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它——可持续地——在此过程中它不会减少”。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我们不为我们生活在自然中的方式——即不切实际地想象自然是“在外在的那里”——找理由开脱。
跟老奥提斯为他的孩子和大地唱的歌一样,西蒙·奥提斯所写的诗也是希望之歌,是想象人们如何“往好的方向改变事物”的歌。然而,这不是背对中间地带的自然写作,它没有怀着提升个人意识就可以带来有益的政治变革的愿望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环境问题。相反,这种自然写作意识到尽管铀矿石加工厂因为市场萎缩已于20世纪80年代关闭,但美国土著居民仍在饮用被它们污染的水,它们在印第安社区以有毒的面貌出现。
四、环境正义和变革的生态批评
如果生态批评家的研究是建立在抽象的概念“荒野”之上,把它视作个体寻求安慰的地方并把所有跟他们不同者驱逐在外的话,他们的批评著作理论上将不符合逻辑,政治上也实现不了他们保护濒危的环境的目的。建立在这种抽象、并最终不顾史实的“荒野”概念之上的生态批评,也将无力改变这一领域或者整个世界。我认为后现代理论家们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传记的确重要、它们的确能塑造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但是“在通俗的(关于身份的)本质主义观点与多样化的身份认同的潜在的无限流动性之间的某个地方”,必须建立足够的共同基础(尽管情况各异),以便为政治行动指明方向(时间、地点)。因为有意义的社会和政治变革,通常要求不同群体的人在特定的地点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这一过程的第一步便是理解“他者”的历史经历和基本的文化概念。哈维要求对后现代理论中飘忽不定的方面进行“必要的矫正”,鼓励学者在理论著作中考虑实际问题、与特定的地方联系起来,并且为了有效的变革与特定的人群合作。
以“荒野”为核心的华丽辞藻不管多么鼓舞人心,或能够多么大地提升一代中产阶级环境主义者或者自然爱好者的意识,它都不可能成为有意义的或者特定的政治行动的基础。因为它所做的恰好是许多生态批评家对于后现代理论感到最困惑的地方。后现代理论预先假定了个体差异的无止境的游戏:它允许我们放弃与他人的联系、不去理解他们的经历和差异,允许我们不去寻找可以立足之上、去反抗剥削人民和环境的力量的共同基础。这些工作都是困难、耗时,并且经常令人迷惑的。
因而,转变世界将比让人们意识到他们自身的不同或意识到环境危机更为艰难。借用西蒙·奥提斯的父亲对孩子们的忠告,它将是一项十分困难、而非轻而易举的工作。在我看来,生态批评家们的使命在于运用他们在文学、环境和文化研究中的训练,其目的不是为了证明诸如“差异”、“自然”、“荒野”、“正义”或者“地方”等基本信念的不可能性,而是为了研究更为充分合理的基本概念,来让批评阐释、政治活动更有意义、创造性和可行性。试图理解和改变导致社会和生态问题的地方性、国家性和全球性的过程,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权力关系如何通过社会行为产生,以及它们如何在某个地方和某种局势下获得他们的特殊意义。
这也许意味着,与本人之前论述的园丁和环境正义活动家一样,文学批评家偶尔也可以离开一个宏大的模式或理论转向一个具体的地方,比如去思考生态、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的差异是如何产生的,以及这些差异在特定的地点有什么不同的表现。又或者,他们可以从一个具体的问题出发转向更为一般的基本概念或理论,比如去思考截然不同的社会一生态环境如何意味着对正义或非正义的不同理解。但是通常来说,理论和地方必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在抽向的理论思考中加人现实的物理、地理的地方的考虑能够让我们深刻理解——或者抛弃——一种理论或基本的概念如何可能在世界上发挥作用。
五、不再有更多牺牲
奥提斯在《反击》中说明,除非我们能够找到与那些反抗各种形式的压迫(人类或者非人类的)的人,那些身份被构筑为“他者”的人结盟的共同基础,否则,可牺牲的人口还会继续被牺牲,可奉献的地区也会继续被奉献。这一认识让我们相信,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生活的影响负有责任,并让我们相信,我们应该为社会和环境变革共同合作。
奥提斯强调,有一种作品“是创造性的”,并且鼓励一切有生命的事物之间的“依存”。这部作品没有将让自然独立于文化之外将其浪漫化,而是认识到世界的复杂性。生活于其中,我们必须改变、操控甚至毁灭自然的某些要素,这是我们生存的一个条件。它承认,人类依赖于其他的生命形式,因此人类必须考虑到其他非人类的自然的利益,谦逊地、充满敬意地,以及深思熟虑地对是否使用它们做出选择。在《反击》的结尾篇,奥提斯强调,只有通过合作,“我们的人民和土地才不会有更多无谓的牺牲”。
作为作家、学者和批评家,我们的部分使命在于唤起人们对我们的作品、他人的劳作以及自然世界之间的社会和环境的联系。由于未能解释工作的必要性,我们允许自己不去理会我们在中间地带的行为如何导致了那些被描写为堕落的地方的环境退化。类似于《反击》之类的文学作品向我们展示,承认荒野同自然的联系不仅“在那里”,而且也在我们周围,在囊括了自然与文化的中间地带。
(责任编辑 潘亚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