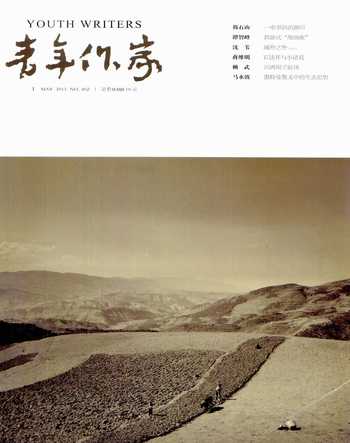哨声(外一篇)
吹了好几声“嘘——”,还是没有一点儿动静,没有一滴尿滴在痰盂里的声音。以前不是这样子的,只要“嘘”三声就撒了。今日痰盂端着半天了,嘴吹痛了,抱儿子手也抱酸了,儿子还是不撒尿。他有些急了,他想:有一天没解小便了,是不是病情加重了?是不是该送医院里去呢?
他爱人走过来,问:“还没撒吗?”
“是啊。”
“我来吧,你端累抱累了。”
“不要紧,你端抱不起的。”
“端抱得起,你不在家时,还不是我端抱的吗?”
他不再说了,就把人移给她,自己站起来捶着发酸的腰,他说:“是不是送医院去看下?”
“不急呗,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况的,再看看。”爱人说完嘴里就一声接一声地“嘘”起来。
他站在一旁听着“嘘”声,就想起爱人以前端痰盂抱儿子撒尿的情景。爱人端痰盂抱儿子撒尿,嘴里一边“嘘”着,一边用手指头拨弄着儿子的小鸡鸡,儿子一会儿就撒尿了。他偶尔也抱儿子撒尿,也学着爱人“嘘——”,嘴里再怎么吹,小鸡鸡再怎么拨弄,儿子就是不撒。等他以为儿子不撒尿放到摇窝里时,儿子的小鸡鸡一挺,一泡清尿射得老高,把摇窝里的小被子打湿一大片。有时抱着端着了半天还不撤,他打儿子的小屁股,儿子只是扯着喉咙“哇——哇——”地乱哭,就是不撒,等他爱人一接手,一吹“嘘——”,儿子就撒了。他对爱人说:“姥姥的,这小子是恋母型的,跟老子不亲。”
他爱人听了高兴死,不停地亲着儿子的小脸蛋,还说:“恋母就是好,儿子喜欢娘有出息的。”
想着过去,看着现在,他心里很难受。他难受的不是儿子,而是自己的老娘。
老娘是在他儿子考上大学那天中风的。那天看见自己一手带大的孙子考上一类大学,老太太一高兴就从酒桌上倒在了地上。老太太中风了,中得厉害,手脚不能动不说,大脑也不清楚了,什么都不知道,跟植物人一样,你一餐不喂她吃饭,她一天都不喊饿。老太太的一日三餐都不是大事,大问题是老太太的拉撒。你不抱着她去解手,她就把大小便拉在床上,有时一天要换好几次被褥,还得跟老太太换衣擦身子。
他们都要上班,自打老太太病后,知道这是个长时间累人的事,就请保姆帮忙照顾,可保姆做几天就跑了,说累死人,稍微不注意老太太就拉了,难照顾。那时候,保姆走马灯似地换了一个又一个,价钱一个比一个高,到最后高价有时也难请到。
没有保姆的时候,他一天都不安神。上班时,稍微有点空就想到家里的老娘,就骑着自行车飞也似地跑回家,一看老娘还在床上躺着,没拉屎撒尿,就放心了,喂点水给老娘喝后又接着去上班;有时跑回家,正好碰上满头大汗的爱人也跑回来了,他无奈地对爱人一笑,说:“你也累的,有我就行了。”
他爱人说:“你啊,一个大老爷们儿,我不放心。”
那时,他真的想好好地亲爱人一下。然而,他们都没有那种心情。这也是真的,为了老太太晚上不把屎尿撒在床上,身子干干净净的,他们夫妻俩两天一轮流,睡前端抱一次,半夜又端抱一次,清晨再端抱一次,一晚上下来比上班还累。
他说:“还没撒吧?我来吧,你抱累了。”
爱人就把老太太交给他,老太太在他怀里像没睡醒的婴儿,眼睛闭着,脸上似笑非笑。他又吹着哨子:“嘘——,嘘——”地“嘘”了半天,老太太还是不小便,他就对老太太说:“妈啊,您不听话是吧?不听话就要打屁屁的哦,您以前就是这样说的哦!妈最听话的,是吧?”接着,他又连“嘘”了三次,也不知是哨声起了作用,还是他开玩笑的话被老太太听见了,老太太终于撒尿了,那尿声像小雨点似地在痰盂里“嘀嘀”作响。
树上有只鸟
窗前有棵树,是什么树老太太看不清,也不知道树名,只记得自打搬到这里来这树就有了的。
老太太八十了,眼睛不太行,白内障,朦朦胧胧,手抻直了看不清几个手指头,只能看个大概,但老太太耳朵好,隔老远能听见别人小声说话。有一次,她几个儿子躲在隔壁房里商量老太太的后事,她听见了,说:“你们瞎操什么心啊?早着呢!”她的几个儿子听了忙说是说着玩的。
屋里静,兴许老太太能听见是常事;可到傍晚,楼梯间有人“咚咚”的脚步声,她就对保姆说:“花啊,快去开门,老二来了。”保姆心里嘀咕:老太太这也能听得清?开门一看,果然是她家老二拎着东西上楼来了。
老太太一辈子吃了很多苦,别的不说,单是把四个儿子拉扯大,个个参加工作,个个成家娶媳妇,这背后艰辛的故事就像老太太那一头的白发。人啊,就这样子,辛苦了一辈子,本该好好享享清福,可身体不行了,不是这儿痛,就是那块不中用了,大鱼大肉不能吃,这高那高的,吃药比吃饭多。好在老太太除了眼睛不行,其他身体器官还凑合,走路拄拐杖也能上下楼,还能跟隔壁的老头老太太们聊上半天。
近来,老太太不爱出门了,闷在家里也不说话,问一句就搭一句,多余的一句也不说。老太太一变化,就吓得儿子们慌了神,都往家里跑,问七问八地像麻雀破了窝。老二说:“妈啊,哪儿不舒服就说,我们送您去医院看;不怕花钱嘛,我们都有钱。”
问急了,老太太就说:“瞎操心,没病。”
“那您老咋的老窝在家里不出门玩儿啊?走走对身体好着呢。”
“还去?”老太太说:“我是不敢再出去串门了——去一家,没几天那家的老家伙就殁了。你们说,是不是我克他们啊?我听说能扯别人的阳寿呢,就跟沾别人的福气一样。”
儿子们一听是这事,就笑了,说:“妈,您老迷信呢,没这回事的!年纪大了,都要走的,这是规律,什么克不克啊。”
不管儿子们怎么劝、如何说,老太太听是听,就是不爱出去串门了。不出门也行,只要不病就好。老太太不出门,就在屋里瞎转悠,这里走走,那里看看,一天到晚把满屋子敲得一片子拐棍响。
老太太每天早上起得早,起来后就站在窗前看半天,也不知看什么。保姆发现,一旦早上窗前的树上有鸟叫,老太太就一脸的笑容,一天心情愉快;如果树上没鸟叫,只有空树枝,老太太一天就不太爱说话了,闷着。保姆知道,喜鹊叫,喜事到,老太太是想讨好彩头。可是,树枝上不是每天都有鸟的。为这事,老太太的儿子们很是揪心,想是不是养只喜鹊,每天把鸟笼挂在那树上,让老太太听鸟叫,让她高兴。可问题是喜鹊不好养不说,也没人管,大家都忙。
这天早上,老太太照旧走到窗前,一时刻,她大声叫着:“花啊,快来看,树上有只鸟!”
保姆跑过来一看,那不是鸟,那是一个塑料袋。她知道老太太眼神不好,看不清,就顺着她应和着,说:“是鸟,是鸟,是只大花鹊呢。”
老太太说:“这只鸟怎么不叫呢?”
“可能……可能天冷哦,所以不叫呐。”
“是吧?”
尽管那只“鸟”一声都没叫,这一天老太太还是很高兴的,时常跑去看;若看见还在,就说这“鸟”真好,跟她有缘分。
不管真鸟假鸟,只要老太太高兴就真好。当然,老太太和保姆都不知道,那树上的塑料袋是老太太的二儿子昨晚特意挂上去的。
[作者简介]阿木,原名王运木,武汉市蔡甸人,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创作,作品见于《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长江文艺》《当代作家》《小说月刊》《芳草》《成宁日报》《南鄂晚报》等文学杂志、报刊,出版个人小小说选集《没有故事的女人》《蝉歌》《难说的事——阿木微型小说精选集》;主编《通山文学六十年》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