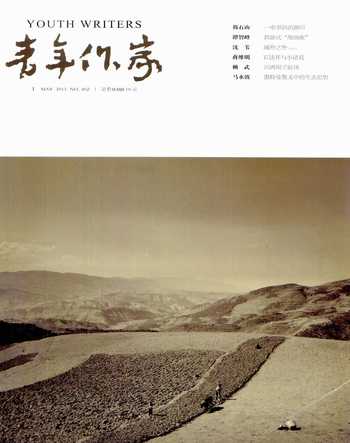南城根叙事
南城根的夜
夜幕最先降临在南城根,是四周那些森林般的高楼遮住了最后的光线。昏暗,像一件黑衣裳,穿在了南城根瘦矮的身体上。
就让我从炒菜时清油的第一声尖叫里说起吧。
那些切碎的葱蒜,跳进锅,“刺啦”一声,心惊肉跳地一叫,就焦在了油锅里。住惯了南城根,从蔬菜的叫喊声和锅铲的碰撞声里,就能听出谁家做什么饭。那尖细、干脆、油星四溅、铲子忙乱的,该是炒洋芋丝、虎皮辣椒,没一会儿,准会响起“咕噜咕噜”熬米汤的声音。那沉闷、“吱吱”细叫、铲子也漫不经心的,定是用肉臊子在炒,大概多是西红柿鸡蛋面了。钻进南城根,过门经窗,百十户人家齐刷刷炒菜的声音,扑面而来,不尽相同,真是人间烟火里,尘埃深处有滋味。
饭熟了。一个人租房住的,闷声闷气,呼哧呼哧,“喋”两碗,就完事了,连个碗筷互相弹唱的声音也听不见。要人多,一家三口,挤一间房,就热闹了,女人骂男人窝囊,半辈子买不了一平方米房,男人回骂:“吵吵吵,下辈子你转世个男人来试试,一碗饭都塞不住你的嘴!”这时,孩子打翻了碗,饭洒在床单上,女人的气就撒孩子身上:“你手断了吗?!把碗也端不稳!养你能干啥?光会吃!”女人从孩子手里把碗夺过来,另一手一把抓起孩子扔到床下,收拾残饭了。小孩子“哇”一声,哭开了。抖动的委屈的细嫩的哭声,飘出窗户,在南城根嘈杂的夜空里飘着飘着,就黑了。也有人穿个大裤衩,蹬双拖鞋,端着碗,在院子游着吃饭,进你家门,看看你做啥饭,入他家屋,看看他吃什么饭,要不就在院子里扯着嗓子,骂:他妈!今天不当心摔了一个碟子,狗的老板罚了我五十元,他怂再燥,我炒了他!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妈!”一院人就起来了,都把头伸出窗,吸溜着饭,骂的骂,笑的笑,让高楼包裹的南城根像乡下的集市,热闹了一阵。
南城根的人,睡觉早。十点多,灯火就渐次熄灭了。谁让这里住着一些靠力气糊口口的人。只有巷子口的两张台球案边,围着几个二愣少年,捣台球,时不时发出一阵乌鸦般的尖笑,伴着台球碰撞的声音,惊飞了围在灯泡下的蚊蝇。
有人说,南城根,住着干那事的女人,半夜有叫声。我是没听过,遂不知真假。可墙上用白粉笔慌乱地写着一溜“提供色情服务131XXX”的字迹,这是真的,我见过。我还知道,南城根,睡得最晚的,是酒店那些当服务员的女孩子,她们十一点多下班后,三五成群,说说笑笑,而且总是用手机播放着一些流行歌曲,把声音开到最大,沿着黏稠的灯光,摸进了黑漆漆的巷子里,只有长靴子的鞋跟敲打水泥地的声音,一片杂乱,回荡在铺开了鼾声的民房间。
南城根有狗,但比罗峪小区少,大多脏兮兮,蹲在门口,像只破拖鞋,人过去,叫两声,就偃旗息鼓了。这些狗,晚上是懒得叫的,不如乡下的狗耳鼻灵敏、一呼百应、气势恢宏。这里的狗,半夜吠一两声,多是梦呓,掀不起大风浪。南城根猫也不多,曾有一段时间,每个院子都养有一只,后来没人管,全野了。这里毕竟不如小区那样,到处严实,猫没去处。每当夜幕落下,野猫就穿梭在房顶上,像箭,“嗖”一声,穿透了城根下稀薄的夜色。虽然猫少,可一到春季,猫叫依然烦人。它们蹲在墙头屋顶,双目一闭,身披灰尘,接连叫起,本就地方狭小,那声音便随处乱窜,即便夜色再浓,月色再淳,那撕心裂肺的叫声也依然越过楼顶,推窗而入,如雷贯耳,叫人心神不宁,烦躁难忍。鲁迅“仇猫”;汪曾祺也说不知猫叫春“是出于快感还是痛感”,但“其声凄厉,实在讨厌”。其实,南城根住的人,受猫叫之扰,半夜起身披衣,怒发冲冠,恨得牙根痒痒者,也不在少数。
当子夜一来,星辰渐灭、晚风不动时,南城根就陷入宁静了。不管有多少喧嚣、有多么破旧,黑夜一遮,城中村的南城根,也就和高楼小区没有任何区别了;只有黑夜深处那些绵长纷乱的梦,是形态各异的,是有差别的,就连那些磨牙梦呓打呼噜的声音也是泾渭分明的。
一切归于宁静,或者寂静。这里没有风,只有贴着地皮的睡眠。
但南城根的夜,不总是宁静的。有一次,半夜两点,“轰隆”一声,似有倒塌之声,然后就是吵吵嚷嚷,人声鼎沸,鸡犬不宁。有人以为地震,穿个裤衩,睡眼曚昽,夺门而出。也有人以为半夜吵架,咽口唾沫,翻身继续睡去。但这嘈杂的声音一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怎么说呢,就是乱哄哄,小小的南城根,灯陆陆续续全亮了,似乎白昼提前来临。后来有人跑出来一看,房倒了,是一户人家的土坯房(南城根多是两层水泥砖房,土坯房只有一两户),因年久失修,加之排水不畅,墙根泥土剥落,直到那天夜里,挺不住了,一松气,倒了;光倒了就倒了,问题是还把住在里面的在酒店当服务员的三个女孩压下面了——最后经过努力,挖出来,送医院,人没大碍,就是一点皮外伤。真是命大。
当然,塌房的事在南城根不会常有,十年半载就那么一半次,那年地震,也没摇倒一间。就这一次,已经让南城根的人受够了,毕竟这里的人,经不起折腾,尤其晚上。
所以,南城根的后半夜,是寂静的。这里没有风,只有贴着地皮的睡眠;在水泥地上,盛开着卑微的琐碎的花。
那些年 住在南城根的小马师
小马师是我的大学同学,二十七岁了。“小马师”是我们上学时赐予他的绰号,他姓马,我们叫“马师”,那时年龄尚小,就叫“小马师”。我们当地有时候称呼人直接把马师傅、牛师傅等,简称“马师”“牛师”,这样叫干脆麻利,开门见山。
小马师住南城根四十五号。
没事干,我就进去溜达一圈。四十五号,没院子,一进门,黑咕隆咚,南北两边,二层楼面对面挨着,东边是上下的楼梯台,三尺宽,一个胖子要上去可能就夹住了——看来房东盖房时,费了脑筋,他尽量滕出每一寸空间来整一间巴掌大的屋子,收房租,挣钱。楼顶搭了一块蓝色防雨棚,滤出了一点微弱的光。小马师住二楼最边上,每次去,都碰上他隔壁的四川女人,穿着掉色的大睡衣,吊着蜡黄的脸,睡眼惺忪,从一楼哼哧哼哧提水。
不敲门,直接推开进去,好家伙,小马师穿个三角裤衩趴床上看黄碟;见我进来,慌忙按个暂停,呼一下坐起来,嘿嘿笑几声,一丝尴尬从脸上一扫而过,说,嗨,啥碟嘛,一点不精彩,实战的地方就那两下,啥时候借你研究一下。他从裤子里摸出烟,叼上,火机一打,一团烟罩住了干瘦的脸。他的房子不大,黑洞洞,光线微弱,像贫血。屋里摆个双人床,支张桌子,就剩转身的地方了。那张床,太大,褥子和床单太小,铺上去,盖不住,上下两边都裸着黑乎乎的干床板,像大人穿了小孩的衣服,胳膊腿子露了一大截,又搞笑又可怜。四周的墙壁上贴着几张足球海报,沾满了灰,角都打着卷儿。床头的空地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一堆饮料瓶,杂七杂八的瓶子。他从来不烧水,渴了,只喝饮料。我说你有恋瓶癖啊,他说攒它几个月,看我都喝些啥玩意儿,时间一长还能换包烟钱。
小马师并不是经常看黄碟,他人老实着呢。他的屋子用他的话说,就是驻天水市接待处,啥人来,都接待,管住、管吃、管娱乐。乡里的同学朋友来,没地去,在他那挤一夜,末了他再请人家一份早点。城里的一伙狐朋狗友,没事干,去他那喝一圈,斗个地主。甚至有人把刚哄到手的女人也领过去,将他打发了,鸠占鹊巢;小马师悻悻地说,晚上小心我床板,别震塌了,明天一早我收房费。那人迫不及待地把他推出门,压低声音说,赶紧去,兄弟要急着办事呢,下来我给你弄个,你耍一下;小马师露着大门牙,嘎嘎笑着,边走边说音量调低、不要扰民啊,便自个儿找别人去住了。
小马师二00八年一毕业就住南城根了,也算老住户,中途换个几个窝,但都围着南城根打游击。刚毕业的小马师给网吧当网管,晚上上班,白天睡觉,似乎昼夜颠倒了。你去,他总跟死人一样叉在大床上磨牙打呼噜,一张脸油汪汪、黑乎乎,跟煎焦的油饼一样。尤其是那脚臭,简直不堪忍受,臭味波涛汹涌般从窗户溢出去,到处窜;满院人深受其害,见他就骂,可他晚出早归,见上的机会不多,白天去算账,可他睡死了任你怎么咒。后来小马师觉得与其被别人奴役,还不如给自己做牛做马,就在五里铺摆了几张台球案,当起了小老板,日子滋润了一段时间,也时不时带我们吃个大盘鸡、涮个火锅。但好景不长,几个流氓常在那里滋事,后来和另一拨流氓干上了,互相短兵相接,你剁我砍,弄了个人仰马翻,差点出了人命。小马师的台球杆被打成了几半截,台球案也皮开肉绽了;更严重的是。自从那次打架事件以后,就没人来捣球了,简直是门可罗雀。最后小马师遭遇滑铁卢,折本赔钱,回到南城根,在那黑洞洞的窝里,睡了好几天,茶饭不思。当然,这期间,小马师还参加了两次事业单位考试,但都榜上无名。
几个来回,折腾完了,人累了,心乏了。小马师似乎洗心革面了,每天宅在南城根的黑屋子,端着本资料书在复习。这期间,他还招了近十个学生,租了个教室,办了补习班。虽然补习班挣不了几个钱,但也能混口饭吃,还不影响复习。这样一箭三雕,用他的话说,何乐不为。
后来,小马师深居简出少了,我去的次数也少了。一次去,他正气哄哄唠叨什么。问了半天,原来隔壁四川女人昨天洗了睡衣,走廊上搭了一晚,第二天丢了,便站在二楼对着小马师的门骂起了:老娘一个破睡衣,你都偷,啥子人嘛!是不是过几天你连老娘也偷撒?小马师气不过,回了几句,那女人才歇了。小马师说,简直什么人嘛,我又不是变态,偷你那恶心玩意儿干啥!老子要偷,也偷他个貌美如花的,你那黄脸婆送我我都嫌弃呢。
最后一次去小马师南城根的房子,是年底了。天寒地冻,北风呼啸。人们穿着肥厚的棉衣,缩头弯腰,进进出出在南城根,有^提着包裹,有人扛着被褥,像逃难一样,准备回家了。到四十五号院,这次敲了门,进去,小马师正在烧开水,准备泡方便面,看来他不烧水的恶习改了。床上一个染黄头发的女子,裹在被子里,正在玩手机,一边玩一边莫名其妙地笑。小马师说,我女朋友,这次是正式的,你还没见过吧?后来才知道是小马师的一个网友,聊着聊着就谈上了。她在天水一家美容院上班,是外县的。
再后来小马师考上了,分到乡下的村校当老师去了;南城根的房子,在过年前就搬了,年过完,再没有来。带不走的一些盆盆罐罐、破椅烂桌,廉价给房东处理了。后来,听说他结婚了,可媳妇不是上次见的那女的。有时候,经过南城根四十五号院,就想钻进去,老觉得里面还住着小马师,可一进院,却发现里面的人全陌生了。一切都恍恍惚惚,似乎有个人真生活在南城根,似乎压根就是幻觉。南城根,像小马师这样的人,来了走了,一茬一茬,都在光阴深处消散了、空白了,只有南城根,像一块膏药,贴在那些年、那些人的记忆上。
[作者简介]王选,甘肃天水人,一九八七年出生。作品散见《山东文学》《黄河文学》《诗选刊》《诗歌月刊》《当代小说》《星星》《中国诗歌》等,著有作品集《葵花之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