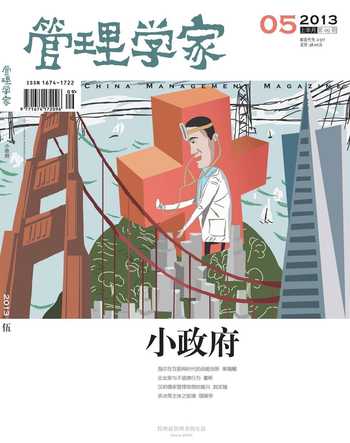《新语》和汉初政治的转向
陆贾的思想,集中反映在《新语》中。综观该书,明显以儒学为基调。四库总目提要说:“据其书论之,则大旨皆崇王道,黜霸术,归本于修身用人。其称引《老子》者,惟《思务篇》引‘上德不德一语,馀皆以孔氏为宗。所援据多《春秋》、《论语》之文。汉儒自董仲舒外,未有如是之醇正也。流传既久,其真其赝,存而不论可矣。”对这一提要,余嘉锡有详细的考辨。但大体来说,提要的定位是恰当的。尤其是对这种流传已久、影响广泛的古籍,论证其思想影响要比考证篇章真伪更重要。哪怕是伪作赝品,当它已经被世人当作原作真品用于社会时,它就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新语》从汉代开始,就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值得把它作为古代管理思想演变过程中的一个节点来对待。
四库提要把陆贾作为与董仲舒并列的“醇儒”,说明《新语》的儒学倾向是十分明显的。但陆贾在儒学基调中渗透了无为和道术思想,所以,今日学术界也有人把陆贾列入汉初新道家。总体上看,陆贾所倡导的,是适应大一统王朝体制,以清静无为的手段,建立可传之久远的理想王朝。《新语》现存十二篇,有些恐怕已经不是当时陆贾所作而是后人羼入,不过基本思想逻辑保持着一致性。
《新语》的主要内容,是从强调道德仁义开始的。陆贾认为,仁义是治国基础。他以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构建“道基”作为社会治理的框架,这是陆贾不同于先秦儒学的地方,说明他已经有了以儒家为主线,杂采诸子,实现思想大一统的倾向。这正是政治大一统的学术化表现。对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整体观察,使陆贾为“王道”确立了自然法意义上的正当性。在人类发展历史上,“先圣”确立了人道,人道展开就是王道。“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此后由“中圣”确立了教化原则,贯彻王道。“中圣乃设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仪,明父子之礼,君臣之义。”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弃贪鄙之心,兴清洁之行。“后圣”则用五经六艺把教化具体化,建立各种礼乐制度。“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穷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宗诸天地,纂修篇章,垂诸来世,被诸鸟兽,以匡衰乱,天人合策,原道悉备,智者达其心,百工穷其巧,乃调之以管弦丝竹之音,设钟鼓歌舞之乐,以节奢侈,正风俗,通文雅。”(《道基》)这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王道演化脉络,并赋予王道以最重要的仁义内核。“是以君子握道而治,据德而行,席仁而坐,杖义而强,虚无寂寞,通动无量。故制事因短,而动益长,以圆制规,以矩立方。”坚持以仁义为治国准则,就可上承天命,下诛暴虐,忠进谗退,扶正祛邪;不守仁义,国家就会走上秦朝二世而亡的覆灭道路。
道既具有经验性,又具有先验性。道在历史,亦在人心。所以,道既有传承久远的历史佐证,又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心理自证。陆贾称:“道近不必出于久远,取其致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齐桓、晋文之小善,鲁之十二公,至今之为政,足以知成败之效,何必于三王?故古人之所行者,亦与今世同。”(《术事》)一部《春秋》,不需要追溯到五帝三代,仅仅通过鲁国的史事记载,遵循天道与人道,陈述人世善与恶,就足以把治道说清楚。“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由此,陆贾放弃了先秦儒学言必称三代的旧习,而是立足于当下,明确了自己为汉代新帝国确立治道的使命。追溯历史教训,也不必上溯桀纣,有秦二世的例证足矣。由此,陆贾实现了儒学的一个重大转化,不是“兴灭继绝”,而是面向未来。
作为新兴起的大一统帝国,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在大规模和有效性之间寻求合适的治理准则。先秦时期的国家规模有限,五帝三王的直接治理范围并不大。而先秦儒学论证仁政王道,基本上没有考虑过规模问题。像孟子那样鼓吹“百里而王”,在战国群雄并起时代已经失去了可操作性,更不要说秦以后的统一王朝。荀子设想的以礼制规范天下,尚未得到实践证明。要复兴儒学,必须直面大一统帝国的广大范围。对此,陆贾的方案是:以仁义为价值取向,寻求合适的辅政助手,奉行无为而治的基本策略。辅政者就像君主之杖,“杖圣者帝,杖贤者王,杖仁者霸,杖义者强,杖谗者灭,杖贼者亡。”(《辅政》)秦的教训,就是以李斯、赵高为杖。
对于如何选择辅政之杖,陆贾深受道家以柔克刚思想的影响。他称:“怀刚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长,躁疾者为厥速,迟重者为常存,尚勇者为悔近,温厚者行宽舒,怀急促者必有所亏,柔懦者制刚强,小慧者不可以御大,小辨者不可以说众,商贾巧为贩卖之利,而屈为贞良,邪臣好为诈伪,自媚饰非,而不能为公方,藏其端巧,逃其事功。”(《辅政》)作为君主,在鉴别人才上,应该明白“察察者有所不见,恢恢者何所不容;朴质者近忠,便巧者近亡”。“谗夫似贤,美言似信,听之者惑,观之者冥。”(同上)这些论证,明显把道家与儒家合为一体。
治理国家依赖人才,人才并不缺乏。就像名贵木材,自然生长在山林,就看君主能不能用。即便是穷乡僻壤的山野之民,身怀不羁之能、德配圣贤之美者也大有人在。“人君莫不知求贤以自助,近贤以自辅;然贤圣或隐于田里,而不预国家之事者,乃观听之臣不明于下,则闭塞之讥归于君;闭塞之讥归于君,则忠贤之士弃于野;忠贤之士弃于野,则佞臣之党存于朝;佞臣之党存于朝,则下不忠于君;下不忠于君,则上不明于下;上不明于下,是故天下所以倾覆也。”(《资质》)要保证王朝的长治久安,就需要君主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进贤良,退奸佞。
在治理策略上,陆贾强调取守异势,清静无为。他批评秦政道:“秦始皇设刑罚,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行,以服外国,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无为》)相对于成文法制,陆贾特别强调教化和楷模形成的习惯规范。“是以君子尚宽舒以裦其身,行身中和以致疏远;民畏其威而从其化,怀其德而归其境,美其治而不敢违其政。民不罚而畏,不赏而劝,渐渍于道德,而被服于中和之所致也。”(同上)这里陆贾所言,已经是《中庸》的德治主张,遵循儒家倡导的移风易俗途径。所以,陆贾所说的无为,不同于道家的崇尚自然,而是儒家的君子垂范。陆贾对理想的治理臻境有十分具体的描述,他说:“夫形重者则心烦,事众者则身劳;心烦者则刑罚纵横而无所立,身劳者则百端回邪而无所就。是以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鸡不夜鸣,耆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于是赏善罚恶而润色之,兴辟雍庠序而教诲之,然后贤愚异议,廉鄙异科,长幼异节,上下有差,强弱相扶,大小相怀,尊卑相承,雁行相随,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岂待坚甲利兵、深牢刻令、朝夕切切而后行哉?”(《至德》)显然,他和孟子描绘的仁政场面异曲同工,孟子以“制民之产”来实现仁政,陆贾以无为和教化来实现仁政。
鉴于秦朝建立的皇帝制度,在信息传递上有着严重的屏蔽和扭曲现象,陆贾提出,统治者必须注意“辨惑”。与荀子主张的“解蔽”相比,荀子侧重于认知偏差和技术性信息扭曲,而陆贾侧重于社会偏差和权力性信息扭曲。尤其是针对秦朝赵高“指鹿为马”的教训,陆贾强调,有媚俗而造成的信息偏差,有媚上而造成的信息偏差,两者都要防范。否则,视之者谬,论之者误。儒者要做直言不讳的君子,“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为苟容,虽无功于世,而名足称也;虽言不用于国家,而举措之言可法也。”(《辨惑》)对于君主来说,“夫众口毁誉,浮石沉木。群邪相抑,以直为曲。视之不察,以白为黑。夫曲直之异形,白黑之殊色,乃天下之易见也,然而目缪心惑者,众邪误之。”(同上),所以,用人区分正邪,是君主第一要务。由此,陆贾确立了后来为政“亲君子,远小人”的基调。
从思想角度看,陆贾并未对先秦儒学进行深入的理论发掘,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把道家的无为与儒家的有为、把道家的治术与儒家的权变结合起来,把面向以往的儒学改造为面向未来的儒学,把儒者讽喻朝政的本色转化为辅佐朝政的间色,进而确立了“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的主旨(《本行》),为儒学在汉初的复兴开辟了道路。不过,尽管陆贾绝不言利,而且倡导“尊于位而无德者绌,富于财而无义者刑,贱而好德者尊,贫而有义者荣”的政治局面,却在客观上为儒者追逐利禄提供了正当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