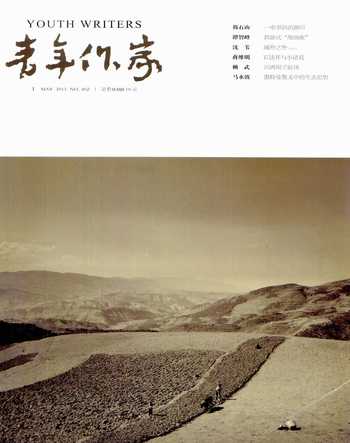我是一个怯懦的作家
王宏任先生是我所敬重的一位作家。
认识宏任先生的朋友,看了或许会撇撇嘴角,不以为然。这,我理解。但是,我要说,你所看到的只是表象。这是因为,盗亦有道,在道的认知上,我们之间,有不小的差异。
不说宏任兄了,说说新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先生吧。
若有人问起我对此公的看法,我也要说,莫言先生是我所敬重的一位作家。我的敬重,不全是他的获得“诺奖”。相反,我倒觉得,“诺奖”的那个授奖词,实在不怎么高明,曲里拐弯,遮遮掩掩,想说什么又不明说。而在我看来,应当明确地上,这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作家,不光关注中国当代现实,同时也关注造成这种现实的历史。举的作品例子是《丰乳肥臀》,错了,应当举《生死疲劳》,至少应当两个都举上。
我敬重宏任先生,跟敬重莫言先生的理由是一样的,不光关注当代现实,还关注造成这种现实的历史。这就是我前而所说的“洛亦有道”的“盗之道”。
与宏任先生接触,早在十年前。那时我编一本刊物,宏任给我们投稿;我喜欢他的稿子,发过两篇。再后来,我们搞了一次评奖,授予他“优秀作家”的名头。发过些什么作品,不去翻刊物了,好在为写这个序,宏任用电子信箱发来几篇,其中一篇是《我亲身经历的生产队》。上了中学后,我就离开了家乡,但我的家人,包括婚后我的妻子与一双儿女,一直在家乡农村生活,所以对生产队、人民公社这一基层的组织,我还是有相当的了解的。宏任所写的是,他自己在生产队生活劳动的经历,包括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我没有这样的经历,也没有这样的感受,但我得承认,他对生产队这一组织形式的解剖与批判,是有道理的,也是深刻的。
另有一篇《食堂挽歌》,不光写了当年农村食堂的龌龊,还写了参加工作后单位食堂同样的龌龊,可以说是一篇深中肯綮的社会批判文章。
同时发来的还有一篇《地主——一个百年难尽的话题》,全文一万五千字的样子,主要由《1978年以前关于地主的书写》《1978年以后关于地主的书写》《地主与革命》《历史评价土地改革》四部分构成。内容就不说了,让我吃惊的是,书里所摘录的两位“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的话语——一位是周同宾,一位是史铁生。
周同宾在《土地梦》里说:“我们村里有几家地主,都是东家领着长工干活儿,锄地、收麦,都是东家干在前头;大忙时候,东家吃高粱面花卷,给长工蒸白馍,东家吃辣椒、豆豉,长工的菜里总有腥荤……那几家的地,都是三亩五亩买来的,历经几代才置下那份家业……永不是我后来从小说中、电影里、图画上所看到的地主的可恶形象。”(《北京文学》一九九七年七期)
史铁生在《记忆与印象》里说:“太姥爷,一个典型的中国地主……他有几千亩地的时候,出门赶集,见到路旁的一脬牛粪他也要兜在衣襟里捡回来,抖搂到自家地里。他只看重一种东西地。‘周扒皮那样的地主一定会让他笑话:你把长工都得罪了就不怕人家糟蹋你的地?……太姥爷比‘周扒皮有远见,对长工从不怠慢……长工吃什么他也跟长工一起吃什么,甚至长工们剩下的东西他也要再利用一遍,以自家肠胃将其酿制成自家地里的肥。他守望自家的地,盼望收获很多粮食,卖很多钱,买很多地。他不想这些为什么,他自己最风光的时候,也不过是一个坐在自己土地中央的邋里邋遢的瘦老头。”(《小说选刊》二00一年九期)
看了这样的话语,我只有惭愧。我家的成分是富农,我姥姥家是地主。我是在“文革”前就上了高中、继而上了大学的,有那么十多年,我最怕的事情,就是人家说我与反动家庭划不清界限。我先前的写小说,只是为了将妻子儿女的户口迁到城市跟我生活在一起。我所写的是农村题材小说,但我对农村实际上没有什么感情,还有一种厌恶与恐惧。当我把要办的事情都办了,知道再写农村题材的小说,势必要接触到农村的历史时,但主动放弃了小说写作,躲到书斋里研究起与现实无关的文学人物,写传记文学作品了。
在强大的现实政治面前,我承认自己是个滑头,是个懦夫,只是还没有到心如死灰的地步。
虽说不写小说了,但多少年来,我一直密切地注视着文学界。心里一直对那些敢于正视农村现实、也敢于正视造成这现实的历史的作家怀着深深的敬意。周同宾先生早就相识,也是因为这一点,多少年来,我有了得意的作品,总会寄他一册。没想到的是,神仙似的史铁生先生,也会说出这样的话,想起以前挖苦他“《我那遥远的清平湾》写的跟回姥姥家一样”,真是不应该。我真正敬重莫言,并不是他写了《红高粱》之后,而是他写了《生死疲劳》之后——我并没有看过,其大致内容是此书出版后的第二年春天,参加一次小说评奖活动时,主持人介绍的;一听那内容,就毫不犹豫地投了一票。
自己不敢做,做不到的事,别人做了,能不敬重?
再说一遍,王宏任先生是我所敬重的一位作家。
你有一千条理由说他够不上,我有这一条理由就够上,且还有馀头。
(本文系为《王宏任散文选》写的序)
[作者简介]韩石山,当代作家,一九四七年出生,山西临猗县人;一九七零0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曾任《山西文学》主编、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徐志摩传》《李健吾传》《韩石山文学评论集》《民国文人风骨》及自传《装模作样——浪迹文坛三十年》等著作三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