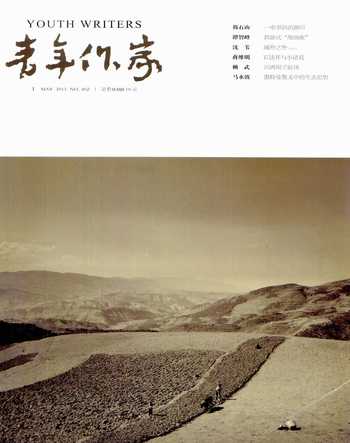一串歪斜的脚印
一
题名中嵌入“歪斜”二字,不是人前撒娇,故作稚嫩,实在喜欢这两个字的本义。回顾我在文学批评这条路上走过的身影(假若一个人可以在多年之后,看到自己当初的身姿的话),踉踉跄跄,歪歪斜斜,实在是最好的描述。如果说,这还只是比喻,若与正统的批评路子相比,“歪斜”二字就不是比喻,而是实指了。
写作之初,我给自己定下了两个禁忌;一是不写诗;二是不写评论文章。不写诗,是我觉得,旧诗都让古人写尽了,新诗根本就不是诗,只有天才才能写得了新诗,我是地才,还是不要沾这个边为好。评论文章,则怕是从那个时代的“大批判文章”得下的印象,觉得这活儿,就不是我这样出身不好的人应当干的;理论是灰色的,评论也不会多么光亮。
写诗的禁忌,至今没有破除;而不写评论文章的禁忌,很快就破除了。
一九八0年春夏间,曾参加由中国作家协会办的“文学讲习所第五期”的学习。这个所,后来改名为“鲁迅文学院”;我们这个第五期,是延续五十年代“中央文学研究所”的顺序排下来的,实则是新时期的第一期;学员三十一二名,除了我这样的平庸之辈外,多是全国文学界的青年才俊。那几年,“全国短篇小说奖”获得者,是个很高的名头,我们这一期学员里头,首届获奖者就很有几位。其中一位叫“刘富道”的,跟我很要好。他的获奖作品是《眼镜》,隔了一年,又以《南湖月》获同一奖项。
一九八二年春天,我的一篇小说获得一个小奖,去广州领奖返回路过武汉,舍弃卧铺票,下车去看望富道。闲谈中,说起眼下的文学评论,都感叹跟不上创作的趟儿。他说有人写过评他小说的文章,评价不低,却不得要领,搔不到痒处,更让人难受。我说,我来写一篇试试。你能写得了?这话他当时肯定没有说,那不是他的风格,而他细眯眯的小眼,把什么都说了,我不会看不出来。只是约定了一个时限,说他的短篇小说集子,已编起送出版社,很快就会出来,待出来后寄我再写不迟。
那时我已离开汾西县中学,去了汾西县城关公社挂职深入生活。到了秋天,他的集子出来了,又寄来几篇新发表的小说。我便据以写了篇八九千字的评论文章,题名为《心中唱着一支妙曲——刘富道的小说艺术》。
给谁家呢?那两三年,心气高得很,觉得中国的文学刊物,哪儿会不认韩某人的文章,正好的我短篇小说集子,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文学评论》的杨世伟先生写过评论文章,便寄给了杨先生。
这一宝,还真押对了。《文学评论》一九八三年第一期全文刊出,编后记里,还夸了两句,说作家写的评论,如何鲜活生动。实际上,这篇文章,有些散漫,不像个评论,倒像篇读书随笔;只能说结构还有章法,文辞也还讲究,该有气势的地方,一点也不示人以弱。比如开头几句,是这样的:“富道兄将他的集子寄给我,仅仅是出于情谊,并非要我写点什么。他知道,我是写什么评论文章的。同样,仅仅是出于情谊,我将他的集子细细看了一遍,看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要写点什么:我比他更知道自己,我从未写过评论别人作品的文章。但是现在,我却不能不写点什么。”明眼人一眼就知道,这是谁的文风;若还看不出来,将最后一句里的“但是”改为“然而”,脑子里马上就会闪出一个“鲁”字来。——若还看不出来,我只有感叹你的纯洁与无知了。
这还只是开头,正文里,竟有我与刘富道的对话。说是鲜活生动,倒也不假,不敢说句句见机智、处处显才华,总是能见能显的地方绝不会轻易放过。比如那个篇名,就是由误听而来。在武汉,富道跟我聊天,说他每写一篇小说,必定“心中藏着一个妙处”,相当于说,他写小说时,必有一个包袱在那儿兜着,到了最后才抖开。他那湖北口音,我听来竟是“心中唱着一支妙曲”,后来是弄清了,可我觉得,还是误听了的句子更有意趣。一个作家写作时,心里老在唱着一支妙曲,笔下该是如何的轻盈灵动,人物该是如何的顾盼多姿。
那几年,作家写文学评论的很少,要写也多在一些文学类报刊上登载,像我这样,长篇大论且登在《文学评论》上的,少之又少。
真正奠定了我在文学评论上的一点声名的,是过了两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评贾平凹小说的文章。
一九八四年秋天,承几位老作家的美意,调我到山西省作家协会,名分是专业作家,先做的是创办《黄河》杂志。为了约稿,跟贾平凹先生有过联系,他那时势头正好,中篇小说,一篇接一篇,几乎篇篇都获好评。未必是让我为他写评论文章,极有可能只是同道间的一种切磋,知道我已看过他的什么,又寄来几篇我没有看过的。那时我刚安下家,事儿不多,也就全看了。看了这么多作品,不写点什么,总觉得亏了,于是便写了篇一万多字的评论文章,名为《且化浓墨写春山——漫评贾平凹的中篇近作》,仍寄《文学评论》,很快又发表了。
这次的文章,不那么散漫了,有了整体的考虑,也有了批评的意识。觉得光说好话,显得品位太低了;机警俏皮,也只能说是小焉者之道;切实的剖析、中肯的指谬,才是评论文章的正途,也才能显出自己身手的不凡。我所采用的办法是,好处要说足,不好处也要说足,绝不含含糊糊、模棱两可。看了贾氏的几个中篇,能感到既有独特的风格,又有共同的局限,这就是故事的模式化、人物的类型化。关于前者,我是这样说的:“读他的几个中篇,总感到是一个味儿:商州山地的一种或几种古老风俗,当前农村一种或几种致富门路,旷男怨女之间的一场或几场感情纠葛。难得的是,他能为文造情,写得那么洒脱、那么兴致勃勃。”关于后者,是这样说的:“或许是个人气质的原因吧,平凹作品中的女人都是情种,男人都是些谦谦君子,即使事业上百折不挠,在女人面前都总是那么木讷和腼腆。”
几个中篇里,我最喜欢的是《天狗》,对此篇的评价也就特别的高。
“天狗”是作品中一个木匠的名字,像作者其他几个中篇的男主角一样,也是个木讷腼腆而心里透亮的人物,暗恋着已不年轻却异常温柔体贴的师娘。师娘待他总像没有成人的人,一只小狗。而他,也就圆满着师娘的看法,装出一脸混混沌沌、天地不醒的憨相。待师傅受伤后,他娶下了带夫改嫁的师娘。
在这篇作品里,平凹将他善于写农村年轻女性的本事发挥到了极致。我的赞赏,也到了挥霍的程度。在分析了天狗的心理之后,说到师娘:“这是怎样的一个精灵哟!年近四十却有着少女的纯情,感情细腻真挚又绝无半点轻浮。是日落前的最后一抹晚霞,是月上东山后的最初一片迷人的清辉。‘乞月一节,写尽了她的俏丽与温存。她的‘声调是那么的柔润,从天狗的心上电一般酥酥通过。”末后说,“《天狗》虽未脱风俗、致富、儿女情的老套,但布局疏朗,不枝不蔓,通篇又缭绕着凄惋幽怨的情思,达到了一种高雅的艺术境界,也可说是已臻思想的高度。”
接连在《文学评论》上发了两篇评论长文,一时间我写评论的声名,似乎盖过了我的那些平庸的小说。好些文学界的朋友,或是直白相告,要我为他写篇文章,或是意意思思地表达,是否也来上一篇?我呢,那些年也真是海纳百川,气冲霄汉,只要说出口而又时间允许,莫不有求必应、有应必佳;且还是不写则已,写则必长。不必做什么精确的统计了,光收入《韩石山文学评论集》里,写山西作家的评论文章,就有评钟道新的《聪明的小说家》,评李锐的《沉下去的与升上去的》,评权文学的《在艺术的山凹里》,评田东照的《他超越了自己》,评孙涛的《纷纭的人生图景》,评崔巍的《黄土地上的执著》。当然,不全是本省作家的,一有机会,还要评一些全国名家,比如评王蒙的《当代长篇小说的文化阻隔》,评林斤澜的《明日来寻都是诗》,评蒋子龙的《(阴差阳错)的文化意识》。
到了一九八九年,编企业家的传略赚了几个钱,做什么呢,总不能老揣在怀里吧,便拿出一部分,出了本文学评论集。是刘富道联系长江文艺出版社办成的,顺势请他写了篇序。说是“顺势”,也是真心的请求,他的文章之好,是我素所敬重的。商议书名的时候,我想了这个想了那个,富道说,干脆就取名《韩石山文学评论集》吧,又气派又醒目。我说,敢吗?富道说,有什么不敢的,你这么做了,别人也就这么认了,要不,你想在文学评论上出人头地,还不知等到哪一辈子。一想也是,像我样档次的作家,等着出版社找来,嵌上姓名出本文学评论集子,是这辈子都不敢指望的事。
那几年,出版社做事也还认真,长江文艺出版社的领导,专门派人来太原监印。
一九八九年五月,大红封面,带点现代派设计风格的《韩石山文学评论集》出版了。
这一阶段,可说是我从事文学批评的起步期。很有点像农村青年,想当个木匠,只能是先给亲戚家做个凳子给邻居家做个柜子,练练手再说。
二
进入九十年代,我的心绪坏极了,小说出了几本,毫无影响,当年在文讲所学习的同学,这个那个,一个个红得发紫省内跟我一茬的年轻作家,实际是中年人了,那个这个,接连有佳作问世。我知道自己的长处,也知道自己的短处,在小说写作上,是无法与时下的才俊们争一雌雄的。
最大的问题在于,名分上我是写农村题材的小说作家,而实际上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我对农村从来就没有好感。也就不会有真正的热情。那些年之所以写农村题材的小说,是因为在山西这个地方,在文学创作上,各种条件的制约,只能如此也甘愿如此。有时候还暗自欣喜,以为自己真有这方面的才华;而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担心,知道总有一天会走到山穷水尽、水落石出的地步。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也就是那个时候,我认定自己,再写下去也只是个三流作家。
只有转向,才能起死回生。
几经考虑,我决定转入现代文学人物的研究、传记文学的写作。在这上头,我还是有点优势的。上大学学的是历史,虽没有学成个样子,传记的写作,也还懂行。多年从事文学创作,文笔上的功夫还是有的。这两个长项结合在一起,或许会杀出一条血路、闯出一个新局面。在这上头,谢泳先生给了我许多的鼓励。比如我当时还想着是不是写上一段再转,谢泳说,要转,还是越快越好。这样,1993年冬天定下写《李健吾传》,第二年一开春,就与谢泳一起去北京查资料了。他确定研究储安平这一人物与《观察》这一刊物。
此后几年间,仍未放弃写评论文章。
这一时期,我的评论文章仍停留在为朋友帮忙的层面上,只是偶尔地会主动出击,写些自己想写的文章。比如马烽当了中国作协的党组书记,有人说马烽是丁玲的人;丁玲是左派,不如周扬能识时务、支持改革开放。毕竟看书多些,清楚三十年代的文学派系,我觉得,持这种观点的人,要么是不懂得历史,要么是心术不正,有意要蒙蔽历史,糊弄文坛上的年轻一代。于是便写了篇《酒醉的探戈》,从三十年代周扬、丁玲在上海与鲁迅的关系,说到两人到延安后的不同处境,一个操持鲁迅艺术学院,一个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解放后,一个主持中宣部(分管文艺),一个创办中央文学研究所,各有自己的体系,互不服输。概括地说,周扬的势力在中央文宣部门,丁玲的势力在各省市文联。“反右”中丁玲一派受到重创,干将们纷纷落马;未落马者也纷纷离开北京,山西的马烽、西戎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到山西的。“文革”后,周扬先出来,占据了领导岗位,千方百计阻挠丁玲复出;待丁玲克服各种阻力出来,历史留给她的,只能是一个“左派”的位置:老“左”们成了右派,真正的“右派”成了老“左”,这就是历史跟中国的文化精英们开的一个天大的玩笑。(收入《黑沉中的亮丽》一书)
从这篇文章开始,我的文学评论才有了文学批评的意味。以后就叫“文学批评”吧。
大约一九九五年,在天津的一次小说学会的年会上,认为了任芙康先生,当时他是《文学自由谈》的副主编,主持工作。他知道我还写得了批评文章,问我手头可有现成的什么;我说有篇《酒醉的探戈》,写下好久了,不知他敢发不敢发;问清写的什么,他说这怕什么,拿来就是。这样,这篇东西,就在《文学自由谈》上发表了。芙康绝对是个优秀的编辑,也可说是个办刊物的虫子,知道怎样“笼络”人才,怎样把办刊办得水起风生。这是不能不叫人佩服的。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怕个佩服;佩服之后,就没有道理可言了。从此之后,我俩就像是订了君臣的名分,常是他来个电话,说来上一篇吧,我就放下手头的活儿来上一篇;且是不写则已,若写一定是正中他下怀的那种。如果说他是“二郎神”的话,我就是他身边的“哮天犬”了。有那么两年,《文学自由谈》上几乎期期有我的文章。这当然也是因为这刊物是双月刊,几乎期期有,两年下来也只有十一二篇。
芙康还有一招,也是不能不佩服的。那就是,凡是他认为适合他那刊物的文章,管你在什么地方发过,他还可以拿来发表:改吧改吧,便是一篇新作了。
例子是现成的,就是那篇《谢冕,教人怎么敢信你》。
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文艺报》组织的。
一九九七年夏天,我和芙康一起去云南,参加一个文学活动,认识了《文艺报》的编辑历健先生。八月,历健组织文章,批评北大教授谢冕,不该跟他的弟子孟繁华合作,编了两套大致相同的《中国文学经典》(另一套似乎叫“中国文学经典荟萃”);知道我写得了这类文章,给我来电话,要我在太原再找两个人,写篇谈话式的文章。我约了《山西日报》副刊的李杜和省作协理研室的阎晶明二位,就在小阎的办公室里谈了一次,效果不怎么好;后来是小阎说的吧,干脆一人写一篇算了,当下分了题目,小阎谈学理,李杜谈入选作品,我谈谢冕一人不该同时推出两部经典,中心都要落在一个教授,两部经典,叫人该信哪部?写起后,寄给历健,表示满意。九月二十七日,《文艺报》同时刊出李杜、阎晶明和我的文章。芙康看了报,觉得我的文章也可以在他那儿发一下;改吧改吧,便在稍后一期的《文学自由谈》上发表了。
没想到,这篇文章,成了我从事文学批评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几年间,朋友们见了,无不谈论这篇文章。至少有两家出版社,要出我的文学随笔集,所看中的就是这篇,只要收入这篇,别的随便搭配。
这篇文章之所以造成很大的影响,不光是因为我的文章太刁钻古怪,也与谢冕的弟子们的猛烈反击有关。而我呢,竟也一以当十,愈战愈勇。比如同年秋天,南京《东方文化周刊》第四十九期上,同时刊出四篇文章,除一篇不偏不倚、故作中允之论外,其他三都是替谢冕辩护的,作者分别是程某、贺某和徐某——过去的事了,我不愿意再说他们的名字。
数徐某的一篇最为嚣张、尖刻阴损,一点也不在我后来的反驳文章之下。“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礼记》上的这句话,我还是记得的。徐文名为《你以为你是谁》,比如这样的句子:“韩石山因为无知,所以胆大,推断起别人无所顾忌。”“他想出名,但无缘出名,或者说无才、无德出名,瞑(应为“冥”——韩注)思苦想,终于想出个‘石破天惊的妙法:捧人捧不成,干脆骂大人物,谁的名气大骂谁。”谢冕的另一个大弟子孟繁华,则在《中华读书报》上,以答记者问的形式,狠狠地将我贬低了一通,说我怎样地不懂学理,胡搅蛮缠。对这两位,我都写了反批评文章,回击徐的叫《不管我是谁》,回击孟的叫《先说公理,再说学理》。
徐某不是说我“你以为你是谁”吗,我的文章中,是这样反驳的:“我是我父亲的儿子,是我儿子的父亲,我是个不学无术的笨伯,是个无恶不作的混蛋,我什么都可以是,就是不是你的谢老师,就是不是这两套《经典》的主编人。”又说,从徐某蛮横的语气里,我敢断定此人是个从偏远乡村里出来而又不用功学习的那类学生;只有这样的学生,才会认为谁批评他的老师谁就是想借此出名,才会用这种手段来报效师门。
这已经是一九九八年二月间的事了。
主要是这次对谢冕的批评,及其后对谢冕弟子们的反击,让我在文坛得了个恶名,叫“文坛刀客”。最近我为《文学报》看稿,有个叫“古远清”的学者,为他的朋友谢冕的一套书写介绍文章,其中就说,韩石山不是文坛恶棍,至少也是个文坛恶人,劝谢冕再编文集时,应当将这个恶人的文章附上。这样做,一点也不会掩去谢教授的光辉。可惜的是,文章刊出,奉承我的那句话,叫编辑勾去了。古教授见了,见里定然不以为然他不知道,我比他更为遗憾——我从来不认为,在当今文坛当个恶人甚至坏人,是什么不名誉的事。
在古教授的眼里,韩某人就像条疯狗似的,在文坛上四处浪荡,寻找像谢冕这样的好人,扑上去狠狠地咬上一口。
下面这件事,看看是谁在咬谁,谁的本事更大些,谁的心地更毒些。
二000年,我担任《山西文学》主编,忙于编务,很少写批评文章。当时的心理,真的像邓丽君小姐的一首歌所唱的那样,希望当今文坛,对我这个三流作者能网开一面,“慢慢地,慢慢地,把我忘记”。但是,世上的事就是这么怪,人要是名声坏了,喝水也会磕着牙,大白天也会撞上鬼。
且说事儿。二00三年五月中旬,正是“非典”期间,有位读者,送我一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艺批评学教程》,说让我看看,某页上有“骂”我的话。书和信,都放在传达室,说非典期间,还是不见面为好。
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理论编》。关于我的一段话,在该编第十一章《氛围论与争鸣论》的第二节《氛围论》中。原文为:这种“棒杀”式的文章,“不仅蔑视学理,而且常夹杂着格调低下的人身攻击……谢冕重复编选二十世纪文学经典,或许有不当之处,但韩石山却对之进行了人身攻击,不仅有失作为一位批评家的严肃,甚至有失文人风范”(第164-165页)。
这本书的参与者虽有十多人,主编周忠厚说,实则是以他的教案为底本完成的。我断定这几句话就是周忠厚写下的。
我的反驳文章叫《我不配上中国人民大学的教科书》,对周忠厚这种以教案当专著的教授狠狠地挖苦了一通;收入《谁红跟谁急》时,在《辑前小语》里,对中国人民大学这样的大学也挖苦了一通,说中国的大学里,我最看不上眼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的大学,以“人民”命名的,就它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些叫“人民”的确实有道理,各地都有它的分支机构,一个大学怎么叫“人民”呢,莫非全中国就这么一所大学,其他大学都是它的分校?这样的大学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全国性的党政干部培训学校。
这一时期写下的文章,后来大都收入二00六年出版的《谁红跟谁急》一书中。这本书,真该请任芙康先生写个序,没有他的引诱与催促,我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写下那么多的批评文章。
这本书的编排有点怪,不是以我的写作时间为序,而是以我批评的对象的姓氏笔画为序,计有王朔、王蒙、刘心武、任芙康、陈漱渝、余秋雨、余杰、摩罗、孔庆东、汪曾祺、周忠厚、赵俪生、贾平凹、钱钟书、萧乾、梁从诫、韩东、朱文、韩少功、童志刚、鲁迅、路遥、谢冕、魏明伦等二十多位。我曾经说过,中国文坛上,我批评过的人数,超过一个排,加上后来写的,看来差不了。
在《文学自由谈》上接连发表文章并结集出版《谁红跟谁急》,可以说是我在文学批评上的风光期。
三
然而,在文学批评上,我最为得意的也是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不是《谁红跟谁急》,而是我的《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
这是一本现代文学的研究著作,也是一本文学批评的单本著作,重在事实的疏理、是非的辨析;二00五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初版,到了二0一二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又出了修订版。初版出来后,反响之强烈,出乎我的意料。正面的不说了,反面的最能看出个什么——有人写文章,指斥韩某人所秉持的是“一种破坏文化的逻辑”;有人写了整本的书,大骂韩某人如何的“操蛋”。
且听我从容道来。
二00五年春天,一直在北京漂着的儿子,原在一刊物做得好好的,忽然心血来潮,辞了职要办个小公司出书。办就办吧,在北京办什么的都有,何况他要办的是个文化公司,要出的是书呢。料不到的是,一出手就打上了他老爸的主意。他知道他这个老爸,要钱没钱,要关系没有关系,有的就是一点写作的本事。电话里说,你不是在《山西文学》上发了篇演讲吗?说是呀;叫《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是吧?说是呀。下面就不成话了:我看你这篇演讲怪好的,就是好多意思还没有说清,还可以再往深里挖挖。这样吧,写上本书,就用这个名字;不用多写,二十几万字就行了。写了给我发过来,别的你就甭管了。
一篇演讲稿,不过万余字,怎么能扩展成一本二十多万字的书呢?
我当下就要拒绝,老伴不答应了,夺过电话说,你爸说让他想想,你该做什么先做着。电话一放,脸色立马就变了,指着我的鼻子训斥道:那些女孩子,电话里嗲着声儿说个韩老师,给我写篇文章吧,你马上就是对对对;说个韩老师,给我编本书吧,你马上又是对对对。儿子要办个公司让你写本书,就拿捏起来了。有你这么当老子的吗!真是个贱骨头上不得台盘!
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写。
好在我书房里,关于鲁迅的书、关于胡适的书有的是。缺点什么,找同院的董大中先生、谢泳先生借来就是了。儿子给的时限是三个月,那些日子,真是全家动员,一派繁忙景象,不亚于农村的抢收抢种。我只管写正文,要引述什么了,在书上用铅笔画出,女儿女婿连同老伴,分头录入。每录入一段,用优盘拷过来再由我整合通顺。
不到三个月,书稿完成了。
出版,就没这么顺当了。儿子的小公司,只管发行,出版是出版社的事。
在中国,任何出版社的任何出版物,都是要经过一级一级审查。此书曾送上海一家出版社,二审已通过了,三审打了下来。我并不埋怨他们。我从来认为,人我同理,只要是一个正常的审查程序,别人有通不过的,你遇上了也不要怨恨。我还要感谢他们,这家出版社的一个编辑,记得姓朱,是位女同志,认真地通读了书稿,画出该删去的地方。后来送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我一句都没有恢复。等于她为我把了次关,才有了“友谊”送审通过的可能。
“友谊”也让作些删节,二话不说,删去就是。
我只盯着一两句话,看让不让删,只要这一两句话不删,删什么都行。其主要的一句是:“中国若不打算走向现代化则罢,若打算走向现代化,又要在文化上选择一个从旧时代到新时代的传承式的人物,只能是胡适而不能是鲁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版第309页)
二00五年十月,《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正式出版。首印一万五千册。一时间,国内文化界竟形成一个不小的热潮,数十家报纸刊发消息,有的还摘录与评论。至今仍记得,《新民晚报》一位叫“李菁”的记者。写的一篇报道评价甚高。
这样的书,除了出版社审查,还要送新闻出版局审查;没有禁止发行,多半是沾了写法的光。看过书的朋友,好几个跟我说,书里你的话很少,几乎全是材料,好在还酣畅顺溜,要不是看不下去的。他们不知道,这也正是我用心良苦的地方。不这样,自己的话说多了,能出版吗?不说别的,光那个怪怪的书名,就没有出版的可能。
初版万余册,三两年即销售一空。六年过去了,陕西人民出版社又出了修订本。已然有相当数量的读者,预计将来还会有更多的读者。
用一本书的容量批判我的,是福建作家、鲁迅研究者房向东先生。其书名《著名作家的胡言乱语——韩石山的鲁迅论批判》;书前还有北京大学一位姓袁的教授写的长序,名为《反鲁英雄韩石山、苏雪林优劣比较沦》;上海书店二0一一年一月出版,二十多万字;封底有推荐语,其中说:“本书是一部从题材到风格都可称别开生面的鲁迅研究专著,主题是对近年来到处演讲出书的‘文坛刀客韩石山的‘鲁迅论作出比较系统的、纯学术性的批判。”
书中骂我的话是:“韩石山是若干个关于鲁迅与‘文革与专制主义关系的论客中最为操蛋的一个,操蛋就操蛋在不加论证地蛮横的下定义。”(见该书第154页)
“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逭。”多亏这是一则古代的民谣,而不是当今的律条,否则真不知会是怎样的一个后果。奇怪的是,作下这么大的孽,我却只有高山大海、遗世独立、凭栏长啸、心旷神怡的感觉:真是没得救了。
想不到的是,我一位多年的老朋友,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先生,也会动了怒,写出一篇杀气腾腾的文章,名曰《又一种破坏文化的逻辑》,副题为《评<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并论近年来的“崇胡贬鲁”之风》,登在二00六年《南方文坛》第四期上。为这篇论文,元宝还获得了该刊的一个年度奖,奖金人民币若干元。
元宝很会写文章,峻急的批评文字中,仍荡漾着些许诗意。比如我主张将多数鲁迅作品从中学课本上撤下,留下两三篇就足够了,元宝说:“我倒想请教韩石山,不喜欢鲁迅是你的权利,安知中小学生就一定和你一样不喜欢呢?中小学语文教科书在现代文学中不选鲁迅,还有什么作家更值得入选?永远让中小学生在荷花荡漾、荷塘月色和桨声灯影的秦淮河里提迷藏吗?”
我的反驳文章叫《让我们一起谦卑服善——致郜元宝先生》,写成后寄给《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女士,承蒙不弃,也给登了。
我的文章,其峻急刻薄的程度,一点不在元宝先生之下。且看这样几句:“我一边看一边不由地感叹,元宝不愧是大学教授、博导,不愧是文艺理论家,不愧是鲁迅研究的专家,就是有学问,就是懂逻辑,是理不是理都能说成理且头头是道……真的,我一点都不反感。我只是想着,看元宝能教我点什么,让我在观点上有所修正,在资料上有所补充,至不济,在写文章的方法上能学上两手。”接下来笔锋一转,“可是元宝,我失望了,我什么也没有得到,得到的只有一个感觉,你这么年轻,这么好学,怎么思想就这么僵化,见识就这么陈腐,说理就这么专横,连文章也越写越差了呢。当然,你是好人,这我一辈子都不会变的。”
对郜元宝那么尊祟鲁迅又那么鄙视胡适,我是无法理解的,并就此写道:“元宝,咱们不说我的书了,我的书确实一无是处,咱们平心静气地谈点别的好不好?你是安徽人,和胡适算是老乡,你真的认为你的这个老乡就那样不给你争气吗?你真的认为胡适在人身自由、民主政体上的见识,反在鲁迅之下吗?你真的以为‘从一九一八年参加新文化运动到一九二六年离开北京,鲁迅的成绩谁人能比吗?你真的认为,那么长的时期内,中小学课本上选那么多的鲁迅作品,而对胡适的作品一篇也不选,是人心之所向吗?说了那么多年鲁迅,就不该让我们的人民认识胡适的价值吗?你是大学教授,真的不认为该在你或别的文学教授的课堂上,是作为一个人物而不是作为一种政策的赐予(比如改革开放的政策)、是作为一个历史的存在而不是作为一个别的什么的陪衬(比如鲁迅的陪衬),多给你们的学生讲讲胡适吗?”
最后说:“不说了,这次什么都不多说了,再说你也不会听我这样的破坏你们的文化逻辑的论者的话的,未了,我只想说一句,但愿你或许会听从,就是不管各自的年龄如何、各自的地位如何,也不管各自所操持的理念如何,仅仅作为一个读书人,让我们一起谦卑服善。”
说到这里,还想说句题外话。去年莫言获得诺奖后,我见过几位评论家的文章,动不动就说鲁迅当年对推荐他得“诺奖”的态度。近日又看到郜元宝的这样一篇文章,题名叫《因莫言获奖而想起鲁迅的一些话》,也是先引了鲁迅的那句话。
我有个奇怪的感觉,这次莫言获奖,最难堪的不是那些自认为不比莫言差的小说作家,而是那些有“鲁研”背景的文学评论家们。记得有位作家说,莫言能获奖,中国至少有十个作家该获奖。这样说固然荒唐,前提还是中国作家应当有人获奖,只是嫌一个太少了。而那些有“鲁研”背景的文学评论家们就不同了,没有人获奖,他们永远有话可说,说鲁迅早就说过了,梁启超不配,他自己也不配;希望“诺奖”评委不要对“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这样“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只要诺奖不给中国人,这句话就永远有效,其功效在于,不光中国的文学评论家听信鲁迅的这一套,连“诺奖”的评委们也听信鲁迅的这一套。只要中国作家无人获奖,他们就永远有话可说,就永远占据着一个恣意评判中国文学的制高点。在他们看来,鲁迅的话,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魔咒,谁也解不了,也就永远不会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作家获得此奖。而现在,“诺奖”评委这些孱头们,竟然不听鲁迅的话了,竟然筷子里头挑旗杆,挑出一个莫言给了这么大的一个奖,让他们往后怎么再重复鲁迅的话呢?几十年前鲁迅都不配,几十年后的莫言就配得了吗?活活气煞人也!
这类文学评论家里,郜元宝是最为典型的一位。
纵然这样,我仍要说,郜元宝先生是“鲁研”背景下,最有才华的一位评论家,也是最有益惑力的一位说教者。当然,如果元宝先生不反对,我还要说,他仍是我在学界的一位要好的朋友。
该说句总括的话了,真不好说,想想,还是说了吧。《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是我文学批评的殿后之作,也是集大成之作。这年我已五十八岁,距写《心中唱着一支妙曲》已二十三年了。此后,很少写文学批评文章。
不是我厌倦了文学批评,是我觉得,人老了,就得像个老了的样子。
二0一三年一月三十日于潺湲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