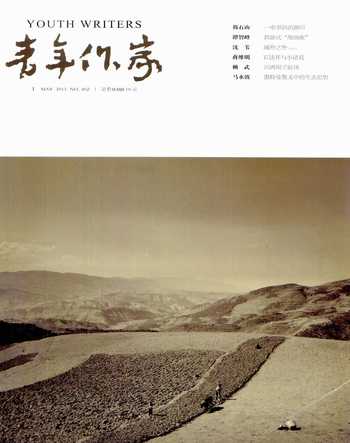斜卧式“维纳斯”
谭智锋
“维纳斯”是西方艺术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形象。自乔尔乔涅在《沉睡的维纳斯》中塑造了斜卧式的裸像“维纳斯”以来,这个经典图式已成为众多裸像艺术家创作灵感的不竭源泉。本文对乔尔乔涅、提香、马奈及摩尔等人所创造的“维纳斯”的身体意象进行分析,探讨斜卧式女性裸像在不同时代所蕴含的文化精神和艺术理念。
——编者按
斜卧式的女性裸像
作为女性身体意象的代表人物,裸像“维纳斯”一直是欧洲艺术魂牵梦绕的一个艺术形象。古希腊时期女性裸像虽然没有像男性裸像那样经历了复杂的谱系化的探索之路,但却产生了像《克尼多斯的维纳斯》《米洛斯的维纳斯》这样的艺术杰作,充分地体现了古典时期女性身体的理想美。不过,“维纳斯”在古典时期的后期就开始逐渐被艺术冷落,中世纪时期又成了道德和宗教责难的对象,这个艺术传统历经了极具破坏性的断裂。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维纳斯”才开始逐渐再次现身于艺术的殿堂,并有了更为丰富多样的表现,而且在后来的艺术中不断发展出各种各样的形态和模式。这样,在历史发展和社会语境的变迁中,“维纳斯”从罗马神话中的女神逐渐演变成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符号,不断反映着裸像艺术家们文化思想和艺术理念的嬗变。
作为一种表意的符号,人类的身体姿态是表达情绪的基本方式之一,也是传达文化精神、艺术风格的重要代码之一。在裸像艺术的历史长河中,“维纳斯”的主要姿势也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发生变化,从古典时期主要的立姿发展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及其之后的坐姿和卧姿。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艺术家们在斜卧式姿态中找到了能够更充分揭示不同时代文化特征,并展示其最为动人、最为深刻的艺术魅力的“维纳斯”形象。斜卧的女性身体将身体拉伸到最长,使之具有最大程度展示自身的可能性,象征着敞开、开放,象征着对所有人的接纳。从图像学和心理学来说,斜卧式是最具“女性特质”的一种姿势,这样的姿势与其他身体部位的形态结合在一起,更能充分地说出女性身体的秘密以及揭示隐藏其中的文化主题和复杂意味,比如能传达出一种更加世俗化、人性化的情感,比如能通过目光的抗争而揭露窥视的“阴谋”,比如能呈现身体的“无蔽”空间而揭示其与宇宙的关系等等。相反,男性裸像更多采取的是站立姿势或者端坐姿势,因为这更能展现其人体力量、英雄气概及悲壮情怀。
第一次让女性裸像“维纳斯”躺下来的是乔尔乔涅的《沉睡的维纳斯》。乔尔乔涅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个有着非凡魅力的画家,对后继者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对于审美哲学家来说,在真实的乔尔乔涅和他现存可靠的作品之外,还有一个‘乔尔乔涅风格,它体现在不同人身上。”(沃尔特·佩特《文艺复兴艺术与诗的研究》)而这幅斜卧式的“维纳斯”就是“乔尔乔涅风格”的集中体现。对于裸像艺术来说,这是一幅完美的、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画作。肯尼斯·克拉克认为,由于沉睡的“维纳斯”如此静谧、自然,以致大家不能马上注意到她的独创性,“她不是古典的,一个斜倚着的裸体妇女从未成为任何古典著名作品的题材,虽然在酒神石棺上可以发现类似的裸像”(肯尼斯·克拉克《裸体艺术》)。酒神石棺上斜卧的裸像是作为群像中的一部分,而且并不是最为重要的角色,但乔尔乔涅的“维纳斯”则占据了整个画面的中心,是艺术作品的关键点,她的“躺下来”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斜卧式维纳斯”如此地独具魅力,因此成了后来女性裸像的一个经典图式,影响了众多裸像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从乔尔乔涅开始,经过提香、委拉斯贵支、安格尔、戈雅、马奈、莫迪里阿尼、亨利·摩尔等人的不断演绎,斜卧式“维纳斯”这座神奇的女神像,在艺术领域中持久地散发着诱人的光芒。
世俗“维纳斯”:从沉睡中苏醒过来
文艺复兴时期是“维纳斯”重见天日的重要阶段,标志着“维纳斯”在艺术史中再次谱就她的辉煌图卷。所谓“文艺复兴”,即指“在古典规范的影响下,艺术和文学的复兴”,其主要思想是关怀人、尊重人,突出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而对人的价值的肯定,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人体美的展现,因此裸像“维纳斯”就再次应运而生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以古希腊的美学传统为楷模,捕绘了多种多样的“维纳斯”,并以此来恢复古代对人体美的颂扬。肯尼斯·兜拉克认为,文艺复兴高峰时期的“维纳斯”并不是在罗马发明的,而是在威尼斯发明的。首先发明具有古典风格“维纳斯”的是威尼斯学派的重要人物乔尔乔涅。他创造了“维纳斯”美感的楷范,并将“维纳斯”纳入了自然化的范畴。而威尼斯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提香则是将“维纳斯”进一步自然化、世俗化的另一位艺术大师。乔尔乔涅的《沉睡的维纳斯》与提香的《乌尔比诺的维纳斯》是威尼斯“维纳斯”的代表作品。这两幅画相隔三十年,它们体现了“维纳斯”从一位带有些许人性特征但仍是神圣女神的艺术形象,发展到一位完全“苏醒”过来的世俗化女性形象的过程。
乔尔乔涅的“维纳斯”置身于优美的大自然之中。她的身后是一幅恬静的田园风光图——流动的云彩、安宁的山坡、房屋和树木,这些自然风景起伏一致,与人体的曲线节奏相互呼应。天空中落目的余晖与人体柔和的淡黄色相映,整幅画呈现出一副温情脉脉、微微欲醉的基调。“维纳斯”斜卧在大自然中的躯体优美而温柔、匀称而舒展,左手轻轻地搭在自己修长的双脚间,遮住私处,右手则枕在脑后云雾般的长发之下,构成了一条富有节奏的曲线。她的身体被这条轻盈的曲线包了起来,就像一个被裹起来的花苞,封闭在一个圆融、自在的状态之中。“维纳斯”双眼微闭,以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姿态,融入这种超凡脱俗的语境之中。她成了大自然的化身,仍保留着神性的光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像与以往人物画作品的一个显著区别就在于关注自然,其因就在于当时人文精神的绽放,同时也归功于透视法的发明。乔尔乔涅将神话人物移置到了大自然中,赋予自然与人体同样的重要地位,而两者的水乳交融则给人一种理想美的享受。沉睡中的“维纳斯”是人与自然(神)的合体,是人的肉体与人的灵魂的合一。乔尔乔涅的“维纳斯”仍流淌着自然神话的血液,而提香的“维纳斯”则已完全来自人间。
提香的《乌尔比诺的维纳斯》,比乔尔乔涅的《沉睡的维纳斯》晚了整整三十年,基本沿用了后者的斜卧图式,只是整个身体稍微向右倾了一下,右臂和右乳的位置稍微有些变动。但在《乌尔比诺的维纳斯》中,“维纳斯”已经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她留有一头漂亮的金色长卷发,戴着精美的发饰、珍珠耳环、手镯和戒指,右手拿着玫瑰花,透出一种贵妇人特有的高贵而淑雅的神情——毫无神性的“维纳斯”将她那热烈而挑逗的目光投向画外,满怀激情地等待着情人的到来。她那含情脉脉的目光象征着“维纳斯”已经从自然神性之中“苏醒”过来,传达出她对于世俗生活的强烈欲望;这时的“维纳斯”已经被移到了装饰华贵的室内,《沉睡的维纳斯》中云彩、树木、远山、村庄等自然风光式的背景被室内的陈设、两个女佣、一只白色哈巴狗的世俗生活场景所取代;而背景则被墨绿色的帘幕分割成两半,一半是女佣在室内忙活的身影,另一半则处于黑暗之中,帘幕的存在使人产生一种偷窥的欲望。这一切都意味着提香的“维纳斯”已经彻底地从天上来到了人间。一五三八年的提香已不再是三十年前的提香,不再是乔尔乔涅的朋友和卡多尔人的那个提香,而是大公贵族们的朋友的提香。当时的社会时尚已经对大自然中的裸体美失去了兴趣,贵族大公们所需要的是斜卧在床上或倚在椅子上的“维纳斯”,需要的是体现他们生活趣味的“维纳斯”。这时,“维纳斯”彻底地进入了世俗生活之中。
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曾借宾客普赛尼阿斯的话断言有两个“维纳斯”——“天上的”和“世俗的”,柏拉图后来又将她们称为“神圣的维纳斯”和“自然的维纳斯”。如果按照柏拉图的划分法,《沉睡的维纳斯》应该属于神圣的“维纳斯”,离天上的“维纳斯”更近一些,而苏醒过来的《乌尔比诺的维纳斯》则彻底地成为了世俗的“维纳斯”。在提香的笔下,“维纳斯”彻底从神性中苏醒过来,完成了从神话走向自然、走向世俗生活的历程。
目光的抗争:《奥林匹亚》
“当我们的艺术家们给我们维纳斯时,他们修正自然,他们撒谎。爱多艾德·马奈问他自己,为什么撒谎,为什么不说出真相;他为我们引见奥林匹亚,这个属于我们时代的姑娘,你们可以在人行道上遇上她。”(彼得·布鲁克斯《身体活》)左拉对马奈这幅极具颠覆性的《奥林匹亚》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将其视为马奈“个性定型”的标志。而约翰·拉塞尔则将其视为“十九世纪最具挑战意义的作品之一”。与乔尔乔涅、提香的“维纳斯”相比,马奈的这幅画作提出了诸多富有挑战性的议题。在这里,文艺复兴时期极为重要的透视效果消失了,画面没有任何景深,所有形象都被挤在一个平面上;更重要的是,“维纳斯”的艺术形象及其所体现的文化精神也发生了断裂般的变化。
《奥林匹亚》在一八六五年的巴黎秋季官方沙龙上展出之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和争议,激怒了评论家以及艺术爱好者,“他们愤怒的真正原因在于这幅画几乎是文艺复兴以来第一个在可能环境中真实妇女的裸像”(肯尼斯·克拉克《裸体艺术》)。在《奥林匹亚》中,乔尔乔涅式的“维纳斯”的腿部姿势基本保持不变,但左手却微微地张开五指,大方而有力地搁在右腿上,脚上也穿上了一双精致的拖鞋,耳鬓别着一朵鲜花;背景是一片暗褐色,由碎花帘子分割开来,身旁的黑人女仆手捧一束也许是崇拜者刚刚送来的献媚的鲜花;最右边隐没在黑色背景之中的是一只尾巴翘在空中、象征着男性性能力的黑猫,定定地盯着它的女主人。这一切都意味着这是一个真实的场景,是一个在当时社会中可以经常见到此真实裸像的环境。画中的环境以及女主角身上的饰物同时也表明了她的真实身份——妓女。在当时,尽管将妓女作为表述对象并非不可能,但却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社会要求它必须符合男性心目中的女性形象,或者必须强化其温顺而优雅的特点。而马奈的“维纳斯”没有任何道德的伪饰,满脸不无轻蔑的表情展示了一个离经叛道的妓女形象。这必然会使观看者感到窘迫,也必然会遭到那些评论家强烈的批评。克拉克在《一八六五年有关<奥林匹亚>各种论述的前言》中指出,当年在提到马奈的六十多篇文章中,就有诸多将这位“维纳斯”说成“穿着橡皮衣的怪物”“黄肚子娼妇”“保尔·尼盖黑夜的少女”“长袜阶层的女人”之类的谴责之词(弗兰西斯·弗兰契娜、查尔斯·哈里《现代艺术和现代主义》)。
除了“维纳斯”所处的环境及其所表明的身份,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使得这幅画能产生如此巨大的争议,那就“维纳斯”的目光。《奥林匹亚》中女主角的眼光直接、大胆、犀利,冷冷地直视着画家以及所有的观看者。在此之前,如波提切利、乔尔乔涅、提香、库尔贝、戈雅等人笔下“维纳斯”的眼光,要么无动于衷,要么温顺动人,只是为了讨好男性观看者的“窥视”心理,这样的“维纳斯”的身体只是男性观看者“可触摸”的身体;而在《奥林匹亚》之中,这种可触摸性被取消了,画中女性的眼光直逼观看者,洞穿了“窥视者”的窥视,让“窥视者”现身,并使“窥视者”开始感到不自在。关于男性的这种“凝视”,劳拉·穆尔维曾论述过:“男性观众躲在幽暗的电影院中观看画面中巨大的女性形象,满足的是自身的色情心理,女性在此只是被物化的身体。直到画面中的女性也把目光投向了画面之外,男性观众的偷窥心理被识破,羞愧难当。女性意识在这种挑衅中苏醒。被观看者拥有了与观看者同等的权力。”(劳拉·穆尔维《视觉快感和叙事性电影》)所以,作为“窥视者”的评论家和艺术爱好者,在这幅画面前不可避免地感到了羞耻和愤怒。
“维纳斯”作为观看的对象,在传统裸像中经常受到男性眼光的影响,因为画家、观赏者、收藏者通常都是男性。正如约翰·伯格指出的:“男性观察女性,女性注意自己被别人观察。这不仅决定了大多数的男女关系,还决定了女性自己的内在关系,女性自身的观察者是男性,而被观察者为女性。因此,她把自己变作对象——而且是一个极特殊的视觉对象:景观。”(约翰·伯格《观看之道》)在西方绘画中,波提切利、乔尔乔涅、提香、安格尔、戈雅等人的“维纳斯”都是作为景观而存在的,她们都在像男性般地审视并打造着自己的女性气质。但随着社会与艺术的发展。艺术家们对此产生了怀疑。在马奈的《奥林匹亚》中,“维纳斯”自己也对她的角色感到不满,并进行了反抗,她以其略带嘲弄的神情和直逼观者的目光将欲使自己成为“景观”的男性的窥视揭示了出来,使隐藏着的“窥视者”现身于明亮处。在马奈这里,观看女性的方式第一次发生了变化。
“无蔽”的身体意象
进入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几乎所有的经典艺术形象都被艺术家们进行了更为大胆、更为彻底的探讨,裸像“维纳斯”也不例外。在对“维纳斯”的大胆探讨中,英国现代雕塑家亨利-摩尔无疑是作出重大贡献的艺术家之一。摩尔对人体形象、尤其是对女性人体形象情有独钟,“我自始便对女体造型较对男体的兴趣大,几乎我所有的素描和雕塑的构想都来自女体”(《摩尔论艺》陆军/编著)。他一生中创作了大量以女性裸像为主题的雕塑作品,其中斜卧的“维纳斯”是其创作生涯中最持久、最重要的象征形象之一。在摩尔看来,站立、端坐和斜卧这三种姿态中,斜卧的姿态弹性最大,最具造型美和空间感,是表现雕塑的永恒魅力的最佳姿态。
自一九二六年到一九八0年,摩尔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斜卧女性裸像的探讨,惊人地创作了数十件斜卧的“维纳斯”。这些斜卧像基本都是斜卧、回首的姿态,自始至终都没有什么变化,但从霍顿石到混凝土、木雕、青铜、石膏、大理石,从具象到抽象,从一个形体到两段式、三段式甚至几件套形体,雕塑材料和艺术风格都在不断发生变化。摩尔早期的斜卧“维纳斯”受埃及人像、亚述浮雕、非洲黑人木雕以及墨西哥印第安人石雕的影响,体态丰硕,线条流畅,富有力感,展现出内含的强大生命力,让人想起原始艺术崇拜的强大生育能力;一九三0年之后,摩尔开始与巴黎前卫艺术家毕加索、阿尔普、贾科梅蒂等人接触,人体雕塑变得抽象起来,同时在探索中淋漓尽致地发挥了打开雕塑身体内部的“孔洞”技术——摩尔的“维纳斯”通过打开身体内部的空间,通过对身体的遮蔽与敞开之间的争执,去除了传统空间对身体的遮蔽,延伸了身体的新的可感受性。
一九三八年的石雕作品《斜倚的人像》,是摩尔“维纳斯”的一个代表作,也是他最得意的作品之一。在这件作品中,“维纳斯”的右肘、臀部和合一的脚部着地,支撑着整个身体,头部微微向上仰起,乳房与臀部之间的部分被凿空,胸腔和腹部都消失了,大窟窿边上的双乳显得尤为突出;而双腿之间的部分也被凿出了一个小孔洞,曲起的双膝,微微张开,呈现出山丘隆起的态势。——“维纳斯”的身体呈现出大自然生命力的质感,令人联想到古老的石柱和礁石,使人想起自然力作用之下的山峦和沟谷;穿过“维纳斯”身体的两个大孔洞,则赋予了雕塑本身更丰富的形态和意义。它打破了西方传统雕塑的固有概念——雕塑是被空间所包围着的实体,将空间置入了雕塑自身,即身体内部,为身体及其空间中的“空虚”带来了延伸的精神氛围。“空虚并非一无所有。它也不是缺乏。在雕塑表现中有空虚在游戏,其游戏方式是寻索着——谋筹着创建诸位置。”“诸位置开启一个地带并且持留之,把一种自由之境聚集在自身周围;此种自由之境允诺各个物以一种栖留,允诺在物中间的人以一种栖居。”(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维纳斯”被打开的身体中,“世界”敞开了出来;古老的山石、苍凉的风、自由的云彩、上帝的光、辽阔的黑夜、身体的疼痛、坚韧的承受、瞬间的体悟,这一切都集聚于“维纳斯”的身上。摩尔的“维纳斯”创造了一种自由之境,开启了“世界”,呈现了雕塑(身体)“无蔽”的存在。我们在“维纳斯”的身体中感受到了我们被淡忘已久的真实“存在”。
二十世纪的我们越来越远离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作品、我们的制度、我们的环境,都不再是人类身体自身的反映,逐渐变成了程序、系统和结构的寄生物。由于工具理性对人的统治,使得人们逐渐失去了作为自身存在根基的“身体”感受,丧失了“诗意的栖居”的生存条件。而我们的先祖最早却是通过诉诸身体隐喻,对自然和社会进行思索的。“往昔的先辈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身体来思考宇宙。并通过宇宙来思考自己的身体,彼此构成一种浑然一体、比例得当的宇宙模型。”(约翰·奥成尔《身体五态——重塑关系形貌》)摩尔通过探讨打开空间的雕塑身体以及将雕塑置于大自然之中,重新找回了身体的真实“存在”以及身体与宇宙的关系。在摩尔的“维纳斯”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身体的“敞开”和感觉的延伸,我们可以感受到身体与山坡、田野、森林等自然风景的协调。那些安置在大自然中的身体,就像是从大地中生长出来的生物,它们不仅有着外形上的相似,而且有着类似的力势,有着息息相通的生命气息。同时,通过身体中的孔洞,身体与蓝天白云、花草树木、风、光等大自然中的物体进行互动交流,相互嬉戏,身体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被打开身体的“维纳斯”安然地躺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使人隐约感到了宇宙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