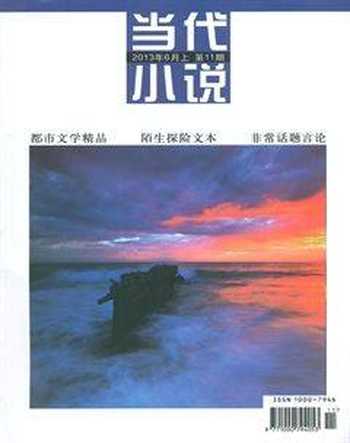如约而至
小米
老王跟人交谈,谈到生死,老王往往会说:“我还能活四年呢。”人们纷纷摇头,对他说的,均不能信。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问题在于老王从前没这么说过,他仿佛也是突然或偶然地,得知了这个消息,这才信以为真的。不仅是老王,在村里,任何人都不曾如此肯定地谈论过自己的大限。这当然并不奇怪:谁要是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岂不成了神仙?也是因此,村里人背地里给老王起了个“王半仙”的绰号。
老王不知自己“获此殊荣”,他的家人,也是毫不知情。这也是有原因的,虽然人们觉得这个绰号太像老王了,但因为老王在村里是得到普遍尊重的人之一。一个被你尊重的人,你不按辈分叫他爷、叫他叔、叫他哥,这也就罢了,叫老王也不是不可以,称呼他的绰号对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就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了。所以,“王半仙”这个绰号,并未因此而传开。只在每当老王说起他的寿命的时候,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来,之后,想起绰号的那人,就会会心地一笑,如此而已。
事实是,村里的大部分人,都叫他老王。这已经是对老王的尊称了。老王当然是有一个名字的,老王的名字,叫王明道。但是,年纪小的人,对他直呼其名,又觉得不够尊重他。在村里,老王这一支人脉传到现在,辈分已属最低。俗话说,高房出矮辈。老王的境遇恰恰就是这样,老王除了能够在自己的三个儿子和孙子面前充大,出了家门,老王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小辈,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老王的祖辈是家族里的老大,延续到了老王这里,他的骨头(家乡俗语,代指年龄)虽老,辈分却低,有资格把老王叫成“老孙子”的小孩子也不是少数,叫他老王已经是一种抬举了。
这也是有人竟敢给他取“王半仙”这个绰号的原因。
过了大约一年,老王改了口,挂在他嘴边的话,也与时俱进,成了:“我还能活三年呢。”老王的口气非常肯定,神色更加坦然。他的嘴中所言,仿佛不是说他自己,他说的,更像与他毫不相关的人。人活到了一定的年龄,该经历的经历过了,该见识的见识过了。大风大浪里去过,从大悲大喜的境遇里也已经走出来了,活着不怕,死亦不惧,这当然不奇怪。老王现在就已到了这样的境界。我的乡亲们是非常迷信的,他们普遍认为,一个人,生有时候,死有地方,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不是自己可以控制得了的。那么,生就好好地生,死了就死了,不值得怨天尤人,更不必诚惶诚恐。
老王这么肯定地谈论自己的寿命,当然是有他自己的理由的。
原来,这么说之前,老王做了一梦,梦见他要被两个穿了黑白衣服的陌生人,带到一个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去。老王觉得这两人形迹可疑,去了肯定没什么好事,于是努力地反抗着他们,可是,他的反抗是多么的苍白无力啊,老王觉得自己的身子轻飘飘的,他感到,他反抗的动作就跟风一样绵软无力。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老王只得跟他们一同去,去了才发觉,那地方居然人来人往,热闹非常。可是,老王很快就发觉,人们的神情异常庄重,仿佛他们的生命中有什么大事,就要发生一般。那出出进进之人,人人规规矩矩,无不井然有序。老王在两人的带领下,很快走到了前路的尽头,穿过一条曲曲折折的走廊之后,即将步入一个高大威武的殿堂。就在被挟持着跨入门槛的瞬间,老王抬起头来,看见一个一脸威严的人,坐在大厅正中的几案后面,对着他的脸,大声呵斥他:“谁让你现在来的?去去去去去!四年以后你再来!”
那高坐于殿堂之上的人,回頭又对挟持他的人,同样大声地呵斥道:“叫你们把大王庄的王明道带来,你们仔细看看,这个人是大王庄的王明道吗?这是王李庄的王明道。”那两个挟持老王的人,立即将伸进门槛里的脚,悄悄地,收了回来,然后低下头去,恭恭敬敬,唯唯诺诺。老王回头看看,这才发现,两人已是汗流浃背的样子,连气也不敢大声地喘了。
那个坐在殿堂之上的人,低头沉思了片刻,看上去,他的面色虽然缓和了许多,却仍不罢休,继续教训老王身边的那两个人:“你们的活计虽说辛苦了些,可是,真真事关一个人的生死,咋能这么不小心呢?幸亏我发现得及时,要是我也像你们这样马马虎虎,浮皮潦草,岂不酿成大错?”
老王只觉得眼前的情景庄严肃穆,那呵斥他的人,也是不怒自威。老王觉得一左一右挟持他的两人,手已经松开了,而且,他们迅速转身,扔下老王,飞快地走了。老王明白,摆在他面前的就是传说中的鬼门关,那一步如果踩了进去,就再也出不来了。老王吓出一身的汗来,诚惶诚恐,不知道怎样才对。就在这时候,坐在大殿中间的人又对老王说话了:“天机不可泄漏。今晚的事情,你回去以后,不能对任何人说,听清楚了没有?”老王点了点头,那人说:“去吧。”老王于是低了头,匆匆离开。就在他走出长廊的一刹那,老王只觉得脑子里“轰”的一声响,他一下子醒了过来。老王醒来才明白,他还睡在自己的炕上,刚刚发生的事情,不过是做了一个梦而已。
老王躺在自己的炕上,心知他所遇上的,自然远非常人,肯定就是传说中的阎王,而那两个错把老王带去的人,必定是传说中索命的无常。
人们常说,来的时候给条命,去的时候给场病。这话就是论说人的生死的。乡亲们觉得,一个人要是快死了,却不是死在这样或那样的病中,不就成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嘛!老王这时已病了一个多月了,谁也不知道老王得的是什么病,连村里的赤脚医生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总之,老王四肢无力,步履艰难,而且,总是睡不够。看上去,老王常常虚汗涔涔,面黄肌瘦,是一副十足的病相。老王的小儿子三娃子,这里那里地,找了好几个赤脚医生,给他吃了不知道多少服药,老王的病情非但不见有什么好转,反而越来越重了。
老王现在才明白他的“病因”了。他认为,他没有病。是索命的无常盘算着要取他的性命了,他才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的。
老王躺在自己的炕上,前思后想,辗转反侧。他想,“四年以后你再来”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他的寿命还有四年吗?老王觉得,阎王话里头的意思,一定是这样的。
好不容易捱到天快亮的时候,老王又呼呼地,睡起来了。
第二天早晨,老王一觉醒来,恰逢三娃子从外面匆匆跑进屋子,对一家人说,“大王庄的那个跟爸爸同名同姓的人,不明不白地死了。”三娃子喘了一口气,接着说,“你说奇怪不奇怪,那人头一天还好好的,没病没灾,不疼不痒。说是睡了一觉醒来,出门起夜,死在了茅坑旁边,只差了那么一点点,他就掉进粪池子里了。” 老王不惊不奇地说:“昨天晚上我就知道,大王庄的王明道,活不到今天了。”
三娃子不明白了,他也是刚刚得到这个消息的,那么,还在炕上躺着的老王,一个多月以来,连门也从未出过一次的老王,在炕上躺了就足足有半个月的老王,居然说他昨天晚上就知道大王庄的王明道死了,这不是“空口说白话(胡编乱造不可信)”呢嘛!可是,三娃子也懒得跟父亲争论,说:“到了今天我才晓得,你原来是一个天上地下无所不知的人呢。”老王听得出来,三娃子这话,是在挖苦他呢。老王不再言语了。老王心想,要三娃子明白他的理由,肯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不如不说。
吃完了早饭,三娃子又打算给父亲抓药去。
老王不在炕上躺着了,他要起来。这对三娃子来说,是一个意外。
三娃子说:“你还是好好地休养着吧,我现在就给你抓药去。”
老王说:“我又没病,吃个啥药?”
三娃子说:“你都病了这么长的时间了,还说自己没病。”顿了顿,三娃子又说:“你是老糊涂了?还是病糊涂了?一早上说的全都是胡话。”
老王说:“我那是在替别人害病呢。”
三娃子觉得父亲的话很好笑,但他发觉,跟以往比起来,父亲的精神,确实好了不少。
老王不让三娃子去抓药,三娃子寻思了一会儿,也就不去了。三娃子心里想的是,那就观察一天再说吧,反正是个慢性病,一天不吃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老王从此不再吃药了。他的病也一天天地好了起来。
过了十来天,老王居然跟着三娃子,干起农活来了。
三娃子这才确信,老王的病,是真的好了。
老王的年龄本来就不算大。在农村,五十多岁的人,正是干农活的年纪。
此后得了空闲,跟人谈起关于生死的话题来,老王就会非常肯定地说:“我还有四年的阳寿呢。”老王说得不容置疑,甚至有了沾沾自喜的口吻,仿佛能够多活四年,是占了大王庄那个王明道的便宜一般。
人们普遍觉得,人既不能知生,又焉能知死?皆以为老王是信口雌黄,均不能信,但见其振振有词,又不像开玩笑。何况,老王从来就不是一个信口开河之人!所以,就有人问他:“你咋知道你还能活四年?”老王想起阎王在梦中对他的叮嘱来,他不敢作出任何解释,只好支支吾吾地说:“我反正知道。”人问他:“总得有个前因后果吧?”老王說:“这个……我不能说。天机不可泄漏。”人们对老王的话,只得将信将疑,任其言说,也只能姑妄听之。
老王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在很多人面前虽然不是长辈,但毕竟还有年龄在那儿摆着,谁也不好急赤白脸地反驳他,跟他较真。没那个必要。
人们心里想的是,四年以后,看你还能咋说?
老王这么说了两年。后来,连老王自己也不再说起那句话了。老王想,活得好好的,却老是把死挂在嘴边,也不是个事儿!
让人想不到的是,四年以后,老王果然死了。
老王死的那一年,生产大队正在热火朝天地修一条跟“红旗渠”非常相似的水渠,仅仅是,这条水渠的灌溉面积远不如红旗渠那么大,不如红旗渠那么长,更不如红旗渠那么有名。对全生产大队的人来说,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水渠修好后,可以灌溉其中三个生产队的五六百亩土地,能够让这些山坡上的旱地成为旱涝保收的稳产田,这么一来,这三个生产队的社员们就再也不用靠天吃饭了。
修这条水渠,在水源附近的山腰上,必需经过一段长约一公里的山崖,其中大约两百米的一段,是坚硬的石崖,而且,这一段石崖屹立高耸,寸草不生,从下面上不去,从侧面过不去,别说施工了,想要接近,都很困难。惟一的办法是,用数十米长的绳子把作业人员从高处吊下来,才能凿出炮眼。也是因此,这一段水渠是不可能挖得出来的,要用放炮的方法先炸出通道,再用铁锤和钢钎,凿出一条水渠来才行。也是因此,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生产大队专门成立了专业队,时任大队民兵连连长的我父亲,又兼任了专业队队长。大队支书这么安排是因为,即将抽调出来修水渠的专业队队员,多半都是民兵,而这些民兵,都对父亲的号令,百依百顺,恭敬有加。父亲的专业队队员,也是从能够受益的这三个生产队里抽调出来的,他们都是年轻力壮的精干劳力,只有极个别的队员是会放炮的技术人员。老王不是民兵,他已经快六十岁了,作为民兵,他的年龄就太大了。老王是技术人员之一。 能够成为专业队队员,是光荣而又实惠的事情。这是因为,在生产队做其它的农活,一个劳力一天最多挣十二分工分,专业队队员只要出了一天工,就能保证挣到十五分的工分。这个诱惑实在是太大了。何况,在用得着老王的时候,老王怎么可以置身事外呢?他也是积极地报了名,又被父亲这个队长第一个确定下来的专业队队员。话又说回来,老王是生产队惟一的放炮技术员,即使老王不报名,父亲也要点他的将。虽然别的生产队并不缺乏放炮的行家里手,可是,放炮毕竟是个危险活儿,不是信得过的人,父亲不放心。老王是父亲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当然信得过他。
老王的小儿子三娃子肯定是民兵,同时,他也成了一名专业队队员。按理说,一个家庭只能出一个专业队队员,因为他们从事的是一件风险很大的工作,万一出了事,一个家庭一下子损失两个主要劳动力,那就是塌了天的事情。可是,老王要父亲把他看成技术人员,而不是专业队队员。父亲当然明白老王话里头的意思,父亲想,老王的心思无非是,第一,作为技术人员,他是一个应该得到大家尊重的人,第二,他可以不用占一个名额。这么一来,他的儿子三娃子也就有了进入专业队的资格。
父亲猜错了,老王要三娃子也参加专业队,原因在于,他想把放炮的经验与技术,手把手地教给三娃子。等三娃子全部掌握并能运用自如之后,生产队再有了放炮的活计,他就可以不用出面了。老王心里惦记着的,还是他那个梦。老王是在专业队成立的三年前做了那个遇见阎王的梦的。所以,专业队成立的时候,老王固执地认为,他的寿命还有一年的时间了,向儿子传授多年来他放炮的体会和经验,也就成了刻不容缓的事情。虽说会放炮算不得什么手艺,也不是可以养家糊口的本领,但老王觉得,自己再无一技之长,如果三娃子有了这样的本领,在这个村子里,好歹不会被人看低。那时候,生产队隔三差五地就需要放一次炮,可是,像修水渠这种大规模放炮的机会,并不常见。老王觉得这是个给三娃子传授技艺的绝佳机会。老王的三个儿子里,他最疼爱的,就是这个三娃子。古话说得好:皇帝爱长子,百姓疼小儿。老王老两口不跟老大或老二一起过,偏要跟年龄最小的三娃子在一起生活,就是最好的例证。
眼看要到阎王说的四年的期限了,老王照旧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连感冒之类的小病也没有生过。
过了四年的期限了,老王还活着。
老王也觉得奇怪:是不是我把那个梦记错了?可是,四年前的那个梦,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就像昨天晚上刚刚发生的事情。老王于是明白,自己活在人世的时间,已经不能再用年来计算,是该用天来计算的时候了。
老王这么想的时候,三娃子不知道老王的心思,村里的人也早已忘了老王前几年还一直挂在嘴边的那一句话了。
老王的两个老人都是他亲自送他们上山的,儿女们是他与早亡的妻子,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大了的,如今,该出嫁的出了嫁了,该娶媳妇的,也都娶了媳妇,他们的婚姻大事都是老王独自一人给他们操办的,他们分家之后要住的房子,也是老王给他们修起来的。老王觉得,无论哪天伸胳膊蹬腿(死的代称)了,他都可以闭得上眼了。
老王的棺材是老王亲自备的木料,是他请来了木匠,在两年前就做好了的。柏木做的虽然好,但不是他的命里该有的,老王给自己预备的寿材,是普普通通的松木。不仅如此,连自己的寿衣,老王也在一年前就已请了裁缝,做好了。该给儿女们安排的事情,他也提前做了安排。
老王已经做好了死的所有准备。但是,老王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会死,老王怕自己头天晚上睡了,第二天就不会醒来。所以,老王每天睡觉前,又多了一项重要的工作,他不仅要洗脸、洗脚,他还要仔仔细细地,洗净他的身子。人都是干干净净地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老王觉得,人更得干干净净地离开这个世界才对。
这天,老王照旧与三娃子一起出门,到修水渠的悬崖上,去修水渠。老王就这么平常地开始了新的一天。老王也是最近才觉得,人的一生,真是“每一天都是新的”啊。
老王不知道,这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天了。但是,过了四年的期限之后,在冥冥之中,老王似乎每天都在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这一天,到了太阳快落山的时候,老王才装好了三眼炮。
炮是当队长的我父亲让三娃子去点的。如今的三娃子,在老王的调教下,也是父亲信得过的技术人员了。
可是,三眼炮只炸响了两眼。无论怎么等,另外一眼,就是不响。
半个小时过去了,炮還是没有炸响。
炮眼所在位置的斜对面,恰好是一条人来人往的大路,本村的人,外村的人,都得从那条路上过,眼下又到了收工的时间。也就是说,炮响与不响,都得有个结果才行,不然,很不安全。
大家都认为这肯定是一眼哑炮,是不可能再爆炸的了。
这样的哑炮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时不时地,就有一眼炮,成了哑炮。一旦成了哑炮,一直是三娃子去处理的。
三娃子要下去看看。当队长的父亲,包括所有的专业队队员,都同意了。父亲还叮嘱三娃子:“你要把导火索和雷管从炸药里弄出来,扔了。大不了明天重新装一次。”
可是今天,老王不让三娃子去处理,他要亲自去。
老王去,当然更好。
父亲同意了。
几个队员刚把老王用绳子吊下去,父亲他们突然听见,那一眼迟迟不响的炮,炸响了。
哑炮就跟在那儿耐心地等待着老王的到来一般,老王刚一下去,炮就迫不及待,炸了。
老王就那么飞了出去。
老王飞出去的样子,没有一个人看见。
冥冥之中,老王也觉得自己飞起来了。这种感觉真好。还是在小时候的梦中,老王就不止一次地,有过这种飞起来的感觉。小时候,从这样的梦中醒来之后,老王把梦中的情形讲给父母听,老王的父母对小时候的老王说,傻孩子,那是你在长个子呢。老王想,我现在不可能还在长个子呢吧?老王这样想的时候突然觉得,就在他的左边和右边,有两个穿了黑白衣服的人,将他的胳膊抓得紧紧的。老王这才明白他并不是做梦,是那两个让人讨厌的无常鬼,找他索命来了。老王气愤地对他们说:“你们又不是认不得我,抓这么紧干啥?放开,放开。”老王一边挣扎一边说:“我是不会逃走的,到阎王爷那儿去的路我也认得,我自己会去的。”老王话音未落,就看见穿了黑白衣服的两人,彼此对望一眼之后,不约而同地,松开了抓他的手。
老王以为自己会掉下去,可是没有。老王独自一人,仍在飞翔着,就跟小鸟一样,哦不,应该说,是跟鹰一样飞翔着才对。小鸟只能飞行,只有鹰才配得上使用飞翔这个词。
老王觉得自己飞翔着,耳边有呼呼的风在响,老王低头朝下看,他看见树木在身下,大山在身下,白云在身下……一切一切都在他的身下。老王回头一望,黑白装扮的那两个无常鬼已经远远地被他抛在身后了,他们正在拼命靠近他。老王觉得愉悦极了,舒畅极了,他一辈子都不曾这么舒服地飞过。
老王想,人都是怕死的,我也知道我正在死,可是,死有啥可怕的呢?老王觉得挺纳闷的。
老王的后事是生产队出面给他办的。
给老王操办后事的时候,人们这才想起老王曾经说过的话来:“我还能活四年呢。”他们在背地里交头接耳,嘀嘀咕咕,议论纷纷:“不愧是个半仙,果然不多不少,活满了四年,他就走了。”
人们这才觉得老王不一般,他们既为老王惋惜,又替自己后悔。当初要是多一个心眼,问一问老王,他为什么会把自己的生死掐算得那么准确就好了。人们觉得,老王那么说,肯定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事实已经证明,老王的道理,是经得住事实的考验的。谁敢说,明了自己的生死,一定就是无用的呢。他们觉得,一个人要是知道了自己的大限,就可以像老王那样,把身后事安排得妥妥帖帖的,至少不必带着遗憾离开人世。
乡亲们都认为老王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当得起“王半仙”这个绰号。甚至有人说,老王死后,肯定是成了仙了。
人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显然,这已经跟老王无关了。
老王死了快三年了,水渠才全面完工。修了整整四年水渠,只死了老王一个人,对村里人来说,这已经是很大的幸运了。父亲把通渠庆典的日子选在了三年前老王出事的那一天。这个日子是当专业队队长的我父亲跟老王的三个儿子商量之后做出的决定。因为那一天,三娃子他们三兄弟,要给老王烧三年纸。在我的家乡,给亡灵烧三年纸是一个非常隆重的仪式,因为,只有到了这一天,才可以给过世的人,立一块碑,以示纪念。
在父亲的心目中,水渠就是老王的无字碑。
责任编辑:李 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