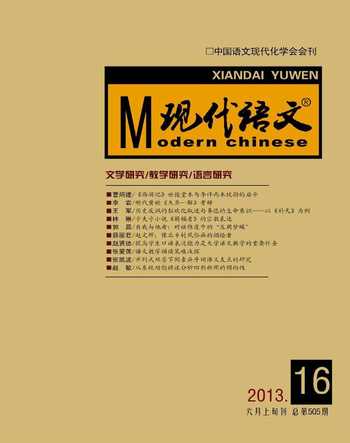苏轼作品中禅宗思想的渗透与挖掘
陈建忠 张保太
摘 要:受禅宗思想的影响,苏轼在秉持儒家积极进取、洒脱达观的思想基础上,吸取禅宗随缘自适的思想,坦然面对人生,保持自己随遇而安、荣辱不惊的人格尊严。本文即从分析禅宗文化对苏轼的影响入手,对苏轼诗文随缘自适的处世哲学、人生如梦的禅学主题进行了具体解读,以期能还原一个真实的苏轼。
关键词:苏轼诗文 禅宗思想 随缘放旷
众所周知,苏轼的豪放风格是建立在积极进取、洒脱达观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儒家的入世、“致君尧舜”是苏轼诗词的主导思想。但当苏轼在仕宦道路上遭受打击、迫害之时,却能随遇而安,既不蛮干硬拼,也不消沉隐世,而是以旷达的态度解脱苦闷,“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我们认为这正是苏轼深受禅宗思想影响的结果。
苏轼虽受儒学影响颇深,但同中国广大的封建士大夫一样,“早岁便怀齐物志”,与庄子结下难了之缘。《苏辙集·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写到:“(东坡)初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庄子说:“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苏轼就是这样的“德者”。其原因就在于苏轼视贬所与“吾乡”齐一,于是便“安土忘怀”,这种精神胜利法与庄子的“万物其一”并无二致。“升沉何足道,等是蛮与触”,“早知臭腐即神奇,海北天南总是归”,“何处青山不堪老,当年明月巧相随”。其诗词如是观,其文亦如是观。
如《超然台记》便是如此。此文作于密州,其时苏轼因两次上书神宗反对王安石新法,均未被采纳,便郁郁不得志,请求离京外任。先是通判繁华的杭州,三年后改任密州。杭、密生活水平相去悬殊:杭州欢宴不断,密州却“斋厨索然,日食杞菊”。苏轼借老庄“万物齐一”的思想安慰自己道:“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如能“万物齐一”,超然物外,无美恶之辨,将“舟楫之安”等同于“车马之劳”,处“雕墙之美”同“采椽之居”,视“湖山之观”匹“桑麻之野”,则“吾安往而不乐”。因此当苏轼临老谪居海外,穷愁颠越,无不自得,超然物外,便不难理解了。
然而实现这份超然,更离不了禅宗的影响。从个性和气质看,苏轼是一个颇有见识、才华横溢的文人才子,尤其是他格外丰富的感情世界,常常表现出一种高层次的内在孤独感。他总是带有哲学思想去多愁善感,去思考人生、自然、社会等大命题,为民族、时代和人类命运而忧心忡忡。而此时此刻,在他苦苦求解时,禅宗给他指明了一个思想出口。
禅宗认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它主张在现世求得一种自由解脱,关键在于“真性自空”,使心灵处于一种空虚的境地。这种“空”,不是简单的“空无”,而是心处尘世,精神上却一尘不染。也就是说,摆脱人世间的有无、生死、得失等功利欲望的束缚,根本解决人本性中绝对自由之追求与客观现实的矛盾,达到精神自由的境界。禅宗所崇尚的这一超然玄悟的心性,深深影响了苏轼的人生观,他追求真率自然,不受事物的羁绊,形成狂放不羁和通达洒脱的个性,正所谓“任性逍遥,随缘放旷”(苏轼《论修养帖寄子由》)。
苏轼因父病故,扶丧归里。他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皆因新法的施行与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所见的“平和世界”。
熙宁四年(1071)出任为杭州通判后,苏轼遍游佛寺,向高僧怀琏、慧辩、元净、契嵩、惠勤、参寥等参法。苏辙在《偶游大愚见余杭明雅照师旧识子瞻能言西湖旧游将行赋诗送之》一诗中回忆道:“昔年苏夫子,杖屦无不之。三百六十寺,处处题清诗。”熙宁七年(1074)苏轼出任密州太守。在密州山穷水恶之中,历历在目的是人民疾苦,参禅礼佛成了苏轼排解郁闷的重要渠道。可以说,密州是苏轼思想倾向于禅宗的开端。
苏轼接受禅宗也是有其现实因缘的。苏轼生长于佛教传播相当发达的四川,他自幼生活的眉山,与佛教圣地峨眉山相去不远,距著名的乐山大佛更近。处在峨嵋佛教文化圈内,苏轼家庭的宗教气氛也十分浓郁,其父苏洵系云门宗四世圆通居讷皈依弟子,其母程夫人亦系优婆夷,其弟、其继妻都信佛,家中供有五代贯休所绘的十八罗汉水墨画像。等苏洵和程夫人逝世后,苏轼将他们生平喜爱之物捐给寺院,并作《十八罗汉颂叙》。苏东坡之弟苏辙,亦系佛教居士,名列“唐宋散文八大家”之内。他在《试院唱酬十一首·次前韵三首》中写道:“老去在家同出家,《楞伽》四卷即生涯。”苏轼的续室王闰之亦好佛,东坡曾在她的生日时根据《金光明最胜王经》的教义,买鱼放生为其祝寿,并作《蝶恋花》词云:“放尽穷鳞看圉圉,天公为下曼陀雨。”以及后来苏轼在杭州纳的歌妓王朝云更是信佛笃深。由此可见,苏轼接受禅宗是有着深厚的家庭渊源的。
苏轼禅宗思想的深刻化应是在黄州时期。其弟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云:“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当绍圣年间苏轼再贬惠州、儋州之时,其佛学修养已汇通三教,且有了深刻的认识。
从1057年母丧到1074年出任密州,近二十年的风风雨雨,使苏轼深深体会到世道艰难、宦海多波,此时也许在王闰之和固有的家庭环境影响之下,苏轼主动向禅宗靠拢,从中汲取营养,去追求那种“外物无芥蒂于心”的精神宁静,以使自己在生活中顺其自然,随遇而安,“无往而不自得”,始终保持通达乐观的生活态度。
这种生活态度表现在诗词中,就是出现了大量的人生“如梦”“如幻”之类的词语。这些都缘自佛教的空、净思想。基于十二因缘的基本理论,释迦牟尼提出了著名的“三法印”佛教人生观,即“诸行无常印、诸法无我印、涅槃寂静印”。既然人生一切现象皆依据因缘和合,且人的一生永远在流转变化之中,那么人、人生便没有真实本体,就像《金刚般若经》中所谓众生之相“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苏轼的笔下,人生的空幻意识比比皆是:密州时期的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不但是人生变化不定的写照,也是佛家因缘和合的阐释。更加明显的还有“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是梦”的感慨。不同于佛教的是,苏轼能将人生本质的无意义与当下生活的有意义相结合,从而追求现实生活的滋味、内容、意义。而这种矛盾的结合,形成巨大的张力,成为苏轼豪放超旷风格的生长土壤。
由此可见,在禅宗“任性逍遥,随缘放旷”思想的影响下,苏轼最终以一种不可抑制的冲动,一种无法遏制的欲望尽情表现其张扬的个性、潇洒的英姿,为我们展现了一位“天下之无思虑者形象”。苏轼的一生在政治上是不得志的,也正因为政治上的不得志,让他有机会了解中国博大精深的禅宗文化,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方向,追求内心的平衡和心灵的超脱。禅宗思想改变了苏轼的人生态度和行为方式,更铸就了他文学上的辉煌!
(陈建忠,张保太 甘肃省酒泉市肃州中学 73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