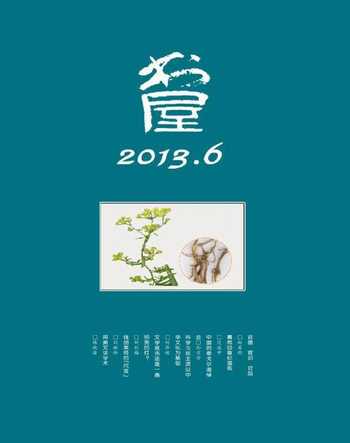中国的泰戈尔追悼会
孙宜学
一
1941年8月7日,泰戈尔去世。
噩耗传到中国,一直关注着泰戈尔健康的中国人为之哀伤〔1〕,各地的报纸都很快发布了这一消息。中国政界、文化界也纷纷以各种形式悼念诗人,回忆他对中国的深情厚谊,痛惜失去一位伟大的诗人,中国失去一位真诚的朋友。
8月8日,《新华日报》就发表悼文,追忆“我发动神圣抗战后,(泰戈尔)氏对我尤为同情”〔2〕。东方文化协会等团体也电唁泰戈尔家属,以致哀悼〔3〕。蒋介石则通过谭云山转达对泰戈尔病逝的哀悼,并发去唁电,痛称“耆贤不作,声委无闻,东方文明,丧失木铎,引望南邻,无任悼念”〔4〕。香港中外各界人士也于8月17日下午举行了悼念活动〔5〕。
9月20日,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及国民党组织部部长的朱家骅致函国立北平研究院、国立中央大学、国立西南联大、国立云南大学、中国哲学会、中印学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就为泰戈尔举行追悼大会事商榷:
敬启者:印度泰戈尔先生对于中印文化颇多贡献,尤以中日战事发生后,对于我国之抗战表示深切之同情,且常著文主张正义,痛斥日寇。日前据报载,已于本年8月7日逝世,兹拟由各文化机关共同发起于11月初旬在重庆、昆明两地同时举行追悼大会,以资纪念。〔6〕
收函后,各机构和团体纷纷回复,表示赞同,并就时间、地点、演讲人人选、祭文撰写等具体事项反复磋商。后来,发起单位又增加了国立中央图书馆。
10月31日,各发起单位代表在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集会,举行第一次“泰戈尔先生追悼大会筹备会”会议。出席者有中印学会的陈天锡、中央大学的徐仲年、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的林紫贵和郭尼迪,中央研究院的陈绍贤、叶企孙及刘次箫。经商议决定,泰戈尔追悼会和纪念演讲会分别在国立中央图书馆和重庆大学大礼堂举行,其中追悼大会由中央研究院负责筹备,朱家骅任主席并致开幕辞,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和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道藩分别演讲;中央大学负责筹备重庆大学的纪念演讲会,讲演会主席由中央大学校长顾孟余担当,并特约讲演人若干。
会议议定:11月29日下午二点至三点举行公祭,三点始举行追悼大会,七点半起举行纪念演讲会。会议还请各发起单位分别致函在渝各文化机关团体参加公祭和追悼会,其中包括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东方文化协会、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复旦大学等二十三家单位。
11月24日下午三时,筹备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议决请中央广播电台于29日下午播放泰戈尔留声机片;致函宪兵队及重庆警察总局,请届时派宪警在会场内外担任警备及维持秩序;致函国民政府参军处商借军乐队。由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派人与中央摄影场接洽,届时负责会场拍照。筹备会还详细商讨了公祭仪式和追悼会仪式,以及各相关工作的具体分工,甚至着装:“司仪读祭文及司上香献花者均着中山装,以昭一律。”〔7〕
11月28、29日,《大公报》连续发布“泰戈尔先生追悼大会筹备会启事”。
28日,《新华日报》亦发出29日追悼活动的预告:“追悼泰戈尔,渝、昆两地明日分别举行。”
战时中国陪都重庆,在日寇环伺、战火频燃、国事维艰的生死危亡之际,不分党派、不分团体同心协力,在为一位印度诗人,从容地、真诚地、庄重地准备着一场追悼会。
重庆因而多了一些凝重和哀伤,这种情绪通过各种方式传播到全国。国人带着一份友谊的温暖,在共同等待着这个庄严肃穆的时刻,以寄托自己的感激和哀悼。
二
11月29日下午二时,追悼会如期举行。
中央图书馆笼罩在一派庄严、肃穆的气氛中,花圈、挽联比比皆是。中国佛学会、中印学会、东方文化协会、《扫荡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中国哲学会、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等各机关、团体二百余人在此公祭泰戈尔。戴季陶为主祭,朱家骅、陈立夫、国立北平研究院院长李书华、张道藩等十一人陪祭。中华儿女“掬诚遥奠”泰戈尔诗魂。祭文、挽联都盛赞泰戈尔的文学成就,如蒋介石的挽联是“诗圣云亡”〔8〕。朱家骅称泰戈尔为“绝代诗才”。但当时的中国人更看重泰戈尔在社会革命方面的价值,尤其是其对中国抗战的具体支持:“七七难作,抗御东胡;远道眷念,大声疾呼;祝我胜利,建国是图。”(朱家骅语)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的祭文中有“近睹倭患,慨然如伤;同情予我,语重心长”之语。吴铁城的祭文:“东寇猖獗,我武维扬;同情寄予,胜利相忘。”〔9〕中国哲学会用“灿烂死中生,发心狮子吼”的挽词赞扬泰戈尔以诗人身份抨击日寇侵华暴行〔10〕;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则称“他曾为印度不合作运动而愤怒,他曾为中国反侵略战争而呐喊,他曾为东方兄弟的命运而忧思”〔11〕。
公祭毕,追悼大会开始。
主席朱家骅首先致辞。他着重指出,中国人悼念泰戈尔,不只是因为世界失去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而是因为泰戈尔“人格之伟大、同情心之深厚以及主持国际正义之精神”:
泰氏既笃好和平,而以相爱互助为人类进化之极则,故于侵略国家深恶而痛绝,于被侵略国予以深切之同情。自我国抗战军兴以来,泰氏屡发宣言并致电我国政府及人民,赞助鼓励,不遗余力,因之我国人民益了然于和平之真谛、抗战之神圣,而益知中华与倭寇既无共同之原则,自不能并立于天地之间也〔12〕。
朱家骅致辞毕,戴季陶、陈立夫分别讲演。
戴季陶为国民党元老,对中印文化交流贡献颇巨,与泰戈尔也相交颇深。他曾与泰戈尔、谭云山、蔡元培等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印两国的中印学会,并任中国的中印学会监事会主席;他还从经费、图书等方面坚定支持泰戈尔创办国际大学的中国学院。1940年11月,他率中国高级友好访问团访问印度,泰戈尔因病虽不能见他,但仍安排在国际大学举行欢迎会,并亲笔写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戴季陶还被聘为国际大学七护法人之一(相当于大学董事会董事)〔13〕。
戴季陶痛感泰戈尔的去世不仅是印度的大损失,更是中印文化交流的巨大损失。因为泰戈尔刚刚恢复的中印两国中断已久的文化交流,恰似“襁褓之孩,所赖于保育之力者,大而且切”,因此,“尊公之舍世,其于两国文化复兴,实共失所怙”〔14〕。
陈立夫以“无限怅惘”概括中国人追悼泰戈尔的三种心情:“我们以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悼惜世界上失去了一个伟大诗人;我们以争取抗战胜利的人,悼惜失去了一个同情于我们的友人;我们更以负荷复兴中国文化责任的人,悼惜失去了一个东方文化的柱石。”“在当代伟大的诗人中,泰戈尔先生是最能了解中国的。自然在我们民族抗战的怒潮高吼时候,他也最能同情我们的。泰戈尔先生的公子来电说,太翁弥留的时候,还殷殷以中国为念。这是最珍贵的同情,是先天富于诗性的中华民族所最感念而永远不忘的。”陈立夫呼吁以“文化的建设来答谢这一个伟大诗人的同情”〔15〕。
当天下午,张道藩在中央广播电台发表广播讲演,盛赞泰戈尔作为诗人和中印文明使者的功绩,尤赞其对中印友谊和中国抗战的贡献。讲演毕,电台“将太翁遗著之音乐诗歌,曾经制成留声片者,择其中若干种……分别用长短波广播”〔16〕。
当晚七时半,重庆各界代表在重庆大学大礼堂举行纪念讲演大会,“到会者至为踊跃”〔17〕。讲演会由顾孟余主持并致开会辞,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楼光来发表演说。很多与会者虽然没机会公开演讲,但人人心中都有一篇悼文〔18〕。
三
根据追悼大会筹备会的计划,追悼会后,将编辑泰戈尔先生纪念册。
12月5日下午三点至四点,时任重庆《文史杂志》社副社长暨中央大学教授的顾颉刚在中央图书馆主持讨论会,商议编辑“泰戈尔先生纪念册”,并成立“泰戈尔先生纪念册编辑委员会”。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国立编译馆馆长陈可忠、国立中央研究院秘书刘次箫参加。
纪念册材料的搜集及撰述人员的安排是:
1.序文,戴季陶和朱家骅各撰一篇。
2.分请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蒋介石、中央执监委员会各常务委员暨各部、处、会首长及国府各院、部、会长官题。
3.传略、年谱及著作表、各种照片、乐谱,请谭云山、周达夫撰述和设法搜集。
4.来华讲学纪事:请张君劢、张歆海、林徽因撰述。
5.函电,函请国府文官处、委员长侍从室、戴季陶及张君劢、陆小曼代为搜集。
6.纪念文字:
(1)文学部分请楼光来、柳无忌(时任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徐仲年(时任国立中央大学法语系教授)撰写。
(2)哲学部分请冯友兰、贺自昭(时任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教授)、方东美(时任中国哲学会理事、国立中央大学教授)撰写。
(3)艺术部分请林徽因、徐仲年撰写,同时并请谭云山、周达夫转托印度学者代撰,再译为中文。
(4)教育部分请谭云山撰写。
编委会还致函各机关团体补送挽诗或挽联。会后不久,谭云山、周达夫起草了一份英文函,由谭云山转交印度国际大学和泰戈尔家人,“详述举行追悼公祭及纪念讲演会经过暨编辑纪念册之意义,请其供给资料”〔19〕。
可惜的是,在那样一个艰难时世,纪念册可能无果而终了!
四
泰戈尔对中国和日本都有很深的感情。“我对于日本人民有极大的敬重。……曾经一度尊敬与崇拜过日本,并曾经对日本抱过一次很深厚的希望”,但日本不久便暴露了其侵略野心,“出卖了那个新的希望”〔20〕。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倾向,泰戈尔历来都很警觉,并激烈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乘机占领了中国的山东。1916年5月,泰戈尔到日本访问,日本政府希望利用泰戈尔为自己的这种侵略行径歌功颂德,所以一开始热烈欢迎他,称赞他为“日本的友人”。但泰戈尔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毫不留情,在名为“军国主义在日本”等一系列演讲中痛斥日本“大举侵犯其文化祖邦之中国,更在中国如此野蛮横行,且不但要亡中国的国家,并要灭中国的种族。这无异等于发掘日本自己的祖宗的坟墓,来埋葬日本自己的子孙前途”〔21〕。日本政府恼羞成怒,不但辱骂他是一个失败的诗人,而且百般阻挠他在日本的活动,以致于他最后离开日本时,竟没有人敢来为他送行。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之后,泰戈尔立即进行了抨击。1936年4月12日,加尔各答举行反侵略集会,泰戈尔在会上慷慨激昂,抨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并正告日本军国主义者:正义在中国人民一边,英勇的中国人民已经奋起,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最终一定会取得胜利。他还鼓励印度人民行动起来,分担中国兄弟的苦难,并与中国兄弟并肩战斗,打败侵略者。
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侵略中国。泰戈尔闻之义愤填膺,多次以书信、电报、谈话、诗歌等形式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进行抨击。在国际大学,他一见到魏风江和谭云山就安慰说:“我坚信中国是不会被征服的。日本侵略军愈凶残,溃却的日子也就愈早。中国终于会得到独立和自由。”他断言日本必败〔22〕。
1937年秋,泰戈尔染病卧床,蔡元培、戴季陶等人联名发来慰问电。9月21日,泰戈尔复电明确表示:“贵国人民此次对于所加于贵伟大和平国土之非法无理之侵略,作英雄勇武之抵抗,余已不胜钦敬,并且祷阁下等之胜利。余之同情及余国人之同情,实完全寄予贵国。愿正义与人道,由阁下等之凯旋,得以维持。”他还在信中强烈谴责日本军国主义者〔23〕。这封电报迅速在印度各报刊转载,并由路透社向世界各地广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日本当局又惊又惧,就设法买通一个亡命日本的印度人拉什伯里·波斯,以所有旅日商人、学生及侨民的名义从日本给泰戈尔发了一封电报,请求泰戈尔不要发表反日言论,并设法劝阻印度国大党及尼赫鲁氏不要有反日举动。
泰戈尔非常愤慨,立即写信予以驳斥:“今日一个国家侵略另一个国家,其罪过犹不仅在其所怀抱之帝国主义者的野心,而尤在其对于人类之不分皂白地屠杀,比任何瘟魔为更甚。如果全世界的被侵害的良心皆大声疾呼,以反对此种罪过;我何人斯,而可以消弭这种正大的抗议?”〔24〕
泰戈尔驳斥拉什伯里·波斯的消息传到中国,中国人充满感激,也倍感振奋〔25〕。
1938年1月,日本法西斯分子竟然到佛寺祈祷以庆祝战争的胜利。佛陀以大慈大悲成为人们祈求幸福和平的神,而正在屠杀人民的凶手却到寺庙里去庆祝胜利,为自己的杀人罪行掩饰。泰戈尔闻之异常愤怒,当即奋笔疾书,写下《敬礼佛陀的人》一诗,辛辣讽刺日本法西斯分子是食人肉的野兽〔26〕。
1938年7月23日,曾访问过国际大学的日本人野口米次郎致信泰戈尔,公然为侵华日军的暴行辩护,称“印度何以要同情中国而反对日本?日本之所以征伐中国,只是要警戒中国的政府,以拯救中国的人民与文化”。泰戈尔一方面为一个文人如此堕落感到伤心,一方面毫不留情地回信进行驳斥:“要知道中国是个不可征服的国家,日本今日之所行所为,只得自食其恶果。”〔27〕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进一步加剧,泰戈尔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也越来越具体。为了救济战争中受苦的中国学生和难民,他在印度发起了募捐行动,并率先拿出五百卢比作为倡导。他还和国际大学的师生一起在印度各地义务演出,把所得收入用于中国的抗战。1938年4月,谭云山回国之前,他特地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另外还“写了一篇很长的‘使音(Message)亦交我带呈蒋委员长转致中国人民”,对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表示同情和敬意,并预言中国“抵抗必胜,建国必成”〔28〕。蒋介石复信表示感谢。1939年圣诞节,泰戈尔致书蒋介石,赞扬中国人民“以艰苦牺牲之精神,证明中国之伟大,贵国人民之英勇卓绝,其性质不啻一雄伟之史诗,鄙人认为无论如何,贵国将来之胜利,必于人类文明之精神园地中,永留灿烂之光明”〔29〕。1940年11月,泰戈尔在欢迎访印的戴季陶和中国代表团的致辞中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光荣胜利地度过当前的困难,中国将以精神战胜侵略的事迹,昭示于现代”〔30〕。
为了中国的抗战,泰戈尔可以说想尽了一切办法。1939年,他邀请徐悲鸿来印度举办画展,募捐抗战。1940年春,徐悲鸿抵达国际大学,就住在中国学院。泰戈尔热情安排徐悲鸿在国际大学讲学,参加社会活动,结识甘地,让徐悲鸿有机会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1940年2月,在泰戈尔帮助下,徐悲鸿先后在圣地尼克坦和加尔各答两地举办画展,泰戈尔亲自为画展撰写了序言,画展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徐悲鸿将画展所得款项悉数捐给祖国的抗战〔31〕。
中国就这样成了诗人一生的牵挂。1941年2月21日,已身患重病的泰戈尔仍深情地回忆起1924年的中国之行:
我访问过中国,
以前不认识的东道主
在我前额的吉祥痣上写了
“你是我们的知音”。
陌生的面纱不知不觉地垂落了,
心中出现永恒的人。
出乎意料的亲密
开启了欢乐的闸门。
我起了中国名字,
穿上中国服装。
我深深地体会到:
哪里有朋友,
哪里就有新生和生命的奇迹。〔32〕
五
当然,中国人哀悼泰戈尔,也是在哀悼一种人类美好理想的消失。关于这种理想,宗白华曾这样概括:
但是这突破“自然界限”,撕毁“自然束缚”的欧洲精神,也极容易放弃了“自然”的广育众生、一体同仁的慈爱,而束缚于自己的私欲内,走向毁灭人类的歧途。东方的智慧却不是飞翔于“自然”之上而征服之,乃是深潜入于自然的核心而体验之,冥合之,发扬而为普遍的爱。这不正是泰戈尔每一诗里的精神和境界吗?〔33〕
而追求这种精神理想,也正是中华民族的国民性。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与泰戈尔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精神相依。因此,虽然现在:
抛下诗琴和理想去了,
你这灵智的东土诗翁!
……
你去了,有一天
那梦境在地上开了花。〔34〕
但泰戈尔对人类和世界普遍的爱,就如同中国人对老诗人的爱和感谢都将永存!
1939年,泰戈尔曾对谭云山说,他希望中国抗战胜利后再到中国去,与中国人民共同庆祝胜利。
惜哉!诗人早逝。“可是他的精神却永远存在我们的心中!”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的祭文,代表了中国人的心声〔35〕。
1924年4月29日下午,在告别中国的演讲中,泰戈尔曾不无伤感地说:“我的不幸的运命从我的本土跟着我来到异乡,我的部分不完全是同情的阳光”,但他也相信:“敢说他们明白了结果以后一定会得赦免我的。”〔36〕
患难见真情!历经了岁月的淬炼和生死考验,中国心与印度诗魂终于永恒交汇在一起。
愿大师之再来,以求此众群生。
为天中之大天,作仁中之至师。
今天竺与震旦,为法侣以相亲。〔37〕
老诗人的诗魂,在中国不再黯然神伤!
注释:
〔1〕如《国际言论》杂志1937年11月报道“印度诗哲泰戈尔病剧”:“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现在桑田克坦城家中,患病甚剧。”
〔2〕《印度诗圣泰戈尔病逝》,《新华日报》,1941年8月8日
〔3〕《东方文化协会电唁泰戈尔家属》,《新华日报》,1941年8月13日
〔4〕《蒋委员长电唁泰戈尔家属》,《新华日报》,1941年8月12日
〔5〕《港中外人士追悼泰戈尔》,《新华日报》,1941年8月20日
〔6〕〔7〕〔9〕〔12〕〔17〕〔19〕周晓选辑:《中国文化机关团体举行泰戈尔追悼大会史料选》,《民国档案》,2011年第3期。
〔8〕〔11〕〔35〕石源华:《泰戈尔与中印文化交流》,《公共外交》(季刊),2013年春季号。
〔10〕方东美:《坚白精舍诗集》,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32—233页。
〔13〕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编年传记》,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173页。
〔14〕〔16〕〔37〕戴季陶致泰戈尔嗣哲书,见《中印佛教交通史》,(释)东初编著,中华佛教文化馆出版1985年版,第485、485、485—486页。
〔15〕陈立夫:《追悼泰戈尔先生讲稿》,《教育通讯》,1941年第4卷。
〔18〕如柳无忌的《纪念泰戈尔——一篇未曾讲演的演讲稿》,《时事新报·学灯》(渝版,第155期),1941年12月8日。该文为“纪念泰戈尔”专栏中的一篇,另两篇为方东美的《印度诗哲泰戈尔挽词》、长之的《十七年前一个暖和的下午——忆泰戈尔》,由宗白华编辑。
〔20〕〔21〕〔23〕〔24〕〔27〕〔28〕谭云山:《诗圣泰戈尔与中日战争》,《民意》,1939年第65期。〔22〕魏风江:《我的老师泰戈尔》,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174页。〔25〕《印诗人泰戈尔不允阻止排日运动》,《抗战情报》,1937年第2期。〔26〕《泰戈尔作品集》(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87页。〔29〕《教育短波》,1940年第7卷第3期。〔30〕刘圣斌:《印度与世界大战》,(重庆)时与潮社1944年版,第136页。〔31〕徐静斐:《徐悲鸿与泰戈尔》,《清明》,1985年第4期。〔32〕刘安武等主编:《泰戈尔全集》(第8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页。〔33〕宗白华:《<纪念泰戈尔>等编辑后语》,《时事新报·学灯》(渝版),1941年第155期。〔34〕木樨:《悼泰戈尔翁》,《艺术集刊》,1942年8月第一辑。〔36〕泰戈尔:“告别辞”,《小说月报》第15卷8号,1924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