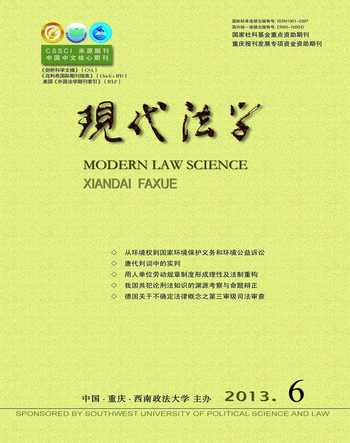关于竞争行为正当性评判泛道德化之反思
蒋舸

摘要:就主流理论和法院实践而言,道德解读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尤其是其一般条款方面占有重要地位。但是竞争有其不同于道德评价的内在规律,在运用一般条款时,应当尊重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文本,关注行为对竞争秩序的客观影响,而不应将道德感作为判断竞争行为正当性的终极标准。
关键词:反不正当竞争;道德标准;竞争本位标准;竞争的本质
中图分类号:DF41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3.06.07
网络接入服务商在网络搜索服务商的搜索结果中插入商业广告是否正当?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诉青岛奥商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青岛市分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青岛鹏飞国际航空旅游服务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0年第8期。 离职员工设立新公司并获取原单位的关键交易机会是否正当?参见:
山东省食品进出口公司、山东山孚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山孚日水有限公司与马达庆、青岛圣克达诚贸易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申字第1065号 (下文简称“海带配额案”)。 无名写手改名换姓为与知名作家同名继而出书是否正当?湖南王跃文诉河北王跃文等侵犯著作权、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年审理。 通过网络爬虫抓取其他网站汇集的信息是否正当?上海汉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与爱帮聚信(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2011)一中民终字第7512号。 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型竞争行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至第15条的类型化条款常显捉襟见肘,需要作为一般条款的第2条施以援手。现阶段对第2条的研究与适用,往往强调其道德属性,但相较于类型化条款,一般条款对尚未形成有效市场规则的领域尤其必须保持开放性。作为总体的良性竞争秩序固然不能脱离道德评价
,大部分(并非全部)的类型化不正当竞争行为构成要件也包含一定程度的道德评价。但一项竞争行为之所以不正当,归根结底是因为其客观效果扭曲了市场机制,破坏了市场结构,而不是因为行为人主观动机恶劣[1]。因此,当市场上出现尚未类型化的新型竞争行为时,着眼点首先应当放在行为的客观效果上,而非行为者的主观动机上。过于强调竞争中的道德因素,会妨碍我们对新型竞争行为是否正当作出正确判断。
一、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中的道德标准分析
(一)一般条款的文本与实施之背离
一般条款由文本和实施两个层面构成:前者是立法者眼中的一般条款,所谓“law on the books”,后者是司法者眼中的一般条款,所谓“law in action”。对于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而言,前者固然重要,但真正影响个案中权利义务之分配、利益格局之变化的却是后者。所以,要回答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是否包含了道德因素,不仅需分析法律文本,而且必须关注法条实施。
就《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文本而言,法条用语并没有将道德作为评判竞争行为正当性的考虑因素。尽管对一般条款的范围存在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在第2条的前两个条款中,哪一款才是一般条款,人们
见仁见智实务中有极少数案例还将规定立法目的的第1条也作为裁判依据,如湖南王跃文诉河北王跃文等侵犯著作权、不正当竞争纠纷案,(2004)长中民三初字第221号。该种解释思路非常有益,但此种作法很少见,在实务中影响不大,故本文不予进一步分析。 ,但无论是法条用语,还是对《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的系统解读,都昭示了强调行为人主观动机的第2条第1款比强调行为客观后果的第2条第2款更适合被视为一般条款。
首先看法条措辞:第2条第1款要求“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这样的措辞仅仅表达了立法者对经营者的期许,并未明确地将违背期许和行为不正当相联系。第2条第2款则规定:“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这一规定将行为效果设定为判断竞争行为是否正当的依据。再看这两款所处的语境:两款均位于总则部分,但其中有资格成为一般条款者必须具备统领类型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能力,或者说必须抽象出类型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共性。考察第5条至第15条列举的11种类型化不正当竞争行为,各条都对行为后果有所涉及,但却并非每一条都关注行为背后的主观动机。例如,根据第13条第3款的规定,只要经营者从事最高奖金额超过5000元的抽奖式有奖销售,无论是否出于恶意,是否意识到了行为给其他经营者和竞争秩序造成的影响,都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监督检查部门可以责令停止并处以罚款(第26条),如果给其他经营者造成损失,还应赔偿损失(第20条)。诚然,类型化不正当竞争行为条款中的一些用辞带有对行为人主观动机进行价值评判的色彩,例如第5条仿冒行为中的“擅自”,第6条限制竞争行为中的“排挤”,第7条权力经营行为中的“滥用”,第11条中的“排挤”等,但其他类型化条款——典型的如前述对超过5000元的有奖销售的禁止——则采取了价值中立的用语,满足于对行为的客观状态进行描述,而不对行为背后的主观动机加以推测。既然道德评判只在部分类型化条款中若隐若现,而在其他类型化条款中无处可寻,自然无法将道德标准作为一以贯之衡量竞争行为正当性的尺度。
前文的分析表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文本已经排除了将道德标准上升为一般条款的可能性,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一认识却未能得以很好地贯彻,相反,很多案件都将对行为人主观动机的推断作为判断行为正当性的主要标准。鉴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案例数量众多,笔者在对共107份司法文书或者裁判摘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在北大法宝的“司法案例—判例与裁判文书”中选择案由为“不正当竞争纠纷”,共检索到2240份文书。为缩小范围,本文分别从限定条款、限缩审级和手动补充知名案例三方面着手。就限定条款而言,在北大法宝“司法案例”栏输入关键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进行全文检索,获16篇司法文书。就限缩审级而言,在北大法宝“司法案例”栏输入关键词“反不正当竞争”进行全文检索,审判法院限定为最高人民法院,获得88篇司法文书。加上本文开头提及的四个典型案例(排除已被检索到的“海带配额案”),初步获得107份司法文书(上述检索时间均为2013年8月27日)。 ,筛选出了14份依《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作出的判决或裁定。在对初步获得的107份司法文书逐一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排除与《反不正当竞争法》无关的文书和重复的文书30份,得到77份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直接相关的文书。根据判决依据的主要条款,这些文书的构成如下:一般条款第2条有14份(占18%),禁止仿冒的第5条有31份(占40%),禁止限制竞争的第6条有1份(占1%),禁止虚假宣传的第9条有11份(占14%),禁止侵害商业秘密的第10条有15份(占20%),禁止诋毁商誉的第14条有5份(占7%)。 这14份文书覆盖了从中级法院参见:(2007)长中民三初字第0246号。 到最高法院参见:(1999)知终字第17号。、从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参见:(2007)高民终字第181号。到经济发展程度相对不高的西部地区参见:(2000)渝高法知终字第18号。 的不同案件,略具代表性。按照判决或裁定的具体依据,这14份文书可以分成三类:
由于第2条第1款体现的是道德标准,而第2条第2款体现的才是客观秩序标准,所以上述表格反映的事实是:在依一般条款断案的司法文书中,只有7%的文书排除了对道德标准的考虑,其余93%都将行为人的动机是否道德纳入了判断其行为是否正当的考虑因素,而且有43%的案件将竞争行为的正当性完全系于对行为人主观动机的考察上。考虑到一般条款针对的本来就是无法套用类型化条款加以判断的、尚在摸索市场规律的、相对新型的竞争行为,以习俗为基础的道德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引人深思。不过,鉴于93%的高比例所揭示的法官对道德标准的普遍认可,有必要先分析一下这种普遍认可的根源,以便有针对性地展开分析。
(二)竞争秩序道德化之观点
一般条款的文本与实施的背离,部分可能源于法官的正义感,部分也源于学术界对竞争秩序道德化的支持[2]。学界讨论一般条款的文献,大致可以分为“道德说”、“秩序说”和“统一说”,分别对应于前面表格中列举的三种情况:只根据第2条第1款、只根据第2条第2款或同时根据两款来判断非类型化竞争行为的正当性。
在这三种学说中,“统一说”[2]尽管比较符合实务界经常一揽子适用第2条前两款的现状,但相关的系统论述很少[3]。“秩序说”尽管符合法律文本直接传递出的意思,但论著寥寥[3]。相关论著在广度方面的局限导致了深度方面的欠缺,既无法从正面深究以不扭曲竞争秩序本身作为判断行为正当性的理由,也难以从反面展开排除道德标准的讨论。相较之下,“道德说”的旗帜最为鲜明,在深入探讨一般条款内容的文献中占据了主要地位[4]。该说从自然法理念出发,追求在市场领域实现公平、公正与和谐,其核心是以道德作为竞争行为正当性的评判标准。
“道德说”的合理之处在于认识到了竞争秩序中既定习俗的重要性,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区分秩序形成的不同阶段,因此忽略了对不同类型的竞争规则之性质的研究。竞争秩序并非一套全盘固化、天衣无缝的规则,而是由已经定型的与尚在流变中的两种类型的规则所构成。在任何时间的横截面上,竞争规则的大部分版图的确都被交易习惯或公认的商业道德所占据,但总有一些地带尚显模糊。这些领域内的各方仍在角力,利益格局尚未定型,各方普遍接受的行为模式还没有出现,或者说,均衡尚未显现。在总结秩序形成的不同阶段所需的规则时,必须对其个性加以考虑,正是基于这一考虑,一般条款才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显得额外重要。
类型化条款和一般条款之间,既有合作,也需要分工,二者各司其职,才能维持整个反不正当竞争法体系的平滑运作。类型化条款的任务是将已经成型的市场理性加以总结,而一般条款的任务更多地则是提示法律文本的读者:在此领域,未必已有成型的市场理性可资借鉴。前者能直接提供行为模式,后者提供的往往是价值判断的指南。一般条款反映的应该是最深层次、最根本的竞争规律,而对这一根本规律的表述,制约着法律文本的受众对竞争本质的理解。当理解竞争行为正当性的标准语言被设定为“道德”时,无论司法者依其原本对竞争的直观认知是否会将竞争行为判为不当,“道德”语言都将在个案中影响司法者用道德框架去限定竞争模式,并潜移默化地让司法者排除对非道德因素的考虑,而专注于对行为动机的考察,忽略对客观结果的认识。甚至在所涉竞争领域既无既定习俗也无道德共识的情况下,上述思维强制仍旧会发生一定的作用。毕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语言的界限就是思想的界限”[4],所以谨慎选择一般条款的语言至关重要。正因为如此,本文拟对道德标准在一般条款中的话语权进行考察,考察或许会略显严苛,但在道德俨然成为判定非类型化竞争行为正当性的主导视角之背景下,一些反动或许并非无益。
二、竞争规则中的道德标准解读
在对道德解读进行分析前,有必要先澄清竞争规则语境下 “道德”的概念。本文不拟在法理层面探讨道德的地位,仅试图廓清“道德”二字在反不正当竞争法领域内可能具有的含义,及不同含义的“道德”在判断竞争行为正当性方面固有的局限。
道德概念的模糊性首先体现为“道德”至少可以指称两种不同的含义 [5],我们权且称为伦理意义上的道德和习俗意义上的道德。前者以崇高的“善”、利他、圣人之德为终极目标,后者以寻常的“好”、不害他、底线之德为满足。前者是价值评判,驰骋于应然,能在未知的领域指引人的实践;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评判,着眼于实然,在尚无陈规可循的新天地中难免举步维艰。仅依上述差别观之,既然一般条款的目的在于为始料不及的新情况提供判断标准,那么不拘于既有体系的、伦理意义上的道德,似乎更有资格判定新型竞争行为的正当性。
但伦理意义上的道德适合成为竞争行为的参照系吗?毕竟,市场遵循的是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而非利他的崇高境界。“自私”这一难登伦理道德大雅之堂的动力,较之“奉献”之类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口号,更有资格成为市场秩序的逻辑起点。是超然于伦理的市场,而非鼓吹思想净化的道德运动,造就了“仓廪足而知礼节”的社会基础[5]。在优胜劣汰的市场体系中,“圣人之德”应让位于“竞争之规”。将竞争规则语境下的道德理解为习俗意义上而非伦理意义上的道德,不仅有比较法上的支持如《巴黎公约》中的“商业之诚实惯例”,或德国1909至2004年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条中的“良俗”。 ,即使试图对竞争秩序进行道德解读的学者也赞同这一限定[6]。
下文将从习俗意义上的道德通常寻求正当性的三个角度加以剖析,探讨道德解读是否能从法理角度、比较法角度或者司法实践角度获得支撑。
(一)道德标准论证的法理误区
在对一般条款的道德解读进行论证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说法是:法的形式理性要求其简练抽象,以致在某种程度上遗漏或违背了个案正义,而个案正义正是法之价值所在[6]32-37。这一论证背后是自然法的信念:“任何一种行为只有在被证明是不道德、不诚实之后,方有可能纳入法律的范围明确予以禁止,这种合法性论证在逻辑上是先于立法的,行为的道德合理与否,构成了立法禁止与否的逻辑起点。”[1]29
上述看法值得推敲。首先,认为“任何一种行为只有在被证明是不道德、不诚实之后,方有可能纳入法律的范围明确予以禁止”,只看到了法律与道德关系中的一种情形,即法律作为道德最低保障的情形,但却忽视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还有其他类型,有的法律规则——在技术性很强的商法或经济法领域——并不能由道德规范推导出,从而导致道德在许多问题上解释力有限。例如,道德感很难在具体追求个案正义时指引审查员对一项经营者集中申报予以批准,但对另一份申报予以拒绝。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决不能被简单化为“法律所禁止”是“道德所禁止”的子集,而“道德所允许”是 “法律所允许”的子集。二者尽管存在重叠,但各自均有无涉对方的专属区域。其次,“个案正义”并不始终等同于公众或者法官的正义感。尤其是在以市场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的部门法领域,道德能起到的作用远比想象的有限。正义感在很大程度上诉诸直觉,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指引着人们无需精细计算便抵达“是”或“非”的终点。对于以市场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的个案中的正义,需要的往往不是直觉而是计算,不是冲动而是平衡。
(二)道德标准论证的立法局限
比较法也被用作对一般条款进行道德解读的证据。几乎所有研究一般条款的文献都提到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 (UWG)最初制订于1896年,在 1909年经历重大修订前不包含一般条款。但1909年修订后的版本一直沿用至2004年。最近一次修订发生于2009年,目的是转化欧盟2005/29/EG指令。 原第1条规定的“良俗”原则。还有很多文献提及了《巴黎公约》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Article 10bis. “违背工商业之诚实惯例”的规定,但这一规定的历史局限性近年来受到了学者的关注[7]。德国学者认为,《巴黎公约》的主要调整对象是专利与商标领域的搭便车行为,而非新型商业实践。所以在运用其规定的“诚实惯例”解决新问题时,应当考虑到其局限性,并持谨慎的态度[8]。鉴于德国立法例在反不正当竞争法领域的重要性,以下对其近年来的发展进行简短的分析:
1909年至2004年间,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良俗”在2004年修法前,一般条款的表述为:“在交易中以竞争为目的实施有违良俗之行为者,可被请求停止行为并赔偿损害。” 作为一般条款的核心概念,我国研究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研究文献均会提及这一条款。不过, “良俗”概念多年来在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领域备受批评,以致立法者在2004年修法时,最终以“不正当性”(Unlauterkeit)取代了之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条中“有违良俗”(gegen die guten Sitten)的规定。因为良俗标准毫无必要地将不道德(Unsittlichkeit)的污点强加给竞争者,而这种作法已显过时。BT.-Drucksache 15/1487:16. 鉴于此,新法采取了“告别良俗”参见:Schricker. Entwicklungstendenzen im Recht des unlauteren Wettbewerbs[J].Gewerblicher Rechtschutz und Urheberrecht,1974,(9): 582.需要说明的是,新法在第2条第7款对“职业所要求的注意义务”之定义中仍保留了部分“良俗”要素,因为该款将诚信原则和市场习惯作为判断职业所要求的注意义务的标准。但该款遭到了学者的猛烈批评,除了重申诚信与市场习惯无力承担判断竞争行为的价值之任务外,批评者还指出以诚信和市场习惯来解释注意义务实属“无用的同义反复”。(参见:Harte-Bavendamm,Henning-Bodewig. UWG[M]. Muenchen: C. H. Beck, 2009:179 – 190.) 的态度。尽管新法没有直接给“不正当性”下定义,德国学界主流观点已然明确,即应当采取目的解释,对不正当性作“去道德化”Schuenemann in Harte-Bavendamm/Henning-Bodewig, UWG, C. H. Beck 2009, 2. Aufl., § 3, Rn. 122-126.的“功能性理解
”[9],确保“竞争导向的市场经济起作用的条件”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参见:Baudenbacher.Suggestivwerbung und Lauterkeitsrecht[M].Schulthess Verlag,1978:134;Emmerich. Unlauterwettbewerb[M].Muenchen:C. H. Beck,2012:53-54;Harte-Bavendamm,Henning-Bodewig.UWG[M]. Muenchen:C. H. Beck, 2009:199.这一转变是对德国学界多年来针对“良俗”标准批判的回应。可见,即使在对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道德解读的典范国家,立法者至少在概念层面已经以竞争本位标准替代了道德标准。虽然概念的更迭不会立即带来司法实践中对一般条款运用的剧烈转变,但立法者在学界讨论多年之后终于从一般条款中去除了“良俗”概念,传递着要求司法者断案时转变视角、谨慎对待道德评价的意图。
(三)道德标准论证的司法困境
尽管上述从法学理论和比较法角度进行的分析已经初步揭示了道德标准不适合评判竞争行为的正当性,但在我国法院的实践中,道德解读在判断竞争行为正当性方面实际上仍起着重要作用。究其原因,道德评判在很大程度上诉诸直觉,在对说理过程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其操作简便迅捷。部分法官已经意识到“按照一般条款认定法律列举以外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时,特别要分析行为对竞争的危害后果;……要注意分析其不同的后果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以此进行定性”。即只有在从损害后果的非道德角度对行为予以定性后,才轮到按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第1款规定的“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原则”以及“公认的商业道德”进行判断。在行为定性方面,非道德权衡是决定性的,道德权衡最多只是辅助性的。但为便于操作,不妨运用前文《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立法精神,即根据竞争行为是否存在“搭便车”、食人而肥己、投机取巧或者巧取豪夺等精神进行衡量。这些精神反而更容易理解和掌握,……可以做到“看得见”和“摸得着”[10]。
可惜这种便捷的操作存在两个
方面的问题:第一,如前文所述,反不正当竞争法领域的“道德”,只能是市场的道德、习俗意义上的道德,伦理之德或称圣人道德并不宜被用于调整市场交易。法官如果要适用道德标准,首先必须指明与系争行为相关的市场习惯是什么。但在审判实践中,少见法官对相关市场习惯的具体说明。如果对道德标准有涵摄,也往往体现于指出行为人的动机应受谴责,或者宽泛地认为其行为不道德,但体现着朴素正义感的模糊道德诉求并非总能契合市场的需求。这种不一致的客观存在往往为成熟的司法实践所承认,所以在美国,秉持“不劳而获即不正当”的INS v. AP案248 U.S. 215 (1918). 多数意见——哪怕该案曾被赋予“不正当竞争法之基石”地位[11]——在后续审判中难以被贯彻[11]15。欧盟中的普通法系国家对竞争自由——包括对所谓“不劳而获”的模仿自由——均给予充分的尊重。绝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也拒绝将“搭便车”直接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除非在“搭便车”的同时,还妨碍了信息真实、自由地流动[12]。
第二,法官们感到道德标准“更容易理解和掌握”的前提是我国对法院判决的说理(即涵摄部分)要求不高。对一些显而易见违背市场运作机制的行为而言,用“看得见”和“摸得着”的道德标准进行评判既符合我国司法从业人员的习惯,又能快速地解决问题,在我国现有的司法背景下,或许有一定的合理性(当然,在这些黑白分明的领域,撇开道德标准,诉诸竞争秩序,同样可以迅速得出结论)。但问题在于,一般条款存在的最根本意义,在于解决超乎立法者预料的新问题。在经济现实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新问题很有可能是“疑难杂症”。对于疑难杂症,宽泛的公平正义观恰恰无能为力,甚至可能将司法导向错误方向。关于朴素公平正义观驱使下对竞争秩序的危险裁剪,参见:崔国斌.知识产权法官造法批判[J].中国法学,2006,(1):146. 而且,在司法实践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判决的涵摄部分应当越来越详尽。下文即分析道德在解读竞争秩序方面的局限性:以道德为标尺,难以演绎出令人信服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之涵摄。
三、道德解读之局限
无论是伦理意义上的道德,还是习俗意义上的道德,都以多元化、不可预见性、滞后性和价值预设性为特点,与普世性、指引性、进化性和价值中立的竞争规则多有不合。鉴于前文已述及竞争语境中的道德只能是习俗意义上的道德,为避免分析过程枝蔓横溢,下文拟以习俗意义上的道德为重点,指出欲以道德来设定竞争的禁区,有画地为牢之虞。
(一)道德标准的多元性和竞争规律的普世性
健康的竞争规律具有普世性。反垄断在美国是通向竞争秩序之路,在中国也不例外。与之相对,道德命题则往往模糊而多样。如波斯纳所言,即便能找出几条也许任何人类社会都相同的普适道德律,“但是,这些原则都太抽象了,无法用作衡量标准”[6]。特定社会中人们所称的道德,包括在特定竞争环境下的所谓良俗,往往是时代性、地方性、个体性的知识。德国学者在批判“良俗”标准时就曾指出:“良俗”之“俗”的用词本身都必须采取复数形式德语中“gutten Sitten”(良俗)的“Sitten”,是“Sitte”(风俗、道德)的复数形式。 ,怎么可以指引市场[8]119?在社会处于高速发展、社会成员价值取向日趋多元的当今中国社会,道德多元化倾向更为明显。可想而知,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针对同一问题的市场习俗可能完全不同:在还没有完全进入快节奏、大规模市场经济的地区,经营者之间、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很大程度上还保有熟人社会的互动习惯;而在早已融入激烈的全球经济竞争的地区,经营者之间、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都已习惯了“喻于利”而非“喻于义”。我们很难乐观地想像,界定道德共同体这一困扰道德哲学家的难题[13],在当今中国的市场经济领域中突然不再是问题。
以前文提及的“海带配额”不正当竞争案为例,在事实方面,各审法院均认定被告马达庆在原告就职期间投资设立了与原告构成竞争关系的公司,而且该公司在被告离职后,很大程度上仰赖被告在原工作岗位上获取的社会关系资源,取代了原告在对日海带出口领域的市场地位。但从同样的事实出发,各审法院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一审法院认为,被告“马达庆将本属于原告的竞争优势转为其投资设立的公司所有,属于将日本客户对自己基于履行职务行为所产生信赖的滥用,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原则,也违背了公认的商业道德”[14],从而构成不正当竞争。二审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则认为,“在没有法定的和约定的竞业限制以及不侵害商业秘密等特定民事权益的情况下……,马达庆的被控行为没有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也没有违反公认的商业道德,其行为不具有不正当性。”不仅各级法院在被告马达庆是否违背诚信原则和商业道德的问题上见仁见智,而且学者们站在整体社会利益的角度[15]和原告的职工从自身利益出发得出的结论据(2009)民申字第1065号判决书记载,
(被告)攫取了山东食品公司、山孚集团公司和山孚日水公司的海带贸易机会,夺取了山东食品公司千名离退休、退养、在岗职工的“养命钱”,激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职工代表多次赴省进京上访。也南辕北辙。同样的客观事实却引发了截然不同的主观认识,这显示出在市场转型、走向更为充分竞争的过程中,不同群体对市场正义有着不同的理解或期待。无论是保守还是开放(两个词均在中性意义上使用)的观点,每个人的看法都是其出生地域、成长环境、性别年龄、教育背景、审美情趣甚至带有偶然因素的个人经历叠加在特定问题上的投影,很难被观点相左者的几句道德说教改变。
上述观察意味着道德标准在发展竞争规则的司法实践中预示的危险:当法官名义上需要以市场之良俗断案,实则市场还没有就良俗形成固定看法时,不同的法官很可能从相同的良俗概念出发,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主审法官名义上需要探究的是所谓社会大众的道德观,但当竞争在新领域开疆拓土时,这种所谓客观的道德可能根本尚未形成,或者至少法官难以得知。BGH GRUR 1960, 558, 560 f. - Eintritt in Kundenbestellung.本案是德国法院实践中屈指可数的、采用问卷调查形式探究特定商业惯例的案例之一。 试图探求所谓民众立场的作法,在司法实践中可能引起混乱。例如,采取民众主义立场的沃伦法院在反托拉斯法领域曾有的混乱,该混乱终结于经济分析在反托拉斯领域对民众主义立场的胜利。(参见:波斯纳.道德和法律理论的疑问[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65.) 一旦客观道德缺位,决策者的主观道德便开始起作用,最终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往往是个人好恶[16]。遵从“良俗”的指引,终点往往是法官个人道德感的垄断[17]。
(二)道德评判的不可预见性与竞争规则的指引性
上文提到的道德多元性,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道德规范直接上升为竞争规则的可能性,因为竞争规则应当具备明确的指引性,告诉竞争者其行为是否会为竞争法所禁止。但在与传统道德无涉的新型竞争模式下,假道德之名作出的“所谓解释只是各取所需的礼貌说法而已”,而结论也不过是令人难以捉摸的“执拗的道德直觉”[6]57。若仅仅告诉市场参与者遵循道德准则行事,对他们预判自己的行为尤其是突破传统行业惯例的行为并无多大助益。
道德起源于熟人社会,而市场经济——甚至早在其步入全球化时代之前很久——早已突破了血缘和友情的框架,进入了陌生人间博弈的时代。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7]。在普遍的层面上,起源于熟人社会的道德体系与陌生人秩序间本已存在鸿沟,不可能完全被消除。中国的道德传统尤其注重差序格局和人际关系[18],其与市场经济间的距离尤其需要努力方可化解。诚然,理想状态的法官应该客观中立,摆脱熟人社会的底色,洞察市场的正义。问题在于,法官的道德“正义”和客观的市场“正义”并不总是吻合。当抽象的“法官”转变为具体的“法官”,理论上完美的法官被现实中(和其他任何职业的从业者一样)不可能完美的法官所取代时,上述距离导致了决策者缺乏智识上的依托而流于武断,决策缺乏一贯的标准而丧失指引性。对法官而言,在道德无法给其明确指引的空白地带,如果立法仍要求法官以道德为指南,法官能诉诸的其实只有其个体化的内心确认。对于竞争者而言,法官的这种内心确认往往难以从外部得知,从而无法预见自己即将采取的行为是否会被判定为不正当。我们或许可以想像:一位生长在乡土社会的法官拥有比成长于都市的法官更保守的竞争观,一位善于观察细节的法官比在形象思维方面粗枝大叶的法官更倾向于否认竞争者间的模仿。成长环境和观察能力原本无关道德,但当道德工具达不到指导裁判的目的、立法者又不曾指出合理可行的标准时,便轮到既无关道德确信也无关竞争秩序的因素来左右案件结果了。道德视角中的世界既因人而异也因角度而异,但竞争却有其普世的规律。若以个体化的道德来规范普世化的竞争,无论司法者还是竞争者都难免无所适从。
(三)道德实践的滞后性与竞争活动的进化性
习俗意义上的道德反映的是既定时空领域中既定人群在一定程度上的既有共识,其智识指向过去,终于现在,其诉求定于守成,而非求新,故其适用限于规则已固化的领域。但若要在以推陈出新为永恒主题的市场竞争领域运用道德标准,将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一项习俗的确立,往往以无数实践为前哨。常常是在社会已客观接纳了某种实践后,人们才从主观角度对该实践背后的习俗命题予以追认。商业实践同样遵循如下原则:要从合理的个案上升为普适的习俗,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
习俗的被动性和滞后性有违竞争主动推陈出新和永恒自我演化的属性,要在竞争中制胜,最重要的不在亦步亦趋,而在占领先机。在现代商品社会中,这一点体现得尤其明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基本温饱问题的普遍解决,消费者的需求呈现出开放化和多样化的趋势,而这两种趋势都激励着竞争者不断摒弃既有实践、寻求新的竞争优势。
从开放化的角度而言,如今众多市场领域的竞争者显然不能仅仅凭借以更低的价格使人吃饱穿暖而在竞争中取胜,而是需要发掘出甚至连消费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需求,再通过取得优势来胜过其他竞争者。有别于竞争充分、参与者理性的传统经济学模型,真实世界中的市场并不完全,消费者也并不总是理性。要求消费者知道市场上“一个苹果可以换到几个橘子”以及“他们希望换到几个橘子”,经常是不现实的奢望[8]。换句话说,过去的市场是先有消费者的需求(用流行的话语表述属于“刚需”),后有竞争者的供给,这种供给更多是被动适应性的。现在的市场往往是先有竞争者的供给,后
有消费者的需求,供给更多呈现出引导性的特征。试想,假如消费者一旦衣服够穿便不再添置新衣,一旦手机能通话、发短信便不再购置新手机,这样的市场是多么地死气沉沉。之所以现实生活中的市场远比上述假想市场有活力,很大程度上并非因为消费者主动提出花样翻新的需求,而是因为相互竞争的市场参与者们始终在绞尽脑汁探求甚至培育新型消费。现代市场中的“真正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是否能以给定的边际成本获取给定的商品或服务,而在于哪些商品和服务能够以最廉价的方式满足人们的需求”,而对这一问题的思索“从来都是深入未知领域的探索之旅”[9]。从这个角度讲,现在的经营者比过去的经营者承担着更大的不进则退的压力。如果说过去消费者的需求是一张完全清单,那么现代社会中消费者的需求则是一张未完成的清单。相应地,后者对应的竞争秩序比前者对应的竞争秩序更加复杂、更加多变、更难预料。
从多样性的角度看,传统商品社会中竞争者所能提供的产品内容相对明确。现代社会竞争者提供给消费者的往往是一系列心血的总和,有的时候很难判断究竟什么才是导致消费的决定性因素。当今社会人们对名牌的崇尚可以为证:尽管名牌产品也许的确在质量方面更胜一筹(当然未必),但吸引消费者以更高昂的价格购买名牌的动力常常不在质量差异方面,而可能是知名品牌带给消费者的成就感,或者听到别人赞叹时的愉悦感,甚至是装修豪华的店面带给消费者的特殊购物体验本身。竞争者殚精竭虑地希望摸清究竟是哪些要素或者哪些要素的组合才能打动消费者,较之竞争者只需要控制好价格或者进一步提高质量的过去,现在的竞争者需要更加敏锐、更富想象力、更努力地突破陈规,在试错与纠错、求新与淘汰的过程中与消费者自身都难以言说的需求达成动态的默契。
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物资谈不上丰富的过去,消费者需求的类型有限,竞争者努力的方向就是在某一类既定的产品(商品或服务)领域实现超过其他竞争者的生产效率,从而通过以更低的价格提供相同的产品以达到击败其他竞争者的目的。在这一阶段,提高竞争优势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指向竞争者内部,对整体竞争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小,加之引导竞争中资源流向的主力是消费者既定的需求(例如温饱),因此竞争秩序相对固定。与之相应,商业习俗也较易确定,并且同一实践持续很长时间之后,习俗的滞后性就显得不那么明显,用习俗来作竞争行为正当性的标尺也因之具有可操作性。但在今天,有些领域中的习俗尚未固定便可能已过时,欲以习俗来规制竞争,在有的情况下无异于刻舟求剑。
(四)道德规则的价值预设性与竞争过程的价值中立性
道德标准在试图评判竞争行为时的力不从心,根源于道德预设了一种行为模式比另一种行为模式优越,但竞争就本质而言只是一个发现的过程[19],不预设任何行为的优越性。竞争给我们提供的只是试错和纠错的场所。有竞争者欣欣向荣,就有竞争者黯然离场。“在一个有效的竞争市场中……,个人所能够预期的相对报酬是与他努力的客观结果而不是与人们对他努力所做的主观评价相一致的。……我们的个人正义感频繁地和市场的非人格决定相冲突。”[10]实际上,持竞争本位论者和道德论者在反不正当竞争法领域内追求的目标都是保障竞争,只是在如何保障的方法上有所分歧。按照竞争本位论,对竞争之保障,主要在于以任何一个竞争者为中心出发,都既要保障他对水平层面的其他竞争者享有行动自由和决策自由,也要保障他对产业链垂直层面的上游供应商和下游消费者享有行动自由和决策自由[8]243-244。不应总是通过外部的、预设的价值评判来筛选哪些行为可欲、哪些不可欲。道德论则认为,通过对过往经验的总结(且不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过往经验,甚至针对某些行为没有过往经验可言),竞争的旁观者可以预先判断哪些行为对于市场而言是可欲的,哪些是不可欲的。对不可欲的新型竞争行为,人们应当先行禁止,防患于未然。我们或许可以将两种路径的区别归纳为:竞争本位论者采取的是以维持竞争功能为目标的“对错”判断,而道德本位论者进行的是以行为人主观意图、现存市场结构为参照系的“善恶”判断[20]。“在经济领域中,就应当以经济的方式言说”,将“利”与“非利”而非“善”与“非善”作为主导标准[21]。尽管目标相同,但沿着不同的路径,道德论和竞争本位论有时会南辕北辙。克制引导市场的冲动,市场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正是在此意义上,“竞争秩序”(competitive order)和人们通常所说的“有序竞争”(orderly competition)其实几乎恰好相反[10]111。
有必要明确的是,认为对竞争行为正当性的判断应该与对行为的道德评判脱钩,不应被误读为否认道德在维系竞争秩序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包括习俗在内的道德规范,作为社会自生自发的进化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实践理性,蕴含着超越个人的心智所能充分理解范围之外的合理性,反映了人们在成千上万次互动中总结出的、往往是最能达到反复博弈后之均衡的行为模式,从而避免了每个市场参与者去重复试错与纠错。例如,没有必要让每个新市场上的每个竞争者都尝试一次再认识到:与其互相攻击商誉以致两败俱伤,不如所有参与者从一开始就不要陷入混战。所以“禁止诋毁商誉”的规则——如果将其视为包含道德因素的律令——有其竞争意义上的合理性,因为它指明了通向均衡的道路,保障了竞争的正常运作。正因为如此,反不正当竞争法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类型化的、具体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规范。在这些规范调整的范围内,规则已经基本定型,共识已经基本达成,竞争秩序和道德体验也基本保持一致。本文的目的,既非割裂市场与道德间的自然联系关于此主题的文献甚多,例如:万俊人.论市场经济的道德维度[J].中国社会科学, 2000,(2): 4-13. ,更非意图将二者完全对立,但求指出二者作为不同的体系,其内在规律有所不同。针对新型竞争行为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尤其是其一般条款,由于恰恰经常处于二者不相重合之处,故在对待道德标准方面尤须谨慎。
我们的正义感的确经常与竞争秩序的要求恰好一致,但评判结果的偶合并不能反推出评判标准的一致。以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规制的虚假广告和第14条针对的诋毁竞争对手为例:这两种行为都既违背《反不正当竞争法》,也违背我们的正义感,但这并不意味着《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其予以否定评价的原因在于其有悖正义感。对其加以禁止的真正原因在于这两种行为破坏了“就其本质而言不过是意见形成之过程”的竞争[10]106,造成了对竞争的扭曲。禁止的正当性在于竞争的本身,而非行为在道德上的可非难性。在禁止的表象和禁止的原因之间,必须保持清醒的区分。
四、道德解读之矫正
道德标准的适用限于有成熟的市场道德可循的领域,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其适用的疑难地带,尤其是其一般条款面对的问题,往往恰恰是市场进化过程中碰到的新问题。在完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排除会出现竞争规律与当时人们的朴素正义感相左的情况。因此对行为正当性的分析,应当立足于是否扭曲了竞争这一标准本身。
诚然,判断一种竞争行为是否“扭曲了竞争”,有时并不比回答这种行为是否道德更容易,因为“竞争系统复杂到无法用复杂性低于系统本身的方法来加以判断和说明”[22],但这并不动摇道德无力从根本上评判竞争秩序的结论。竞争的复杂性决定了没有任何理论能向法官提供无需纠结就能得到答案的魔力配方,但竞争的本质同时也决定了不同理论之于竞争秩序的价值有别。哪怕两套标准在一些竞争的最佳模式已然明确的领域内可能“英雄所见略同”,也不意味着它们同样正确地反映了竞争规则的核心价值。这一核心价值很大程度上在于坦承智识有边界,尊重市场的规律,以开放的心态信任竞争的力量,相信一个价值中立的试错与纠错场所的存在,比按照任何聪明人的道德感设计出来的人造规则或者仅仅因为其存在便被推定为合理的习俗更符合社会自身进化的规律[23]。
上述看法其实在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文本中已有反映,其第2条第1款和第2款的不同修辞表明,立法者本已赋予道德和竞争秩序不同的地位:道德感不宜作为判断竞争行为正当性的终极标准,对其他经营者的利益和市场秩序的客观影响才是判断一项行为是否受《反不正当竞争法》禁止的恰当依据。尽管基于现有国情,在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尤其是其一般条款时不可能对每一个案件都进行详细的经济分析[24],但以竞争规律为视角,更多地从市场结构而非道德的角度评价竞争行为,既是在市场规律面前应有的谦虚,也是对法律文本的尊重。
ML
参考文献:
[1] KarlHeinz Fezer.Objektive Theorie der Lauterkeit im Wettbewerb[G]//Ohly.Festschrift fuer Gerhard Schricker.Muenchen:C. H. Beck,2005: 671.
[2] 王先林.论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范围的扩张——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的完善[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0,(6):71.
[3] 邵建东.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一般条款 [J].法学,1995,(2):33.
[4] 孟雁北.反不正当竞争法视野中的商业道德解读——以互联网行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为例证[J].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12,(12): 19-20.
[5] Smith.The Wealth of Nations: The Economics Classic - A Selected Edition for the Contemporary Reader[M].Wiley,2010: 236-237.
[6] 谢晓尧.竞争秩序的道德解读:反不正当竞争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0-16.
[7] Glckne,Henning-Bodewig.EG-Richtlinie über unlautere Geschftspraktiken: Was wird aus dem “neuen” UWG? [M].Wettbewerb in Recht und Praxis,2005: 1317.
[8] Harte-Bavendamm,Henning-Bodewig.UWG[M].Muenchen: C. H. Beck,2009:143 -145.
[9] Emmerich.Unlauterwettbewerb[M].Muenchen: C.H.Beck,2012: 53.
[10] 孔祥俊.商标与不正当竞争法:原理与判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681-682.
[11] Dinwoodie,Janis.Trademarks and Unfair Competition[M].New York:Aspen Publishers,2004: 15.
[12] Ohly.The Freedom of Imitation and Its Limits - An European Perspective[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mpetition Law,2010,(5): 506-507.
[13] 富勒.法律的道德性[M].郑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209-210.
[14] 戴磊.利用工作经验获取贸易机会的行为定性[J].人民司法,2010,(6):4-8.
[15] 刘春田.一丝不苟的法律精神,不拘一格的务实态度——评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对“进口日本海带贸易机会”纠纷的判决[J].电子知识产权,2009,(4):65-69.
[16] Hayek.The Road to Serfdom[M].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 156.
[17] Piper,Ohly,Sosnitza.UWG[M].Muenchen:C. H. Beck,2010:25.
[18]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4-42.
[19] Hayek.Der Wettbewerb als Entdeckungsverfahren[G]//Streit,Vanberg.Grundsaetze einer liberalen Gesellschaftsordnung: Aufsaetze zur Politischen Philosophie und Theorie.Mohr Siebeck,2012:322.
[20] Andriychuk.Thinking inside the Box:Why Competition as a Process Is a Sui Generis Right - A Methodological Observation[G]// Zimmer.The Goals of Competition Law.Northampton: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2: 95,96.
[21] 于飞.违背善良风俗故意致人损害与纯粹经济损失保护[J].法学研究,2012,(4):49.
[22] Stucke.What Is Competition[G]//Zimmer.The Goals of Competition Law.Northampton: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2:52.
[23] Gloy,Loschelder,Erdmann.Wettbewerbsrecht[M].Muenchen:C. H. Beck ,2010:10.
[24] Podszun.Der “More Economic Approach” im Lauterkeitsrecht[J].Wettbewerb in Recht und Praxis,2009,(5): 509-518.
本文责任编辑:邵 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