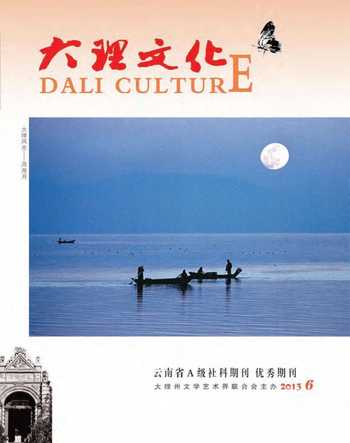烟站记事
吴安臣
熙来攘往皆是客。现在我躲在我屋里乏力地想。很久以来我把这间屋子当作一个无法搬动的固定的巢,这个巢似乎应该永远属于我,只要我想躲在这个巢里,似乎没有人能把我拽出来。寂静的巢包围着我,在巢里看外面的风风雨雨。云卷云舒。这个巢虽然破旧,但有恒久的安全感,我的巢我做主,时至今日我发现其实我错了。这巢终究要离我而去,现在我得自谋去处了。
我住的地方叫烟站,我寄宿好久了。六年前我就住进来了。时间一长我就产生了错觉。以为自己是这儿的主人,潜意识觉得这个事实应铁定无疑了。我在那片满是瓦砾的地方挖了一块菜地。我把那土弄得适合任何蔬菜生长,肥实、平整。但是那块土地而今我无法搬走。我最多临走时多望它几眼,以示我的留恋。
我甚至想象着将来我要在这片茂盛的草地上养一大群羊。到那时白如雪般的羊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那滋味一定不比一个美国的农场主差,同大院的老董也是这么想的,很可惜他也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他的想象甚至超出我们的院落延伸到外面的荒地上,但他也是时至今日连羊毛都没见到一根。这时主人来了,他们在我们的外面任意地挖,任意地改造,把一切弄得缺少章法,打乱了我们经营的秩序。但我们只能看着,表情再不能漠然,因为人家随时可以说你们可以在某时搬走了,那时我们只能夹起尾巴走人。我们只是一些寄居蟹而已。我们的命运就是被驱逐。仿佛移民。
还清楚地记得我刚刚分进学校时,一卷行李和着一身臭汗。气没喘通,总务主任就例行公事地对我说:“小吴。学校没房子给新来的老师住,委屈你一下,你去烟站住!”我才来就要委屈。这委屈的日子还要过多久?心里憋屈,但没敢说出口,因为毛主席说过。干革命工作不能挑肥拣瘦。年轻人不去住。难道叫那些老教师住?但是烟站在哪?刚要问总务主任,却见他已经丢下话走远了。他全不把我当回事。我大声问,他远远地回答,“出校门一直往下400米左右,见到右边的铁大门就是。”
八月了。太阳仍然贼毒。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毒日头似乎要把我晒成干巴才会罢休。孤独的我又是一身臭汗蹒跚到烟站。大门倒是敞开的。不算冷漠。但我心里总感觉怎么像刚进门的新媳妇就给打入冷宫一样的凄落。孤独的我面对着一个空旷的大院,除了一栋陈旧的住宿楼,其他的都是墙面斑驳的仓库,仓库上依稀可以看到背阴的地方有不断向上蔓延的青苔。真可谓“苔痕上阶绿”了。怅然若失地找了一块地方坐下来,却看到那疯长的杂草好像一下就会蔓延到自己脚下,几棵树在火辣的太阳下雕塑般静默着。远离了霓虹闪烁,远离了书声琅琅。再加上青灯古佛,看来在这儿若要修炼成仙的话倒也不失为一个好所在。一阵苦笑。我看到有些房间的门已经不在了。看来盗贼连门都没放过。没有入住感觉这神经就进入了戒备状态。果然我们住进来后光摩托车就丢了三辆。当然这是后话。看来,学校想让这已经废弃的院落来点人气熏染,除了那些野猫,野狗,我是第一个正式入住这荒芜院落的成员。
找到写有我的名字的那扇门。心中算有了着落。推开门,感觉头被什么给缠住了,细看是蛛网,蜘蛛在这扇还没被偷走的门口设置了一个大大的陷阱。想不到今天网到的居然是我这样一个它吃不动的大猎物。一地的老鼠屎,看来老鼠也没少光顾这儿。再看看挡在门下方的木板条,那上面已经被锲而不舍的老鼠啃了一个很大的洞,不知它在这洞里出出进进多少个来回了,这荒芜的房间在前肯定是它休憩的大厅。荒芜的院落,荒芜的房子,加上一个怀着荒芜心情的我。苍凉感就铺天盖地地倾泻了下来。也罢!不要给我晚上在床上抬头还要数星星就行了。推开苍蝇屎密布的窗子,直扑眼帘的却是窗外的一丘荒冢。头稍微伸出去点,甚至还可以看到碑心上的字。是什么老孺人,还是什么老先生之类。至今没心情仔细去看明白,总之一晃时间已经过去了六年。
一扇窗子隔开的仿佛就是阴阳两界,他(她)拥有窗外天地,我拥有窗内人生,各自相安无事。记得入住进来的第二年一朋友来访。夜宿我处,我说叫你一个人睡这,你敢吗?他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那时窗帘还拉着,那夜月色如水,我呼一下把窗帘给拉开了,把他拉到窗子跟前,月色下那荒冢上的草在夜风里不停地摆动着。兀自增添了几分阴森气象。这一看他说,你这家伙明天说给我不行啊?于是那晚上他一直缠着我吹牛,直到我眼皮再也无力抬起。他说了些什么已然记不清楚,但很清楚地记得他第二天眼皮发泡,印堂发暗,我哑然失笑。多大胆的人。居然就被那似乎游荡在外面的魂儿给弄得失了眠。从此我的朋友大多不会在晚上来找我,都戏称晚上来你这一会,保不准带着个青面獠牙的什么精回去。也好,晚上正是我的写作时间,我说。不来的话倒也合适。
之后我搬进了很多的书,睡着看,站着看,走着看,全在斗室之内,接着满脑子的乱想。想到昏昏然。想到不明所以。写下了满纸荒唐言,四处投稿但石沉大海。时至今日写作上已有些许收获,感觉沾了点这地方的“仙气”,还暗自窃笑呢!那时关起门来独自咀嚼痛苦的滋味,慢慢的疗伤之后觉得陋室还是太小。所以紧闭了心门,方觉还是出去到外面呼吸一下空气为好。于是约三五同事在大树浓荫之下杀上几盘军棋,这要不了多少智力的游戏。也倒帮我们打发了不少时间,为一盘棋几个人吵得面红耳赤。甚至为此迷到把煮饭的炒锅也给烧烂了,但过后依然要杀棋,仍然不亦乐乎,初入烟站的乐趣或许就这些吧。跟高雅似乎沾边,但又都是些俗人的玩法。但毕竟是快乐的。
但好景都是难以持久的,不久就闻到外面的恶臭。去查访了一下发现原来是外面有一个酒厂,又喂了许多被酒糟催肥的大猪,这些猪制造垃圾可是一流的。可害苦了我们的鼻子。不过还好!这恶臭是过一段时间才会飘来一回,开始我觉得作为这儿的主人。我们有权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空气问题不可小视,但是交涉几次没人理我。这个时候我就躲回斗室内苦读,要么写点阿猫、阿狗的文章。继续怀揣着它们能变成铅字的愿望,不断地希冀。编织自己梦想的美丽霓裳。你别说真有一些文章见报了。那份欣喜真的让人忘却了猪粪的恶臭。仿佛修炼已臻无色无味之境界。
至此我坚定地把自己视为烟站的主人了,于是后来进驻院落的我似乎都可以把他们当成敌对者,可以发自己的满腹牢骚,可以对他们说我的意见,他们还只得听着。第一拨人是一伙架高压线的,外地人。他们是我入住后的第一批“侵略者”。他们似乎忘却了他们外来者的身份,开始就肆无忌惮的谈笑。南腔北调的声音回荡在我耳边。很不受听,于是我沉着脸去表达我的不快,他们呢,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于是就有一个主管跑过来赶快递给我一支烟,我摆摆手,他把手尴尬地缩了回去。不好意思的笑着说。以后一定不会影响你们了,我们这些工人不知道这些,请你们原谅之类,果然以后清净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漠然地看着他们。觉得自己的空间已经被局部侵犯了,他们不止于碍眼,简直要把我愤怒的火焰点燃了。
第二拨人来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的干预有点乏力了,因为他们是来收烟的,俨然房东一样的高傲。不断进出的骡马和车子,各色人等,把这个烟站弄得像个热闹的集贸市场。不断飘扬的粉尘和烟叶的味道充斥着我脆弱的脑袋,我茫然地看着外面。好像我的壳已经成为外面这个喧嚷世界的殖民地了,我的眼里饱含屈辱的冷光。后来收烟的不断压级终于引发了一场“战争”,那时骡马奔走。烟农们拿着扁担怒视着收烟的。我的心里不知是该快意呢。还是该恼怒。总之这件事弄得我感觉自己像个清末的中国公民。就好像日本和俄国在我的国土上打仗一样,我已经不能保持领土完整,但是我也只是敢站在幕后冷眼看这一切。并且很清楚即使自己站出来了。没人会认我这根“葱”。或许人家还嫌我碍事呢。后来政府出面把争端平息了。但告诫收烟的不管什么等级的烟都要收。那些收烟的迫于压力强忍怒气收了一些垃圾烟。收来后也不拉走,大火一把烧在外面的旷野里。于是整个烟站弥漫着尼古丁和焦油的味道。出门很远感觉那股味道还在追寻着我。几乎窒息的我到外面大口地喘气。在自己的住处我几乎被尼古丁和噪音害死了。却没有向任何地方申诉的权力。更无人说这不公正。那段时间我的神经向着崩溃的边缘滑行,我无心再把脑袋扎在书里了。那些人终于丢下一些烂烟叶走了,人走了,但是气味仍残留着,我愈加感到这个领地的非真实性。
第三拨人是收亚麻的,因为他们看中了我们这儿闲置的仓库,和收烟的差不多一样的忙乱。仍是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纠结和矛盾。诞生着新的噪音。新的烟尘,那些带着锯齿状的亚麻随时追随在我裤脚上。我小心翼翼的让着它们。但是最终我还是被它们包围着,无辜而无奈。照样没人理会我,仿佛我也是外面来的一员。学校也不出面干涉,于是我只有忍耐。我想养一群羊来占据草地的愿望不断地建立起又被毁灭掉,因为草地总是有很多人去践踏。把一块甚至可以做高尔夫球场的草地弄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那些亚麻堆在仓库里后,他们还特别叮嘱我要注意火烛,不然亚麻着火了我似乎脱不了干系。仿佛已经提前告诫过我这个“纵火犯”,我再次感到窝囊和憋屈。看来一切都是虚假的。我也只有住在这里的权力。屋子漏水了。我刚刚想修补下。学校领导就说我只有看守权。没有改造权,于是大雨天我在屋内看小雨嘀哒。心痛得仿佛陈子昂登上幽州台,独怆然而涕下。想哭。但是觉得雨水就够多了。再加上泪水这陈旧的房子怕支撑不了这巨大的哀愁,省了眼泪,心里却梗了一样硬物样的不畅。
再后来就来了烟站原来的主人。他们一来就财大气粗的动动这,动动那,对哪儿不满意就敲下。打下,随自己的意愿,我看到的不再是些所谓的“侵略者”,而是房东,房东对我还算客气,于是我开始变得诚惶诚恐,仿佛这些年来贪了他们很多便宜,捞了很多好处,那位经理对我说,他要把外面我们原先下棋的石桌敲烂。改成花台。我说行,你家的东西嘛!他说你帮我参谋下,我说我不懂。逃开,看,他给我了多大的面子啊!
愚钝至今方悟到:其实进进出出的都是过客,看来只有那些随意改造自己的巢的人才是主人,其他的最终都只得选择离开,我的巢不在这里。我仿佛第一次从巢里走出来。这时我发现阳光太刺目,我有点眩晕了,老窝好像就这样给人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