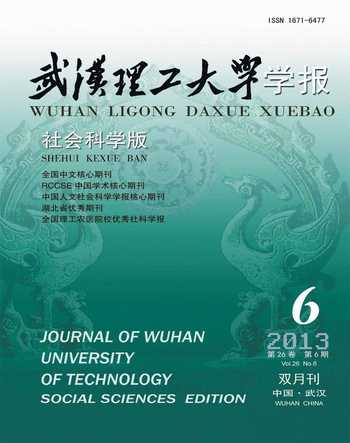论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度”的把握
喻世华
摘要:在《水浒传》中,与苏轼有关的描写只有三处——高俅的发迹史,玉兰陪酒唱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宋朝四绝苏、黄、米、蔡的所指。但三处描写中两处存有诸多错误,一处则有争议。从历史真实的角度分析,三处描写漏洞明显,经不起推敲。然而从文学虚构的角度来看,三处描写却是成功的,至少与作者的美学观念和表达的主题以及塑造的人物形象一致。由此观之,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关系,真实与虚构之间“度”的把握,值得认真探讨。
关键词:《水浒传》;苏轼;历史真实;文学虚构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水浒传》与苏轼有关的描写只有三处。三处描写都是作为故事的背景出现的,初看似乎寻常,深思却让人诧异:三处描写中两处存有诸多错误,一处则有争议。究竟是作者粗心所致(历史戏说),还是有意为之(文学虚构的需要)?笔者认为,实有对其作一番探究的必要。
一、《水浒传》中与苏轼有关的三处描写
在《水浒传》中,涉及到苏轼的三处描写分别如下:
第一处与苏轼有关的描写出现在第二回叙述高俅的发迹史时。闲汉高俅因勾引王员外儿子赌钱,被王员外一纸诉状告发,断了四十脊杖,迭配出界发放,流浪到淮西临淮州;又被闲汉柳世权收留,后因得了赦宥罪犯的机会回到东京;柳世权将高俅荐给东京开药铺的董将士,董将仕又将其转荐给小苏学士:
门吏转报,小苏学士出来见了高俅,看罢来书知道高俅原是帮闲浮浪的人,心下想道:“我这里如何安着得他?不如做个人情,荐他去驸马王晋卿府里,做个亲随。人都唤他做小王都太尉,便喜欢这样的人。”当时回了董将仕书札,留高俅在府里,住了一夜。次日写了一封书呈,使个干人,送高俅去那小王都太尉处。这太尉乃是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驸马。他喜爱风流人物,正用这样的人。一见小苏学士差人驰书送这高俅来,拜见了便喜,随即写回书,收留高俅在府内做个亲随。自此高俅遭际在王都尉府中,出入如同家人一般[1] 17。
在作者笔下,高俅由于品行很差,被人当皮球一样推来送去,直到遭际小王都太尉王晋卿才安身。高俅的发迹非常偶然,王晋卿指派高俅给端王送东西,端王发现高俅踢球水平高,不肯放高俅回府,而更为凑巧的是“未及两个月,哲宗皇帝宴驾,无有太子,文武百官商议,册立端王为天子,立帝号曰徽宗……后来没半年之间,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1]20。
第二处与苏轼有关的描写出现在第三十回的玉兰陪酒唱的词曲上。张团练买通张都监设计陷害武松,中秋之夜,张都监设家宴宴请武松,张都监的养娘玉兰陪酒唱的词曲是苏轼最为著名的曲子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那张都监指着玉兰道: “这里别无外人,只有我心腹之人武都头在此。你可唱个中秋对月时景的曲儿,教我们听则个。”玉兰执着象板,向前各道一个万福,顿开喉咙,唱一只东坡学士中秋《水调歌》。唱道是: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只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高卷珠帘,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万里共蝉娟。”[1]399
第三处与苏轼有关的描写出现在第三十九回和第四十回的关于宋朝四绝苏、黄、米、蔡的定义上。在第三十九回,梁山英雄为救宋江,需要戴宗给江州知府蔡九送一封假信保住宋江的性命:
晁盖愁道:“好却是好,只是没有人会写蔡京笔迹。”吴学究道:“吴用已思量心里了。如今天下盛行四家字体,是苏东坡、黄鲁直、米元章、蔡京四家字体。苏、黄、米、蔡,宋朝‘四绝……”[1]542
在第四十回,因这封假信本是父亲写给儿子的家信却错用了蔡京的名讳图章,以致被无为军通判黄文炳识破。作者通过黄文炳的嘴再次明确苏、黄、米、蔡的蔡为蔡京,黄文炳告诉蔡九道:
“这封书被人瞒过了相公。方今天下盛行苏、黄、米、蔡四家字体,谁不习学得?况兼这个图书,是令尊府恩相做翰林学士时使出来,法帖文字上,多有人曾见。如今升转太师丞相,如何肯把翰林图书使出来?”[1]549
上述三处有关苏轼的描写,都是背景材料,谈不上对苏轼的褒贬,作为苏轼研究者,大可一笑置之,而且小说家言,似也没有较真的必要。但《水浒传》作为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仅仅三处涉及苏轼的描写就出现诸多错误,似又有辨证和分析的必要。
二、对与苏轼有关的三处描写的辨析
《水浒传》与苏轼有关的三处描写,从历史真实的角度看,可以说漏洞百出;而从文学虚构的角度说,作者这样处理又体现了艺术的真实。
从历史角度看,《水浒传》与苏轼有关的三处描写中两处与历史真实存在较大差距,一处存在争议。
第一处叙述高俅发迹史时与苏轼有关的描写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小苏学士究竟指谁?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才识》记载:“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也。”[2]按照王辟之的说法,老苏指苏洵,大苏指苏轼,小苏指苏辙。从小苏学士处置高俅的简单描写看,倒也符合苏辙的为人处世态度——谨小慎微,不与“帮闲浮浪的人”交往。但考诸历史,高俅实乃“东坡先生小史”,将高俅送给王晋卿的实际上是大苏而非小苏,南宋王明清的《挥麈后录》“高俅本东坡小史”条载:“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笔扎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帅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史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3]138王明清的记载很明确,苏轼出帅定州,先是将高俅送给曾布,曾布婉辞才转送给王晋卿的。换句话说,将高俅送给王晋卿的是大苏学士苏轼而非小苏学士苏辙。熟悉宋朝历史和苏轼情况的人都知道,苏轼出帅定州在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九月,当时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政治形势骤变,苏轼已经预感到“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4]。因此,苏轼将跟随自己的小史高俅妥善安置,正是苏轼为人负责的一贯作风。先是“留以予曾文肃”,大致原因有三:一是曾文肃(曾布)是曾巩的弟弟,与苏轼兄弟存有私交;二是曾文肃是新党人物,在即将到来的政治变局中,可能占据有利位置,需要“笔扎颇工”的“小史”;三是可以为高俅提供一个安身之处。在曾文肃“以史令已多辞之”的情况下,苏轼将高俅转送给王晋卿,更是在情理之中。苏轼与王晋卿关系非同一般,过从甚密,根据“乌台诗案”苏轼的交代材料,早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双方就有交往:“熙宁二年,轼在京授差遣,王诜作驸马。后轼去王诜宅,与王诜写作诗赋,并《莲花经》等,本人累经送酒食茶果等与轼。当年内王诜又送弓一张、箭十只、包指十个与轼。”[5]这种交往历经“乌台诗案”的考验,一直延续到元祐时期①。
二是驸马王晋卿身份出现明显错误。考诸史实,《宋史·王全斌传》附其曾孙《王凯传》载:“子缄,缄子诜,字晋卿,能诗善画,尚蜀国长公主,官至留后。”[6]8926而据《宋史·公主传》记载,英宗四女,蜀国长公主为英宗第二女,“魏国大长公主,帝第二女,母曰宣仁圣烈皇后。嘉祐八年,封宝安公主。神宗立,进舒国长公主,改蜀国,下嫁左卫将军王诜”[6]8779。王晋卿所尚蜀国长公主是神宗皇帝一母同胞的亲妹妹,是哲宗皇帝、徽宗皇帝的亲姑姑。《水浒传》作者将王晋卿辈分降了一辈,认为王晋卿“乃是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驸马”,明显把辈分弄错了。
三是关于高俅的描写失真。《水浒传》描写的高俅劣迹斑斑,是将林冲等好汉逼上梁山的罪魁祸首,是《水浒传》里最主要的反派角色,但王明清《挥麈后录》“高俅本东坡小史”条载:“然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问恤甚勤。靖康初,佑陵南下,俅从驾至临淮,以疾为解,辞归京师。当时侍行如童贯、梁师成辈皆坐诛,而俅独死于牖下。(胡元功云)”[3]138从王明清的记载看,历史上真实的高俅并不是一个恶贯满盈的坏蛋:一是高俅对苏轼颇有情义。在徽宗统治的绝大部分时期,苏轼其人其文属于禁区,政治上被打入另册,诗文处于被取缔状态。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七月,蔡京拜相,极力主张继续追贬元祐党人,查禁元祐学术:“蔡京籍文臣执政官文彦博等二十二人,待制以上官苏轼等三十五人,馀官秦观等四十八人,内臣张士良等八人,武臣王献可等四人,等其罪状,谓之奸党,请御书刻石于端礼门。”[7]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和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朝廷又两度重申除毁苏轼诸人文集的禁令。在这样的政治高压形势下,曾与苏轼有过交往的人士遇苏氏子弟避之惟恐不及,邵博《闻见后录》载:“晁以道言,当东坡盛时,李公麟至,为画家庙像。后东坡南迁,公麟在京师遇苏氏两院子弟于途,以扇障面不一揖,其薄如此。故以道鄙之,尽弃平日所有公麟之画于人。”[8]高俅官至开府仪同三司,在恩宠无比之时,仍然能够“不忘苏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问恤甚勤”,这比落井下石的文人似乎还高一等。二是高俅并非当时臭名昭著的“六贼”之一②,并非蔡京、童贯似的千夫所指,与蔡京、童贯、梁师成的结局也不同。蔡京被写入《奸臣传》,童贯、梁师成遭到诛杀,而高俅算是自然寿终:靖康初年,高俅因为疾病,随驾至临淮时辞职回到京师汴梁,不久病死于家里——“俅独死于牖下”。
第二处描写玉兰唱东坡学士中秋《水调歌》同样出现了三处错误:一是将“又恐琼楼玉宇”改成了“只恐琼楼玉宇”,二是将“转朱阁”改成了“高卷珠帘”, 三是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改成了“但愿人长久,万里共蝉娟”[9] 。从艺术角度看,三处改写与原作有霄壤之别。
第三处描写关于宋朝书法“四绝”的所指存在争议。宋朝书法“四绝”, 又称“宋四家”,一般指苏、黄、米、蔡。 苏、黄、米指苏东坡、黄鲁直、米元章不存在争议,而蔡,按《辞海》的解释,指蔡襄[10]而非蔡京。由于声名狼藉,蔡京一般被排除于“宋四家”或宋朝书法“四绝”之外。第三处描写将蔡指为蔡京,与苏东坡、黄鲁直、米元章并列,与通常流行的看法有别,是存在争议的。
综上所述,不能说《水浒传》三处与苏轼有关的文字一点根据都没有,但大都张冠李戴,虽然有历史的影子,但都严重变形。
从文学的角度分析,《水浒传》描写苏轼的文字存在明显的历史错误,那究竟是因作者粗心,还是其有意为之呢?笔者认为,虽不能完全排除作者因粗疏造成的错误,但更可能与作者的美学观念、表达的主题以及塑造的人物形象有关,也就是说,极有可能是作者对历史的有意改写。
首先,可能与作者的美学观念有关。人物类型化是中国传统小说塑造人物所遵循的基本美学原则——好人与坏人泾渭分明,好人从小都好,从头到脚都好,而坏人从小都坏,从头到脚都坏。从《水浒传》作者秉持的美学观念来看,高俅发迹史中存在的问题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作为贯穿水浒全书最重要的反派角色,高俅一出场就被完全定型:出身不好——“浮浪破落户子弟”;不务正业——“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球”“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品行不好——“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颇能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有犯罪前科——勾引王员外儿子赌钱“断了四十脊杖”;人缘很差——“东京城里人民,不许容他在家宿食”,收留他的人是“开赌坊的闲汉柳大郎”这样的社会闲杂人员。一般人对高俅是避而远之的,故董将仕将高俅推给小苏学士,小苏学士又将高俅推给小王都太尉。董将仕、小苏学士是不喜欢高俅这类“帮闲的破落户”的。因此,历史上是大苏(苏轼)还是小苏(苏辙)将高俅送给小王都太尉并不重要(小苏或者大苏在小说中的作用实际上与董将仕相同,只是为了反衬高俅为人的不堪;作者用小苏代替大苏,更有利于对高俅形象的塑造,也更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值得我们注意的倒是对小王都太尉辈分的改动。王晋卿与苏轼同年,生于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如果王明清记叙“东坡自翰苑出帅中山”将高俅送给王晋卿属实,时间当在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王晋卿是年57岁。接近花甲之年的王晋卿,即使如小苏学士认为的“喜欢这样的人(帮闲浮浪的人)”,与高俅、小舅端王(后来的宋徽宗)在一起厮混,辈分上不合适,年龄上差距过大,作为玩伴多少显得牵强,反不如“是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驸马”更为合情合理。
总之,不管作者是有意改动历史还是无意出现的知识错误——小苏大苏身份的混淆、高俅身份上的错误以及小王都太尉辈分上的错误——这些都更符合中国传统小说塑造人物所遵循的基本美学原则。换句话说,小苏大苏身份的混淆、高俅身份上的错误以及小王都太尉辈分上的错误,是小说塑造人物时“必须的错误”。《水浒传》中的高俅必然也必须是彻头彻尾的邪恶——这是作者塑造人物的先决条件,也是作者美学观念导致的必然结果。
其次,可能与作者要表达的主题有关。《水浒传》的主题,简单来说是逼上梁山、官逼民反,表面上看主角是梁山108位好汉,但仔细分析,高俅才是撬动梁山好汉造反的原动力,才是《水浒传》暗中真正的主角。金圣叹对此有精到的见解:“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乱自下生,不可训也,作者之所必避也;乱自上作,不可长也,作者之所深惧也。一部大书七十回,而开书先写高俅,有以也。”[11]43对于高俅的发迹,金圣叹进而指出:“小苏学士,小王中尉,小舅端王。嗟乎!既已群小相聚矣,高俅即欲不得志,亦岂得哉!”[11]46金圣叹的看法既精到但也存在片面性。小王都太尉,特别是小舅端王(徽宗)与高俅的发迹的确有关系,金圣叹用“群小”指代不无道理,但将小苏学士包含在“群小”当中就明显牵强。小苏学士与高俅不同道,甚至与小王都太尉不同道:“小苏学士,出来见了高俅,看罢来书,知道高俅原是帮闲浮浪的人,心下想道:‘我这里如何安着得他,不如做个人情,荐他去驸马王晋卿府里做个亲随。人都唤他做小王都太尉,便喜欢这样的人。”金圣叹见到“小苏学士,小王中尉,小舅端王”中同样有“小”字就断定是“群小相聚”使高俅发迹,多少有脱离文本望文生义、主观臆断的嫌疑。另外,还需指出的是,金圣叹腰斩水浒,其实有削弱他自己所说的“乱由上作”的主题之嫌。100回本以高俅始并以高俅终,更能突出“乱由上作”的主题。鲁迅对金圣叹寻求伏线及腰斩水浒的做法曾有尖锐的批评:“他抬起小说传奇来,和《左传》《杜诗》并列,实不过拾了袁宏道辈的唾余;而且经他一批,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这余荫,便使有一批人,堕入了对于《红楼梦》之类,总在寻求伏线,挑剔破绽的泥塘”。“自称得到古本,乱改《西厢》字句的案子且不说罢,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12]。
再次,可能与作者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有关。如果说第一处出现的诸多错误与塑造高俅形象有关,那么第二处、第三处出现的错误或者争议同样与塑造人物形象有关。玉兰唱的“东坡学士中秋《水调歌》”,即《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是一首稍有文化的中国人都熟悉的词。其中出现的三处错误,当然可以理解为作者学识的粗疏,但其实存在另外的可能:玉兰作为下层歌女,文化层次不高,其主人张都监也非文才之士,作者将著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让玉兰唱错,更符合下层歌女的身份,也隐含了对张都监等人附庸风雅的讽刺。至于将蔡京与苏东坡、黄鲁直、米元章并列为“宋朝‘四绝”,主要是为了突出蔡九的身分特殊,是为了塑造人物形象和情节发展需要作出的特殊界定。因此,不管作者是有意还是无意,《水浒传》有关苏轼的三处错误或者争议,对于塑造人物形象、展示人物性格均可以看作是必须的、有意的错误。
综上所述,《水浒传》三处与苏轼有关的描写,从历史真实的角度上说可能经不起推敲,但从文学虚构描写的艺术真实的角度上看却是非常成功的,至少与作者的美学观念、表达的主题及塑造的人物形象一致。
三、《水浒传》叙事美学的启示
从叙事美学角度分析,《水浒传》中与苏轼有关的三处描写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关系问题,二是人物描写的类型化问题。这两个问题对文学创作都很重要。
首先,文学创作中应该如何处理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关系。这是评判《水浒传》中三处与苏轼有关的叙写文字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历史要求真实,文学崇尚虚构,如何处理历史与文学、真实与虚构的关系,是历史小说不能回避的问题。《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都面临这个问题,鲁迅先生在评论《三国演义》处理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关系时有一段著名的话:“容易招人误会。因为中间所叙的事情,有七分是实的,三分是虚的;惟其实多虚少,所以人们或不免并信虚者为真。如王渔洋是有名的诗人,也是学者,而他有一个诗的题目叫‘落凤坡吊庞士元,这‘落凤坡只有《三国演义》上有,别无根据,王渔洋却被它闹昏了。” [13]291《三国演义》文字的七实三虚的确容易造成误会,但《水浒传》中与苏轼有关的三处描写严格说并不存在这个问题,从叙事美学角度看,由于与作者的美学观念、表达的主题及塑造的人物形象一致,《水浒传》中与苏轼有关的三处描写不但不存在问题,而且是相当成功的。除非是专门研究苏轼的专业人士,否则是很难发现其虚构与真实的细微差别的。
不但古典小说面临着处理历史与文学、真实与虚构的关系问题,现代小说如《李自成》《康熙大帝》《雍正王朝》同样面临这个问题,特别是现当代小说,由于与历史真实存在不小的距离,常常遭到人们的质疑与非议。劳伦斯·勒纳认为,“对于历史与虚构之间的关系所作的最好描述,是柯林武德作出的……‘历史学家的图画意在真实”[14]。而文学就其本质来说,是虚构的叙事艺术。在《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的叙述和描写中,尽管与历史真实多有不合,但一直雄居中国古典文学经典之列,关键在于人们把《水浒传》《三国演义》当小说看,而不是当历史教科书看。人们对现代小说如《李自成》《康熙大帝》《雍正王朝》质疑或者非议,其实与今天的时代思潮有关:“在一个务实的、追求‘真实而非崇尚想象力的时代”,“叙事尤其是虚构叙事正在迅速地没落。这是一个论证和论争的时代,而不是叙事或讲故事的时代……因为虚构叙事既不能提供论证也不能提供信息”[15]。直白地说,今天的人们对小说虚构已经缺乏审美的从容,在小说与历史、虚构与真实之间,更看重后者。这当然不是正确解读小说的方法。正确的解读方法是回到文本,这也是胡塞尔现象学运用于文学作品的方法:“由于胡塞尔排除‘真正的客体,所以文学作品真实的历史背景、它的作者、产生的条件和读者都不受重视;现象学批评完全重视的是一种完全‘于意识之内的对文本的理解,丝毫不受外界事物的影响。”[16]这为我们解决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关系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回到文本。
其次是人物描写类型化问题。《水浒传》与苏轼有关的三处改写,都与塑造人物——高俅、张都监、蔡九的形象有关。类型化是中国古典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基本方法,鲁迅先生对此曾有精辟论述,在评论《三国演义》类型化人物时曾说:“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13]291《水浒传》里的高俅也是这样一个“一点好处都没有”的类型化人物。这种“‘类型化人物,有时又被称做‘漫画式人物……是作者围绕着一个单独概念或者素质创造出来的”[17]232。E.M.福斯特又将其称为“扁形人物”“体液性人物”,并认为“真正的扁形人物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17]232。高俅就是“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的人物,《水浒传》里的其他人物也是“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的人物,比如“高俅是坏蛋”,“宋江是及时雨”,“吴用是智多星”,等等。这种“扁形人物”当然有不少优点:“不管他们在小说里的什么地方出现,都能让读者一眼就认出来——读者用的是感情之眼”[17]232,“读者容易在事后把他们回想起来”[17]232。但这种“扁形人物”的缺陷也是明显的,鲁迅在肯定《红楼梦》时曾委婉地批评了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类型化:“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13]306如果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描写高俅,高俅的形象当更为丰满、复杂、生动,有可能塑造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给人以惊奇之感”[17]237“变化莫测,如同生活本身一样难以意料”的“圆形人物”[17]238。《水浒传》作者受制于自己的美学观念,受制于主题的表达,给我们塑造了一个扁平型、类型化的高俅形象,这不能不是一种遗憾。当然,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苛求古人。
综上所述,《水浒传》与苏轼有关的三处描写虽然都存在历史错误或者争议,虽然从中寻找其历史上的瑕疵是容易的,但文学不是历史,从文学角度看,三处错误或者争议与作者的美学观念、表达的主题以及塑造的人物形象一致。因而,可以认为是作者有意为之的。总之,文学与历史、虚构与真实之间存在相当复杂的关系,类型化描写也自有其长处和短处,关键在于“度”的把握。这是《水浒传》中与苏轼有关的三处描写留给我们最重要、最深刻的启示。
注释:
① 苏轼与王晋卿的关系,张荣国在《王诜与苏轼之交游》曾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参见《 荣宝斋》2010第5期、第9期)。在《苏轼诗集》中保留了数量不少的诗文往来,根据笔者统计,仅苏轼写给王晋卿的和诗就有30首(参见王文诰、冯应榴编辑的《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可见二者关系非同一般。
② “六贼”源自陈东在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的上书:“太学生陈东等伏阙上书,乞诛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六贼,大略言:‘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内,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从而结怨于二国,败祖宗之盟,失中国之信,创开边隙,使天下危如丝发。此六贼异名同罪,伏愿陛下擒此六贼,肆诸市朝,传首四方,以谢天下。”(参见毕沅《续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 2496-2497页)可知高俅不在“六贼”之列。
[参考文献]
[1]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百回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2]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M].隋同文,点校.青州:青州古籍文献编委会,2008:45.
[3] 王明清.挥麈后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4] 王文诰,冯应榴.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1991.
[5] 颜中其.苏东坡佚事汇编[M].长沙:岳麓书社,1984: 285.
[6] 脱脱.宋史 [M].北京:中华书局,1977.
[7] 毕 沅.续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7:2244-2245.
[8] 邵 博.邵氏闻见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215.
[9] 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173-174.
[10]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艺术分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385.
[11] 金圣叹. 金圣叹全集一: 水浒传[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12] 鲁 迅.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27.
[13] 鲁 迅. 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14] 勒纳.历史与虚构[M]∥阎 嘉.文学理论精粹读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99.
[15] 耿占春.叙事美学[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1.
[16] 伊格尔顿. 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57.
[17] 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童庆炳,赵 勇.文学理论新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文 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