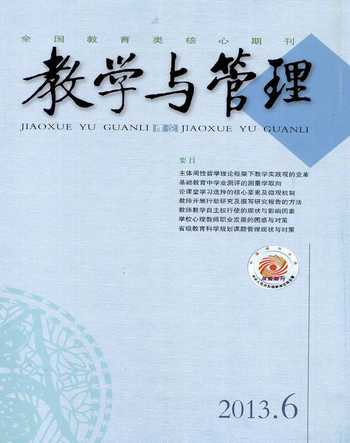略论教育知识的归属
万正维
“教育知识”在当代知识论的学术语境下灌注了理论内涵。然而,概念内涵的更新不等于观念的创新,“教育知识”若要与“教育理论”等术语相区分,避免“新瓶老酒”之诟病,宜先明确其自身独特的性质与定义。探讨“性质”与“定义”应以“属概念”的界定为前提,由此,教育知识的“归属”便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理论课题。本文拟立足于知识类型的划分,从“划归依据”、“归属特点”与“理论启示”等初探教育知识的“归属”。
一、知识及其类型
何谓“知识”。这或许是历来最难解的哲学问题之一。难处不仅在于解答本身有多种角度,欲得公允的观点殊为不易;更难者恐还在“知识”概念的弥散性,指称内容充溢于各理智领域,难以划出确切的认知界限。本文对知识的界定采用传统“三要素”理论,即仅当(1)命题P是真的,(2)S相信P,(3)S的信念P恰当地得到辩护(justification),三个条件都得到满足时才能说“S具有关于P的知识”[1]。为更加明确“知识”的涵义,特将其与“理论”概念相比较。广义上“知识”包括“理论”,但知识论视野中的“知识”有别于“理论”。一方面,知识含有“信念”成分,某命题若不为人相信则绝无可能成为知识,知识具有“亲主体”(pro-subject)的性质;理论一旦产生则竭力凸显其“中立性”,含有“去主体”(de-subject)意蕴,成立与否皆力避主体信念的影响。另一方面,“辩护”是知识的构成要素之一,没有获得辩护的命题不能称为“知识”;与知识的辩护相对的是理论的证明,但证明并非理论本身的构成要素,如常有所谓“有待证明的理论”。由此,知识和理论不容混淆,否则将失去其独有的学术视角。
知识的辩护类型。根据“三要素”理论,“辩护”是知识生成的关键,辩护类型可作为划分知识类型之依据。已有研究主要从形式(即辩护方式)上将辩护类型分为“内在主义”、“外在主义”与“语境主义”等。本文重在从实质(即辩护证据)上分析辩护类型。知识的辩护证据大致有“事实”、“价值”以及“意念”三类,相应的辩护类型即为“事实辩护”、“价值辩护”与“意念辩护”。“事实”与“价值”解读者甚众,其涵义明晰易晓,“意念”则须稍作说明。所谓“意念”,简而言之,是一种心理力量,含有认识和逻辑成分[2],是研究主体对人类主体的自觉归附,以类主体的精神力量专注于求解某一知识难题的特殊意识。我国古人很早就开始关注“意念”,例如,“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3],论者已认识到,意念的对象并非简单的事物形象,而是更高级的某种存在;又如,王弼的“言意论”认识到,意念是“圣人”制定的,可根据意念所表现的内容探寻圣人的本意[4]。此处若把“圣人”理解为人的“类主体”而非“个体”主体,则无疑是十分深刻而独到的见解。
知识类型与辩护类型密切相关。依据上述划分,可将知识分为“事实知识”、“价值知识”与“意念知识”。“事实知识”指,知识辩护的最终证据是“事实”,命题的指称对象与“事实”一致;“价值知识”指,知识辩护的最终证据“价值”,命题涵义以一般价值取向为支撑;“意念知识”指,知识辩护的最终证据是知识主体的意念,这种意念不是个人的意念,而是知识主体向类主体的自觉归附而感悟出的坚定意念。综观三类知识可得,其一,知识的辩护证据皆非“个体”的主观臆想。“事实”证据的非主观性自是无庸赘言,“价值”与“意念”作为辩护证据,是知识主体以人类主体的精神力量对知识的深度确证,并非个体的价值偏好与意想信念。其二,比较“事实”、“价值”与“意念”三个范畴,事实属于客体范畴,“价值”属于主客结合范畴,意念属于主体范畴,三者包含了所有辩护的证据类型。从逻辑上看,上述知识类型的划分是周延的。其三,知识类型的判断依据是“知识辩护的最终证据”。“最终证据”对应的知识体系中的命题可称为“基本命题”,基本命题是知识体系中的“阿基米德点”,其辩护证据的类型是决定知识归属的重要参照。
二、教育知识的划归依据
据上述,分析某种知识的辩护与类型,须找出支撑其体系的基本命题,基本命题的辩护证据是判断知识归属的重要依据。那么,教育知识体系中是否存在“基本命题”呢?本文认为,教育知识体系中有两类基本命题,一是本体性命题,二是目的性命题。本体性命题,即关于“教育是什么”的命题。各种教育知识体系都预设了对“教育是什么”的回答与辩护;回答与辩护既标明知识主体的教育本体立场,又确保和支撑整个知识体系的一致性与稳定性。作为其他命题的辩护基础,本体性命题常以隐性的方式渗透于整个教育知识体系。分析隐性的本体性命题,需要对教育知识体系作整体考察,才能归纳和概括出表达“教育本体”思想的命题。目的性命题,即关于“教育为了什么”的命题,引导教育知识体系的发展方向,是显在而“活跃”的要素,在教育知识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历史上各种教育学说都是从教育目的的假设中推衍出来的建议体系;目的性命题是教育知识的一大逻辑前提,其不同用法和含义决定着教育知识的不同性质[5]。
本体性命题的辩护证据。对“教育是什么”的辩护,从根本上说不能以“事实”为证据。现实的教育错综复杂,“教育是什么”基本上是个无法求解的知识难题[6],更是难以用确定的事实或价值证据对其辩护。本体性命题的辩护是形而上的论证过程,辩护证据是人的类主体“意念”。本体性命题的辩护需要知识主体自觉感悟、移入人的类主体意念,借助类主体意念深刻反省辩护命题,最终形成坚定的个体意念。不同知识主体对同一本体性命题的辩护程度不同,这缘于个体对类主体意念的感悟能力不同,个体的“感悟能力”集中反映了其自身的人文素养,决定其对人类主体的归附程度。一般而言,人文素养越高对类主体意念的反省和认识越深刻,然而深刻的感悟极有可能一时间得不到其他知识主体的认同,如赫尔巴特曾为此悲叹道:“我那可怜的教育学没能喊出它的声音来。”[7]但随着人类素养的普遍提升,最终必然获得更多认同,也正如随后赫尔巴特思想影响的迅速扩大。
本体性命题辩护的历史考察。拉开历史的帷幕不难发现,一部教育知识史就是一部知识主体感悟类主体意念,并以此辩护教育基本命题的历史。大体说来,人们对本体性命题的回答和辩护形成有“工具论”—“适应论”—“生活论”—“教化论”等知识体系。“工具论”贯穿古代教育思想。以柏拉图教育思想为例,柏氏以教育可将各类素质的人“筛选”出来过正义生活为意念,以此辩护教育是建构“理想国”不可缺少的工具,提出“工具论”的教育知识体系。此后,卢梭以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崇拜”思想反对“工具论”,他以“出自造物者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8]为意念,以此辩护教育就是适应人发展,提出“适应论”的教育知识体系。杜威从另一角度批判了“工具论”,他以“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教育即生长”为意念,辩护教育本身就是生活而非生活的预备,提出了“生活论”教育知识体系。近来我国论者提出,教育是一种促进人精神发展的而避免规训的教化[9],论者以人的“自由”本质为意念,辩护教育是一种自由的实践(即教化)而不是束缚自由的实践(即规训),提出“教化论”的教育知识体系。综上,知识主体感悟类主体所获的意念,既为本体性命题提供坚定信念,又作为主体性证据助其辩护,不断催生新的知识体系,是教育知识演进的内在动力。
目的性命题的辩护证据。目的性命题的辩护以社会一般价值为证据,体现了知识主体对社会一般价值的认同。在辩护中,知识主体须自觉感受社会价值取向,深沉追问“教育何为”?并将所得化为教育自身的追求。本体性命题是知识主体内向反思教育本体而获得辩护,目的性命题则是知识主体外向导入社会价值而获得辩护。教育活动总是以具体的人为对象,社会价值通常在教育活动中凝结为人的理想模型,因此关于人的理想模型自然成为目的性命题的核心要素。据有论者研究,教育思想史上有关人的理想模型大致有,“宗教人”—“自然人”—“理性人”—“社会人”等[10]。各自的辩护逻辑大致如下,“宗教人”(Homo Riligiosus),以热爱、赞美、信仰和服从上帝的价值取向为证据,辩护教育就是为完善人的神性;“自然人”(Homo Naturalis),以遵循和尊重自然的价值取向为证据,辩护教育应帮助人发展自身固有的内在倾向;“理性人”(Homo Sapiens),以崇尚理性生活的价值取向为证据,辩护教育应该培养有理性的人;“社会人”(Homo Sociologicus),以社会生存和发展的价值取向为证据,辩护教育应促使人的社会化。
三、教育知识的归属及启示
教育知识的类型。知识类型的划归须依循其基本命题的辩护证据,此论若属不谬则可得出下述结论:教育知识体系包含“本体性命题”与“目的性命题”两类基本命题,其辩护证据分属“意念”与“价值”,由此,教育知识当横跨价值知识与意念知识两大类型,具有“两栖性”特点。此特点表明,不能将教育知识仅作为价值知识而忽视了沉思与追寻类主体的意念,也不能将教育知识只作为意念知识而忽视了感悟与遵循社会一般价值取向。由于意念知识与价值知识的辩护遵从不同的理路,各自拥有不同类型的辩护证据,故教育知识既相当丰富和复杂,又充斥着各种争论和“迷惘”。不少争论甚至伴随着教育知识的始终,例如,教育知识的科学化问题,教育知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教育的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问题等等。不清楚教育知识的归属特点或许正是许多争论“山重水复疑无路”之症结,利用教育知识归属理论或能为解决理论纷争提供新的思路。限于篇幅,现以“教育知识的科学化问题”与“教育知识与教育实践的关系问题”为例粗作分析。
“教育知识科学化”既应放在整个知识史中反思,又应结合知识的辩护理论分析。据福科(MichelFoucault)研究,“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11],知识演变是各种权力争斗的痕迹。在知识史上,意念知识,如远古神话知识与古代宗教知识,因其是统治阶级解释君权的理论根据,最先被认可为人类知识。随着市民社会发展成熟,社会本身需要以正义、公平等一般社会价值来维护,市民阶级也需要以世俗价值体系反抗神权。以社会一般价值为辩护证据的价值知识开始获得统治阶级承认。工业革命后,追求物质利益的资产阶级居统治地位,自然科学因能助其攫取物质利益而被宣称为“知识”,不符自然科学辩护特征者被贬为“非知识”。在事实知识主导知识界的背景下,教育知识为辩护自己的“知识身份”便努力改变辩护方式,取向事实知识的辩护路径。然而,吊诡的是,当知识主体改以“事实”作为教育知识的辩护证据,教育知识却失去了“知识”的身份。甚至有人称道,“理论(知识)”对于教育来说只是一个“尊称”[12]。可见,“教育知识科学化”并不是出于深刻认识教育知识的辩护性质与类型归属的结果,实乃教育知识在知识“场域”中的迷梦。若以上述归属理论观之,教育知识属于意念知识和价值知识,“事实”并不能为其提供最终辩护,其基本命题的辩护证据属于“价值”与“意念”。因此,只有“价值”与“意念”才能为教育知识筑就坚实的基础,建成辉煌的知识体系的大厦。
教育知识与实践的关系通常有两种表述,一种常见表述为:“教育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结合”以一定程度的“符合”为前提,教育知识与实践相“符合”意味着,实践活动直接为教育知识提供辩护,教育知识自动发挥对教育实践的影响。然而据前文所述,能为教育知识提供最终辩护的不是客体性证据,而是非客体性证据的“价值”与“意念”,而且知识具有“亲主体”特性,教育知识只有以主体信念(包括知识和实践主体)为“中介”才能影响实践活动。因此,上述表述显然是“去主体”的“理论”思维的认识结果,而非从“知识”角度出发得出的研究结论,其中“教育知识”只是“教育理论”的“替身”,整个表述不过是“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翻版而已。另一常见表述为:“教育知识指导实践。”判断这一常识性表述宜先明确,上述三类知识与实践的关系各不相同,处理知识与实践的关系时,需要区别对待而不能相互僭越对知识的期望。事实知识以客观事实为辩护证据,客观事实具有较强的稳定性,由它辩护而成的事实知识可以“指导”实践主体对其余同类事实的认识和改造。价值知识以社会价值为辩护证据,社会价值的可变性使此类知识不具有确定性,它只能通过“引导”教育实践主体的价值追求来影响实践。意念知识以知识主体感悟的类主体意念为辩护依据,它可“启发”实践主体感悟类主体意念,助其祛除实践主体的“洞穴假相”,使其以类主体的气度从事教育实践。教育知识属于价值知识与意念知识,它只能“引导”教育实践主体的价值追求、“启发”实践主体积极感悟类主体意念,“间接”地影响教育实践。由是观之,“教育知识指导实践”以事实知识作用实践的方式类推价值知识和意念知识,是对教育知识与实践关系的又一误解。
参考文献
[1] 徐向东.怀疑论、知识与辩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 金丹元.传统艺术思维与意念.文艺理论研究,1999(6).
[3] 庄子·秋水.王岩峻,吉云,译注.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
[4] 任继愈.中国哲学史(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5] 瞿葆奎,等.教育基本理论之研究(1978~1995).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
[6] 顾明远.对教育定义的思考.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1).
[7] [美] S·E·佛罗斯特.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吴元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
[8] [法]卢梭.爱弥儿.李平沤,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9] 金生鈜.规训与教化.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10] 石中英.重塑教育知识中人的形象.教育研究,2002(6).
[11] [法]M·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2] [英]奥康纳.教育理论是什么.瞿葆奎,译.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 关燕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