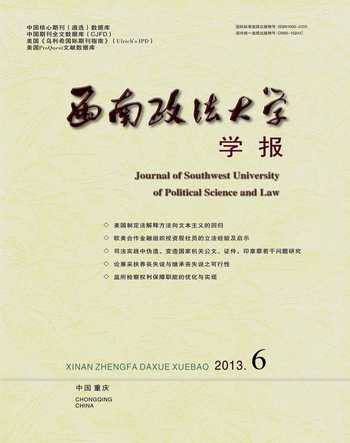美国制定法解释方法向文本主义的回归
摘要:作为美国制定法解释方法的文本主义经历了平白意义规则和新文本主义两个发展阶段。以斯卡利亚为代表的新文本主义对在制定法解释领域长期占据正统地位的意图主义解释方法进行了批判,并对早期平白意义规则进行了扬弃,将文本重新置于制定法解释的中心位置,强调制定法语词的通常、自然与客观意义,并认为文本通常意义的确定无需借助于立法者意图或立法史等文本外材料,而只须根据“普通说英语者标准”,运用词典、语法、解释准则等语言学方面的工具并考虑制定法文本的语境、结构与整体等语义性背景即可确定。
关键词:平白意义规则;意图主义;新文本主义;通常意义
中图分类号:DF07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3.06.01
文本主义(textualism)一词,最早是用来对清教神学进行批判的一个术语。1952年,文本主义一词才首次出现在美国的法律文献中,当时该词具有明显的贬义色彩,意指固守文本的僵化保守的态度。在“扬斯顿钢铁公司总统许可权案”中,法官罗伯特o杰克逊(Robert Jackson)在附随意见中写道,“列举的权力应有伸缩的空间以支持那些看起来合理的,切合实际的蕴含,而不应有教条的文本主义所要求的僵硬性。”(参见: Yongstown Sheet & Tube Co. v. Sawyer, 343 U. S. 579, 640 (1952).) 以后文本主义一词逐渐被用来指称与意图主义(或目的主义)在美国,制定法解释中的目的常指某一制定法在总体上意欲实现的目标,而意图则更多指立法者对具体问题意欲如何处理。对目的和意图及作为制定法解释方法的目的主义和意图主义之间的关系,理论上存有争议,几种代表性的观点是:第一,认为意图主义与目的主义可以等同和互换;第二,认为意图主义和目的主义是两种相互区别的制定法解释方法;第三,认为目的主义可以被包含在意图主义之中。此外,还有很多学者虽然承认意图和目的之间的区别,但在行文时仍经常用意图一词来概括指称一般目的和具体意图。本文在写作的过程中未将目的主义与意图主义再作严格的区分。 相对应的一种法律解释方法。作为制定法解释方法的文本主义经历了早期的平白意义规则和后来的“新文本主义”两个发展阶段,其中每一个阶段都与意图主义解释方法纠缠在一起。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前,文本主义与意图主义一直处于彼此竞争的状态,二十年代以后,意图主义逐渐胜出,并在五十年代前后成为美国学界关于制定法解释的正统理论。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卡利亚和联邦法院法官伊斯特布鲁克等人在对意图主义解释进路进行激烈批判,并在对早期平白意义规则进行扬弃的基础上,力倡了一种“新文本主义”的制定法解释方法 以斯卡利亚为代表的新文本主义既可指称宪法解释的方法,可指称制定法解释的方法,虽然这二者间存在极大关联,但也有着一些明显的差异,例如斯卡利亚认为,对于宪法解释,背景性材料无所不包。但在对制定法进行解释时,背景性材料却有着严格的限制。本文限于讨论作为制定法解释方法的新文本主义。(参见:Antonin Scalia. A Matter of Interpretation: Federal Courts and the Law[M]. Princeton Unive Press,1997:37.),重新强调法律文本在解释中的压倒性地位并摒弃从立法史等文本外材料辨明立法者意图进而偏离乃至违背文本通常意义的做法,不仅在学界激起了广泛的讨论,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平白意义规则的衰落与意图主义的兴起平白意义规则是文本主义的早期表现形式,该规则可以追溯至英国法中的“字面规则”和“黄金规则”。在制定法解释的过程中,英国法院基于对自身在宪政结构中地位和角色的认知,一般倾向于恪守文本字面意义的严格主义解释方法,拒绝在解释过程中对制定法目的、意图及文本背后掩藏的经济与社会政策进行探究。在十九世纪后期,这种平白意义的文本主义解释方法已经在美国法中出现,并与形式主义法律推理结合在一起,博得了当时绝大多数法院的支持。1917年发生的“凯米内蒂诉美国”案(Caminetti v. United States)是平白意义规则在美国法院得以适用的一个重要案件。在该案中,法院较为全面的陈述了平白意义规则的内容,认为,“在那些语言清晰,只允许一种意义存在的地方,解释的任务无从产生”,“当语词的意义毋庸质疑,他们必须被当成是立法者意图的最终表达,不允许考虑任何文本外的材料来对之进行损益……语言是平白的,不会导致荒谬或完全不切实际的后果,它就是最终的立法者意图的唯一证据”。进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随着法律现实主义的狂飚猛进,工具主义的法律推理日益盛行,平白意义规则的影响不断萎缩。1940年的“合众国诉货运联合会”案(United States v. American Trucking Assns)被认为是对平白意义规则进行了“致命的打击”,此后,平白意义规则虽然仍间或被提及,但联邦最高法院却再不曾对之完全倚重。到二十世纪七十代末,平白意义规则已完全被“搁置一旁”了[1]。
平白意义规则的要点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认为法官在解释之初就能够区分平白的语词与模糊的语词;第二,在语词意义平白之时,拒绝使用文本外的任何材料来校正或调整文本的意义;第三,不承认在平白的文本之外还存在一个独立的立法者意图或目的,即把文本当成立法者意图的唯一证据;第四,只有当语言的平白意义会导致荒谬的结果时,平白意义规则才允许例外。平白意义规则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批评者的意见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平白意义规则以语词平白与模糊的二分为前提,但对如何实现此种界分却语焉不详。在平白意义规则的支持者看来,“平白意义是初次阅读时最可能跃入脑海的意义”,但这种判断的主观色彩显然过于强烈因而在实践中无法把握。“平白意义本身就不平白”是其始终面临的一个令人尴尬的悖论,而联邦最高法院也曾一度认为,没有确定无误的检测方法来识别和辨认平白或清晰的语言;第二,语言与背景紧密勾连,语词的意义来自于使用它的语言共同体所共享的传统、习惯及其它背景性知识,在去背景化的状态下,语言并不存在清楚唯一的意义,背景知识揭示出那些看上去完全清晰的语言在事实上却是晦暗不明的。因此,法律文本只有被安置于其制定的背景中时,其意义方能被恰当地释放;第三,平白意义规则承认荒谬结果的例外,但如果不旁观制定法语言之外的因素,又如何能确定是否有荒谬的结果发生呢?因此,法官弗兰德利在评论该规则时曾说,平白意义规则是反逻辑的,因为平白意义规则切断了获取能证明意义并不平白的那些素材的通道[2]。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刘翀:美国制定法解释方法向文本主义的回归与平白意义规则相竞争的是意图主义(或目的主义)的解释方法。意图主义强调宪政范围内的立法至上和司法机关作为立法机关忠实代理人的角色,并把作为集体的立法机关的法律文本输出活动等同于个体的言说。从此出发,意图主义者认为,作为议会忠实代理人的法院必须尽可能准确地确认和执行议会的命令。制定法是积极的政策工具,以服务于一些潜在的目的。当制定法的文本与反映在各种背景性线索中的制定法目的不相一致,如同个人的表述常常言不达意那样,此时法院应假定,议会必定是未曾准确表达其真正的意图,作为议会忠实代理人的司法机关应适当调整制定法的文本以使其契合议会本来意图表达的目的。具体而言,意图主义又可分为弱版本的意图主义和强版本的意图主义。弱版本的意图主义把制定法的文本当成解释的起点,但认为在确认了制定法文本的表面意义之后,解释并没有结束,如果法律制定的特定背景环境,各种文本外材料,尤其是立法委员会的报告、议会的辩论记录等立法史料会让法院相信立法机关并不意欲在通常意义上使用语词以令其产生字面上的效果时,根据从背景性材料中辨明的立法者意图来修正文本的通常意义就必不可少。强版本的意图主义则将文本与目的的关系彻底颠倒,认为解释的起点就是经由立法史或其它线索来探究立法者意图或目的,之后对文本的参考不过是对已经发现的立法者意图或目的的再次确认。
意图主义的解释方法可追溯至英国1584年赫顿案中的“除弊规则”。而布菜克斯通在《英国法释义》一书中曾强调过,解释立法者意志的最公正合理的方法是根据最自然与最可能的标记来“探究他在制定法律时的意图”[3],著名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马歇尔也不止一次地对意图主义表示过赞许。此后,意图主义曾一度得到过霍姆斯、卡多佐、汉德、法兰克福特、庞德与富勒等著名法官和学者的支持。这些著名法官和学者曾在不同场合表示过对意图主义的赞许,如庞德认为“真正解释的目标是发现立法者意图确立的规则,发现立法者赖以制定规则的意图,或立法者赋予规则得以表达的那些语词的意义”。(参见:Roscoe Pound. Spurious Interpretation[J]. Colum Law Review, 1907,(7): 381.)霍姆斯认为“作为确定制定法意义的辅助,一般目的之重要性尤胜于语法或形式逻辑所立下的任何规则”。(参见:United States v. Whitridge, 197 U.S. 135, 143 (1905).) 早期意图主义的一个重要案例是“圣三一教会案” (Church of the Holy Trinity v. United States),在该案中,布鲁尔大法官撰写的法院意见声称,“在制定法的字面意义之内,却未必在制定法之内,因为不符合法律的精神和立法者意图”。圣三一教会案为一种激进的意图主义解释方法提供了正当化理由。1940年的“合众国诉货运联合会”案是意图主义解释的另一个重要案件,在该案中,法院宣称,“法院在制定法解释中的职能一目了然,即解释语言以便实现国会的意图”,“如果对制定法语词进行解释的帮助能够获得,当然没有任何‘法律规则能禁止它的使用,无论基于‘表面检测,这些语词的意义是多么地清晰”。而至五十年代,意图主义(或目的主义)已经成为美国学术界关于制定法解释的正统理论,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哈特和赛克斯的努力。作为法律过程学派的集大成者,哈特和赛克斯认为立法是“理性人在理性地追求合理的目的”[4],目的是使制定法成为一个圆融贯通的整体,法院实施法律的目标是不遗余力地贯彻立法者的目的和意图。为此,哈特和赛克斯提出,制定法解释的首要任务是根据文本、结构、背景与历史等来识别或为制定法添加目的。在制定法的目的确定以后,法院应按照最能实现制定法目的的方式来解释制定法的语词,但不应超越制定法语词所能承载的意义范围[4]1374。哈特和赛克斯的制定法解释方法虽然在相当大程度上强调了对制定法文本的尊重,但其在解释之初就要求为制定法添加目的,以及根据目的来确定制定法意义的做法,无疑反映了一种强版本的意图主义的旨趣和追求。也有学者认为哈特和赛克斯的制定法解释方法是一种弱版本的意图主义。(参见:Alexander Aleinikoff. Updating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J]. Michigan Law Review, 1988,(87): 24.)
虽然在意图主义内部存在不同版本和众多分支,但概括起来,意图主义者的主张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意图主义者认为制定法解释的目标在于辨明并实现主观的立法者意图。意图又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是真实的意图,即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真实存在、明确表达的意图;第二是推断的意图,即从立法史等文本外材料中推理出来的立法者意图;第三是想像性的意图,即当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未曾考虑到当前系争的问题时,司法者应将自己置于历史上的立法者位置,想像性地重构出立法者本来意欲如何处理。其次,在文本与意图的关系上,意图主义者竭力主张意图或目的高于文本,“法律位于制定法语言之外或隐藏于制定法语言之中,立法者实际使用的语词可能是立法者意图的有力证据,但语词仅是窥见立法者意图的窗口,立法者意图方是法律”[5]。最后,在解释的素材方面,意图主义者认为,任何能有益法院发现立法者意图的工具都是合法的工具,任何能帮助法院辨明立法者意图的材料都是可以参考的材料。除法律文本外,各种文本外的材料,尤其是立法史,包括立法委员会的报告、议会的辩论记录等,都是极为重要的解释素材。
二、新文本主义对意图主义解释方法的批判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里根总统任命了一批自称为“严格解释者”的联邦法院法官,以斯卡利亚为代表的这批新文本主义法官对于从立法史等文本外材料探究立法者意图的解释方法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新文本主义者不仅对意图主义的理论出发点多有反驳新文本主义者同样鼓吹立法至上和法院作为立法机关忠实代理人的角色,但对此却有着与意图主义者相去甚远的理解。新文本主义者认为,立法机关在立法时拥有不受限制的语词库,能以平白的语言来表达心中的任何的目的和意图,立法机关对立法拟规范的情境及相应的后果有明确的认知,因此,作为立法机关忠实代理人的法院应严格按照立法机关输出的文本来适用法律,而不应揣测立法机关本来应如何规定或者曾经意欲如何规定。也有学者认为新文本主义并不把法院看成是立法机关的忠实代理人,而是看成平等合作者(coequal partner)或自主的解释者(autonomous interpreter)。(参见:Thomas Merrill. Textualism and the Future of Chevron Doctine[J].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Quarterly,1994,(72): 353.) ,还动用了诸如公共选择理论、哲学解释学理论、权力分立与制衡理论、现实主义法学理论等各种理论工具,对意图主义进行了全方位的诘难,其质疑的焦点性问题包括,是否存在一个连贯的立法者意图、法官能否发现立法者意图、意图是否能先于甚至高于文本、立法史能否作为制定法解释的素材等。
(一)对立法者意图的批判
早在1930年,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的健将纳丁就对多成员的立法机关能够聚合一个连贯的立法者意图的观点提出了诸多质疑[6],新文本主义者则运用公共选择理论进一步强化了这些批判。公共选择理论中的阿罗定理认为,在很多场合,多数规则导致了“循环多数”的悖论,无法在三个或多个相互排斥的方案中作出有效的选择,并且参与者越众,议题越多,则投票的结果越大相径庭。阿罗定理表明,没有什么社会选择的方法能避免这种悖论性结果的出现。而在循环多数存在的地方,议程操纵和策略性投票将对最终结果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阿罗定理被众多政治学学者用来证明现代民主政治进程在根本是混乱的、无序的和不可预测的。阿罗定理(Arrows theorem)由诺贝尔奖得主阿罗教授提出,其主要内容可用“挑选宠物”的例子来作一说明。某家庭的三个小孩A、B、C决定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在狗、鹦鹉、猫中选择其一作为家庭饲养的宠物。按照每个小孩对三种动物的喜好程度排序,A是狗、鹦鹉、猫,B是鹦鹉、猫、狗,C是猫、狗、鹦鹉。如果按照一人一票,多数决定的规则进行投票选择,必然形成“循环多数”,无法产生有效的结果。为了解决循环多数的问题,需要分两轮来进行投票。分组及投票结果可包括如下几种可能:1.第一轮狗和鹦鹉,狗胜出,第二轮狗和猫,猫胜出,最终猫获选;2.第一轮狗和猫,猫胜出,第二轮猫和鹦鹉,鹦鹉胜出,最终鹦鹉获选;3.第一轮猫和鹦鹉,鹦鹉胜出,第二轮鹦鹉和狗,狗胜出,最终狗获选。以上说明不同的分组会导致完全不同的选举结果,因此,议程操纵对选举结果具有决定性作用。由于A最不喜欢猫,因此在第一种分组的情形下,如果A按照自己的真实意图来选举,结果对其最为不利。为了避免最坏的结果,A会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进行策略性投票,即A会在第一轮中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选择鹦鹉,则第一轮鹦鹉胜出,第二轮鹦鹉和猫,仍然是鹦鹉胜出。这样在未改变分组的情况下,A也可以获得一个适中的结果。以上说明策略性投票也会对投票结果产生决定性地影响。 而在制定法解释领域,新文本主义的力倡者之一,法官伊斯特布鲁克则运用公共选择理论来否认立法者意图的存在。伊斯特布鲁克认为,尽管立法者各自都有不同的偏好,但要把它们聚合成一个连贯的集体意图却困难重重,有时根本就不可能。其次,法律文本只是立法的一个结果,常常并不能反映立法者,尤其是多数立法者们的偏好、价值取向及对公共政策的真实判断。议程控制导致立法机关最终采纳的可能只是少数人支持的建议,此时,法院即使谙熟每一个立法者的全部偏好,也无法言明作为整体的立法机关的集体意图。再次,在投票交易等策略性投票行为起决定性作用时,法院也无法从晦暗不明的立法过程中获得发现立法者意图的充分信息。因此,伊斯特布鲁克同纳丁一样认为,在多成员的立法机关中,无法萃取出一个统一连贯的立法者意图,司法者预测立法者本来将如何处理它事实上未曾考虑的问题不过是“胡思乱想”而已。斯卡利亚等其他新文本主义者在此问题上也持大致相同的观点。
(二)对历史主义解释方法的批判
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解释学认为,“理解是一种置身于传统过程中的行动,在这过程中过去和现在经常地得以中介”,因此“一切诠释学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总是前理解”。古典解释学要求抛弃成见,按照文本的本来面目去理解文本的意义根本不可能,因为解释者总是身处传统之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背景与环境烙下的印迹,即“成见”。而文本也是一个历史地存在,解释是一场对话,而非单向度的叙述或聆听,所谓文本的意义,在伽达默尔看来是一个视域融合的结果。新文本主义者利用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理论来反对意图主义者的历史主义解释方法。在新文本主义者看来,解释者身处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之中,其对法律文本的理解,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解释者所处的当前背景的影响。“即便集体意图是一个连贯的概念,但最具想像力的法官也无法完全重构出一个历史地存在着的集体意图”,“重构一个过去的事件(尤其是困难如集体思想状态之类),涉及到证据材料的选择、组合与解释,对证据材料的这些处理全部由人来完成,而他们的选择受其对案件事实的总体反应,对司法角色的认知及他们对历史阶段的假定等因素的影响” [7]。
(三)对意图高于文本的批判
意图主义者认为制定法的目的与意图先于和高于文本,而新文本主义者则将霍姆斯的箴言奉为圭臬,“我们不探究立法者意欲如何,我们只问制定法的意思是什么”[8],认为“在制定法解释中,制定法的语词,而非起草者的意图才是法律”[9],“是法律而非立法者的意图在统治”[10]。新文本主义者立基于宪法规定,认为宪法将制定法律的权限授予了立法机关,而惟有制定法的文本才通过了宪法规定的立法程序,即由议会两院通过并提交总统签署。所谓的立法者意图则是主观的,未曾颁布的,因而不具有先于乃至高于文本的权威性。此外,新文本者还认为,从立法史等文本外材料去发现立法者意图并让立法者意图凌架于法律文本之上的做法无疑违背了宪法关于权力分立的基本要求,因为在法官不受文本拘束地探究立法者意图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根据自己的偏好来作出价值判断和政策选择,这种“司法造法”无疑是对立法权的僭越例如,斯卡利亚曾指出:“在追寻未曾明确表达的立法者意图的伪装乃至自我欺骗之下,法官事实上却在追求他们自身的目的与冀望……当你被告知裁判毋须以立法者的所说为基础,而应以立法者的意图为根据,当你确证这二者之间毫无必然联系之时,你拼凑立法者意图的最佳尝试也不过是询问自己,一个明智而聪惠者的本来意图应该为何,而这毫无疑问地会让你得出结论,所谓法律的意思就是你认为其应当具备的意思。”(参见:Antonin Scalia. A Matter of Interpretation: Federal Courts and the Law[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17-18.) ;而立法者通过文本之外的意图与目的来影响甚至控制司法机关对制定法的解释同样是对宪法规定的司法权的侵犯,因为自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以来,“说法律是什么是司法机关的工作”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共识。因此,意图主义者所主张的那种意图高于文本的制定法解释进路不仅无助于提升民主的质量与效果反而动摇了民主与法治的根基。斯卡利亚说,法院偏离制定法本身越远,其对立法意图的尊重就越少,更多是在寻找某种将自身意愿强加于公众的方法。相反,我们越让规则自我言说,则法治越加坚实[11]。让法律的意义决定于立法者的意图而非立法者的宣布,这显然与民主的政府乃至公正的政府不相容[10]17。
(四)对立法史作为解释素材的批判
对立法史能否作为制定法解释的素材是意图主义与新文本主义分歧的焦点之一。新文本主义对此的批驳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文本主义者对立法史本身的可靠性深表怀疑。新文本主义者认为,每次议会都通过了大量立法,相信每位参议员、众议员在投票之前都阅读了全部的立法委员会报告和其它材料是不切实际的[2]899。此外,司法对立法史的过度依赖必将促使利益集团以不正当的方式来影响立法史的撰写,进而达到影响制定法解释的目的。斯卡利亚认为,任何谙熟现代立法委员会报告起草的人都知道,那些立法史中的参考材料最好的也不过是立法委员会的成员基于自身的动机而塞入的私货,而更糟的则是接受职业法律游说者建议的产物;这些材料的根本目的不在于让议员们熟稔法案的意义,而在于影响未来的司法解释。参见:Blanchard v. Bergeron.489 U.S. 87,98-99 (1989). 因此,法院越依赖议会报告等立法史料,则它们的可靠性就越让人怀疑;第二,新文本主义者认为立法史料过于庞杂,缺少适当的处理方法。与现代立法过程相伴随的是汗牛充栋的立法史料,如果允许它们作为解释的素材,则如何对这些庞杂的材料进行处理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对各种立法史料是通盘考虑、等量齐观还是按照其重要性程度分配不同的权重或进行排序,迄今为止仍不清楚。事实上,法官对立法史料的处理极为任意,在那些运用立法史料进行法律解释的案件中,无法确证那些卷帙浩繁的立法史料真的就指向了法官提议的那种解释。法官对待立法史料的态度也不过是如同“走进一场鸡尾酒会,然后随意地扫视人群,找出自己的朋友”[12]。既然如此,与其让法官在浩如烟淼的立法史料中皓首究经,还不如坚持认为立法者以平白的语言宣示了每一部制定法的目的或意图,以使法官能从对立法史的极度冗长的探究中解放出来,并且也能以此来节约潜在的诉讼当事人的时间与金钱并允许那些资源有限的法律从业者能够有效地参与竞争;第三,正是由于立法史料本身不可靠,并且也缺少适当的方法来对庞杂的立法史料进行处理,因此,法官不受制定法文本限制地使用立法史会导致法官将自己的政治、社会或政策观在判决中正当化。
三、回到文本:新文本主义的制定法解释方法新文本主义者在对意图主义解释方法大加挞伐的同时,对早期平白意义规则进行了扬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制定法解释方法。新文本主义者认为,早期平白意义规则否认了语词需要从背景中抽取意义是不正确的,而新文本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则接受了来自语用学理论对早期平白意义规则的批评,认为语词的意义不能被孤立地决定。参见:Smith v. United States.508 U.S. 223,241(1993).此外,新文本主义者还认为,早期平白意义规则以语词意义平白与模糊的二分为前提,未曾拒绝在语词模糊时采纳其它解释方法来确定制定法的意义,而新文本主义者却对语词意义的确定性怀抱极大信心,认为经由对制定法语言的仔细推敲,某一制定法的绝大部分意义通常是可以确定的。斯卡利亚就曾坦率地承认,在其法院同侪认为意义模糊之时,他却常能发现清楚的意义[14]521。而对意图主义的批判又让新本主义者坚定地认为,虽然语词与背景紧密勾连,但语词总有通常意义,制定法解释的目标不是探究主观的立法者意图,而是要确定已经颁布的文本的通常意义。文本通常意义的确定无须借助于神秘的立法者意图,无须探究立法史等文本外材料,无须考虑与制定法相关的经济与社会背景及法律适用的可能后果,而只须根据“普通说英语者标准”,运用字典、语法、解释准则等语言学方面的工具并考虑制定法文本的语境、结构与整体等语义性背景即可确定。新文本主义者的制定法解释方法具体可以阐述如下。
(一)新文本主义的解释目标
新文本主义者主张制定法解释的目标是确定文本的“通常意义”。参见:Chisom v. Roemer,501 U.S. 380,404(1991).与早期“平白意义”的“背景无涉”或“零背景”不同,“通常意义”的存在与识别与某种“共同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新文本主义者认为所有说一种语言的人必然共享了大量的背景性理解,而制定法能传递意义也仅仅是因为,相关的语言共同体在理解特定语词在特定背景下应如何使用时分享了共同的语义学方面的传统,并且这些背景性理解与传统在既定时间内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稳定不变的,是立法者、解释者乃至受制定法影响的社会大众早已达成的普遍共识,因而根据流行的社会惯习与语言规约来确定文本的通常意义成为新文本主义者的核心主张。同时,新文本主义者所主张的“通常意义”是制定法颁布时的原初意义,而非解释者在当下所理解的意义,这呼应着新文本主义者关于法治作为确定规则之治的基本价值判断和追求。
而文本通常意义的识别和确定应根据“普通说英语者标准”来进行。普通说英语者标准最早由霍姆斯斯提出,早在1899年,霍姆斯在一篇有关法律解释的文章中就曾说过,语词意义的确定,应考虑“在那些语词使用的环境中,在一个普通说英语者口中,那些词会具有什么含义”[8]417-418。尽管霍姆斯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一个严格的文本主义者,但霍姆斯的这一论断却被后来的新文本主义者奉为圭臬。例如新文本主义的重要主张者之一法官伊斯特布鲁克就要求通过追问“一个娴熟的、客观的、理性的语言使用者”将会如何使用语言来解释制定法的文本,而斯卡利亚也主张应像一个“普通议员”那样来阅读制定法的文本或强调作为一个“理性人”能从文本中所获致的意义[10]17,认为文本既不应做严格的解释,也不应做宽松的解释,而应作合理的解释以便其包括所有适当的意义[10]23,并说,“严格检测某词能否合理地承载某一特定意义的方法是看你能否在一场鸡尾酒会上以那种意义使用该词而又无人会好奇地看着你。”参见:Johnson v. United States. 529 U.S. 694,718 (2000).
在“史密斯诉合众国”一案中,斯卡利亚的反对意见就很好地体现了新文本主义者对语词通常意义的追求及作为判断语词通常意义的普通说英语者标准。某制定法规定“在毒品交易中使用武器”会导致量刑加重,而被告使用枪支交换了一些毒品,系争的问题之一是如何理解制定法文本中的“使用”(use)一词。大法官奥康纳基于传统平白意义规则的立场,不考虑背景,仅通过字典确定了“使用”一词的意义并坚称被告的行为属于“使用”武器。而斯卡利亚则认为应从通常意义上来理解并论证道,“使用某种工具通常是指按照其本来功能使用。当某人问你是否使用拐杖,他并非要询问你是否将你祖父的银柄拐杖陈列于客厅之中,他想知道的是你是否借助拐杖行走。同样,说到‘使用枪支是指按照其独特的目的来使用,即作为武器。”参见:Smith v. United States.508 U.S. 223,241(1993).因而被告的行为不在制定法文字的支配范围内。
但即便是最严格的新文本主义者也很少有不承认存在偏离文本通常意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这些例外的情形最主要的是如下两种。第一,按照语词通常意义来适用法律将会导致“明显荒谬”的结果,斯卡利亚有时把此种情形当成是“书写者错误的例外”。第二,强调制定法文本的通常意义并不否认在某些场合,某些法律专业术语或针对亚群体的技术术语所具有的特殊含义。
(二)新文本主义的典型解释技术
为了实现上述解释目标,新文本论者发展了一系列的解释技术。
1.利用词典和语法
在法律解释中使用词典的做法由来已久,19世纪许多有关《关税法》条款是否能适用于特定种类商品的案件都涉及到词典的运用,著名的尼克思诉赫登(Nix v. Hedden)案即与此相关,当时法院的态度是把词典看成是“记忆或解释的帮助”。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新文本主义解释方法的兴起,解释的重心重新转移到制定法的文本,为确定制定法文字在颁布时的客观与通常意义,参考词典成为了替代立法史的一种专门性技术手段并获得了新文本主义者的青睐,使用词典中的释义来对制定法的语词进行解释已经成为新文本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1981年,在制定法解释中参考词典还仅有一次,但在1992年,倚赖词典来确定制定法语词意义的次数已经上升到22次,并占到当年全部制定法解释案件的三分之一左右[15]357。而新文本主义的旗手斯卡利亚则是引用词典次数最多的大法官,他曾在12年间于五十份法官意见书中引用词典为65个语词做过解释。在新文本主义者看来,词典是客观中立的语义学工具,记载了“任何一位理智而博闻的人”能够理解的用法和含义,从而成为“语词通常意义的最佳来源”[16]1442,参考词典可以有效地避免法官对制定法语词的主观性理解。但新文本主义者对于如何使用词典似乎还未能发展出一种连贯的方法。大致而言,其对待词典的态度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几种情形。第一,直接把词典中的释义当成是语词的通常意义。例如在“奇瑟姆诉罗默”(Chisom v. Romer)一案中,斯卡利亚就曾毫不迟疑地根据《韦氏新国际词典》(第二版)将“法官”从《选举权法》中“议员”(representative)一词的通常意义中排除出去。在此案中,斯卡利亚显然是将词典中的释义等同于语词的通常意义;第二,在词典的多项释义中挑选通常意义。经常某一系争的语词在词典中存有多项释义或在不同的词典中释义不尽相同,此时需要对释义进行取舍,按照斯卡利亚的说法是要区别“语词能被如何使用和语词通常被怎样使用”。例如,在“MCI电信公司诉美国电话电报公司”(MCI Telecommunications Corp. v. AT&T Co.)案中,系争的问题是“修改”(modify)一词是指多大程度上的改变,是仅指“适中的、微小的改变”,还是可以包括“根本的变化”。为此,斯卡利亚查阅了《蓝登社英语词典》,(1987年第二版),《牛津英语词典》(1989年第二版),《布莱克法律词典》(1990年第六版)以及《韦氏新国际词典》(1976年第三版)。前三本词典对于“修改”一词的释义均是“适中的、微小的改变”,而《韦氏新国际词典》则提供了两项释义,认为“修改”一词既可指“微小的改变”,也可指“根本的改变”。斯卡利亚随后认为,韦氏词典的两项释义本身就自相矛盾而且与多数词典的释义相冲突,因此,韦氏词典认为“修改”一词可指“根本性的改变”是该词典的“个性化”释义,不具有普遍性,“修改”一词在诉争的案件中应仅指“适中的微小的改变”;第三,将词典中的释义当成是解释的起点或一个环节,文本语词意义的最终确定还要参照其它因素来确定,例如“皮尔士诉昂德伍德”(Pierce v. Underwood)等诸多案件都是在以此种方法使用词典,事实上,斯卡利亚等新文本主义的力倡者拒绝词典释义的次数也不在少数。
除频繁参照词典来确定文本语词的意义外,像词性、句子的结构、标点符号的使用等语法知识也与词典一样成为新文本主义者在确定文本意义时惯常使用的工具,例如在“克兰登诉美国”(Crandon v. United States)等案件中,斯卡利亚就从语法方面的知识出发对案件中争议的法律问题作了详尽的分析。
2.使用解释准则
解释准则包括实体性准则和语言学准则,实体性准则中暗含着价值判断和政策选择,例如“仁慈规则”(rule of lenity)即是实体性的解释准则,要求对存在歧义的刑法法规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解释。而语言学准则则是价值无涉的关于语词意义应如何理解的文法准则,这些准则与制定法的目的及法律适用的社会效果无关[17]44。新文本主义者极少采用实体性解释准则,但积极采纳语义学方面的解释准则来确定文本的意义,斯卡利亚把这些中立的、非实体性的语义学解释准则当成是推理的常识性规则和发现法律文本意义的重要指示。新文本主义者经常采用的语义学解释准则包括如下几个。第一,“明示其一即排除其它”(Expressio unius),意指当制定法明确提到一类人员或事务中的一个或多个时,可以默认为排除该类中其他没有提到的人或事。斯卡利亚对此准则的一个简明的解释是,“如果你看见一个指示牌上写着:十二岁以下儿童免费进入,那么你就不必再问你的十三岁的小孩是否需要付费。” [1]25“明示其一即排除其它”是新文本主义者最常倚赖的语义学解释准则之一,埃斯克里奇曾夸张地说,自新文本主义兴起以来,在法律解释中使用此准则的情势“如同旷野上的杂草一样疯长”[18]664;第二,从同类中获知(Noscitur a sociis)准则,意指几个词在连续或顺次使用形成一个语词群时,其意义是可以相互映证的,在对其中的某个语词意义有疑问时,可以参考附近与之类似的语词来确定;第三,相同类别(Ejusdem generis)准则,意指当制定法列举了多个项目,之后的一个总括性措词的意义限于与之前所列项目同类的人或事。斯卡利亚曾举例说,当提到“平头钉、铁钉、钉书钉、铆钉、螺丝钉以及其它物品”时,此处的“其它物品”仅指其它紧固件。同样,当某制定法规定禁止隐藏随身携带的“手枪、左轮手枪、德林加枪(一种大口径小手枪)或其它危险武器”时,此处的“其它危险武器”仅应指其它枪支甚至限于手枪类的枪支,而不能随意扩大其意义范围。
3.单一制定法的整体主义解释
单一制定法的整体主义解释要求考虑单一制定法的整体结构,斯卡利亚认为,“制定法解释是整体性地努力,某个条款孤立地看可能模糊不清,但根据制定法框架中的其余部分却经常能被澄清,因为同样的术语在其余地方使用时的语境使其意义清晰,或其中仅有一种允许的意义能产生与法律的其余部分协调一致的实质性效果。”参见:United States Sav. Assn v. Timbers of Inwood Forest. 484,U.S. 365,371(1988).新文本主义者对单一制定法的整体主义解释方法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第一,反对冗余和重复,即认为制定法中的每个部分都应被认为具有某种作用,因而除非绝对必须,否则任何部分都不应当成是无意义的,而议会也不会在制定法中插入不必要的语言,如果对特定语词的某种解释导致另外的语词成为多余,则法院应拒绝此种解释。在“昆吉斯诉美国”(Kungys v. United States)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就把反对冗余规则称为制定法解释中的一项“基本规则”。而在“阿卡迪亚诉俄州能源公司”(Arcadia v. Ohio Power Co.)一案中,俄州能源公司受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的双重管理,同时,《联邦能源法》第318条以一个复杂的并列分句规定了证券交易委员会优先管辖的事项,系争的问题是该条中结尾处的短句“或任何其它主题事项”应作如何理解,斯卡利亚详细分析了《联邦能源法》文本的结构,指出该法其余部分与318条中几个并列分句之间的对应关系,认为任何其它阅读和解释都会导致该条中“或任何其它主题事项”这一短句成为多余;第二,内在连贯,即认为某个特定的语词在单部制定法中有连贯的意义,解释应该前后一致,同样的语词在制定法的不同地方出现时要作相同的理解。若某语词在制定法的某处出现时意义模糊,则可以参照该词在该法的其余地方被使用时的语境来加以确定;第三,契合整体,语词的意义不应从制定法中某个单独的部分孤立地获得,而应从对制定法文本的整体阅读中产生,应考虑哪一种可能的意义才能最契合作为整体的制定法,是否制定法文本的结构支持了该种合理的意义。
4.理想立法者与多制定法的超文本结构
新文本主义者将单部制定法的整体主义解释方法放大至全部制定法,即将全部制定法假定成是由一个理想立法者制定和颁布的“超文本”文件。斯卡利亚曾批评他的法院同侪孤立地解释制定法,而不是把他们当成是一个更为宏大和统一的制定法体系中的一部分[1]409。由于所有或大多数制定法被假定为一个超文本的文件,因而,斯卡利亚经常将那些适用于单部制定法中的解释方法和技巧也适用于这样一个由多制定法形成的超文本结构。
首先,斯卡利亚认为,“明示其一即排斥其它”在此种更为宏大的场景下意味着在一部制定法中已明示其一即在另外的制定法中排除了其它。在“凯西案”(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Hospitals, Inc. v. Casey)中,系争的问题是一部联邦民事权利方面的制定法中规定的“律师费”是否应当包括“专家证人费”。为此,斯卡利亚查看了《有毒物质控制法》和《消费产品安全法》,由于这些法律都明确而具体地提到了专家费用,因此,斯卡利亚认为,系争制定法中的律师费不应包括专家证人费,因为在一部制定法中明示了其一即在另外的制定法中排除了其它,如果议会并不希望如此,那议会对此肯定已作出了相反的明确规定。
其次,应把不同制定法看成相互作用的整体。例如在“宾夕法尼亚州诉联合天然气公司”(Pennsylvania v. Union Gas Co.)一案中,斯卡利亚认为,《环境反应、赔偿与责任综合法》(简称《超级基金法》)中的条款应按照与《超级基金修正案与再授权法》(简称《莎拉法》)相互联结的方式来解读,而不应将他们割裂开来。而在“司法部诉朱利安”(Department of Justice v. Julian)案中,斯卡利亚认为“应以不会导致任何一部制定法无效的方式来阅读已颁布的全部制定法”,因此,《信息自由法》应按照能与《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及《假释法》相协调一致的方式来阅读,而不能使前者取代后者。
再次,相同或类似的语词在不同制定法中应具有相同或近似的意义,无论这些制定法在性质上是否相同。例如在“皮尔士诉昂德伍德”案中,《平等获得司法法》规定,一方当事人在以美国政府为被告的案件中胜诉将被补偿律师费,除非法院认定政府的行为能在“实质上被正当化”(substantially justified)或特殊的情境使补偿不公正。第九巡回法院依赖相关的立法史料解释“实质性地正当化”意味着政府的立场“在法律与事实上有合理的根据”,而已胜诉方则主张法律要求的程度要高于“合理的”程度。为解决系争的问题,斯卡利亚拒绝了上诉法院的解释进路,而是先查阅了词典,在通过词典无法确定系争语词的意义之后,斯卡利亚又在《行政程序法》中找到“实质性证据”(substantial evidence)这一类似语词,并在《联邦民事程序规则》中找到了完全相同的语词,在对这些相同或近似的语词进行分析之后,斯卡利亚认为“实质性地正当化”意味着大体上或在主要方面可以被正当化。而在“昆吉斯诉美国”案中,系争的问题是《移民与国籍法》中“重大事实”(material fact)一词的含义,对此,斯卡利亚参考了许多刑事方面的制定法来界定该词的涵义,这显然是认为类似语词在不同性质的法律中也应被认为具有相同的意义。
5.司法尊重与拒绝制定法的适用
新文本主义在制定法模糊时应如何对待行政解释这一问题上接受了司法尊重原则。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学者兰迪斯和法官法兰克福特就对司法尊重行政解释的问题多有提及,而五十年代前后兴起的法律过程学派曾以“制度能力”这一核心概念为依据对此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1984年的谢弗林案则是解决司法如何对待行政解释的标志性案例,在该案中,史迪文斯大法官从意图主义的立场出发,阐述了分两步操作的司法尊重原则。参见:高秦伟.政策形成与司法审查:美国谢弗林案之启示[J].浙江学刊,2006,(6):142-149. 谢弗林案虽然在斯卡利亚任职联邦最高法院之前作出,而史迪文斯大法官后来也被证实为是意图主义在联邦最高法院最坚定的捍卫者,但谢弗林案与新文本主义在旨趣上却极其近似,都竭力要求法官回避政策制定和政策选择问题,认为对政策进行评估之类的问题应交由可问责的政治分支去解决。因此,谢弗林案所确立的司法尊重原则很容易获得新文本主义者的认同,例如斯卡利亚就是谢弗林案在联邦最高法院最坚定的拥护者之一[19]1663,认为谢弗林案改变了之前在司法是否尊重行政解释问题上逐案评估相关因素的作法(如考虑相关行政机构的专业能力,系争问题的复杂性程度),经由一个总括性的推定,确立了一揽子式的解决方法[14]516。而在具体的案件中,斯卡利亚也不止一次地表达过对谢弗林案所确立的司法尊重原则的赞同,如斯卡利亚曾在判决意见中表示,在制定法模糊之时,法院应尊重行政机构的解释参见:NLBR v. United Food & Commercial Workers Union. 484 U.S. 112,133(1987).,法院必须采纳行政机构关于制定法的合理的解释,除非该解释与明确表达的议会意图相矛盾。INS v. Cardoza-Fonseca,480 U.S. 421,454(1987).但谢弗林案与新文本主义之间仍存在不小的紧张关系,例如斯卡利亚就对谢弗林案的意图主义进路感到不满,而其他文本主义者则试图对谢弗林案的所确立的原则进行文本主义的改良[15]357-358。
除司法尊重外,法官伊斯特布鲁克还提出,在穷尽文本主义的手段之后,若制定法的意义仍然模糊以至不能确定是否可适用于既定案件之时,法官应限制制定法的适用并将问题交还给政治分支以求更为清楚的解决方法[20]544。
四、结语自斯卡利亚任职联邦最高法院以来,联邦最高法院在制定法解释上明显出现了向文本主义回归的倾向,但此种回归绝非是对早期平白意义规则的简单重复,而是扬弃之后的新发展。因此,埃斯克里奇把以斯卡利亚为代表的这种制定法解释方法称之为“新文本主义”。新文本主义的制定法解释方法拒斥虚无飘渺的立法者意图,从对立法史迂回曲折的探究中全身而退,将文本重新置于制定法解释的中心位置,强调制定法语词的通常、自然与客观意义,在激烈批判意图主义解释进路的同时,重新界定了制定法解释的目标并发展了相应的解释技巧。新文本主义的制定法解释方法对美国的司法实践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在联邦最高法院,斯卡利亚于1987年首倡新文本主义方法参见:I.N.S. v. Cardoza-Fonseca, 480 U.S. 421,452-55(1987). 但斯卡利亚在在担任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法官时实际上就已经在很多判决意见中表明了其新文本主义的解释立场。 ,是时应者寥寥,然随着时间推移,此种制定法解释方法已日益受其法院同侪们的重视。新文本主义的制定法解释方法在挑战和动摇自沃伦法院以来的准则的意图主义解释方法方面表现不俗,在将立法史清除出制定法解释方面也较有成效,虽然部分忠贞的大法官们从来未曾放弃过对意图主义的坚守和对立法史料的运用,但就统计学证据来看,联邦最高法院不再提及立法史在全部制定法解释案件中所占的比例正呈不断上升之趋势[15]355,而在提及立法史的案件中,立法史也再不是解释的唯一决定性因素。而一些著名学者和法官的经验主义研究还表明,新文本主义对那些并不认可自己是文本主义支持者的法官们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17]32,像诸如使用词典和利用语法来确定制定法文本意义的解释方法已被非文本主义者普遍接受,而强调制定法文本结构的整体主义解释技术也极为非文本主义的法官所认同。因而有学者曾发出“我们都是文本主义者”的感叹。
新文本主义的制定法解释方法不仅在实务界颇有影响,而且在学界也激起了广泛的关注。新文本主义的认同者不仅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论证此种制定法解释进路的优长,如节约法官、律师及诉讼当事人的时间和金钱成本,促使立法者制定更为细致的法律,便利政府机构之间及立法机关与受制定法影响的社会大众之间的有效交流等,而且支持者们注意到以斯卡利亚为代表的新文本主义的制定法解释方法始终将其合法性与美国宪政的基本结构相勾连,致力于从宪法文本出发的正当性论证和厘清自新政以来已渐趋模糊的三权界限,再次强调法官发现法而不创制法,政策制定与政策选择应由民主选举的可问责的政治分支去解决以及法官不得假解释之机夹带个人私货等。此外,新文本主义者还从制定法解释的角度坚定地捍卫着自洛克以降那些传统而又久远的法治理念,而这些弥足珍贵的法治理念,曾先受现实主义法学思潮的攻诘,后受批判法学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和剥蚀而一度摇摇欲坠。以斯卡利亚为代表的新文本主义者们在制定法解释的过程中重申了传统法治的全部价值追求,例如其对神秘的立法者意图的批判及对文本客观通常意义的强调,呼应的是新文本主义者关于法治的基本判断,即法治是“作为规则之法”的治理,而规则应是公开、明确与可预测的,有时“坏的规则也胜于根本没有规则” [11]1179等等。然而批评者认为新文本主义并不比意图主义高明,其在本质上仍属于基础主义的解释方法,在剔除立法者意图神话的同时,假定了全能的理想立法者和确定连贯的文本意义,无疑是制造了新的神话。不仅如此,批评者还认为新文本主义的制定法解释方法常有自相矛盾之处,如其一般性地拒绝考虑目的、政策与后果等,但时常又表现得首鼠两端;其在词典中寻找语词通常意义的做法被诟病为试图在动物园中发现动物的天然习性,并且其对词典释义的任意取舍也难逃操纵文本意义的嫌疑;其在表面上赞同谢弗林案,却又倾向于主张文本总有清楚确定的意义,如此又致谢弗林案所确立的司法尊重原则常无用武之处,等等。而斯卡利亚本人也坦然承认,立法者谙熟全部制定法并于立法时萦绕于怀,因而可以为制定法的每一个语词设定连贯意义只是一个“善意的虚构”。参见:Green v. Bock Laundry Machine Co., 490 U.S. 504,528(1989).并且,斯卡利亚也从不讳言,他可能会做出不正确的制定法解释,但却对美国民主政治的纠错能力怀抱信心,认为“议会的修正自由是内在的制约,在任何情况下,议会未曾修改制定法来推翻一个不正确的解释都应被记作民主政体所付出的部分代价”[21]97。JS
参考文献:
[1] Patricia Wald.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Use of Legislative History in the 1981 Supreme Court Term[J].Iowa Law Review,1983,(68):195.
[2] Eric Lasky. Perplexing Problems with Plain Meaning [J]. Hofstra Law Review, 1999, (27):910.
[3]威廉·布莱克斯通.英国法释义:第1卷[M].游云庭,缪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71.
[4] Henry Hart & Albert Sacks. The Legal Process: Basic Problems in the Making and Application of Law[M]. Foundation Press,1994:1410.
[5] Alexander Aleinikoff. Updating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J].Michigan Law Review, 1988, (87):23-24.
[6] Max Radin.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J]. Harvard Law Review, 1930, (43):863.
[7] William Eskridge. The New Textualism[J]. UCLA Law Review, 1990, (37):644.
[8] Oliver Holmes. The Theory of Legal Interpretation[J]. Harvard Law Review, 1899, (12):419.
[9] Frank Easterbrook. The Role of Original Intent in Statutory Construction[J].Harvard Journal of Law & Public Policy, 1988, (11):60.
[10] Antonin Scalia. A Matter of Interpretation: Federal Courts and the Law[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17.
[11] Antonin Scalia. The Rule of Law as a Law of Rules[J].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1989, (56):1175.
[12] Richard Pierce. The Role of the Judiciary in Implementing an Agency Theory of Government[J].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1989, (64):1258.
[13] Lawrence Solan. Learning Our Limits: The Decline of Textualism in Statutory Cases[J]. Wisconsin Law Review, 1997, (1997):243.
[14] Antonin Scalia. Judicial Deference to Administrative Interpretations of Law[J]. Duke Law Review,1989,(3):521.
[15] Thomas Merrill. Textualism and the Future of the Chevron Doctrine[J].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Quarterly, 1994, (72):357.
[16] Randolph Raymond. Looking It up: Dictionaries and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J]. Harvard Law Review, 1994, (107):1442.
[17] Jonathan Molot. The Rise and Fall of Textualism[J]. Columbia Law Review, 2006, (106):44.
[18] William Eskridge. The New Textualism[J]. UCLA Law Review, 1990, (37):664.
[19] Michael Herz. Textualism and Taboo: Interpretation and Deference for Justice Scalia[J]. Cardozo Law Review, 1991, (12):1663.
[20] Frank Easterbrook. Statutes Domains[J].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1983, (50):544.
[21] Stephen Plass. The Illusion and Allure of Textualism[J]. Villanova Law Review, 1995, (4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