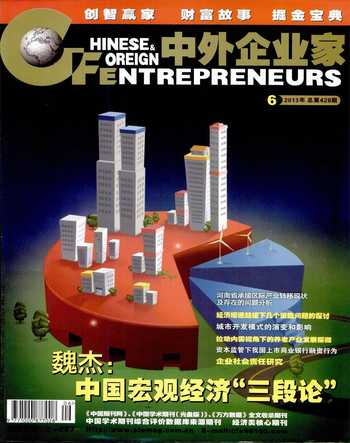不确定性、风险与权力的制度化
刘林 赵芸
摘要:本文从奈特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概念出发,分析了政治社会整体环境的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人受害的状态和确定性条件下政治社会体制整体正义性、个人对风险的态度与政治权力制度化的关系。本文从经济学、文化理论和政治学中进行了跨学科的资源吸收,以结构主义方法进行了整合。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结构进行批判的同时指出了政治权力制度化的普遍主义个人主义文化和社会条件,并在确定性的普遍性意上指出主法治并非西方社会的特殊产物。
关键词:不确定性;风险;文化深层结构;制度化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3)15-0267-02
使权力在制度规范内运行,抵制权力的恣意和武断而驯化权力既是人类的一个普遍性的理想,又是民主、法治、人权等价值追求和国家长治久安、繁荣强盛的一个前提条件。然而有制度并不意味着制度化,原因就出在不同文化、社会建构和形塑的人身上。掌握权力的官员和权力服务对象的百姓如果不是处于普遍主义个人主义的文化背景条件下,权力的制度化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一、不确定性、风险与权力的恣意和武断
关于不确定性和风险,本文从经济学家奈特对这两个概念的界定为出发点,经过稍微的调整,应用到政治学科当中。奈特在《不确定性、风险和利润》中将不确定和风险加以区分。风险是指经济行为主体主观上占有一定信息的前提下对行为事件结果的主观概率估计,可能有概率的类型和分布参数,或者只有类型而没有分布参数。而不确定性是指经济行为主体缺乏知识或信息的情况下对行为事件结果不能形成主观估计的现象,这被称为真正的不确定性,也叫奈特不确定性。
根据这里对奈特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概念的定义的说明,可以显然看出奈特仅是从主体自身也就是内部的视角来分析不确定性的来源,这是一种明显的缺点,因为不确定性更常见的是来源于外部环境的不可预测和控制的随机因素。但是这种外部性不确定性也可以纳入奈特的不确定性概念之中,如果对其定义稍加改变。这样,我们将纳特的不确定性概念定义为经济行为主体在缺乏知识或信息与对源于外部环境的随机因素干扰情况下的决策。因为人们在不确定性背景下也可能仍然要进行决策,所以这时也仍然存在主观的概率估计,这样不确定性和风险就不容易区分了。不过政治学可以将风险定义为来源于其他行为主体的不确定性,尽管该主体自身还可能认为是在进行确定性的行为。这样,从政治社会学角度,我们最终将不确定性理解为环境因素,这里我们不处理自然因素,环境因素就是是指某种体制整体上的正义或不正义,不正义的体制或社会自然充满不确定性,至少使广大的下层人民无所适从;即使是正义的体制或社会,在某些局部方面或者某些时间段内也仍然存在不正义的内容,这样也就仍然使得一部分人或者某个时间段内的多数人生活在不确定性下。同样从政治社会学角度,我们将风险理解为来源于他人的因素。在此,风险是指在环境或体制整体上是正义的前提下,社会中一些人的失范行为给遵守规则的人带来的风险。
就中国语境而言,传统文化对人的定义是“仁”,即是根据人际关系中的他人认知和行为来定义个人的。这就使得中国人无时无刻不生活于各种人际关系的圈子之中。但是这个圈子是狭隘的,是个人私人所能参加的彼此照顾的小圈子,这种小圈子文化是普遍主义规范和制度的大敌,因为规范和制度会被这种小圈子切割而碎片化。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发现明明是公开达成共识或形成规范或制度的东西,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不但权力主体不能一视同仁对待不同的相对人,就是相对人也不愿意真的一视同仁,因为如果权力主体是小圈子中的熟人的话,相对人难免有受特殊关照的期待。只有在面对权力主体是陌生人且找不到门路的情况下才幻想自己能够被公平对待。具有讽刺性的是无论是当年项羽的“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还是今天职业市场上专业成就的女强人,都是在取得了一个大范围客观的认同的情况下还要掉过头来寻求某个狭隘的小圈子的承认。中国人却并不能轻易地跳出形形色色的小圈子的制约,发育成长为普遍主义的自主、独立、负责的主体人格和形成尊重他人尤其是陌生人的权利意识。这是因为中国人一直生活在小圈子当中,尤其是很多情况下,小圈子中的他人已经先行付出了大量的情感、金钱投资,因此很自然地期待各种预期的报酬。在道德上,小圈子中的父母、亲属、师长、朋友、配偶等在好的情况下是无私的,甚至可以达到为他人牺牲生命的程度,但即使是这些看似高尚无私的人,一旦越出生活中的各种小圈子,连对陌生人的权利的起码的尊重意识都可能没有。很多血案起初往往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就因为不知道越出圈子后如何与他人尤其是陌生人打交道,慢慢地就发酵放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出现的大量制度失范根本问题是出在人身上,人的定义和人的存在是与现代社会不应适应的传统文化定义的人。
因此,掌握权力的官员很容易脱离规范和制度的约束而滥用权力。因为这些官员和普通百姓一样也是受到文化的深层结构形塑和制约的,他们也是文化和社会的建构成分,而非任何特殊材料的结构产物。非世袭制的情况下,官员是在家庭和社会中成长而后才人仕的。在中国古代王朝政治环境中,对于流内官员来说,官职是否能够继续保有、升迁或贬谪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官员的权责从来都没有清楚过,还没有哪一个官员能够因为完成了明文规定的职责范围内的事项而能够理所当然地继续任职或升职。朝廷内,不管是明君还是昏庸之主都标榜从善如流,然而就连谏诤的言官也生活在皇帝的喜怒无常的情绪变化之中。在官员群体对百姓的治理中,官员们也把官场内的不确定性带给了百姓。在对百姓的造福过程中,官员们从来都不能把握住应有的界限。比如在征粮征税时,如果征税正本是确定的,那么当征税成本增加而税收却没有相应的成比例增加甚或下降的时候,这就很明然说明了民财民力的困窘,这个时候就不但不能加赋,反而要救济了。如果征税过程是遵守法定规范或制度的,那么当发现有人因交税而陷入卖儿卖女、弃田潜逃的时候,那么征税的临界点同样可以清楚的识别。如果税收制度是确定的,那么何至于不能发现轻税而税收增加、重税而税收减少的经济原理呢,又何至于长期重农抑商,对商业竭泽而渔呢?可是这些确定性的前提都不存在,所以甚至到了百姓大规模的逃亡的时候,官府仍然还要将税赋强制摊派在没有逃亡的百姓头上,而与此同时仁慈的君主和地方官却在还能掌控局势的时候在流民涌入的地方开设粥厂。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这本是非常浅显易懂的道理,然而中国传统文化非但没有孕育出尊重财产权的传统,反而形成了抄家文化。这既是政治社会中不确定性的产物,又进一步强化了不确定性。财产对于任何人的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是不言而喻的,而财产理所当然地是私有的,然而西方近代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口号到了中国就变味了。但中国又有哪一点儿特殊呢?财产不能得到保障,个人生活即无保障,从而个人既不能独立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和承担应尽的义务,又不可能不处处仰人鼻息,成为顺民或者奴性十足的人。这样的人既意识不到自己的权利,又怎么可能尊重他人的权利呢?又怎么能够遵守普遍客观的规范、制度呢?
政治社会中处处弥漫的不确定性使得没有任何人成为真正的受益者。百姓的顺从和奴性固然使得官员可以恣意妄为,但是小官也仍然生活在大官的不确定性之下,岂能安全地心满意足地享有民脂民膏?最大的官皇帝作为孤家寡人同样生活在百官编织而成的不确定性大网之中,岂可安享荣华富贵?时至今日,这种余毒仍然存在,流风所被,几乎所有制度、规范都不能被不打折扣的遵守,就连宪法规范也逃脱不了此种命运。原因就在于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的根基仍然没有动摇,普遍主义的个人主义仍然没有得到成长。此种文化根基使得权力的制度化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为制度化是化在人身上的,是规范(规则)在人的精神意识当中的内化。制度不仅化在官员身上,而且化在人民身上。只有这样在官员与人民的政治行为互动中才既需要制度作为出发点和评价尺度,又需要依据制度来实现某种目的、成就某种事业。
二、确定性与权力的制度化
人类在本性上对不确定性是抵制的,这就是对确定性的追求。在这一点儿上,不确定性和风险是能够比较清楚地加以区分的。风险是确定性的风险,是个人主观预估的正在进行或未来事件的或然性判断。风险偏好型的人,比如企业家正是企图利用敏锐的洞察力从风险中谋取额外的利润。风险规避型的人,比如工资收入者则是以保险费的形式将风险可能产生的额外利润让渡给投资者而换取稳定的工资收入。这种经济意义上的风险概念应用到政治社会中,则风险就是中性的,也就是说,政治统治者既不应该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到所有人都生活幸福美满的程度,也不应该不为任何异端或歧见者预留一定的生存空间。后者在政治社会中的生存会处于类似于生物在自然界中的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过程中,因为任何异端或歧见如果没有其他人的认可那就会因为社会的排斥而不成异端,而如果有了其他人的认可甚或越来多的人的认可的话,那就会因为社会的承认而不成异端。当然,如果异端不是生存于自愿承担风险的政治社会中,而是处于不确定性之中的话,那么异端就不可能真正产生和存在。因此,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中异端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一个像西方社会中那样值得讨论的主题。
三、结论
对人类的智慧而言不确定性是绝对的,但对确定性的追求无疑也是人类根深蒂固的倾向,这源于人的自主性。本文分析了不确定性环境下的政治社会中权力的恣意和武断、与确定性环境下权力的制度化的文化社会条件。自亨廷顿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化问题之后,政治权力的制度化就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主题,本文继续讨论这一主题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进行了批判,同时指出了普遍主义的个人主义文化和对待异端的态度成为政治权力制度化的前提条件和检验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