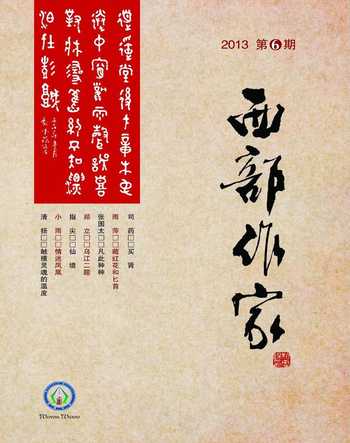梦聊之约
诗天曲
昨晚,我早早地入寝安寐,在深沉沉的一觉中,不料进入了梦游的境界。早上起身后,神情稍许疲乏,一个人呆呆地、半醒半梦地坐在书房里。直到听见楼下叫吃早饭的吆喝声,我方梦境初醒。我拍拍额头,触摸自己是不是真的醒了。此时,我依然想着那梦,它既非同淳于棼的“南柯一梦”,也非似庄生的“化蝶羽飞”,既没有春情荡漾的“遇艳”,更未相遇到人见人喜的“财神”。
我竟会与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人相约在这春寒料峭之夜,他不是走了吗?他的肉身不是消失了吗?我怎么会跟一个……我不禁被昨晚的梦吓了一跳。我木然地起身推开窗户,一轮旭日已冉冉从东方升起,给枯槁憔色中的大地披上了淡暖的金光。不远处,随着“咕咕——咕”的声音,一只斑鸠从高大而秃枝的银杏树上飞倏而去,这叫声,让人感觉着孤独而凄怆。
初春的风,已没有了寒冬那刺疼的感觉,但微微的凉意,已把我完全地撩醒。我回忆着昨晚的梦,肯定着与那个人相遇了,还聊得很投机。我惘然着,不停地思索着。人们常说,梦是假的。但昨晚的梦太逼真了,其实梦何以为真假,我宁可相信梦是真的,梦一定是神的无形力量在
牵引,要不,又有谁能说得清?当转回身去的一刹那,写字台上叠放的几本小说与散文集才让我恍然大悟,《命若琴弦》、《务虚笔记》、《病隙碎笔》……原来,梦非无缘,只因醒时所读,读有所思,才致夜有所梦。啊!是的,我昨晚与他相约“梦聊”,而那个人就是——史铁生。
在前年初,我很清楚地记得,史铁生于上年的年底让病魔给带走了,据说他走得无怨无悔,且飘逸得无声无息。正如他自己所言:“我轻轻地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扫尽尘嚣”。七年前,在不经意间,我才知道了他的名字,原由是读过他的《我与地坛》,故对他有了朦胧的了解。读后,我心存了一种好奇和敬仰,这个坐在轮椅上的作家很不平凡,那些质朴而深邃、简约而抒情的文字,曾让我滋生过什么时候能有幸去拜会他的冲动,想去握一下那双曾经挥洒出灵感文字的手。可是,我一直没敢迈出健全的双脚,直到他轻轻地走了——永远地消失了他的肉身。
我一直在想,是读者造就了他,还是他影响了读者;是时代造就了他的名字,还是他造化了历史的经典。我忽然想起“文革”中的另外一位“铁生”,是不是这个名字更容易造就名声?我不经意地在笺纸上写上了二个“铁生”,呆滞地看着,想着,慢慢地觉得眼前两组“铁生”的字分别在放大和缩小。那放大的,被无数个“史”字围拢着,形成了一个光彩的圆圈,在旋转中上升着。我若有所思,尽管这只是在我幻意的一瞬间。
史铁生,他自己怎么也没想到,他的父母给他起的这个名字,竟然会让千千万万的人知道了他。现在,在时空的记忆库里,他的名字已镌刻在人类当代思想文化的里程碑上,他珍贵的文字已驻留在人们心中,点缀了光彩夺目的时代史迹。
按照从小灌输的习惯说法,我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但是“长”了几十年的我,却仍然迷惘着,自己究竟是“一根草”?还是“一朵花”?或者是“一棵树”?惟独每天睡醒后能明白的,就是还延续着肉身的生命。我似乎至今都未能活出个所以然!
我叫土生,请不要误会,我不是出生在农村,而是出生在大上海。在过去被人们称为五马路的边上一幢六层楼里,我一丝不挂地哭闹着坠入红尘。长大后,听旁人说过,困难之年有我本来是多余的,所以,当初的乳名就叫余生。由于父母感觉我缺土,三岁时又改名为土生。后来,五岁丧父,从此,我又随母亲生活在让现代人称颂的苏南的一个美丽水乡。
记得,自懂事起,因为那首经典的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让我知道了北京,知道了天安门——中南海——毛主席。后来才明白北京不但是千年的古城,也是祖国的心脏,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于是,向往京城成了我儿时的梦想,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才真正拥抱了北京,并连续去了二次。那是出差顺便观光,游览了长城、故宫、大会堂、十三陵、纪念堂、颐和园等等。要知道,在那时,能够去北京,已经是很让人羡慕的事了。
然而,也不知什么原因,二次去北京的时候,竟然都忽略了地坛公园,哪怕是路过也没有。我对地坛的模糊了解和感然却是因那本《我与地坛》的缘故,是写作者铁生让我对地坛有了理性的印象。对不起,恕我这么直呼他的名,我想,这样称谓总显得近乎些。当然,他叫铁生,而我叫土生,虽同为一“生”,然分处南北,茫茫红尘中却难于缘见。今天,我终于誓下了一个心愿,一定要踏上那神圣而古老的祭坛,去寻找铁生曾经的履痕。
我只知道铁生走的那年59岁,大我7岁。有幸的是,我和他竟然同属一个年代,所不同的,他站在了那个年代的前列,而我则拉在了末后。迄今为止,我和他最大的区别在于,铁生已经成为了闻名于世的作家,一个有血有肉、有灵有魂的正直作家。而我则为了生活,在那浮躁喧哗、泥泞不堪的路上埋头地行走着,惘然中仍在盲目地寻找着什么,不明不白地迎着风吹雨打,压根儿没想到去看清楚那头顶上的乌云或者太阳。
也就是说,这几十年来,铁生靠着轮椅支撑着残缺的肉身,塑造了一个完美的心魂。而我,撑着健康的肢体,却总是迈不开矫健的步履。即使在平坦的道路行走,也以一双渐渐老花了的眼睛,在探视中疑惑地蹒跚在路面上坑坑洼洼的影子中。自从铁生离世后,我突然茅塞顿开,原来这一路过来的我,竟然是一个健全的“瘸子”,只是在熙熙攘攘中,别人的眼神没能顾及我的“跛脚”罢了。
小时候,我一想到死,心里总有一种怕怕的
感觉。长大后,当我每天从床上起来,会欣喜自己还醒着,也就是说,真的还活着。直到昨天晚上的那一场梦,却不免让我恍惚起来,你说这人的“死去”与“活着”到底以什么来作为标准呢?
太阳光透过窗口照射在我的胸口前,我坐在办公椅上,两手托着腮膀,又进入了思绪。是我活着?还是铁生死了?如果铁生死了,昨天晚上怎么会出现在我的梦里?那神情活灵活现,他侃侃而谈,还不时地用手推推眼镜。我敢肯定,那绝对不是他的肉身,即使按照物质不灭定律,他的肉身也已经转化为其他物质了。灵魂?对,因为铁生说过:灵魂是不灭的。
是的,我和铁生昨晚相约的是一个“梦聊”场境。你说什么?虚拟?幻想?神经质的胡说?这么说吧,我宁愿这样的胡说,因为我有了一次白昼无法达到的“零距离接触”。就连贾平凹先生在他《生活中的一种》文章里也这样说过:“要日记,就记梦。梦醒半夜,不可睁目,慢慢坐起回忆,梦复续之。梦如前世生活,或行善,或凶杀,或作乐,或受苦,记其迹体验心境以察现实,以我观我而我自知,自知乃于嚣烦尘世则自立。”
于是乎,我终于找到了喜欢做梦或者沉浸于梦想的理由,恰似朱熹所言:“如曾点浴沂风雪,自得其乐”。
况且,昨晚和铁生的“梦聊”,使我领悟了一个当代作家所具有的良知和对世事的洞察及析透,让一个“失去”肉身的心魂在慢慢洗涤我“活着”的顽钝脑袋。“梦聊”有什么不好,至少我自己感觉到它的存在。比起那些隐藏身份,不怀好意进行“网聊”,比起毫无共同语言而又相处于虚情假义中的“无聊”,我觉得,“梦聊”要来得真实和自然。而且,它是我内心世界需要洗礼的另一种企求途径。
昨晚的“梦聊”是一个裹着皮肉的心魂与另一个离开肉身的心魂在特定时空里的相约,我在聆听中,感怀“心”的传教,感知“言”的醒悟,感染“情”的爱愿,感念“神”的指行。在“梦聊”分别之际,铁生又重复了他以前说过的话:“史铁生是别人眼中的史铁生,我并非全是史铁生。”在他转过身去的时候,我一直在咀嚼这句话,直到现在。
我发现儿子留在桌子上那本阅旧了的《汉语成语词典》,从头到尾随手一翻,鬼使神差地只留意了二条成语:“邦家之光”和“行尸走肉”。而这时,我记忆一向很差的大脑里,会迸发出臧克家在纪念鲁迅先生逝世13周年时写的诗:“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难道冥冥之中,就这么巧合。
无可否认,史铁生他已经死了,但他却真正地活着,我感到了他那颗心魂的存在,他在幽深的世界里闪耀着“邦家之光”,这光芒,照透并温暖着人世间那些灰暗的心。我以及周围的不少人们,依然为苟且偷生拼命地忙碌着,忙碌得只剩下麻木的躯壳。不妨回观一望,也许你会发现,在躁动的人群里,竟然夹杂着诸多的“行尸走肉”。但愿,这期间不会有你。
肉身尚在,灵魂何在?活着的人,是否需要在匆匆的行走中,稍许停顿一下,去找个安静的地方深眠一觉,或许,能够在不知不觉中亦会走进“梦聊”之境。
噢,顺便提示一下,请千万不要在深夜来打扰本人,因为那是我“梦聊”的待机时刻。正如铁生所言:“白昼有一种魔力,常使人为了姓名的牵挂而拘谨、犹豫,甚至于慌不择路。一俟白昼的魔法遁去,夜的自由到来,姓名脱落为一张扁平的画皮,剩下的东西才渐渐与我重合,虽似朦胧缥缈了,却真实起来。”我如果能在朦胧和缥缈中找回些真实,则梦聊何妨?
好了,就此打住,我还要准备将昨晚上“梦聊”的内容慢慢地梳理出来,我思虑着,最好写出来告诉大家。在今后的梦境里,不定铁生还会与我聊些话题,好吧,可能的话,一月或者一年后……兴许还会写出来。
祈祷人之梦缘常在,心魂常在。梦系铁生,孰若与之而起思维,则人生之意义必常在。悠哉!我并不在乎有谁在黎明后大声敲打紧闭的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