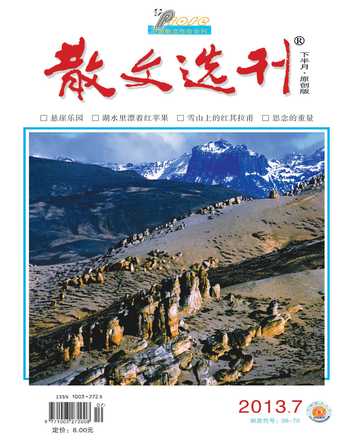书信背后的故事
黄红卫
念书念到四五年级的时候,祖母叫我替她写信,信是写给祖母的女儿的。
祖母的女儿,我应该称“姑妈”,但是我不认识姑妈,这姑妈是祖母与前夫所生,也就是说,当年祖母是以寡妇的身份与我鳏居的祖父结合的,是我父亲及伯父的后娘。祖母嫁过来时,把唯一的女儿送给人家做了童养媳。那时,我父亲4岁,伯父8岁,往后的日子里,祖母与祖父并没有生下一儿半女。
祖母与我身边所有的祖母一样,勤劳、慈祥、仁厚,四个孙辈她亲手带大了两个——大孙子及我这个小孙女。对于祖母的吩咐,我向来是言听计从的。
常常是这样开始写信的,我准备好纸和笔坐在祖母的身旁,端坐着的祖母表情是庄重的,语速是缓慢的。通过祖母的讲述,我了解到姑妈的生活非常不易,婆婆厉害,男人强势,加之久不生育,姑妈处于仆人的地位。这也是姑妈不往亲娘处走动的原因之一。另外,我了解到,姑妈好不容易生养的一女,那个我应该称其“姐姐”的女孩儿,有个别致的名字——小农。因为小农,我陡然增加了写信的兴趣,甚至想象小农的长相、举止、衣着打扮。有一次,我在信尾自作主张添加一句:希望小农姐姐来玩。
姑妈与小农终于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在念高中,而小农早已辍学务农了。她们娘俩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据说乘坐了半天的汽车,又步行了半天。我不知道小农是否冲我信中的“邀请”而来,她喊我“妹子”,拉过我的手翻来覆去地看,说这手又白又嫩,不是吃苦的相。小农屁股没坐稳就开始帮祖母干活,自留地栽种,浇水,洗蚊帐、被子,动作之快令我汗颜。这是我们家与祖母至亲唯一的一次友好交往。
不久,父亲带我们移居到了几百里外的城市,伯父家搬到了几十里外的县城,曾经热闹的宅园仅剩祖父祖母枯守。在这段时间里,因婆婆离世开始当家做主的姑妈来往得很频繁。祖父去世刚过“七七”,父亲突然接到姑妈的通知,姑妈说她准备把祖母接到自己身边去赡养,要这边的兄弟俩一次性付清一笔赡养费,从此井水不犯河水,互不来往。待大家匆匆赶回老宅时,姑妈已替祖母打点好了行装,任兄弟俩如何劝说,她们去意坚决。祖母走了,带着“落叶归根”之外诸多不可违逆的世俗。
祖母走后第二年,父亲违背姑妈的约定动用单位的小车率我们去看望祖母。好不容易找到姑妈家,不冷不热的姑妈指着堂屋里的一张床对我们说,外婆走亲戚去了。我们问亲戚家在哪?姑妈说远哩,你们寻不到的。带着种种疑问,我们无奈离开。望着祖母床上那条熟悉的蓝印花老布被面,童年的记忆祖母的气息扑面而来,我不禁泪水潸然。
后来,有曲里拐弯的消息传来,说祖母其实不在姑妈家,而是与一老翁生活在一起。我不相信,80高龄的祖母,绝对不会另结姻缘的,何况,我们这边已付足了生活费。
但很快,又有确凿的消息传来,祖母已经去世。果然,姑妈连凭吊的机会都没给我们。
20年光阴,可以冲淡一切,比如恩爱,比如仇恨。
20年光阴,却让我把对祖母的怀念沉淀了下来。我清楚,这份日积月累的沉甸甸的沉淀需要释放,我更清楚,释放的最佳形式,只有写信了。因为在过去的20年里,我与大阿哥偷偷寻找过祖母骨灰的下落,终因人生地不熟而不了了之。
我鼓足勇气拿起笔,凭着记忆中的地址,给小农写了一封信。为什么写给小农,是经过权衡的:一则以我推测,作为当事人姑妈,恐已不在世间了;二则小农毕竟是同龄人,容易沟通。信是这样开头的:“小农姐姐,冒昧了。你还记得你外婆有个孙女吗?我就是那个孙女。今天打扰你的目的是想知道我祖母的墓址,清明节快到了,我想去祖母的墓前祭扫,寄托这份无处安放的哀思,仅此而已。我一直没忘记祖母,在我心目中,祖母就是我的亲祖母。若把我俩放在天平的两端称,祖母的情感砝码肯定偏向我这边的。都说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遗憾的是我永远没有机会回报了。我想我此举不会伤害到任何人,牵扯出任何事;我想我此举祖母的在天之灵是愿意看到并乐意接受的。小农姐姐,请相信我。如方便的话,请帮助我……”
人心总是向善的。
今年清明节,在异乡一座陌生姓氏的祠堂里,我与大阿哥双双跪拜在刻有祖母姓名的碑前。一旁小农姐的手心里,始终攥着那封我写给她的信……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