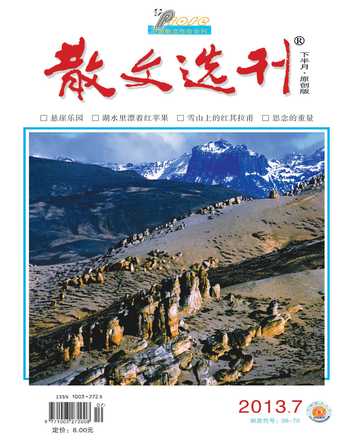“明子”点燃的路
王德凤
我虽然有幸分享一位乡村老人的喜悦!但内心又是那样酸楚,酸楚又派生出无限的敬意。
这源于在云南大理州漾濞县的一个“赶街”日,我遇见的一位卖“松明子”的老奶奶。虽说是暖阳高悬的四月天,城里女人都撑着太阳伞挑选自己的爱物。可老人家却穿着两件毛衣,外罩一件蓝色的棉马夹。黑红色的脸,深浅不一的皱纹布满额头,满头银发一丝不乱,因没牙而干瘪的嘴巴却笑得开心。她面前摆放着10斤左右的“松明子”,也就是用来引火的“明子”,那些略显黄红又有些透明的“明子”,在空气中散发着松脂的清香,大小不一的碎块呈现出不同的造型,安逸般卧躺在老人绿色的头巾上。
漾濞因博南古道而被人所知,又因盛产泡核桃而闻名。沿袭博南之风集市也就格外热闹。长长的街道两旁摆满了山货,吃的,用的看得人眼花缭乱。叫卖声、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老奶奶却一声不响朝着过往的人笑,那笑如孩子般天真纯透。久违的“明子”在国人物质生活匮乏,烧柴、烧煤煮饭的年代,是每家必不可少的。“明子”是一种松脂聚集的木材,形成在松树等油脂类树木的木质部分。因它易燃,当时家家户户把它用斧头劈成指头粗细放在锅灶旁边,随时取用。因为火柴很难直接点燃木柴,所以只有先用火柴点燃一小块“明子”,架到要点火的木柴中间,木柴上面再放煤。就这样逐层燃起,一炉红红的火才能燃烧起来。那时家家都离不开它。如今随着液化气、管道煤气、电磁炉、沼气的使用,“明子”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
老奶奶的“明子”能卖出去吗?我带着疑惑问老人家。她笑着点头说:“能,能卖出去!这是我第五次‘赶街了,如果今天还卖不出去,下回‘赶街我还要来呢!”老人说话间深深的皱纹里,仿佛都盛满了她下一个希望和更多的期待,那希望里的期待又是那样自信。“老奶奶,家里日子怎么样?孩子们生活过得好吧?”我问。她回答说:“三个儿子,两个在县城都有退休工资,小儿子在农村有一大片核桃树,盖了楼,我住在一楼最好的那间。”“家里缺钱吗?”她摇摇头说:“不缺,不缺!”“那您这么大年纪还来‘赶街?”老人举起青筋凸显的拳头回答:“我不老,今年才82岁!我要把家里的‘明子背出来换钱,等小孙子放假回来给他,让他多买些书看。我小孙子在昆明念大学呢!”说完她脸上又堆满骄傲和自豪。“老奶奶,从你家到这里,要走多远的路?”老人低头想想说:“三个钟头还多呢!天不亮我就出门,上山,再上山,还要过桥,快呢!到这里天就大亮了。”“很累吧!”我又问。她指着旁边一个拐杖说:“不累,还有它帮忙呢!”她看看我又说:“你买不买‘明子?”我摇摇头。
接下来她又笑着说:“看出来了,你是爱看‘明子的。”我点点头又问老奶奶说:“如果你念大学的孙子说很茫然,不,如果你孙子说念了大学以后也不知道路在哪里该怎么办呢?”老奶奶不假思索地说:“书,越念,越亮堂!我小时候家里穷,不供我念书,我哭红了眼,还是不让我念,我就把羊赶到山上悄悄跑回学校,站在石头上耳朵贴在窗上偷听,有一次不小心脚底一滑摔了跤。”说到此她露出胳膊上的伤疤给我看……“我还是学会了一些字,我跟大儿子学写10个数。再后来我给小孙子买糖,小孙子念小学时,给他一块糖教我认一个字,不给糖他不教,他要玩呢!我会写自己的名字。”说完她很认真地用有些发颤的手指在地上写下了“李桂芳”三个字。她写字的神情很专注,我这时才发现老人十个手指都皴裂出一道道深深的口子,因为用力过大血沿着口子往外浸出来,似乎要把那地上的名字染红、凝固。
当年那个乡村小女童的读书梦,摔伤的胳膊,干裂粗糙的手拿出糖求孙子教她写字。想到这些我心颤颤的,再看那地上的字分明是蘸着心血写成的呀!此时,她手指裂开的道道口子黏上了一层土,仍带着天真般的笑看着我说:“我不是文盲吧!漾濞我也会写,我用10块糖才学会的,我写给你看!”我急忙竖着大拇指给她看。“老奶奶,你不是文盲,你不要写了!”我不忍看到她血和着土写在地上的字。稍停片刻,老人家想起来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又说:“如果我小孙子说念了大学不知道路在哪里,我就告诉他用脚走,就有路了。天黑看不见就点‘明子,绊倒了,起来接着走,别停下,走着,走着,天就大亮了,这不难呀!”
我给老人道了谢,怕误她的生意转而看别的摊位……当我顶着午后的烈日,原路返回准备离开时,老奶奶面前的“明子”终于卖出了几块,估计有一斤。老人正用很旧的手帕包裹着钱,然后小心翼翼地揣在贴身的内衣口袋里。三元钱一斤,这十斤左右的“明子”,三个多小时的山路,对82岁的老人来说还要赶几个“街”?这一切她的小孙子知道吗?她抬头又看到了我,格外小心取出旧旧的手帕举起来让我看,又问我说:“三元钱,能买几本书?”“能买好多本!”我带着安慰般的口吻说。她又高兴地告诉我说:“再赶几个‘街,‘明子都卖了,就能买这么多书了。”她用手比划出一尺的厚度,干瘪的嘴笑得更开心了。我也同她一起笑,让她知道我在分享她的盼望和喜悦!为那能点燃光亮的“明子”,为脚踩下去就有路。可看到老人那双手,那拐杖,还有裹着老人汗水的“明子”,不知为什么我又真的想流泪。
望着这位乡村祖母想着她对孙子的期盼。我的内心是那样感动和钦佩,那写在地上的名字,是胳膊上的伤疤,是糖块伴着甜苦中的人生追求,那是用脚铺就在地上的路,那路因“明子”而燃亮着,并一直向着远方无限延伸……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