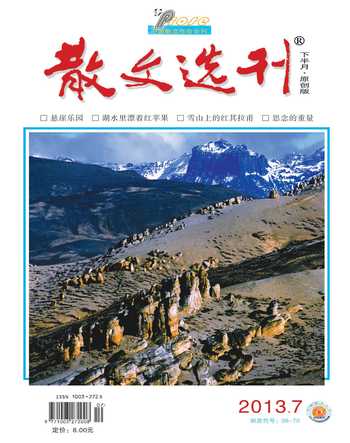姐
位娟
看着脚下的白云,时而悠闲地散步,时而匆忙地奔腾,就感觉融在了其中了。但,我能飘到哪里啊?
终于下飞机了,随着人流我走出站台。再也无意于周围的风景了,仿佛一切都不存在,仿佛空荡荡的大地就我一个人。
从机场到医院不是很远,步行就好了。这时天麻麻黑,下弦月像弯刀一样跟随着我。好像在收割着我身后的原野。太阳的制造,月亮的收割,谁也控制不了的啊!在我们的一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想想,哪一次泪水不是因为爱?
我这次坐飞机回家,是去医院看望我大姐的。姐姐得了肝癌。癌症,我都不敢提这两个字,就连别人说话的口型我都害怕。仿佛是怪兽,是魔鬼,正一口一口地撕咬着我的大姐。大姐比我大十好几岁,我就是大姐哄大的,在我眼里,大姐比娘更像娘,比娘更亲。小时候,农活多,爹娘顾不上我,姐为了我只上了小学三年级。在姐花枝招展的时光,姐的身上散发的不是青春的香味,而是我的屎尿味儿。都是我拖累了大姐,如果不是我,姐会去读书,会考大学,也许会有个好工作,而不至于一辈子种地……
医院就在眼前,之于当时的我,是多么遥远,恍若隔世之感,好像这个地方本不应当和我相干,本不应当和姐相干,姐不该在这里,姐不该离开我。姐依然是走在我身边,走在我前面,为我遮挡阳光,为我遮挡风雨的那个小姑娘。就这样,我不知不觉走到了医院的花坛前,一位跪在月色下的背影让我从幻想里警醒。她那么虔诚地跪着,嘴里念念有词。白色的上衣,黑色的裤子,长长的秀发披在脑后,让我想起白娘子为夫跪求灵丹妙药的情景来。我相信,她一定是为得了重病的亲人求平安的,我相信月亮一定会看得到,我相信上帝也一定会看得到……我也不自觉地跪下来,祈祷神佑我姐能康复!突然,有人呵呵笑着朝这边走来,吓得我腾的一声站起来,匆匆离开。而那位女子依然跪着,依然念念有词。我的脸蓦地发烫,惭愧啊!我竟然没她虔诚!我对不起你啊,姐!上帝,原谅我这一次吧。而此刻那个女子应该充满意希望的,她和我相较来说,比我幸福,因为她不会为了今晚而愧疚。
拖着沉重的步子,来到姐的病房。在病房前,我的脚迟疑了好一阵才敢进去,我控制住我自己,鼓励着我自己,见到姐一定不能哭!姐看到了我,朝我伸手,颤颤地说一声:“荣儿,来了。”然后,姐的眼圈红了,抽搐地哭起来。手术后刀口因为震颤而令姐更痛苦,苍白的脸变得青紫起来。我拉着姐的手,把痛苦的泪水使劲压回胸腔,擦干姐的泪说:“姐,我来看你了,你还不高兴啊?你的病会好起来的!你说过我是个有福的人,会给你带来好运的,带来奇迹的。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我顺着墙头爬上屋顶,又从屋顶上摔下来。那一次,可把你吓坏了,脸都白了,哭得声音比狼都难听。而我却一点也没伤着,倒是你把我揍了一顿!这一次,一定有奇迹发生在你身上!姐。”姐被我说得竟然又哭又笑,然后安定下来,给我讲我小时候的事。
我们姐妹说笑着,姐夫递给我一杯水。这时,我才注意到姐夫。本来瘦弱身子,现在更瘦了,衣服有点大,空荡荡的,像一股风就能吹跑。姐夫是建筑工人,和水泥,坯墙,垒墙,多重的体力活啊!姐夫这么瘦的身子,不知怎么挺过去的。现在城里一套房子就百几十万,而姐夫一月也就三千多,总觉得不平!但是,为了给姐看病,姐夫说,把瓦房卖了也愿意!姐,一个多月就不能自理了,是姐夫端屎端尿地精心伺候着,姐虽说很瘦,但很干净,我真得感谢眼前的这个男人!我给了他三万块钱,当时,我心里是惭愧的,我知道,这远远不够,但我只有这些力量了。姐夫拼命不要,我说,你让我少一些惭愧吧,要不,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他才接,还说,以后会还给我的,憨厚的姐夫,我能再要这个钱吗?
姐夫给我买了晚饭,姐只能喝些稀汤。我来时,给姐几千块钱买了几盒燕窝,听说很补身子。姐埋怨我,说,这么贵的东西,咋是咱吃的啊!我也不知怎么个吃法。姐夫说,燕子的窝,不都是草吗?这能吃吗?最后我们研究了半天,把瓶子取了出来,才知道,温温直接就能喝。姐喝了两口,说,有个好味儿,不舍得喝,一天喝两口就行了。是我硬逼着姐喝完的。我对姐说,喝吧,喝完我再给你买。姐拼命摆手,说一盒,够她种一季地了!
两天后,医生给姐开了一大堆药,让姐回家打针,说,在这儿,在家都一样,在家吃睡更方便些,而且这里消费又高。我们费力地把姐抬到车上,姐一路吐个不停,好像一只风筝,要不是我们手中的那根线,早就轻飘飘地飞走了。姐靠着我,让我感觉我和姐就像一棵不可分割的树。姐每痛苦一下,我的枝叶也颤抖一下,心里一阵阵揪着疼。终于车行到姐的家乡了。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只不过麦田里坟又多了些,而且大了些,好像大地上的一双双眼睛,一个个耳朵。本来坟上应该长有茂盛的青草,或者野花的,为什么没有呢?我问姐夫。姐夫说,前一阵子平坟,上面下来平的,后来群众不愿意,闹了起来。最后,还是把平过的坟重新堆了起了!
终于到姐的村子了。以前是一些草房散落在田间地头,现在仿佛还有茅草在阳光下嘶鸣。草房都换成瓦房或平房了,冷冷的砖头,少了些泥土的温馨。走进姐家,看四周,都是原野。让人仿佛立于世外,不知生死。说起生死,此时,疼痛中竟有几分释然了。死亡,是每个人必须的归宿。我也会死的,死了后,去找姐,找大,找娘,找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很多亲人相聚在一起,我竟然升起了一点向往。生死界限突觉模糊起来。这时,姐的大黄狗,摇着尾巴,蹭着我的腿,它可是第一次见我,一点对我不陌生,仿佛它早就知道我们的前世今生缘。看着它温柔地舔着我的手,我一点也不感到脏,也许它的舔,永远留在我记忆里,也就是说,大黄狗走进了我的生命。就像我和姐手挽手走进了原野,大黄永远踽踽跟着。
我正在出神,口袋里的电话把我吓了一跳,她像月光下突遇一条蛇,把我一下拽到现实的坑塘。
我的大地啊,都盼望我们好好活着。
责任编辑:子非
美术插图:知止